
衛福部統計,每年約有15,000名兒少身處「脆弱家庭」,面對貧窮、不當教養、家庭照顧功能不足、成員關係衝突或疏離等多重脆弱因子。這些童年逆境經驗未必留下外傷,卻可能讓孩子落入心理創傷;照顧者的身心與行為議題,也經常複製給下一代。
近10年,「家庭會傷人」的觀念被更多人看見與理解。除了長期在第一線服務的社工,也有醫師、心理師走出診間,試著踏進脆弱家庭、安置機構、矯正學校,探向兒少與家長的心理狀態,帶入醫療資源,發現自己的能與不能。改變未必能立刻發生,他們的願望,是讓傷害到此為止。
去年(2024)中旬開始,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兒童心智科主任陳力源與一名心理師,每個月都要穿過勵志中學的三道厚重鐵門,進入這所少年矯正學校的戒護區,為有身心議題的學生看診。
他的患者是16歲少女小咪(化名)與17歲少女雨彤(化名),兩位相差一歲的少女,有相似的坎坷命運。小咪的父母關係不睦,從小目睹家暴的她,國中開始逃家、中輟,在多個縣市輾轉流浪。去年被協尋到案後,因涉入多起性剝削案件,被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往勵志中學收容。雨彤是身心障礙者,從小在安置機構長大,逃離機構後涉入性剝削案件,也進了勵志中學收容。眼看雨彤即將成年,幾乎所有少年適用的資源與服務,都將在她成年後退場,要穩定接受治療,就得把握感化教育期間,因此台北地院輾轉找上陳力源合作,進入門禁森嚴的矯正學校,治療兩位有高度兒少身心醫療需求的少女。

勵志中學輔導主任康瑞芷表示,學校過去與醫師的合作多聚焦在診療與藥物調整。陳力源作為兒童青少年精神專科醫師,則帶入更多心理與社會層面的觀點,協助教師陪伴少年,幫助學生釐清自身狀態,讓學校多一個不同於心理師與輔導老師的視角。
投入少年司法工作27年,台北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很有感的變化,是少年身心議題的複雜度、行為強度正節節升高:對父母施暴的少年;歷經性侵、人口販運,社會化且善於操控他人的國中中輟女生;合併人際危機、反覆自殘、無差別施用各類毒品,自我毀滅⋯⋯許多調保官包括王以凡自己,都得陪少年去看身心科。
王以凡進一步分析存在較高風險,需要特別關注和輔導的65位「高風險列管保護管束少年」,當她回溯少年生命史,發現25%高風險列管少年有施用毒品,高達40%有家暴、被忽視、目睹暴力等創傷經驗。一名少年身上,常有複合、多重的成癮、自殺等議題。
因此北院結合「嚴重情緒行為者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及精神病早期介入計畫(簡稱嚴重情緒行為改善方案)」,為高醫療需求少年提供個案管理的團隊照顧,獲得更細緻的精神醫療資源,目前有18名少年接受此服務。
陳力源指出,大腦中負責決策與思考的「前額葉皮質」,約在24~25歲才會成熟,青少年因自我調節能力未發展完全,易受情緒與衝動驅使。若在成長過程中經歷創傷,會影響前額葉發育,使部分腦區變得較薄、較小,嚴重時甚至近似腦傷,造成生理疾病,心理也常出現低自尊,看似自信、姿態高,實則內在脆弱、易被冒犯;不安全的依附,在關係中過度投入,或快速退縮;另外是伴隨壓力賀爾蒙失調、大腦認知功能減退、情緒缺乏彈性,連帶增加醫療介入難度。
「創傷知情照護(Trauma-Informed Care, TIC)」,則是在理解創傷如何影響大腦與身體的知識基礎下,為創傷倖存者提供支持的方法。TIC在本世紀初期由美國臨床心理學家提出,面對患者或個案時,著重的不再是「你出了什麼問題」,而是關注「你發生了什麼事」。目的不在「治療」創傷,而是作為療癒的起點,透過以下4個步驟,協助曾經無助、受控的創傷倖存者,再次掌握自身生活的主導與選擇權:
- 理解創傷
- 辨認創傷
- 利用創傷知識作回應
- 防止再度受創
這套照護方法被廣泛運用在醫療、教育、社會工作、司法矯正等領域,約在10年前引入台灣,從社政、司法,逐漸落實到醫療。
北院輔導高風險少年時,也設計體適能課程,運動後由心理師引導討論人際互動與情緒,協助少年梳理生命經驗。去年的拳擊課,調保官每週陪打,王以凡曾接下一位來自藥癮家庭少女的重拳,肩膀受傷,復健8個月,「那少女窮追猛打,每拳都比男生還重,滿滿情緒與怒火。」

童年逆境的傷,少女用拳頭傳達給王以凡,在診間與陳力源相遇的少年,則是用書。
陳力源表示,政治、疫情、經濟與整體社會環境的變動,都對兒少心理狀態產生影響:
「不過,我遇到的少年⋯⋯我不會說百分之百,但我想有99%,因為家庭受到非常多的創傷。」
陳力源分享三本少年患者送他的書:《以為長大就會好了: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致無法拒絕長大的我們》,以及談親職化兒童處境的《為了這個家,我殺了我自己:兒少照顧者的重生日記》。
第三本書出版時,門診有好幾個孩子向陳力源提起這本書:「其中一個孩子知道我沒看過,就把書丟給我,說:『陳力源,去看書!』 他們這麼渴望我讀這些書,因為裡面有他們的心聲。」
陳力源從求學時期就喜歡觀察、傾聽別人的故事,醫師養成階段主修薩提爾家族治療,卻在投入醫療現場後感到失落:「一診可能有50幾個患者,我在診間得用短短幾分鐘,片段、病理化地處理患者的需求,沒時間看見整個家族的脈絡,」更別說大醫院還有繁重行政工作要忙。
直到5年多前參與衛福部推動的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安置機構創傷知情等計畫,陳力源終於有機會踏出診間,進入校園、安置機構與社區。他表示,醫師習慣在「醫療環境」進行治療,看門診、開藥,看不好就收住院,多數不習慣走進社區。即便有這個心,這耗時且缺乏產值的作法,不易受到醫院支持,但他認為進入患者的原生環境,才能完整看見一個人;一旦抽離「開藥」這項武器,還能找到其他方式協助患者與環境連結。
即便前往家暴、酒癮家庭時差點被狗咬;嘗試敲開旅館房門,讓房內思覺失調母女就醫時險被誤會為尋歡客,這被他形容為「野外生存」的看診模式,讓他在患者的生活場域,完整看見創傷的因與果。陳力源形容,這好比製作農產品的產銷履歷,溯源陽光、土壤與養分如何影響它的生長,尋找毒性壓力從何而來。

進入矯正學校,是陳力源累積多年「野戰」經驗後的決定。過去「嚴重情緒行為改善方案」的治療對象多為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自閉症或重度智能障礙的兒少,而他在安置機構遇見的孩子,不見得有手冊,卻有很強的情緒與行為議題,矯正系統裡的少年個案更是「地獄等級」,是非常大的醫療挑戰。
他以ADHD比例偏高的司法少年為例,回溯學校端,ADHD兒童會因注意力差、靜不下來,被歸類為「難教」、「不會讀書」的學生。若家庭功能不佳,不容易支援跟辨識兒少需求,就會錯失醫療的介入時機,最後以各種衝動控制困難,或學業與人際雙重挫敗的行為,再落入安置或警政司法系統裡。
過去醫療常位處最後端,等教育與輔導撐不住才介入,現在更早進場並肩作戰,但能否順利拉回矯正學校裡的「地獄級」孩子?
對於每位司法少年,台北地院每月召開例行內部督導會議,用同儕督導方式共同設想協助方法,之後會召開例行的跨網絡會議,與服務少年的各單位討論分工;少年矯正學校的個案,則另外與彰基團隊約時間詳細討論。但王以凡也說,北院的少年案件量在全國法院中算低,一名調保官承接的保護管束件數平均30案,這讓調保官得以「精緻辦案」,管得很多、很深入。

陳力源這端,得與心理師學習、理解孩子所處的次文化,並處理入校診療的繁瑣行政流程。他表示,醫療人員不像生輔員、老師那樣天天在現場面對高強度少年,「最初有些人聽了我們跟孩子的會談內容,會露出『你們還太嫩』的表情,覺得我們不懂、被孩子誤導;或覺得我們的建議在打高空,這是前期比較挑戰的地方。」
信任需要時間與時機累積,入校幾次後,他發現這群身在「搖滾區」的隊友也傷痕累累,「有生輔員說他們(也)需要被創傷知情。」合作半年多後,某次一位生輔員談起少年的困難狀況,情緒激動,陳力源即時表達理解、給予回饋,對方直率地說:「啊!你們(醫師、心理師)終於有點用了!」從那次開始,雙方合作順暢許多。
這提醒陳力源,助人者間的同理,是實踐創傷知情的第一步。把孩子身處的「生態系」與一起協力的隊友照顧好,才可能真正幫助孩子。隨著網絡合作,兩名少女的生命議題逐漸被理清、狀況趨於穩定,北院遂在近期轉介第三名需要心理治療的個案給陳力源團隊。
若陳力源面對的是「地獄」等級個案,台南慈恩心理治療所的會談室,便是為那些在不同心理廢墟中徘徊的脆家敞開大門。
43歲的慈恩心理治療所所長、臨床心理師邱似齡,可說是「在監所長大的小孩」。她母親在矯正體系服務40多年,歷經看守所、女子監獄戒護科長、戒治所、精神病監,以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祕書身分退休。「從成人到少年,凶神惡煞到生病的人,我媽都經歷過。我從小(去探班)就在監所跑來跑去。」
邱似齡熟悉矯正系統,專長之一是兒少心理,又是臨床心理與犯罪防治研究雙碩士,但她形容自己是個認真的人,無法承受少年的背叛與戲弄,所以長期主力與台南市社會局合作,為安置兒少心理諮商,而非司法少年。
邱似齡在兒少與他們的脆家身上看見不同樣貌的心理廢墟。在安置機構長大的失家少年身上,邱似齡看見「填不滿的慾望」──機構的生活不富足,不過有吃有住,有零用金,節日時還能許願讓善心人贊助禮物;少年會連續許願4、5個藍芽音響,東西有了還想再要,卻無法得到滿足,反映心理匱乏。
有的孩子,被家長一起拉進情緒黑洞。一名男子與妻子離異後,將兩個孩子關在家中,禁止他們上學,聲稱是為了保護他們。最終這名父親被剝奪親權,孩子被安置,與父親形同生命共同體的孩子,感受到的不是保護,而是家庭被拆散的不安與痛苦。
另一類,是「家長無法合作」的家庭。父母社經地位普遍不低,重視知識與物質條件,但若教養觀差異大,雙方自我意識又強,便難以合作育兒。當父母衝突不斷,還要求孩子選邊站,夾在中間的孩子陷入深層的內在撕裂,萬一這時學校出現壓力事件,孩子往往全面退縮,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拒學。

要預防孩子走入心理廢墟,關鍵在父母是否具備足夠的教養知能,從源頭避免創傷發生。然而,陳力源與邱似齡在實務中最常遇到的,是「有心無力的家長」。
陳力源表示,許多家長很愛孩子,有關心、理解孩子的心,只是缺乏親職技巧,例如孩子犯錯就一味指責碎念,反而讓孩子疏遠。因此他在門診常做的是親職技巧指導,包括將創傷知情的概念傳達給家長,請他們觀察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跟脈絡,而非只標籤孩子「不乖」的行為,要求立刻改變。
邱似齡進一步分析,當代家長的困境,是社會不斷教導孩子重視自己的感受,不少父母的成長過程卻缺乏被好好對待的體感。親職功能薄弱的家庭,可能延續上一代的打罵教育,否定甚至忽視孩子的需要;即使是高知識背景的父母,雖明白要傾聽、同理與正向教養,卻因欠缺體感,難以將這些理念知行合一,化為日常行動。
很多家長覺得自己有在聆聽孩子說話,孩子卻不這麼認為。邱似齡舉例:
「真正的『好好聆聽』,是我說了什麼,對方不只是聽見,還試著進到我的經驗裡,去感受、回應。當孩子分享傷心沮喪事,期待是家長的接住與同理:『我懂,你一定很難過。』而不是:『不要哭,別這麼負面,撐一下就過了。』」
類似情境也發生在校園與社會、心理工作現場。創傷知情成為顯學,坊間不乏以創傷知情為主題的研習或工作坊,但「知」與「行」是兩回事。陳力源坦言,學校端的差異很大,「有把自己裝備得很好的老師,也有老師的心理狀態不理想,難運用創傷知情概念去跟孩子工作。」
邱似齡指出,這一輩的老師與助人者,同樣缺乏創傷知情的真實體感:
「你要怎麼在被孩子激怒時,仍能穩定情緒、好好與孩子談話?如果一個人不曾被這樣安頓,現在卻被期待要去安頓孩子,只能仰賴他的身心是否足夠穩定、健全。」
甚至有些時候,兒少工作者亦來自高壓、破碎的家庭。他們成為創傷倖存者,長成優秀的大人,但若沒有好好療癒心傷,面對境遇相仿的孩子,恐觸發創傷反應。「他們很努力,也具備知識。只是知行合一需要時間和經驗累積,且需要豐厚被好好對待的體感,」邱似齡說。
她表示,除了創傷知情的研習、培力,督導機制也有助工作者釐清內在阻礙。只不過現實資源分配是倒置的,大學心理輔導中心經費、資源相對多,最前端、最基層的中小學,反而較難獲得這類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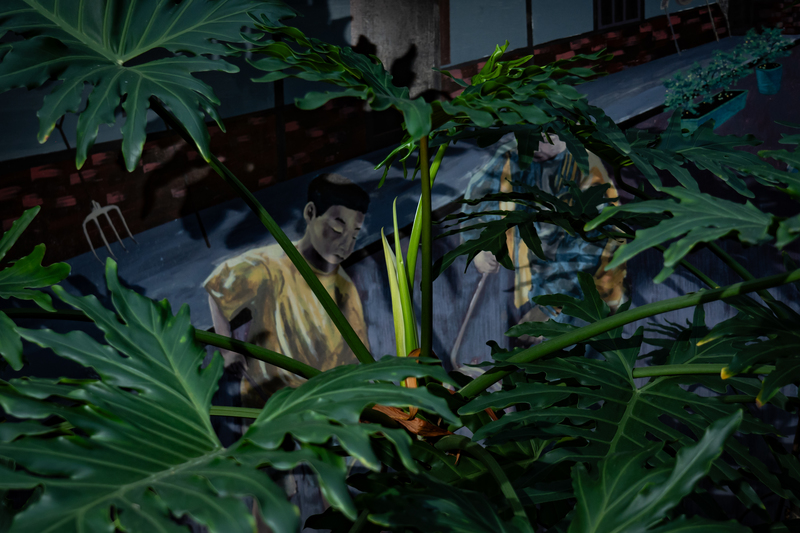
即便看見孩子的傷、介入各種醫療資源,世界上沒有任何特效藥能迅速撫平童年傷痕。很多人問邱似齡,花這麼多心力支持這群看似不討喜的少年,究竟能看到什麼改變?她很坦白地說,看不太到立即性回饋,但工作者的陪伴,就是為少年添一分被愛、被好好對待的體感。
這顆陪伴種子,有時會在預料之外的時刻發芽。有個陳力源治療過的安置機構孩子,在離院同時一併離開醫療系統。他以為醫療介入失敗,但時隔半年,少年帶著伴侶主動來到他的診間,想了解自己的情緒問題從何而來──創傷知情照護的工作,便由此重啟。
作為一名不斷從少年身上學習的兒童心智科醫師,陳力源又因此明白一件事:醫療看似無法立刻帶來改變,卻不是全然徒勞,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驗證。而時間,是少年最豐沛的本錢。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