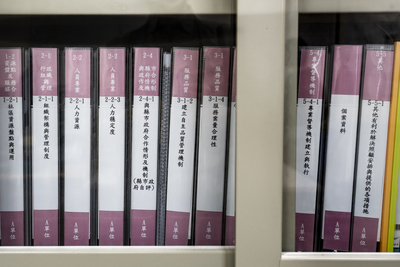長照界近來流行一句玩笑話:「以後我們的長照,只能靠兩種人──外國人和機器人!」對照《報導者》採訪所見,這話倒有幾分警世的真實。
「找不到人」是長照體系各種服務單位及各種層級人力的痛點──居家服務、日照中心、住宿機構都面臨「民眾有需求,但找不到人,所以沒有服務/開不了床」的窘境。夜間與假日的照顧服務仍然罕見,連白天的服務人力調度也可能面臨困難;身負連結個案與服務重任的個案管理師不斷流失,讓各縣市政府的長照計畫書都把「留住長照個管師」列為施政目標。
為了補足基層照顧人力,衛福部試辦「住宿式長照機構與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攬才留用試辦計畫」,招東南亞學生先念書再綁約服務,首屆22人已全數被業界預訂,再搭配以「外籍中階技術人才」補充人力;勞動部則力推「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計畫」,讓民眾自費買服務。不過,這些措施真能補起長照3.0的人力荒嗎?
長照2.0居家照顧服務員(簡稱居服員)魏力虎的一天和他的同行略有不同:每天傍晚6點跨上摩托車騎往案家,7、8點開始工作,11點多收工、拎宵夜回家吃,半夜洗漱就寢。他是為數不多、專做夜間時段的居服員。
「一開始做白天,後來想,反正我晚上睡不著,不如不要跟大家拚白天,」魏力虎說,入行是因為中年失業。入行前半年,他在一間評鑑優等的住宿式長照機構輪夜班,1人顧14床:「換尿布5分鐘結束,趕快換下一位,一連串不斷重複。因為沒有時間,我們也沒辦法跟他們(住民)聊天,甚至連話都沒有講。我沒辦法慢慢來,沒辦法問他『你還好嗎』。」沒辦法好好對待人的歉疚感,讓他日漸灰心。後來,他在高強度的工作中弄傷了腰,轉作一對一照顧的居服員。
如今的魏力虎已有7年居服資歷,由白天轉戰夜間。夜間時段的工作內容,在他看來和白天大同小異:「一樣是生活。沒有特別難,或特別奇怪。」大多是協助上床睡覺;距上一班居服員服務已隔數小時,被照顧者就需要換尿布、喝個水,準備就寢,「因為沒有人一起住,或家人沒辦法。」

雖然居服是長照2.0使用率最高的服務項目,但夜間、假日幾無居服人力,已是常態。
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簡稱居盟)理事長涂心寧指出,近20年居服單位的規模出現結構性變化:2016年、長照1.0計畫尾聲,全台僅有186個居服單位,平均每單位聘僱約47.9名居服員,人力規模大,有利於彈性調度與排班;到了2024年,全台灣居服單位數量增至2,235個,但每單位平均聘僱的居服員人數降至24.3人,「當個別居服單位服務人力規模縮小、在工時上限下,可運用排班人力就減少了,在熱門時段,有的單位就排不出人。」
當單一居服單位派不出人,由不同居服單位的居服員湊班「共案照顧」──由多位居服員輪流排班照顧一位個案──的情況便日益常見。
但以使用者視角來看,共案照顧雖然確保有人服務,也增加了溝通成本。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祕書長劉于濟正是共案照顧的服務使用者。他在一週之間會遇到3~4位居服員,「今天週一是一個、週二是一個、週三是另一個,我就要去調適3次。早上一班、下午一班、晚上再一班,我一天也要調整3次,」溝通成本大幅增加,讓劉于濟總覺得卡,「再怎麼溝通也很難100%複製出我想要的。」即使他自認因肌肉萎縮症從小練就溝通照顧需求的本事,面對太多照顧者,也難免心累。
當居服員白天已經排班困難,夜間人力更是令人頭痛。夜間居服人力不足,上班族的家庭照顧者回家後,就很難「喘一口氣」。台北市紅心字會資深個案管理師施勝茂觀察,不少照顧者日間就用盡了政府所核定的長照服務時數,無法再申請夜間服務。
住在花蓮市的蓮金瑛是用盡政府核定時數,仍然蠟燭兩頭燒的人。她今年69歲,照顧98歲、患有失智症的母親2年多,使用長照2.0的居服,偶爾也把母親託付給日照中心。
我們和蓮金瑛一起從日照中心走回她母親的住處。她推著母親的輪椅,小心閃避路面不平整的地方,向記者解釋,兩年前母親還牽著腳踏車到處走,她猜想可能那時候母親已經失智:「後來跌倒,就差很大。現在她不太認得我們,每天叫我的名稱都在改。」
「以前她晚上不用人陪,現在就怕她起來,摔,我才過來住。」蓮金瑛指了指4、5坪大的房間角落:「我就打地舖(跟她睡同一個房間)!因為她跑出去會回不來。」蓮金瑛對母親曾經半夜無法入眠、獨自外出摔傷記憶猶新:「98歲喔,跟我撐兩夜不睡,一直說要搬家。」
這天中午,正好居服員來備餐、餵飯。不過,沒等母親吃完飯,蓮金瑛就說她得走了,「長照(指母親的居服員)每天只來兩個小時,」趁母親有人陪,蓮金瑛要先趕回自己家,「買便當給我老公吃,趕快把他晚上的也煮一煮,下午1點(居服員離開前)要趕快回來。我老公大我7歲,他膝蓋痛(外出不方便),也需要人顧。」臨走前她說:「我哥死了,我弟也死了,只剩我一個孩子。這是我的娘啊!我不能不顧。」

「晚上基本上是找不到人的,」施勝茂說,媒合成功的居服員服務時間一般介於上午6點到晚上8點,偶爾能安排晚上10點的服務,但那得有居服員「剛好住在案家附近」,或交通時間「10幾分鐘能到」,才比較可能。
因應少子化、缺工的社會趨勢,多年來學界不斷提倡「一對多」的照顧模式;針對夜間需求,衛福部也從2015年起推動「小規模多機能服務」(簡稱小規機)。當照顧者沒辦法負擔夜間照顧時,可讓被照顧者到日照中心的暫留床過夜,每個月臨時住宿上限為15日。
儘管需求殷切,但願意開辦的單位寥寥可數,多數仍因人力與成本的雙重壓力卻步。
「人真的找不進來。直到今年我們人力比較穩定,才開出3床,」紅心字會副祕書長許雅青說,台北市聘僱一名夜間照服員僅能收到1.5床的給支付費用,小規機必須達到一定人數才能攤平成本。因此他們也採取和以往不同的策略試試水溫:改變過去「週一至週五隨選」的的托顧模式,將夜宿服務固定在週三、週四。
許雅青解釋,這樣可以讓工作人員在週四的夜班結束後,直接連休週五、週六、週日。他們也堅持提供「連續兩晚」的服務:「只有一天的話,民眾感覺不出來臨時住宿對照顧者的好處在哪裡?兩天的感受就很明顯。」讓團隊欣慰的是,開辦之後有位長期照顧伴侶的老太太,變成穩定的服務使用者,晚上終於能夠好好睡個覺。

如何降低個案管理師離職率?以台北市政府為例,採雙管齊下策略:
- 針對資源不足區域規劃擴增更多長照單位,期待每單位的個管師就能分散、降低案量;
- 從2023年起祭出案量監控措施,要求個管師平均案量大於120人的長照單位必須積極增聘人手;如果連續3個月平均案量大於120人,會被違規記點。
但業內人士告訴《報導者》,增設更多長照單位可能無濟於事,因為新設立的單位多半也是「從業內挖角」,挖東牆補西牆,整體個管師依然缺人。
以台北市政府為例,照管中心會不定期與社區整合型中心(負責個案管理的A單位)確認每月最高服務量並簽訂契約。
假設A單位與地方政府簽訂契約登載的每月最高服務量為2,000案,目前全單位的案量為1,250案、聘有個案管理師9位,則每人平均案量為138~139案。如果遇到1位個案管理師離職,導致全單位個案管理師人數剩8位,那段空窗期間,個案管理師的每人平均案量就會變成156~157案,超出150案的規定上限。
不過,若現有總案量未高過契約登載的每月最高服務量,地方政府仍會繼續派案給該個案管理單位,導致在補到人之前,每位個管師的均分案量過大。
施勝茂也曾請教社工,他認為:「獨居老人及社會福利社工可以做得很深入,大概是手上負責30到60案的時候。確實,當案量比較少的時候,我可以記得住每一個家屬大概的需求、他家長怎麼樣,可以做全人照顧的安排。但你說150案更甚至更多,一忙起來我真的無法合作得很深入。」
既然要留才,為何不加薪?各長照單位也有苦衷:在政府給付多年未調的情況下,若政府調高民眾自費比例,可能使用者就寧願不要服務了。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劉立凡分析,相對於性命攸關的急性醫療,民眾願意付高代價保命,但是,「長照(服務)的價格敏感度很高。對家庭來說,如果長照便宜一點,就多用一點;如果貴一點的話,就想辦法窩在家裡、自己照顧。所以你會發現,長照2.0的體系下,大家會盡量把給付上限用滿,但以目前情況來說,想自費的人相對少。」
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治醫師、前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則呼籲,台灣邁向長照3.0最重要的樞紐就是社區整合型中心的個管師,是照顧可以精緻化的關鍵。他認為,120案的個案管理重擔極不合理,:「第一個,他背很多案子,光是care plan(新案的照顧計畫)就寫不完。第二個,個管可能會很心虛啊!為什麼虛?他可能隱約知道個案可能有變化,可是也沒人一起討論,很孤立無援,久了就缺乏成就感。」然後就走人了。
至於每月多少案更合理?許立民打個比方:「 一個主治醫師要記得25個以上的病人就很困難了。當然,長照(個案)的變化不會像醫院那麼快,流動性也可能沒有那麼大;我覺得,初評的新案加上需要review的(舊案),大概50案就不行了。」理想的50案,對比現實的120或150案,這距離實在遙遠。
若再依長照人力鏈往上溯源,啟動長照任務的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衛生局)的照顧管理專員(簡稱照專),負責回應1966長照專線接收的民眾需求,再與長照服務單位的個案管理師協調,部分縣市照專甚至會和個管師共同前往案家訪視。但「照專留不住」也令地方政府頭大。
攤開六都的「113年長照2.0整合型計畫書」,每個縣市都把招募、提升照管專員留任率納入施政目標,也監控照管專員案量,避免他們過於疲憊而離職。
2017年時立法院預算中心曾發布報告,指出2011~2016年長照1.0階段,照管專員人力嚴重缺乏、人均案量近600案。8年後,《報導者》彙整2021至2023年長照2.0尾聲六都照管專員及督導人力,發現部分地區照專平均案量仍逾300案,六都中,無一縣市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劃的每人至多200案。
又以台南市政府為例,計畫書中寫著,照專離職原因,包括無法適應外訪工作、業務量繁重影響家庭、健康因素及生涯;應對措施則包含:「聘足額照管人員,按服務量每200人配置照管專員1名,並由專人主責行政業務,照管人員回歸專業業務。」
由於照專薪資全國統一,物價高的都會地區更難留得住照專。台北市府就在報告書中將人才難尋或可歸咎於「高物價」和「高風險」:
照管人員全國統一薪資,但本市房屋租金昂貴、生活費支出高,照管人員礙於現實考量,決定「返鄉」服務,省下房租費用,造成照管人員離職,轉往其他縣市;照專家訪對象多元,潛藏高風險危害,卻無任何風險工作費用加給,無誘因讓人員久任。
為了留任照專,台北市政府提出5大解決措施,包含:在各大平台廣發招募資訊、提供新進人員輔導培訓、安排教育訓練提升專業之能、每月辦理例會以利照專反映問題、提供文康活動費、國旅卡休假補助費及交通補助費。但是,這5項措施卻未提及如何解決「高物價」及「高風險」問題。

長照人力短缺,居服、日照、住宿機構展開搶人大戰;工作強度高又得輪班的住宿機構在這場人力競爭中,往往是輸家。結果是:機構業者有床沒人力、床位開不出來,需求者一床難求。
如今業界流傳著一句玩笑話:現在連VVIP和自己人都喬不到床。
到底全台灣兩千多家住宿機構總共缺多少人?衛福部曾函文各縣市政府,請住宿機構回報缺人情況。但一位不願具名的業界人士指出,依這函的問法,應該得不到答案:「如果我寫缺一個護理師,我不是明白告訴你,我『護病比』日不到嗎?只要缺(人)就違法,所以我一定寫0。那照顧服務員呢?要開多少床,人要夠啊,所以也會寫0,只是空床不計算。所以(衛福部)永遠調查不了真相。」
住宿機構人力吃緊,開不了床之外,更令人擔心的是照顧品質。照顧工作原本就是人力密集的行業,沒有人手,只能將步驟拆解、簡化,照顧流程變成工廠般的生產線。
擔任住宿機構社工逾10年,張凱傑(化名)觀察到,受限於人力調度,像洗澡這樣的服務也都沒辦法以尊重住民隱私、身心愉快的方式進行。他任職的機構請大夜班的照顧人員在早上加班1~2小時,利用大夜和早班重疊的人力替住民洗澡,「這就變成早上8點要洗澡。你想,冬天那麼冷,有時候可能只有10幾度,得從暖暖的被子裡起來洗澡。」他認為,更理想的洗澡時間點,應該是活動之後,或氣溫比較高的時候,「把洗澡就當作白天的活動 ,讓他們好好洗、不要這麼趕?可是人力上沒辦法調度出來。」也因此,多數住宿機構的住民冬天一週才洗兩次澡。
即便已經重疊兩班人力,時間有限之下,替住民洗澡變得像流水線:住民在浴室門外一字排開等候,3位照服員明確分工,一人負責脫衣服,一人把住民推進浴室扶著,一人負責沖洗。排隊等待洗澡時,照顧人員會讓住民坐在便盆椅上,「因為很多長者都便祕,他們(照服員)會算好時間先塞甘油,讓他們坐在便盆椅上大號,大完坐一陣子,再趕快推去洗澡。」
曾在雙北地區一間超過120床的住宿長照機構擔任照顧人員的小詩(化名),談起前份工作,對那份匆促感也記憶猶新:「不停的清潔餵飯洗澡,每兩、三個鐘頭一次。洗澡時段,每天大概要洗10來床,一個人負責洗,一個負責做裡面的前置動作,洗完我就是汗流浹背,很流水線、很趕。」
流水線般的照顧現場,讓第一線的直接照顧者工作壓力更大,導致更多人離職,無疑是惡性循環。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李韶芬形容,住宿機構這些流水線般的洗澡、快速塞嘴餵飯,只求效率的情況是「照顧趕工」──意即,受限於集體資源投入的匱乏,照顧現場的人力窘迫,照顧工作者只能日復一日麻痺自我感官、想辦法完成勞動任務,這限縮了照顧工作者在照顧上的能動性,而受傷害的風險則由住民承擔。
面對第一線照顧人力流失,住宿式照顧機構只能加聘外籍移工,或乾脆選擇關床。李梅英表示,士林靈糧堂旗下有間住宿機構,扣掉隔離床有43床,但開辦前兩年只能負荷20多位住民入住:「有一整層都是空著,因為沒人(照顧)。Waiting list (登記等待入住的名單)有50幾個人。」她感嘆:「每次看到(政府說)資源布建,談蓋機構、蓋機構,可是人(力)在哪裡?這個問題要面對。」
非常搶手的雙連安養中心品質總監李莉也說,雖然雙連還是以本國籍員工為主要照顧人力,「招聘照服員確實有些困難,」兩年前也開始進用移工,目前聘僱14人。
李莉觀察,業內多數長照機構,外籍移工已經是主要人力,「(本國籍照服員)幾乎都跑去社區型(如:居服單位、日照中心)⋯⋯但是我一直覺得,外籍(移工)雖然是助力,可是不期待他變成主力,尤其細部的溝通、文化敏感度,」還是需要本土的照服員才行。
在搶人大戰中,已有機構祭出留才獎勵。位於台中海線、由永信基金會設立的老牌住宿機構「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從2022年起推出護理師、照顧服務員「留任獎金」。永信基金會執行長趙明明說:「居服員留任2年可以領取5萬元留任獎金,護理師留任3年後可以領取10萬元獎金。我們會先把獎金整筆發給你,如果你不留任,再繳回來就好。」
目前松柏園共有16位護理人員、26位照顧服務員簽立留任獎金合約,從制度上路至今,留任率分別為62%、69%。永信基金會發展部主任葉建鑫表示,雖然還沒有達到理想的目標,但留任獎金制度有助於維持人力穩定和照顧品質。

人力失血的長照,必須立即尋找新血。民間各種長照單位積極向鄰近學校洽談產學合作,招生實習生或兼職。
「長照相關科系的學生在大二、大三的時候就可以考證照、兼職。因為缺人,我們和這些學校合作,現在有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的實習生來兼職,」位於台北市的稻香社區長照機構負責人黃美淑說。稻香日照中心由台北榮總、關渡醫院挹注資源成立,但剛成立就遇上人力荒。
黃美淑記得,那段時間遇到一位同仁離職、新人還又沒報到,有天一位原本說那天不來日照的長輩居然跑來了,這樣照顧人力比就不對了,「嚇死我!我只好跟他溝通說,那你趕快回去喔!」
不過,日照中心到校園招人,也不見得有優勢。
「去學校招募時,我們常常講不過別人。比如說國北護長照學程,他們的學長姊出去是開居服單位,」居服底薪4、5萬元起跳,「那我再去跟人說3萬2,好像就差很多──這個薪水是衛福部訂的(低標),」黃美淑解釋,榮總體系可以再加,但也不好高於行情太多。
政府則是推出三支箭:「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攬才留用試辦計畫」向新南向國家學生招手,並「開放中階外籍技術人才投入日照、夜間居服及團體家屋」。這三支箭中,前二者尚在試辦,後者尚未上路。多元陪伴計畫有43名人力、產學專班的22名外籍學生還在就學孵育中;社福類中階人力目前有33,413人通過勞動部核可,但衛福部擴大中階人力服務範圍的計畫尚未有具體細節,不確定有多少中階人力願意投入社區服務。
面對長照體系中龐大的臨時性、短期、夜間照顧需求,勞動部於今年(2025)4月啟動「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讓民眾在長照2.0服務之外,可自費向公益社團法人申請短期、臨時照顧人力,包含本國籍照服員和外籍移工。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祕書長陳景寧曾撰文指出,臨時性、短期性、急迫性需求確實存在,有時因長照2.0服務派不出人力,或家人骨折、手術後復原等不符合長照申請資格,國人會透過人力仲介業或線上媒合平台,自費聘請看護解決,多元陪伴計畫讓民眾的臨時性照顧多了一項選擇。
根據勞動部統計,計畫上路3個月後,6家非營利的試辦單位進用本國勞工32人、外國籍移工11人,總累計服務485人次、服務時數4,814小時,顯示民眾對此類彈性服務確有需求。計畫於今年9月擴大辦理,再添7家試辦單位,全台共有15縣市納入服務範圍。

在台北信義區的紅心字會是試辦單位之一,首度進用外籍移工投入到宅服務。副祕書長許雅青觀察,計畫開跑3個多月,前來申請的民眾需求多集中於「外籍看護來台前的空窗期」、「外籍看護休假或短期返國」以及「親友臨時需要過夜照顧」。她表示,「初期真的遇到很多在長照2.0得不到滿足的民眾,轉過頭來申請這個試辦計畫。」
例如:長照2.0的居家服務時數太少,不敷使用,或是夜間真的有照顧需求,民眾會考慮搭配使用多元計畫。
作為輔導單位,李梅英本來擔心多元陪伴照顧服務會不會搶了長照2.0的市場,「但目前我們看到沒有,反而是真的有補充性。」她強調,多元陪伴服務計畫的出現,也讓長照2.0系統的個案管理師,增加介紹給案家的資源選項。此外,這個計畫的移工適用《勞基法》、薪水較高;為了不要和家庭或機構搶工,只用「期滿轉出的移工」。

由於《就業服務法》聘僱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工作年限上限為14年、產業移工工作年限12年,如果雇主將符合資格的移工轉任為中階技術人力,可使他們繼續在台工作,且無工作年限限制。
這項政策在2022年4月30日上路,規定在台工作滿6年以上的移工,及取得我國副學士(專科)以上學位的僑外生符合薪資或技術條件者,可由雇主申請為中階技術人力留用。薪資標準如下:
- 產業類:每月經常性薪資逾3.3萬元或年總薪資逾50萬元(僑外生首次聘僱3萬元,續聘回歸3.3萬元)。
- 社福類:機構看護每月經常性薪資逾2.9萬元、家庭看護每月總薪資逾2.4萬元。
根據勞動部統計,「留用外國中階技術工作人力計畫」上路3年,截至2025年9月底,在台移工人數約58萬人,中階技術人才已核可產業類22,283人、社福類33,413人,共核准5萬多人。
不過,這場搶人大戰中,大型機構明顯占有優勢,招募本就艱困的小型機構更難以取勝。輔英科大高齡長照系系主任程紋貞觀察:「計畫分別由政府、產業各支付一半的人才培育費用,要培育一位新南向的二專專班學生,產業2年約需提供25~26萬元(支付培育學生的相關費用),學生畢業後綁約3年(在住宿機構任職)。25~26萬元對小型機構而言似乎有些壓力,但相對於大型機構或體系而言就較具吸引力。」
攤開已登記合作意向的住宿機構名單,上頭多數是中、大型機構,預訂人數已超越目前招生的22人,供不應求,「有一個大型集團一直來問,可不可以給他們40個人?」
程紋貞分析,對負擔得起費用的業者來說,「綁約3年」是極具吸引力的條款:「現在的長照人力,因為職場對於職務的定位、進階或升遷的管道不明確,相關科系畢業學生的投入不穩定。很多機構提供(本國籍學生)『安心就學方案』提早預約人才,但有意願的學生不多。」受到綁約3年條款限制的新南向產攜合作專班學生,自然成為業者爭相競爭的人力。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