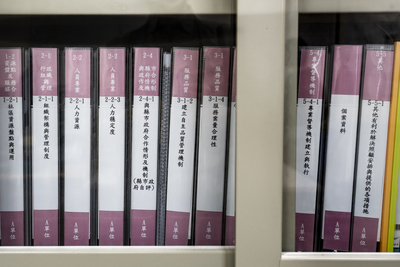多數人對長照的印象,大概是老人一旦跌倒、臥床,就一路向下,直到終站。但事實不必然如此。世界各國早已推動另一種思維:「復能(reablement)」。藉由專業者介入長照,在生活中完成日常任務:車禍癱瘓的患者能重新站起、親手煮一杯咖啡;臥床多年的阿媽經過訓練,能自己走下樓與鄰居閒聊。
「讓長照變成短照」,是「復能」最白話的意義。
然而,台灣的長照現場,大多數民眾並不認識「復能」這個選項;制度上,長照給付缺乏讓專業團隊積極復能的誘因,也讓不同專業之間難以協作。到底在理想的照顧現場,復能應該是什麼模樣?2026年正式上路的長照3.0應如何翻轉觀念,尋回長者尊嚴?
群山環抱的Tgbin桃山部落緊鄰著大安溪與雪山坑溪的匯流處,是台中和平區與苗栗交界的泰雅族部落。在綠林掩映處,矗立著「亞布運動中心」小屋,在山林裡顯得格外顯眼。少了城市中健身房裡的冷漠感,數著「1下、2下、3下」的,不是健身教練,而是照顧長輩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簡稱居服員);使勁在健身機器上要再把手舉高、腳再多抬一下的揮汗者,正是山裡的老人家。
不論是衰老、中風或車禍的長輩,不須下山花整天的時間就為了不到一小時的復健,免費使用的「亞布運動中心」像是送給部落族人的健康禮物,但它的出現,是因為一場嚴重意外。
桃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亞布尤民,45歲從派出所副所長退休後,2023年,53歲的他騎摩托車返家途中被撞了。

「傷到脊椎3節,應該會癱瘓。」55歲的亞布尤民回憶,3位醫師在加護病房討論他是高位脊髓損傷,喪失自主呼吸能力,是不是該氣切?躺在床上的亞布尤民四肢不能動,內心疑惑著:「我怎麼可能連呼吸都不會?」
他不想仰賴呼吸器,用上跑步的技巧,「就深呼吸,吸兩次、吐兩次。」奇蹟般地,一週後他恢復了自主呼吸。看著他ㄧ路走過來的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創辦人林依瑩形容,「從他身上看見強大的生命意志力,身體哪邊可以動,就拚命復健跟練習。」
果真,亞布尤民一步步從「能坐」到「能站」,最後重新踏出醫院,他現在還能經營咖啡店和露營場,手沖咖啡給遊客喝。「我可以烘豆子和端咖啡,」雖然還不能跑,但他滿心感謝信仰給他的力量,「強迫自己承認現在的狀況,接受,然後努力。」
在醫院裡,他看到許多部落居民同為復健奔波。長照交通車會一路接老人上車,通常山裡乘客早上7點半就上車,到了醫院已經9點,長輩復健40分鐘,就得結束;有些偏遠部落,交通車也到不了。有天他對林依瑩說:「我想為家鄉做一個運動中心,把醫院裡的器材搬到山上來。」
亞布尤民找兒子把空地組合屋拆了,搭了小屋。曾任台中市副市長的林依瑩協助募款24萬元,她說,「我出裝潢,他出器材。 每一台他都精挑細選。」朋友奉獻了兩個十字架。亞布尤民笑著解釋:「這些都是我在醫院用過、覺得有效的器材。」
連附近位於位於苗栗泰安的Mepuwal象鼻部落患者也來這裡運動、訓練患肢,「開車只要15分鐘;如果出去豐原,就要1小時。」有族人到這裡持續運動,兩個月就回到學校當保全;還有50多歲的中風病人在住院兩個月之後,就回家1年多,錯過6個月的復健黃金期,「身體僵掉了,」亞布尤民形容,雖然這位族人有些偏癱,還能自己開車來運動,「今天他請假沒來,因為要幫孩子收成四季豆。」
縮短部落與醫院復健的距離,再由居服員協助老人家在家復能,恢復生活功能。這座自力建造的亞布運動中心,在山間部落重寫失能者復能的故事。
一旦失能,積極「復健」、在宅「復能」都不可或缺。前者是在醫療場所下,在黃金期快速恢復肌肉、骨骼機能;復能則是在家透過輔具、環境調整與日常訓練,讓失能患者完成生活任務,比如自行走到廁所,如此可以減少照顧成本。後者對於個案及家屬可能是挑戰,但能讓失能者儘可能恢復原來的日常、促進生活品質的滿意度,正是長照2.0「復能」的精髓。
「但復能服務太被低估了,」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主任陳正芬說。
陳正芬指出,政府衝長照涵蓋率,沒有好好跟人民溝通正確的長照概念,台灣人的觀念仍停留在「老了就是要被照顧,幹嘛要辛苦學習走路,你照顧我就好了」;但在長照3.0,這觀念必須徹底翻轉,她甚至建議居服員應改名為「照顧支持員」,傳達的訊息是「我不是來服務你的,而是來支持你自力生活的」,角色才會被正確理解。
復能應該融入長輩的日常生活起居。陳正芬以打掃為例,當居服員進場,「應該要針對你為什麼不能打掃,透過物理治療師合作找出原因,協助訓練恢復打掃能力,需要『與個案一起做』(doing with),而不是直接代勞,變成傳統的『幫他做』(doing for)。」
另一個問題是,不論日照或居服,長照服務提供者成功協助長輩復能時,政府的給支付金額卻反而減少,而不是獎勵。張竣傑解釋,如果個案失能程度高,服務單位收到的給付較高;「一旦你很努力,協助長輩從坐輪椅、到可以站起來、甚至可以走路,結果CMS(失能程度)級數變低,能收到的錢變少了,等於是變相的懲罰。」
有些長照單位不免擔心,個案變好、結案了,收入就少了。「不要擔心沒有案源啦,台灣愈來愈老,長照個案量會源源不絕的,」陳正芬說,反而是成功幫他復能,不論居服、個管師都會很有成就感;她主張長照3.0也必須讓成功復能的單位及服務者獲得獎勵金等的誘因,「這是多贏。」

復能是由跨專業團隊為長者搭建「回家的橋梁」,即使是在住宿機構中,當「每天的練習」乘上「時間」,身體就可能重新尋回力量。
青松健康管理部經理曾寶儀說,以前長輩住進機構,容易跌倒就約束、尿失禁就包尿布;但現在不同,「你容易跌倒,我要訓練你走路;你尿失禁、我就常帶你上廁所。」就是要讓長輩動起來。
除了機構的照顧服務員(簡稱照服員)給予復能協助,烏日青松住宿長照機構旁邊規劃了診所,面對社區開放,也方便住民就診。診所二樓的復能空間還設了廚房與中島檯,模擬回家後的生活情境,練習倒水、開冰箱、吃飯,甚至簡單烹煮,為返家後的自立生活預作準備。
復能照護耗費人力與時間,但青松健康總經理周孟賢認為,這樣的投入值得,「幫長輩復能,後續照顧反而更省力;更重要的是,能讓他們找回尊嚴。」青松還會為成功復能返家的長輩舉辦小型「畢業典禮」,慶祝新生。

不過,讓長輩重新站起來,有些家屬卻擔心得很:「他會走了,就難照顧了。」曾寶儀帶著一位長輩慢慢恢復肌力、到能扶牆走路,家屬卻非常憂慮,怕長輩回家跌倒。曾寶儀說,「我們一定是希望長輩愈來愈好,如果家屬有疑慮,我們會幫忙思考回家如何照顧。」比如說,會站 之後,不要求快練走,所到之處都安排可以扶的椅子或櫃子,或是用助行器。家人能站起來、會自己走,總是比臥床好。
陳正芬觀察,現代長者有「一跌倒就再也站不起來」、對年老失能的集體焦慮,「但你不要怕啊,失能也可以復能的。」她舉例,有位熟識的阿媽因為生病臥床3週,肌力流失,出院回家後就只能坐輪椅,哭著擔心自己「這輩子都站不起來了」;陳正芬對阿媽信心喊話,同時連結復能資源,「一個星期之後,阿媽高興到拿着助行器炫耀地走給我看。」
復能的過程並不舒服、甚至痛苦,需要旁人鼓勵與自己「想要好起來」的渴望。張峻傑說,為長輩找到「努力的理由」很重要。有位蘇澳75歲的阿公每天都上三樓去拜祖先牌位,中風之後他只能在一樓躺著,天天哭自己很不孝。張峻傑勸他:「和老師(指職能治療師等)好好學,你3個月就可以走、6個月練爬樓梯,練好你就可以去拜祖先了。」這是很大的動能,阿公第一個月就有進步,信心大增,不用人催,自己天天練腳力。故事結局當然是:阿公又能天天為祖先點炷香了 。
與其希望長輩「可以自己走路」,不如設下一個具體目標,像是「走到樓上拜祖先」,但過程是一小步一小步的拆解:先練會站起來,再練邁出步伐、才能爬樓梯。過程漫長,病人和家屬都要有耐心。
上班族陳麥蒂(化名)請一位物理治療師朋友,到家裡看過脊椎開刀後腳力不行的媽媽,朋友給了一台迷你的復健腳踏器,要老人家看最愛的電視政論節目時就踩,最好是「愈生氣就踩愈快」,出門走路也是每日功課。陳麥蒂說,當然希望媽媽可以自己走路,「那時她跌倒,我完全拉不動她,兩個人一起跌坐地上。」如果讓媽媽復能到能自己走,她的世界不會只有家裡。
「『長照』倒過來念,就是『照常』,」張竣傑解釋,讓人回到生活日常中,恢復能力;太多人誤解醫院復健出院後,就不用復能了。

復能的目標,是讓被照顧者重新找回原本就有的生活能力。這條路需要多種專業共同協作,但在現行制度下,專業之間的接力與分工卻被切割得零碎。
愛寧診所的醫師廖少鋒在居家醫療現場,不只要處理病人的病況,還得在關鍵時刻判斷何時該讓治療師介入復能。有位70歲阿媽,因為摔斷骨盆疼痛難耐、不敢動,長期臥床後出現褥瘡。家屬先送她去機構,又因不忍而帶回家,申請長照2.0。
「我去看她的狀況,覺得還有機會恢復,」廖少鋒說,他先照顧傷口,等病情穩定後再請長照個管師轉銜給復能團隊:先讓營養師幫阿媽增加體力,接著物理治療師接手。3個月後,阿媽竟能自己走下樓,親自開門迎接他。
面對醫療與照護間的整合缺口,已有機構嘗試組成跨專業團隊。例如瑞之盟醫事專業整合服務的成員包括語言治療師、營養師、職能治療師與物理治療師等,共同擬定復能計畫,目標是在短期內密集指導個案與照顧者,協助恢復生活能力、減輕照顧負擔。
問題在於,目前語言治療師與營養師在居家醫療中並無健保給付,只能依長照的專業給付支應。瑞之盟執行長邵健容指出,復能是跨專業合作的過程,一週只能一個專業類別進場太少了,若各別專業介入間隔太長,照顧者與個案就難以在黃金時間得到最佳成效。
例如,第一週是物理治療師、第二週是語言治療師、第三週才回到物理治療師,如此隔了兩週物理治療師才看得到個案,在這期間若動作不對、無法及時修正,這兩週的練習就可惜了。如果要多個專業每週來,個案得自費。
阿炎伯一家就是瑞之盟服務的案例。84歲的阿炎伯因肺炎、呼吸衰竭,住院將近兩個月終於出院,瘦到只剩33公斤,帶著尿管、鼻胃管、氧氣瓶回家,極度虛弱,吞嚥功能受損,連喝水都困難,他常沮喪地指著喉嚨說:「它不讓過,我也沒辦法。」
在個管師轉介下,專業團隊陸續介入,瑞之盟語言治療師李康茹設計阿炎伯的復能訓練:阿炎伯很愛唱歌,語言治療師就帶著他一起發聲練習;呼吸治療師鼓勵他吹口琴,訓練肺活量;營養師調整飲食,恢復體力。多方協助下,阿炎伯移除管路,能由口進食,品嘗食物美味,重拾過往的生活。由於阿炎伯願意自費,多種專業便能同時介入協助復能。
邵健容說:「最怕健保做健保、長照做長照;醫師與治療師之間缺乏連結。」真正的整合,必須補接上斷點。
好所宅到宅支援診所院長、家醫科醫師黃子華有親身經歷。他在雲林從事居家醫療,覺得專業服務很重要,像中風者出院回家後,應要專業服務到宅,訓練移除鼻胃管;但他跟長照個管師反映,個管師反而跟家屬說,「你不要聽信黃醫師,專業服務一週只有一次,沒有用的,你要復健就要去醫院,我幫你排交通車,一週去三趟才有用。」

成功大學老年研究所教授劉立凡2022年一篇論文與此呼應。該研究中使用專業服務的案主幾乎多為社經地位較高、家中有外籍看護者,主要原因為專業服務單價較貴,額度用得比較快,家屬擔心服務時數用光,加上復能練習需要家屬在旁協助,外籍看護就變成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復能並非新的概念,早年台北市就曾試辦「石頭湯計畫」,嘗試在社區整合醫療與長照資源,採小規模、一條龍的跨專業團隊及結合社區資源合作模式。當時參與的個管師、君蔚居家長照機構組長陳婉瑜說,「用個別化的方式復能,被照顧者整體功能進步得非常快。在社區實驗場域裡,你甚至分不清誰是照顧者、誰是被照顧者,」這樣就是成功了。
這樣復能成果,關鍵在於個管師能否展現評估需求的敏感度,並靈活調度資源。但陳婉瑜無奈解釋,這在長照2.0的制度下難以複製:「照顧計畫的變更都要經過多重討論,個管師花費時間與使用服務家屬討論後,還得經過照管中心的照專同意,若照專不同意,還得想辦法說服與反覆溝通,照專一年家訪一次,對個案的狀況掌控有限。」此外,若個管師與照專的見解不同,可能會被照專反覆退件。
楊舒琴分析,「照專一個人手上管500案,上次見到個案是一年前,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麼樣子。若照專不相信個管師,個管師很多事根本沒辦法做。」
陳正芬也說,學生的碩士論文正研究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復能的配對,初步發現:失能者通常會不想再多麻煩家人、照顧者也選省力的照顧方式、居家服務與復能沒有銜接,如此一來,「長照服務就一直製造『失能依賴』。」
陳正芬說,若要將「害怕失能」的無力感由長輩肩上卸下,「復能」實踐必須再加油。她舉例,日本很早就有零約束、零尿布、零臥床的「三零政策」,她希望台灣也可以做到。日本的「零臥床作戰」目的是讓長照從被動臥床照護模式,轉向促進長者自立生活;這樣的理念需要實務上照護流程、體制轉換、照護人力、智慧穿戴裝置等翻轉與落實。零臥床運動產生了多面向的益處:一是讓許多臥床的長者,原本關節攣縮,在3個月的練習後,能夠自己用助行器行走;二是降低照顧負擔, 提升長者的自理能力,長照就能變成「短照」。
陳正芬認為,零臥床運動不僅是一項照護實踐,更是一場社會運動,挑戰了傳統的照顧觀念,將照顧的重點從「照顧者的便利」轉變為「長者的尊嚴」;所以,「我們要讓臥床或使用輪椅的長輩對自己有信心,不要自我放棄。」 如果失能者可以知道,如何跟日照或居服,以及復能專業者一起合作,就可能從病床移到輪椅、再從輪椅慢慢站起來,「一天一分鐘,然後一天多次,就有可能改變人生後半場。」
復能的過程雖緩慢,專業支持讓改變一點一滴發生。阿炎伯從臥床,到能坐起、能扶著助行器站立,再到最後能夠自由行走,原本讓他煩惱的喉嚨與呼吸、吞嚥問題不復存在。採訪最後,阿炎伯親自以口琴吹奏了一曲〈望春風〉,旋律由他口中的樂器流洩,伴隨著他重獲的有力氣息。那一刻,那聲音不只是音樂,而是一段強而有力的生命節奏。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