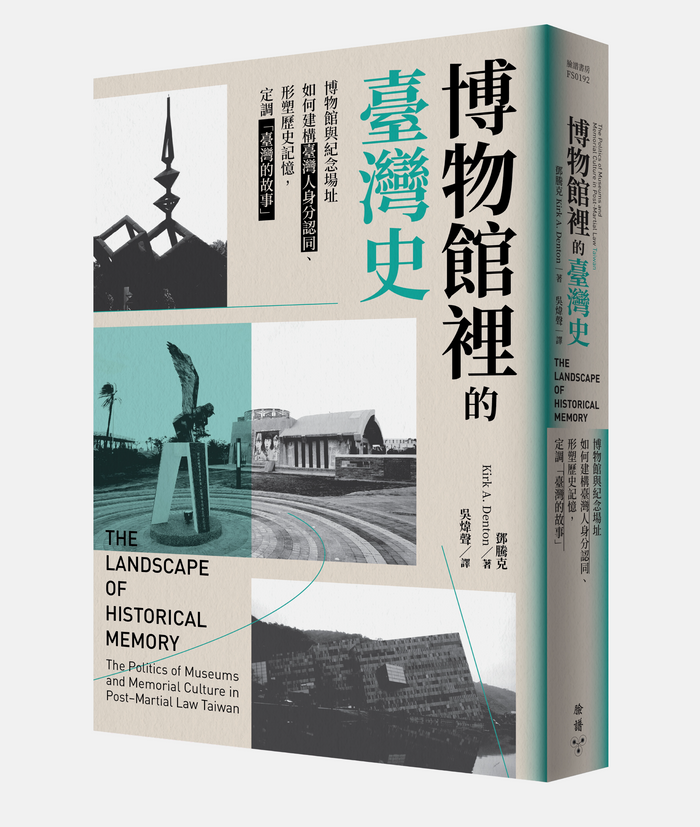書評

《博物館裡的臺灣史》一書作者鄧騰克(Kirk A. Denton)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退休教授。根據其教職官網資料顯示,他的學術專長為「大中華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 in Greater China)及中國現代文學。教授課程中,除了現代中國文學、亞美電影、中國電影、魯迅、流行文化之外,也包含了台灣文學。鄧騰克早在1980年秋,即前往上海復旦大學展開一年的學習,為文革以降的第一批美國留學生之一。中國文化經驗讓他產生探索的興趣,決定繼續攻讀學位,後陸續於1982年完成伊利諾大學中文碩士,以及1988年多倫多大學的中國文學博士。2009年,鄧騰克受邀於中興大學客座,這個階段,他的研究取徑已經從原本的文學與文化,發展出對博物館主題的探索研究。雖然是從中國博物館的研究為起點,但兩岸之間的異同與變遷路徑所寓含的政治性課題,引導他在完成中國大陸博物館專書後,轉而以台灣作為探索基地。
作者自承雖是中國文學訓練背景,但基於現實條件限制,西方世界的中國研究學者,其研究範圍顯然是要更為廣泛駁雜的;另一方面,受文化研究理論強調跨領域、打破文化類型範疇界線等影響,如何不斷地跨越學門、理論觀點、研究範疇與語言的各種邊界,特別是其間多組觀看視角翻轉與不斷越界,讓閱讀這本書充滿挑戰及樂趣。原本作者的書寫為英文,但藉由譯者悉心的翻譯,順暢優美的文句與段落之間,讓人忍不住回頭反思,這些描述原本的中文語境為何,被英文研究者理解後,以英文表達,我們再從中文來想像。在這閱讀與不斷越界往返的過程中,不得不佩服研究者的用功認真,對台灣博物館實務的深刻理解,以及精準地選題,才構成了這本著作。
延續對文化體制的關注,鄧騰克曾經於受訪時指出,博物館與紀念場所對於討論歷史記憶,政治性重構過去、全球化、後殖民與後社會主義的身分重構等議題,提供了相當鮮明的公共空間。這本書的原書名中文直譯為《歷史記憶地景:解嚴後台灣的博物館與記憶文化政治》,「解嚴後台灣」是個清楚的時空框架,他從歷史記憶入手,關切於如何以包含博物館、文化園區、生態博物館等機制,編織出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
鄧騰克認為,1980~1990年代,解嚴後的台灣社會,當政治逐漸自由化,從學術研究、大眾媒體到藝術創作(包含文學與電影),各界紛紛投身於各種視角,積極探索與主張台灣新的國家認同形式之際,博物館設置與其展示論述,顯然也是促成且反映這些對台灣的認同與歷史記憶之政治化解釋,經由博物館的取徑,再進入公共領域中。特別是,台灣的博物館機構大多數均由公部門所主導設置;這些公共機構如何宣稱與訴說台灣歷史,進而產生其影響力,意味著統治集團、國家預算、政黨思維與文化治理,對塑造新形勢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有著其深遠且穩固的影響與作用。這也正是吸引作者充滿探索企圖的詮釋視角。
事實上,對於博物館與族裔認同、國族國家建構,及國家機器意識形態作用緊密相關的批判已經不是新鮮的議題,國內博物館學領域研究中,也不乏相關的研究產出。然而,有意思的是,研究者的外來觀察視角,經由他的田野調查與經驗研究,向我們重新訴說了一個由台灣諸多博物館和文化園區,所共同作用出來的當代政治認同變遷歷史,讓我們得以如同審視鏡中自己一般,不斷地問自己,究竟我們看到的,是如何的一種自我認知圖像。甚至可以說,許多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習以為常,且未加質疑之處,經由一個外來觀察者的提問,讓許多問題意識被重新置疑,這無疑是這本書最大的貢獻。
作者按照博物館類型來書寫,以敘事學的取徑,分析博物館展品如何建構起過往的故事,將這些故事與政治、文化和經濟背景與動機連結起來,既探索展品本身,及博物館所使用的媒介,也討論博物館建築與城市環境中的建築風格與象徵意義。換言之,就是把理解博物館視為閱讀「文本」(p.22)。這樣的寫作策略下,既兼顧了博物館的類型與構成,也梳理出台灣博物館發展與推進的歷史軌跡,讓本書有著愉悅且易於理解的閱讀經驗。「多元文化主義」與「去中國化」成為博物館設置與展示建構過程中,逐步被替代與轉化的記憶論述;甚且,在全書10章的篇幅內,最初以歷史類博物館切入,接著強調記憶、白色恐怖、國民黨集權統治、轉型正義等等,聚焦於政治歷史的博物館與文化園區,而後逐漸轉向文學博物館、原住民博物館、生態博物館等類型,一直到書末作者思考台灣與世界對話的世界宗教博物館與故宮南院,讓本書書名所關切的「歷史記憶地景」可以跨越狹隘的政治史範疇,繼而構成一個更為全面的歷史記憶觀照。

歷史詮釋與記憶重構工程,當然是政治與歷史博物館意義競逐的戰場。作者詳加挖掘了從陳水扁選上台北市長所著力於建構的二二八紀念碑、二二八紀念館,也談到馬英九接任市長後的各種政治攻防歷史,以及中央設置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歷程。從最初,如何著眼於紀念,以塑造新的歷史記憶,療癒整個國家(p.127),到後來國民黨開始主張,二二八紀念活動不再是族群或政治上的怪罪競賽,而是將台灣描繪成正視黑暗歷史,走向自由民主社會的國家(p.137)。作者提出了一項相當重要的觀察與反思:前述這些負面記憶,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論述攻防過程中,都逐漸地導向為「人權」議題,並且收攏在主張「和平」的論述中。他認為,台灣人權博物館不管怎麼樣穿上和平論述的外衣,將其作為合法化/正當化的一種形式,館方在展示發生過的苦難,以及防止苦難發生的權利之間仍有所斷裂。綠營傾向揭露前者,藍營則偏好展示後者(p.149)。故此,國民黨執政時期,將景美營區與綠島兩處關押政治犯的場域,均冠上「人權文化園區」之名,即國民黨不願公開不堪的歷史,但願意從主張台灣是尊重人權的民主社會,來認可這些場址與歷史,以提升台灣的全球形象。
書中經常出現「藍營」(blue camp)與「綠營」(green camp)的用語與分類方式,固然讓人不禁莞爾,但也不得不問,如此一來,是不是持續地強化了藍綠之間的分野,以及這兩個顏色政治符號所意涵的詮釋視角?是否反而讓我們因過度習於顏色政治的觀點,而不免遺漏了其他的線索,以及想像和認識歷史的方式?
不論是中文書名,或者「歷史記憶地景」一詞,均讓這本書中描繪的博物館與狹義的政治運作緊密相連,書中大篇幅聚焦於統治者/公部門在博物館及其展示論述,承載著從白色恐怖、轉型正義到對於和平與人權的高度期待之情。
然而,該書最後探討原住民、族群與土地倫理,接著論述原住民文化如何被主題樂園化地對待,以嫁接起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貼近(/誤讀?),批判在博物館裡展現原住民文化乃是從解嚴之後為起點,實則再次強化以歷史服務台灣本土派政治目的,刻意隱去漢人對土地上第一民族壓迫的過往(p.290)。生態博物館與地方創生的討論,聚焦於社群之經營,最終,則指出台灣在後解嚴時代的自我想像基石,在於我們的世界主義認同(cosmopolitan identity)(p.329)。
這樣的寰宇主義,在不同的博物館與展覽中多樣紛呈,不僅指出這座島嶼受到荷蘭、西班牙、漢人、滿人、日本與原住民的影響,而這個多元身分認同還為台灣當前的民主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礎,讓我們可以跟其他政治體制的民主國家更靠近,離一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遠一點。而海洋島嶼國家特徵,讓我們可以輕易地透過海洋貿易,跟全世界往來。鄧騰克具慧眼地從世界宗教博物館的普世價值,以及故宮南院積極意圖串聯亞洲館舍的任務出發,使得台灣的歷史記憶地景超越狹義的地緣政治想像,連結上前述許多博物館共同關切的台灣歷史與認同,從而讓台灣社會希望融入並影響世界的企圖,得以在此彰顯。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透過外來研究者的觀點,我們在博物館與展示所描繪的選擇性記憶與遺忘中,得以藉由自身的再次詮釋,找到自己所願意安身立命的認同所在。
(編按:本文由臉譜出版提供,內文經《報導者》編輯。)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