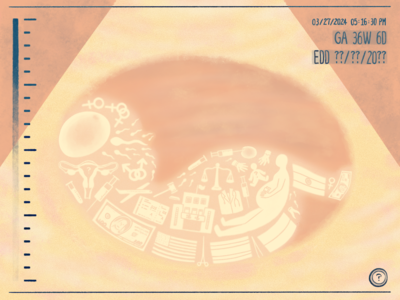2007年《人工生殖法》上路至今,台灣每年約有700個孩子透過匿名捐贈精卵誕生,第一代在立法後出生的子女已陸續年滿18歲。醫學倫理上,這些具完全行為能力的子女,已有權知悉生物學父母(biological parent)的資訊,從而探究血緣來歷、建構更完整的身分認同。但在台灣,絕大多數子女不曾思索過這些議題,因為他們的身世,是家中最大的祕密。
今年(2026),《人工生殖法》迎來上路後最大幅度修正,單身女性與女同志配偶可望適用捐精人工生殖,這代表會有更多孩子直面身世課題。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法首度將身世告知寫進草案條文,子女成年後甚至有機會聯繫捐贈者。孩子的知情權與捐贈者的隱私權如何權衡?修法關鍵時刻,《報導者》採訪家長、子女、醫界與學者,試圖補上台灣人工生殖醫療長期佚失的討論拼圖。
Ruth和Elisa(皆為化名)是大學同學,畢業後,Ruth擔任律師,Elisa朝科技業發展。多年後再聚首,她們面臨共同的人生關卡──生孩子。
Ruth一直想當媽媽,34歲那年,她與沒有婚育打算的男友分手後立刻去凍卵。「婚跟生是兩件事,結婚沒有年齡限制,生育有。」
Elisa是女同志,4年前開始與太太規劃生育。因不確定《人工生殖法》修法進度,兩人選擇赴美求醫,現已將凍卵運往美國,並在精子銀行選好精子,預計今年夏天植入胚胎。
談到未來如何跟孩子談起捐精者,Ruth與Elisa想法一致:「當孩子開口問,我就會說出所有知道的事。」

她們能告訴孩子的內容,將有懸殊的資訊量落差。
Elisa能在跨國的精子銀行看到捐精者從小到大的照片,還有自介、學經歷、醫療史與上百項基因檢測結果,甚至喜愛的音樂類型。「我不認識他,可是從這些介紹,會感受到他是個活生生的人。」
這對Ruth而言有好有壞,她認為揭露的資訊太少,無助真正認識一個人。身為時常承接家事案件的律師,她還想知道捐贈者是否有家族成癮史與家暴史。但萬一揭露過多,她覺得家長會忍不住去搜尋對方,影響捐贈者的隱私。
對比Elisa細節滿滿的告知,Ruth兩句話就能將捐贈者描述完畢。「不知道孩子會不會反問『妳什麼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生下我』?」Ruth露出苦惱表情,接著溫柔笑道:「我會說,因為我很期待你的到來。」
目前正在立法院逐條審查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有機會為台灣的精卵捐贈後代撥開身世迷霧。
過去一年多,是否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配偶、代理孕母適用《人工生殖法》,成為社會熱議話題。朝野立委提出20個版本,去年(2025)12月公布的行政院版草案則脫鉤代孕,將未婚、同婚女性納入適用對象。
- 行政院版《人工生殖法》草案第40條: 人工生殖子女係使用第三人捐贈之生殖細胞所生者,有知悉該捐贈人之身高、血型、膚色及國籍之權利。受術配偶或未婚受術女性得於適當時期告知子女。
- 行政院版《人工生殖法》草案第41條: 人工生殖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詢下列事項: 一、人工生殖子女與其結婚之對象有無違反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規定之虞。 二、人工生殖子女與其結婚登記之對象有無違反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五條規定之虞。 三、人工生殖子女與其收養人或被收養人有無違反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條之一規定之虞。 四、其他有無違反法規關於一定親屬關係限制規定之虞。 使用第三人捐贈生殖細胞所生之人工生殖子女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遺傳性疾病或有器官移植需要時,人工生殖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基於醫療需求,向中央主管機關查詢其生殖細胞捐贈人之姓名及聯絡方法。 依前項規定查詢之捐贈人,以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捐贈生殖細胞者為限。但取得捐贈人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 行政院版《人工生殖法》草案第42條: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使用第三人捐贈生殖細胞所生之人工生殖子女於成年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詢第四十條規定以外之捐贈人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取得捐贈人之同意,始得提供。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以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建立之人工生殖資料庫所載捐贈人資料通知捐贈人,於通知後六十日內未取得捐贈人同意或未獲回復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否准該人工生殖子女之申請。
- 陳培瑜
- 林月琴
- 黃捷
- 洪申翰、范雲、林楚茵
- 王育敏、蘇清泉
- 王正旭
「該讓孩子知道身世嗎?」在現行制度下,台灣僅限異性戀夫妻使用捐贈精卵,而不孕長期被貼上負面標籤,使身世告知彷彿在宣告「誰不能生孩子」。相較被收養的子女已能透過戶籍謄本記事欄得知生父母資訊,透過捐贈精卵出生的孩子,無從在任何官方文件看出端倪。少了制度推力,外表又看不出來,不說似乎也沒關係。眼見孩子一天天成長,更不知道從何說起。
所謂「生恩不如養恩大」,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基因從何而來,真有那麼重要?
諮商心理師洪于珊長期協助同志家庭與收養家庭進行身世告知準備,她表示,個人的自我認同,與家庭關係緊密相繫。人們常將自己的性格、興趣等特質歸因給「像爸爸」、「像媽媽」,並成為理解「我是誰」的基礎。當發現自己與父母的關係不是原本理解的那樣,過往建立的認同框架恐隨之崩解。
「這就像人生導航突然偏離原路,必須重新計算路線。有人消化一下就過了,很快找到新的方向;有人可能因此混沌很多年 或跟家人的關係變得很複雜。」洪于珊說:「所以我會跟家長說,不做身世告知,是跟未來賭一把,因為你不知道孩子會不會自己發現,在面對時,會展現哪種天生氣質。」
她表示,對身世的隱瞞,常重創親子間最核心的信任。「所以比較晚才知道身世的孩子,第一反應不是要找『生父、生母』,是質疑爸媽究竟還騙了我哪些事。」當最親的人都成了懷疑對象,孩子會很難再去信任別人。
祕密是家裡的未爆彈,相關判決指出,隱瞞這類重大事實,不僅傷害孩子,甚至會撕裂家族關係。
專研身分法的政治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戴瑀如,長期關注人工生殖子女的權益,並深度參與本次修法。她形容,「血緣認知權」猶如《人工生殖法》的最後一片拼圖,讓這部法案有機會真正完整。

她也指出,透過精卵捐贈出生的子女,處在無法為自己主張權利的弱勢位置,只要不過度侵害捐贈者的基本權利,法律理應優先保障子女的人格權,然而政院版草案中,捐贈者的隱私權仍占上風。
長期推動身世告知的彩虹平權大平台、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共同聲明,政院版草案以「血緣認知權」為篇名,內容多聚焦血緣與遺傳疾病,恐限縮其內涵,呼籲以「身世知悉權」代之,回歸以孩子成長與發展需求為核心的理解;並建議在捐贈者同意下,擴充捐贈動機、自我描述或給孩子的一段話等非識別性資訊。

但隨著受術家庭增加、捐贈者亦有後代,浮現亂倫風險。TFC台北婦產科診所生殖中心創辦人曾啟瑞,1980年代曾參與創建台北榮總婦產科的精子庫。他表示,當年的權宜之計,是在孩子活產後告知捐贈者姓氏,降低近親通婚可能。他也觀察,儘管社會對助孕科技的態度比以往開放,多數家長對孩子的身世仍相當保守,有些連孩子是試管嬰兒都不提。

每個「不告知」的決定,藏著社會、文化、不孕汙名和挫敗感交織的複雜因素。
對菲菲(化名)來說,她正等待夫妻間的療傷與共識。先生在不孕治療受挫後非常低落,對相關話題高度敏感。她那時一邊消化自身感受,一邊承接對方情緒,在諮商師與朋友陪伴下度過低潮。後來,先生或出於對她的愧疚、或回應家人期待,最終同意借精。一年多前,寶寶健康誕生,夫妻現在是育兒好隊友,唯獨在是否告知身世上還沒有定論,「我懷孕時跟先生聊過,先生說他不知道,可能他自己也很糾結。」
儘管如此,菲菲仔細保存醫療資料,並準備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建立正向觀念,為告知打下心理基礎:「若有天小孩主動詢問,表示他一定發現了什麼,我會誠實回答。」
諮商心理師洪于珊則發現,家長的遲疑,多源自不安全感,擔心告知得不好反而傷到孩子,也怕孩子去找捐贈者、疏離原生家庭。她指出,當家長對自身角色與親子關係有信心,捐贈者的存在不再那麼具威脅性,家長便能鼓起勇氣與孩子談身世。
「若我是孩子,我想知道自己的誕生方式嗎?」常與家長接觸的送子鳥品牌部品牌專員戴瑋萱思考,告知或許有助孩子發展人格,但也可能埋下芥蒂,當進入青春期,孩子會不會將親子衝突歸咎「我不是你親生的,你才這樣對我」?這個未知變數,也是家長的不安。
告知後的發展難料,舉棋不定的家長,寧可先避免孩子身世露出破綻。送子鳥7年前引入AI技術,比對受贈方臉部特徵,配對外貌最相近的捐贈者,恰恰反映多數家長除健康條件外,最在意的就是「萬一孩子跟我不像,可能會對身世起疑」。外貌的相似度,還能深化家長與孩子的連結,有助建立更穩固的親子關係。
不過張棻華與戴瑋萱也觀察到,近年願意公開分享不孕治療經驗的家長逐漸增加,甚至有人拍影片記錄借卵歷程。《報導者》在其他生殖中心的採訪亦發現,少數夫妻已不再執著於孩子是否與自己血型相符,反映不孕汙名與身世守密文化開始鬆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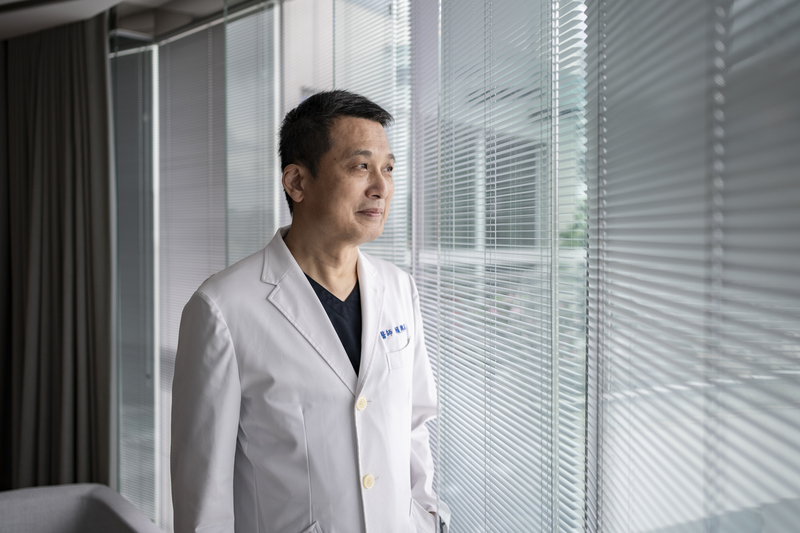
「人的觀念會隨時代改變,」送子鳥創辦人賴興華說,他支持家長對孩子告知身世,「孩子的人生路很長,未來生活是他自己要去面對,他有知的權利。」他表示,說不定愈來愈多家長對告知抱持開放心態,只是沒公開說出來,人工生殖機構不妨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家長的意向與擔心的癥結點。
「國際趨勢是走向公開透明,英國很早就開放精卵捐贈後代查詢身世資訊,我認為台灣現在是討論這問題的好時機。」賴興華說。
歐美、紐澳多為移民社會,家譜學蔚為風潮。2000年代中後期,唾液檢測式的消費型DNA產品迅速普及,當中的「親屬比對」功能,讓不少原先只想知道祖先來自何方的民眾,不僅發現生父母另有其人,還多了數十、上百名出自同一捐贈者的「半手足(half-sibling)」,這些子女透過社群平台等管道「科技尋親」,聯繫捐贈者與手足,使匿名捐贈制度在實務上形同瓦解,成為各國政府健全身世知情權的隱性推力。
儘管消費型基因檢測尚未在台灣普及,戴瑀如認為有必要未雨綢繆。她指出,私下尋親的現象,反映法規未能即時回應社會需求,使當事人自力救濟,卻也可能引發騷擾與衝突。建立透明、合法的聯繫管道,才能權衡各方利益,提供制度性保障。
時至今日,全球兩大消費型DNA檢測公司已累積近4,000萬人次的DNA樣本。使用者可在基因公司的會員網站看到自己的家族樹,並透過網站的私訊功能聯繫家族樹上的成員。若精卵捐贈者本人或家人在同間公司做檢測,且未關閉網站的配對功能,其後代就能發現雙方關聯。
由於價格低廉還常有節日促銷,這類檢測工具已成為西方國家耶誕節送禮的熱門之選。檢測結果約3到6週出爐,因此精卵捐贈後代之間流傳一個黑色笑話:每到新年伊始,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多出好幾個手足,甚至將歲末年初稱作「身世揭曉季」(DC discovery season)。科技讓家族祕密無所遁形,一篇《BBC》的報導標題就直白寫著「耶誕禮物可能毀了你的家庭」。
而在早年未嚴格限制精卵捐贈次數、生殖醫療產業與跨國精卵銀行監管鬆散的背景下,一些男性在小範圍內的醫療院所長期捐精;還有「超級捐贈者(super donor)」透過制度漏洞大量捐精;甚至有醫師參與其中的人工生殖詐欺(fertility fraud),產生難以計數後代。DNA科技意外揭露這些犯罪與問題,為眾多子女帶來真相和痛苦,因為有些人發現自己與前男友或枕邊人有血緣關係。
子女「知」的權益浮上檯面,伴隨而來的問題是:捐贈者會不會被嚇跑?
「當捐贈者知道自己的資料有一天會被(子女)找到,他們還願意捐嗎?」台中宜蘊生殖中心院長王懷麟直接點出生殖醫學界的常見疑慮。
王懷麟表示,該不該對子女告知身世,應該是家長的選擇,而非用制度規範。他認同孩子的知情權很重要,也聽聞部分國外案例中,孩子想知道自身特質、興趣是否源自捐贈者,「但實際上興趣也可能是後天培養出來的,與遺傳不見得直接相關。」

不過他支持在攸關生命的醫療需求下,讓子女或家長聯繫捐贈者,只是現行法規與修法草案,都沒有要求捐贈者出面的強制力。他想起一個令他難受的案例,一對夫妻好不容易借卵懷孕,產檢卻發現胎兒疑有遺傳疾病。父親基因正常,院方趕緊聯繫捐卵者,請對方協助抽血檢查,但對方後續就失聯了。由於無法釐清病因,夫妻在胎兒24週時選擇引產。
台灣的捐贈者,會因為擔心「被找到」而卻步嗎?
29歲的小娟(化名)有個讀幼兒園的兒子,她從兒子出生後開始跨國捐卵,已在台灣、美國、烏克蘭等地捐卵10次。
是否想過自己的卵子創造了什麼樣的生命?小娟說,捐卵女生的群組裡,確實有人表達這樣的好奇。「但對我來說,講現實點,(家長)就買斷了嘛,之後跟我無關。我頂多問仲介有沒有活產、孩子長怎樣、健不健康。」她覺得既然已給出卵子,就不會再過問受贈家庭的生活。
小娟表示,除美國外,她目前捐卵的國家皆採匿名捐贈。如果這些國家未來法規有變,子女聯繫她、想進一步了解她的資訊,她會先與對方家長討論,再決定要不要說,不會逕自接觸孩子。
要是哪天子女透過DNA檢測找到她呢?小娟目前難以想像,「現在覺得卵捐出去之後就與我無關,但說不定十幾年後,心境又不一樣。」

《報導者》訪談生殖中心時,也發現未必所有捐贈者都想與受贈家庭劃清界線。當家長透過諮詢師詢問捐贈者的興趣、生活習慣等非辨識資訊,捐贈者大都願意回應,也不乏捐贈者主動詢問子女是否順利出生。
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黃于玲,曾在研究中訪談30多名台灣捐卵者。她表示,捐贈精卵前必須通過人工生殖機構的諮詢,但這些諮詢多停留在流程說明,捐贈者也會在過程中被告知,《人工生殖法》已明定捐、受贈雙方未來再無關聯;多數捐贈者,就斷了對這段關係的想像。
不過,有捐卵者在她的訪談中表示,若父母選擇對孩子揭露身世,她不排斥孩子未來與她聯繫。因為希望這孩子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其他人與他有所連結。
「所以對於這樣(保持聯繫可能)的關係,當一些捐卵者想得比較仔細的時候,她們會覺得:『為什麼不呢?』」黃于玲說。

但當事涉「關係」,事情就變得複雜。黃于玲說:「你要理解捐卵者的感受,要面對一個人,不只是面對一個身體或幾顆卵子。」若把這些複雜性納入捐贈前的討論與思考,恐被視為拖慢人工生殖流程的負擔,「所以(生殖產業)乾脆不要把關係放進來,把捐贈者的聲音簡化為『不要有關係最省事』。」
然而,「關係」正是影響捐贈者在子女成年後是否願意回應聯繫請求的關鍵。黃于玲認為,若捐贈者始終未被視為子女生命歷程的一部分,只知道新法規定「子女以後有事就會來找你」,當子女真正提出聯繫,捐贈者可能會退縮。
她表示,生殖中心的責任不應僅止於行政說明,而是在國健署帶動下,建立更完整的諮詢機制,讓捐贈者在做出決定前,仔細思考這選擇將如何影響自己與他人的一生。
她也坦言,目前台灣對捐贈者、受贈家庭或子女的研究都極為不足,若要發展符合本土文化脈絡的政策,有賴政府、學界與醫學會投入更多調查。
子女會希望與捐贈者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女同志Vivian和Corrine赴泰國進行人工生殖時,便決定在精子銀行尋找願意具名捐贈的捐精者。Vivian是法律人,她指出,「孩子要不要找(捐贈者)是其次,可是你不能沒有這個資料。而且孩子知道自己真實血緣,是很基本的權利。」
她們的女兒「脆瓜」今年10歲,有雙大眼睛、長睫毛與深咖啡色長髮。再過8年,她就能聯繫精子銀行,詢問這位美籍捐精者的聯繫方式。

自小就熟知身世、也能侃侃而談的脆瓜,被問起想不想與對方見面,她說:「還沒想過,搭飛機很遠,而且我看過他的照片了。」
寫信呢?Vivian說,她可以代筆寫英文信。「可是萬一他回英文呢?」脆瓜說,要是Vivian不在旁邊,她還要用翻譯軟體,挺麻煩的。
那麼,如果她今天對捐贈者一無所知,她想知道哪些事?
「我想知道他住哪。」
為什麼?
「因為我想去看他,想知道他長得有沒有跟我很像。」脆瓜說:「我不想直接見面,因為見面也不知道要講什麼,會很尷尬。所以,我只想在旁邊,偷偷看他一眼。」
「我們是捐贈精卵受孕者」(We Are Donor Conceived, WADC)組織的調查顯示,子女想聯繫捐贈者的動機相當多元,從獲悉醫療史到期待建立長期關係皆有。約3成子女想與捐贈者建立深厚友誼,14%希望建立類親子關係,9%不想建立任何關係,亦有人希望建立普通朋友或人生導師關係。
但實際上,近4成子女與捐贈者沒有往來,有聯繫者多僅止於普通朋友。相較下,子女更渴望與半手足建立關係,近半數希望與其發展親密友誼。
而WADC成員的共識是:父母不應對孩子隱瞞身世,而即便自小知情,多數子女仍會對捐贈者抱持好奇。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