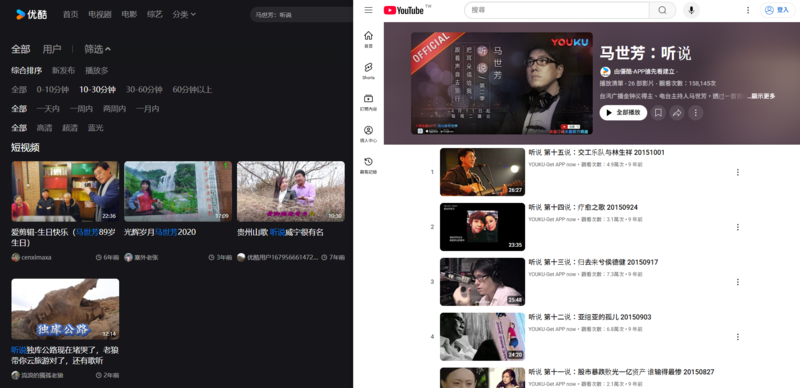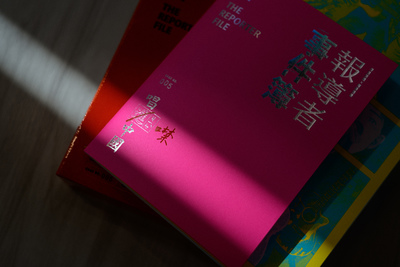在當代中國對外展露霸權野心、對內嚴加管控之前,它曾有過文化的黃金年代。2004年至2018年前後,彼時的中國藝文工作者「相對地」擁有較多創作空間,從音樂到電影,無數叛逆的、反諷的、充滿異議的聲音都能在「遊戲規則下」獨守一畝花田。
當年被中國樂迷譽為「台灣首席文青」的作家、廣播人馬世芳親身經歷過這波餘暉,他在台灣主持音樂節目,也常前往中國舉辦音樂講座。他樂於談論音樂如何反映、推動時代,這股分享藝文知識的熱忱卻成了中國有心人士的眼中釘,馬世芳最後遭上千名「小粉紅」進攻謾罵,就此選擇不再入境中國。
創造過交流,也體會過仇恨,馬世芳身為時代的見證者,如何看待中國十年來的劇烈轉變?對正在經營中國市場,又難以短期離開此舞台的台灣音樂人,以及曾為歌手發言而失落的台灣樂迷們,他又想說些什麼?
總共32集的《聽說》自2015年開播,在豆瓣網上評價9.3分,由馬世芳主持、中國出版品牌「理想國」旗下的「看理想」平台發行,並在「優酷」影音頻道上架,內容從台灣音樂起跑,一路介紹到中國搖滾樂的早期歷史和西洋經典搖滾。
馬世芳會分析音樂背後的創作動機和詞曲細節,深入介紹「音樂如何捲動時代」,於是台灣戒嚴時期的禁歌、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民主運動、西方文藝青年如何衝撞體制,這些主題都出現在他的節目裡,其中的言外之意則交由觀眾自行體會。
正因其內容獨具一格,不時有匿名者回覆那位網友的提問,他們把私藏的節目檔案傳到祕密雲端硬碟裡,靠email分享檔案連結,如此一人傳一人,在豆瓣網的留言串裡互相安慰,更有人寫下這段話:「我們是多麼寂寞的人啊,才會找到『聽說』,才會去聽『聽說』,才會找來這裡。」
結交這些氣味相投、懷抱理想的中國知識青年,是馬世芳當時常赴中國的最大動機。
從事音樂評論、主持工作逾30年,馬世芳曾15度入圍廣播和電視金鐘獎,至今摘下各3座「最佳音樂節目」和「最佳音樂節目主持人」殊榮。2010年開始,馬世芳經常受邀前往中國參加座談、演講活動,逐漸被稱作「台灣首席文青」,各地都有他的書迷和粉絲。
除了實體活動,馬世芳樂於在微博和網友討論音樂,主流與非主流皆信手拈來,話題涵蓋周杰倫的編曲巧思、五月天的成長歷程、陳綺貞如何開創女性創作歌手的新篇章⋯⋯吸引數十萬人為此追蹤。 還有許多中國聽眾會逐集分享馬世芳在台灣錄製的其他電台節目,他與音樂人對談時也從不迴避政治議題。雖然馬世芳訪問香港詞人林夕、中國民謠歌手李志的當下,並不知道這兩人後來會雙雙遭中國政府封殺,他的節目卻在無意中替時代做了見證。
「趁著『台灣』這塊招牌在彼岸文青心中還餘有若干價值的時刻,盡量發揮一點兒我島的影響力。」
當年《聽說》播映後,馬世芳寫下這段幕後心得,後來卻成為小粉紅舉報他「搞台獨」的證據。如今馬世芳已下定決心,不再入境目前的中國。
《報導者》邀請馬世芳接受專訪,完整談論10年間他對兩岸政治環境、藝文產業變遷的觀察。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您在2011年開設微博帳號,逐漸在中國藝文界嶄露頭角的過程裡,您體驗的中國是什麼模樣?
馬世芳(以下簡稱馬):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96年陪家父去北京探親,再來就等到2010年,當時有非常多文化刊物,題目一個比一個硬,我翻開其中一份報紙副刊就嚇壞了,字比螞蟻還小,密密麻麻的。朋友跟我說明,那是應付審查的方法,就算有8,000字也要一天刊登完,絕不能連載,因為有可能第二天就被腰斬。
後來剛好遇上中華民國百年,中國知識界掀起「民國熱」,「理想國」在北京舉辦一系列文化沙龍,邀請中文世界各地的文化人對談,場場爆滿,我記得會場就在天安門廣場旁邊,走過去大概就是10分鐘內的距離,現在不可能辦這樣的活動了。當時有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在觀眾提問時非常激動,站起來大聲地問我們:「請問通往自由平等博愛的道路該往何處走?」
我們在台上就傻了,你知道嗎?他很焦慮,彷彿你現在不告訴他「出門右轉300公尺就是通往自由的道路」之類的答案,他可能就要瘋掉了。我去其他幾座城市辦講座,也常遇到像這樣的年輕人,那時候20多歲的世代,現在大概40來歲吧,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一種非常巨大的焦慮、壓抑,但又有著滿腔渴望。

當時中國媒體出版圈真的聚集很多滿懷理想、有見識、手藝好,非常優秀的人才,我很敬佩他們。可是這樣的人才沒過幾年(進入習近平掌權時代)就被剝奪了大部分的發展機會,很多人壯志難伸,甚至「潤」(Run)出中國,這段時間政治、媒體和文化環境變化太大了。
報:當時理想國是出版品牌,後來如何找上您做《聽說》這節目?
馬:大概在2014、2015年前後,出版審查愈來愈嚴格,做出版的風險愈來愈高,「理想國」創建影音部門,應該是想另闢新戰場,發展新的文化媒體平台,當時網路影音節目正在熱頭上,找資金也比現在容易。
我幾本書的簡體中⽂版都在「理想國」出版,他們就想到可以找我作⼀檔節⽬。畢竟流行音樂從來不只是流行音樂而已,音樂之所以會有那麼巨大的感染力,是因為它勾連到整個社會的集體情緒,那些歌原本可能是為了台灣、香港的聽眾創作,但最終感染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
所以「理想國」就希望做一個節目,從這個共鳴的角度出發,談流行音樂跟社會文化的關係。
當年節目的流量大概是兩、三千萬,我看到這樣的數字覺得高到不可思議,雖然在中國,沒有上億流量就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它確實影響到不少我光憑寫文章恐怕無法觸及的文藝青年。我記得我去成都的書店演講,居然在路上被觀眾認出來請我簽名,我以前在中國從來沒有這種經驗。
報:當時這節目有遇到任何審查,要求下架或刪減嗎?
馬:例如有一集,我介紹了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台灣歌手侯德健,他在兩岸都是爭議人物,那集節目我當然沒有直接講「六四」,但聽得懂的人自然就會知道。當時侯德健已經在北京鳥巢體育館唱過「滾石三十」演唱會,照理說已經解禁了,但後來審查尺度再度收緊,他的名字又不能提,這集節目也就下架了,只剩YouTube還有存檔。
還有一集談「療癒之歌」,我播了以莉.高露的〈今晚天空沒有雲〉,這首歌的創作背景是在太陽花運動時期,立法院外聲援的群眾在深夜街頭疲累不堪,歌裡唱到「並肩相依,手勾著手,我們往後仰躺,淚水沾濕頭髮」。
《聽說》雖由中國平台發行,但攝影、剪輯、後製全都是台灣團隊在台北完成的,我們的團隊把太陽花現場的空拍影片剪進節目裡,原本中國播放平台那邊也沒意見,因為若不知道脈絡,其實也看不出那是什麼。但這集節目上架後就被人舉報,這段畫面只好換掉了。
報:如果那名舉報者不知道照片來自太陽花現場的話,他根本沒辦法舉報吧?
馬:沒錯,在中國有所謂「專業舉報戶」,專門取締和檢舉別人的言行,我在那邊(中國)的朋友戲稱這群人往往會非常透徹、深入地研究有「反賊」嫌疑的東西。
我在深圳參加過一個獨立書店老闆舉辦的音樂節,他有時候會請一些很偏門、小眾的外籍音樂家來演出,觀眾通常也不會太多。結果這些活動一天到晚被小粉紅舉報,那個主辦的哥們半開玩笑地跟我說:他覺得舉報的人有真愛。
因為他看過對方的舉報信,每次都密密麻麻寫一大篇,跟當局解釋這名藝術家做過什麼事、出過什麼作品、講過什麼言論,詳細解說這個人的作品何以會腐蝕中國青年,非抵制不可。
那位老闆曾笑說:「都想拿舉報信來當節目簡介了」。我也覺得這現象挺有趣,怎麼會有人願意花大把時間精神研究你不喜歡的、你覺得危險,甚至深痛惡絕的作品,只為了不能讓其他人接觸到它?
報:除了明顯針對個人的舉報之外,您還遇過哪些審查的案例和細節?
馬:中國政府實施的「社會控制」到底是什麼?長在台灣的我們字面上好像讀得懂,但除非親身體會,我們是很難了解的。
像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96年,陪家父去探望奶奶,她住在一棟高樓裡,那邊住了許多老學者和眷屬,電梯裡頭擺了一張小板凳,有幾位阿姨24小時輪班,負責幫你按電梯上下樓。為什麼需要她們替你按電梯?其實她們的工作是記錄「有誰進出這棟大樓、去幾樓、哪一戶、待到幾點,」這就是社會控制的一個小小部分。
我在書裡寫到「國旗」,必須改成「青天白日旗」,但我覺得沒關係,意思到了就好。還有一次,我們錄《聽說》時做越洋直播拍外景,對方要求事先勘景,鏡頭必須避開所有國旗和「中華民國」的字樣,比方唱片封底「民國75年出版」就不能拍到。街頭要是有法輪功的招牌,更是非避開不可。
我在節目裡提到七〇年代台灣大學生畢業「出國留學」,字幕被改成了「出境」。其實這很荒唐,「出國」說的是去美國啊,緊張什麼,變成欲蓋彌彰。我倒也不會生氣,反正想表達的還是都表達了。
我們做《聽說》從第一季到第二季,就很明顯感受到審查愈來愈嚴,被要求修改的地方愈來愈多。這種事情的癥結,是中國的出版審查、媒體審查根本沒有標準,那是極權政體遂行社會控制的手段。他們不會告訴你紅線在哪裡,有時候寬一點,有時候緊一點,各地的審查尺度也不一樣,有時候北京最嚴,有時候上海最緊張,最後變成大家都要先自我審查,這就是統治者要的。
一個國家社會控制這麼嚴密,甚至鼓勵人民互相舉報,結果就是人與人缺乏信任,法治與契約精神難以立足,你永遠不知道政治風險什麼時候會來找你麻煩。
報:您當時如何衡量自己的風險?
馬:環境如此,你就什麼都不做嗎?還是得試試看吧。但老實說,我真的沒什麼風險,大不了就不去了,錢少賺一點沒關係──只是很多人不是我這樣的。很多人在那裡長期奮鬥,投入了感情、生命、認識同事和朋友,有團隊要養,甚至建立了家庭。
那碰到政治風險,遭遇威脅的時候,還能怎麼辦?假如換成是我在那邊長住,就算不為自己著想,也要保護身邊在乎的人啊。我真不覺得自己有豁出去對抗的勇氣,大概也只能夾著尾巴做人,盡量低調就是了。我很幸運,不用面對那樣的痛苦和難堪。

報:2019年您曾經被舉報「台獨」,當時發生什麼事?您如何面對他們的威脅?
馬:當時微博有⼀位專業舉報戶,專門檢舉各種「港獨、台獨分子」,他是一個小網紅,還當過共產黨的地方小幹部。
此人還找了一堆截圖「證明」我去哪裡演講,還特別引用我在《聽說》節目殺青後的感言,當時我覺得要發揮台灣的文化影響力,所以我說:「我私心想做的是類似於『心戰喊話』那樣的事,」我們兩岸生活環境不同、成長經歷不同,但很多感情是可以互相理解,甚至共通的。
結果那人抓著「心戰喊話」四個字,言之鑿鑿說我一定是圖謀不軌的「台獨」奸細。
報:您之後如何回應這些指控?做了哪些決定?體會到什麼?
馬:我沒有回應,因為任何回應都只會火上添油。從那一刻開始,我幾乎不再上中國社群平台發言。我的微博湧進幾百則辱罵的留言、還有成千上百條私訊,他們用盡一切激烈語言,拋來各種各樣的髒話、詛咒,甚至有不少訊息威脅要殺我全家。幸好,我那時候已經回到台北了。
一開始當然是很不舒服啊,怎麼會一下子要承受這麼多惡意?但我很快想通了,罵我的這些人,99%以上都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他們沒聽過,也沒看過我的節目、沒讀過我的文章,他們根本不知道我是誰,只是在辱罵一個他們心目中虛幻的「台獨小雜種」。
那不是我啊,跟我沒關係啊,你去罵好了,我又不住中國,起碼人身安全是受到保障的。
這個經驗讓我很切實的感受到:在那樣一個言論受管制的社會,帶風向是非常簡單的事。假如當時我住在中國,那情況可能會非常糟糕,我會擔心有人來敲我家門,我可能會接到死亡威脅電話,也可能在公開場合被潑漆或羞辱,甚至遭到暴力攻擊,這都是很實際的恐懼。
發生這件事情(被舉報)之後,我好像更能想像,在中國一旦被貼上當權者不喜歡的標籤,日復一日承受的恐懼和壓力可能是怎麼回事。儘管和真正在中國的異議分子、抗爭者的遭遇相比,我這個根本不算什麼事。
報:不會覺得失去中國市場很可惜嗎?
馬:主持《聽說》酬勞並不算多,而我付出心血、專業換取合理酬勞,是天經地義的事,叫我免費去做節目怎麼可能,對不對?但我也要說,很多在中國從事媒體、藝文相關行業的人,心裡最在乎最在乎的事情,很多情況之下未必是錢。
中國超級大,十幾億人耶,你只要能找到比例上一點點氣味相投的受眾,哪怕只是一點點,像我的「一點點」就是兩、三千萬的流量,你就會有影響力,而且會持續不斷地擴散出去。
當然虛榮成分是有的,被粉絲認出來,合影簽名什麼,你說這沒有一點虛榮嗎,多少有一點。但我最在乎的是:我做的事,是他們真心需要、真心喜歡的,我能為他們的精神生活貢獻一些值得珍惜的東西,能為他們提供一些內在的所需。
開演唱會不就該是為了這樣的聽眾而唱嗎?小說不就該為這樣的讀者而寫嗎?電影不就該為這樣的觀眾而拍嗎?哪怕網路上總會有一些瘋狂群眾,難道你就不唱、不寫、不拍了嗎?
我完全理解想去中國發展的心情,當然可以去啊,我要是還能去,我也會去啊。因為我很想念在那邊認識的朋友,還有在各種各樣的演講場合,看到觀眾席那些一面聽,一面眼睛發光的一張一張臉孔。
他們會在演講結束之後,遞給我一封密密麻麻、掏心掏肺的手寫信。現在去不了中國,我不可能在微信和中國朋友聊敏感話題,也不可能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他們說真心話。我很懷念那些日子,我們可以面對面,百無禁忌地聊各種各樣的事情。

報:您認為在全球陷入保守浪潮,中國對台野心不斷膨脹的當代,文化還能達成什麼?
馬:那些年我去了中國不少地方,認識了許多朋友,從知識人、文青到樂迷,我一直以來的理解就是──共產黨的社會控制再綿密,媒體與出版審查再嚴厲,應該被知道的事情,想知道的人都會知道。
而你一旦知道了,那就“There's no turning back.”(無法回頭)。人生勢必會變得不太一樣。
一旦知道了,你就只能選擇,是要起而行動呢?還是要逃避?還是要做一個順民?不管怎麼選擇,都註定是痛苦的。
這是中國知識人宿命式的悲哀,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大家有各自不同的選擇,有時候只能壓抑、逃避,趁機會來的時候行動一下,有時候實在沒辦法了,也得配合演出,說些違心之論,不管怎樣都痛苦。
不過大環境再壞,還是有許多人在嚴密的文化審查環境中,創造出震動人心的作品。有時候,藝術家能夠用比較抽象晦澀的方式,卻又比誰都精準地描述我們的集體狀態,或者替你說出、描繪我們感受得到,卻還講不清楚的事情。
那些幻滅、壓抑、不甘願,都可能變成創作的燃料。表面上或許是幻滅,但作品依然可以很有力量,他們有話要講,有意見要表達,那是壓不住的,不創作出來會瘋掉啊。
中國的文化人很喜歡講一個句子,叫做「戴著鐐銬跳舞」,就算帶著鐐銬,想辦法也要跳個舞出來,那個舞步依然可以是很動人、很震撼的。就像戒嚴時代的台灣也有審查制度,不也留下許多了不起的作品嗎?
報:當今創作者還有這精神嗎?
馬:Artist(藝術家)作為「公眾人物」的角色,和他們作為「創作者」的角色可以分開來看。作為創作者,愛做什麼都可以,並不一定要在作品裡扛起使命感;作為公眾人物,artist也沒有義務非要對公眾議題表態、行動不可。
真正重要的永遠是作品,不管那個人活成什麼樣子,最終還是得拿作品出來說話。至於創作者作為公民,當然可以對公眾議題表示意見,或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登高一呼,倡議行動、改變社會。
但我們也不需要把自己的信念都寄託在他們身上,要求我們喜歡的創作者也必須參與我們在乎的公眾議題。畢竟他們並不欠我們什麼,哪怕他曾經表態支持某些理念,經歷高強度、長時間的投入,人也是會累的。有時候會需要低調一點,回到私我空間休養生息,或者一段時間過去,在乎的事情不一樣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是為了換取利益,無論是錢財或是名聲,而說了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甚至站到了你曾經珍惜、甚至曾經鼓吹的價值的對立面。
面對壓力,你可以沉默,卻不應該說謊,無論如何不可以變成極權體制的共犯、幫兇,這是我個人的底線。

報:您曾經和樂壇好友、後進們談論過「底線」的問題嗎?如何看待共產黨針對台灣人的文化統戰?
馬:你永遠不知道他們(共產黨)的底線在哪裡,最可怕莫過於此,當你「大」到一個程度,有了利用價值,他們就可能出手要脅你,逼你表忠。
對於這種事情,我只有一句話: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你不可能不知道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你不可能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你必須要有⼼理準備,⼀旦事情發⽣,你終究得做選擇。做了選擇,就得付出代價。
許多曾經深愛他們的粉絲會陷入糾結,既不忍出聲苛責,又不甘繼續支持,有時候搞不清楚該不該罵,有時候又很想同情。也有許多人感到被背叛,從此斬斷情緣,把他們的唱片全燒了,或從此抵制他們的戲,再也不看了。
這些事全部發生在台灣啊,絕⼤部分中國粉絲根本不在乎你有沒有表忠好嗎?是中國政權以這種手段造成台灣的擾動和分裂,醞釀了很多的負面情緒,我覺得這才是最糟糕的事。真正最該譴責的,難道不是一天到晚逼人表忠的那個政權嗎?
報:的確許多台灣樂迷因此所苦,我們如何走出分裂,不讓獨裁趁縫侵蝕我們的認同和情感?
馬:也有人問過我這件事情,而我認為會感到「被背叛」,往往是因為你把很多期待寄託在他們身上,因為他們好像替你實現了什麼、說出了什麼。
那麼從此刻開始,就把這樣的期待拿回來吧,你期待他們為你說出什麼,你現在自己去說吧,你期待他們為你唱出什麼,你何不自己唱唱看?也許從一開始,就沒有誰有義務背起這些期待。
假如我們想⾛上「通往⾃由平等博愛的道路」,這條路⼀定很漫長,我們需要爭取更多戰友,而不是樹立更多仇敵,我們應該求同存異,而不是檢驗彼此的純度。
更何況在創作的世界裡,許多最美的部分是抽象、模糊、難以言說,甚至一說破就沒有價值的。創作信念和政治認同是不一樣的東西,有時候你甚至要接受一個artist的矛盾和遲疑。但也不是說,我們就要無條件地原諒、放下、Let it go,不是的。
所有的傷痛、心碎,感受「被背叛」,都是非常真實的。為什麼會這麼痛,這麼難過?因為他們曾經給過你那麼珍貴的禮贈,那個⼈曾經唱出你唱不出來的什麼,說出你講不清楚的什麼,你才會這麼愛他嘛,所以,要記住這個感覺。
記住這個感覺,假如你決定從此棄追,覺得這個人不值得再愛了,也不需要否定曾經得到的啟發與種種美好,畢竟那些感受還是珍貴的、依舊是真實影響過你的。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