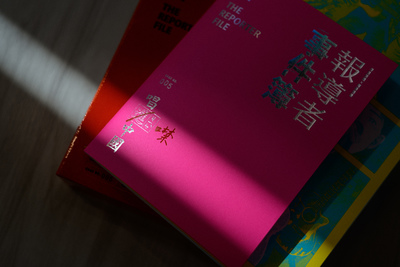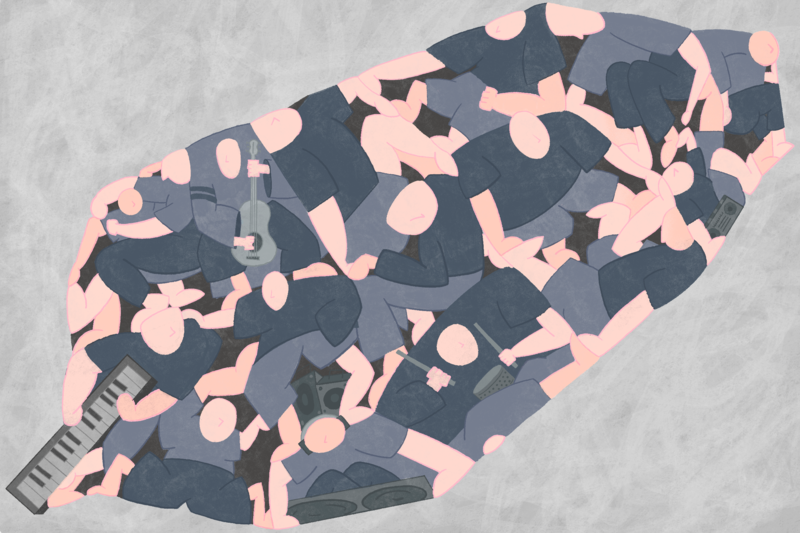
「在台灣只能餓不死自己,去中國才能真的賺錢,再把錢拿回台灣做音樂。」一名出身獨立音樂界的經紀人向《報導者》吐露的現況,也是我們在採訪數十名台灣樂壇人士後,他們的共同心聲。
他們說,台灣音樂界競爭愈趨激烈,音樂製作成本和行銷花費都大幅增加,否則不易被聽見。為了拓展市場,旅運費成本低、語言相通、樂迷基數又龐大的中國,自然成為不少人內心困難的抉擇。
這股掙扎和壓力從何而來?《報導者》從金曲獎報名件數、音樂產業工作者的人數增長和薪資中位數試著找答案,並進一步試問,台灣音樂人如何透過中國累積資本與經驗,又能在中國的政治時局下自保?台灣樂團是否還有別的可能,若想進軍世界,我們的音樂產業又缺乏什麼?
全職經營一組搖滾樂團一年需要多少成本?台灣新生代樂團「裝咖人」去年(2024)的經驗是新台幣250萬元──這筆錢用來支付五名團員薪資、拍攝MV和製作各式行銷文宣,裝咖人的主唱張嘉祥必須身兼多職,親自管理樂團的社群媒體,幫團員們處理行政庶務,盡力減少多餘的人事開銷。
裝咖人自2017年成立,2022年以首張專輯《夜官巡場》入圍金曲獎「最佳新人獎」,張嘉祥卻仍在每天煩惱生存,底線是每個月都讓團員靠表演賺到「2萬元固定收入」,畢竟先養活大家,才有時間繼續創作。假設未來要開始錄製新專輯,五人組還得再籌出至少100萬元的製作預算,這是他們的下一目標。
不斷累積新作品,把作品當成名片爭取登台機會,接著投資更好的硬體設備,讓演出「更精緻」吸引新樂迷,這理應是音樂人的正常成長之路;然而多數台灣獨立樂團、創作歌手卻在過程卡關,就像一間又一間獲利停滯的中小企業,雖能維持運作,卻難有突破,因為整體市場已趨近飽和。

以金曲獎報名件數為例,可看出音樂市場百花齊放:2025年第36屆共1,648張專輯報名,遠多於2014年的398張。加入音樂產業的人也增加很多,文化內容策進院2022年的統計年報指出台灣音樂產業該年總產值為243億元,比10年前高出103億元,而全台6,094名全職音樂產業工作者,也較10年前增加近4,000人。
從數據明顯可見,10年來音樂總產值倍增,讓舞台上的表演者、創作者,以及舞台下的硬體技師、經紀人與行銷企劃共食大餅,不必擔心「玩音樂沒飯吃」,玩音樂成了合理職涯選擇。
但在2022年,文化部報告揭露全台「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工作者的每月總薪資成長率僅有0.1%,遠低於其他行業。2023年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會也委託勞工政策智庫「共力研究社」進行分析,發現台灣藝文工作者近10年的年薪中位數維持在新台幣45萬元至53萬元之間波動,未有顯著成長。
產值提升、從業人數增加,收入卻不見明顯好轉?共力研究社指出,最關鍵因素便是市場飽和,作品數量高於消費者需求,造成「產值乍看變大了」,然而僧多粥少,每名創作者、每間廠牌的「獲利率」持續下滑。
「現況只是讓人餓不死。」
投身獨立音樂界十餘年的鼓手黃堂軒曾在一篇分析音樂產業的文章中感嘆,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不夠精緻的作品會被迅速淘汰,甚至缺乏被聽見的機會,於是錄製專輯、現場演出的硬體成本都在持續上升,導致音樂人的收支更難平衡,收入都得投資在下一部作品上。
此外,發行實體專輯並非當代音樂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真正獲利來自現場演出,所以社群經營、拍MV、設計海報和周邊商品,打造「人設」行銷樂團的重要性倍增。音樂人必須把資本投入「音樂以外」的事情上,才可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裝咖人去年便投資120萬元製作3部MV,張嘉祥解釋,拍MV的用意是「把故事講得更完整」,讓樂迷不只用耳朵聽,也能看著影像,進一步融入音樂。這張《夜官巡場》專輯以台語唱出鄉野奇譚與民俗文化,而且在搖滾樂之外,張嘉祥還把專輯內容寫成小說,獲得2023年台灣文學金典獎。

先從音樂跨入文學,再用影像替《夜官巡場》世界觀畫下句點,同一套概念以三種形式呈現,每種形式都可能觸及到不同興趣圈的群眾,最後匯聚成裝咖人的現場票房。張嘉祥認為,音樂好聽只是音樂人的基本功,當代聽眾們倚賴社群媒體,大量觀看影音平台,他們會期待音樂人做出更多「音樂以外」的創意,讓他們得到「多重的感官體驗」──包含MV,還有現場演出中愈來愈高級的音響、LED牆幕、燈光特效,以及操作這些設備的技師們,硬體和技術到位,才能玩出更多新花招。
這些讓體驗「更豐富」的每項元素,背後都是錢,張嘉祥只好替樂團不斷尋找接案機會和補助,他自嘲,為了活下去,「我們愈來愈像活動公關公司。」
前有市場飽和的收入僵局,後有競爭激烈導致成本提升,台灣音樂人正面臨雙重夾殺。該如何在僵局中創造更多機會?一批音樂人選擇朝海外發展,只要能站上日韓與歐美舞台,回台灣就有機會爭取更好的演出酬勞。還有另一批人則選擇「更大的中文市場」,例如東南亞華僑社群,或者旅運費較便宜、近年展現對台灣獨立音樂喜愛的中國。

同樣成績斐然、出道逾10年的台灣中生代樂團「deca joins」,在2024年共舉辦12場演唱會,其中9站位於中國北京、成都、長沙的千人等級場地,最大場攻進可容納18,000人的上海市梅賽德斯─賓士文化中心;至於台灣的2場,則選在滿場約5,000人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於是同一套表演以票價新台幣1,500元計算,中國累計約售出26,000張票,台灣為10,000張票,兩岸市場相差近兩千萬元收入。
再以五月天為例,他們自2023年起跑《回到那一天》世界巡迴演唱會,截至2025年4月為止共安排71場,其中17場在台灣,11場分散於香港、新加坡及美澳,剩下43場全在中國。舊藝名「張懸」的創作歌手安溥,其《潮水箴言》演唱會預計舉辦7場,5場也在中國。
為什麼台灣樂團、創作歌手在中國如此受歡迎,多年不減?一位長期外派中國的音響工程師肯尼(化名)觀察到,中國政府自COVID-19疫情後加強對內控制的力道,吸引更多中國青年將具有反叛性的「搖滾樂」和「獨立音樂」視為情感寄託,台灣音樂人們在其中代表一種「自由的味道」。
《報導者》也聯繫上一名來自中國南方省分的唱片業企劃程宗昊(化名),他聆聽台灣獨立音樂十餘年,剛開始由陳綺貞、蘇打綠等人領軍的「小清新」 熱潮入坑,接著迷上中國樂迷俗稱「台北三搖」的民謠、英倫搖滾、後搖滾等樂風,喜歡音樂成為他「翻牆」的動機。
面對高壓且「內捲」的升學和職場環境,經濟下滑與政治因素的不穩定感,聽樂團成為中國青年擺脫現實的重要娛樂。長期浸潤在音樂和牆外網路世界,程宗昊自認:「我知道共產黨在做什麼、是什麼樣子,或許像我們這樣的人還是少數,但的確存在。」
程宗昊分析,台灣音樂的流行正好都符合了中國社會變遷,例如2017年「草東沒有派對」爆紅,他們唱出當代青年對大環境的無力感,打中正在追尋「厭世風」的中國樂迷,從此掀起台灣樂團的西進高峰。疫情後中國年輕人尋求慰藉,改由「落日飛車」、deca joins為代表的「浪漫派」和「鬆弛感」占據播放榜單。
此外,近年「方言搖滾樂」也成為中國樂迷的新嗜好,來自哈爾濱的「二手玫瑰」、從廣東省鄉村發跡唱進大城市的「五條人」等樂團,他們操著不同於標準華語的腔調和詞彙吸引年輕人,中國官媒《新華社》還刊出專題報導《方言音樂響起來》介紹此熱潮。
於是一批認真的中國樂迷循線發現「閩南語」和「台語」的差異,開始聽起台灣的台語音樂,裝咖人因此意外收穫中國粉絲。另一組同樣透過音樂傳遞台灣歷史的台灣樂團「珂拉琪」更是爆紅,在中國的串流音樂平台網易雲累積了上萬筆留言、千萬播放數,不少中國網友還在這兩組樂團的頁面中低調、隱晦地討論政治議題。

有別於台灣各城市都可在一天內來回,假設一組樂團在中國展開巡迴演唱會,最常見首站是中國南方的廣東和深圳,接著前往中部的長沙或西部的成都,再把東部的南京、蘇州、上海當成最終站,一趟巡迴可能得趁兩個月內跑完,成員們必須密集搭機逾4,000公里,過程中持續開會與排練,並在壓力下保持身體健康。
對肯尼而言,「想玩音樂、想做一名職業音樂人,這兩件事是不同的,」職業音樂人必須證明自己能撐過高強度的巡演,認真看待這份工作。他舉例,就像運動員成為職業選手之前,也要在各地的小型比賽磨練,忍受舟車勞頓、職業傷害,才能掌握站上大舞台的機會,「在這過程中,我們也會不斷捫心自問:『是不是夠喜歡這件事情(做音樂)?願意繼續撐下去嗎?』」
到中國巡演還有另一好處是,幕後團隊能趁機練兵。肯尼透露,「那裡的主辦單位都很敢砸錢,音響燈光都用最高級的設備,」工作人員們常能碰到台灣沒有代理商引進的硬體。經常往來兩岸的經紀人李揚軒(化名)也強調:
「在台灣市場雖有局限卻『餓不死』的情況下,就是靠中國提高收入後,把經驗、資源帶回台灣,設計出更精緻的舞台。」
《報導者》本次採訪十餘名產業人士,他們全都抱持類似心態。在中國大量巡迴既能賺錢,還能累積團隊的表演功力,甚至向當地樂迷偷渡一些「自由」空氣,乍看一石三鳥;但實際上,這批台灣音樂人永遠繞不開「政治」一事,他們又如何應對?
李揚軒便嗅到,2024年五月天阿信、安溥的表態事件後,業界人士正擔心將失去「不表態的自由」。然而中國舞台對李揚軒仍有必要性,他現在的答案是「減少比例」和「慎選舞台」,例如會在字幕上被中國後製單位吃豆腐,介紹團員時寫著「來自中國台灣」的電視節目,他絕不讓自己的藝人去,這是他們公司的內部共識。
為了不同時得罪兩岸樂迷,這批經紀人仔細管理旗下藝人的社群平台,Facebook、Instagram只發給台灣人看;微博、小紅書才會公布在中國的演出資訊,而且至今堅持用繁體字發文。這是李揚軒維持平衡的小小底線,「我會把中國市場定義為bonus,如果主要收入都倚賴那裡,我們就會被綁住,無法脫身,」他如此強調。
演唱會製作人米妮(化名)表示,她和每一名音樂人合作前,都會反覆確認對方的「創作核心」,了解對方的目標是想名利雙收?或者單純想讓更多樂迷聽到自己的作品?那在題材選擇上,是否願意透過作品傳達一些議題與價值觀,或者不希望作品太嚴肅,只想娛樂大眾?她主張:
「先確認玩音樂的核心,就能知道遇上難關時該如何選擇。尤其是被迫表態後,你一定會失去某批樂迷,結果是好或壞,都要概括承受。」
米妮認為,面對中國市場的政治因素,這是每位音樂人必須事先和團隊溝通的第一關,尤其他們背後乘載數十、甚至上百人的工作團隊,絕不能輕忽這責任。
舉例而言,米妮會評估:「假設表演因為政治問題得取消,對方要求違約得罰款時,我能賠多少錢?」如果合約上的數字大到公司無法負荷,她便會拒絕那機會。但米妮也感嘆,多數音樂人都是「大難臨頭」才開始思考,對風險控管的意識嚴重不足。
「我們不會去問主流藝人這些問題,但獨立音樂人是不同的,因為你來自一個重視創作理念的環境,」米妮笑說,就像偶像歌手會被要求保持良好形象,甚至不能被拍到談戀愛,獨立音樂人的「精神」才是他們有別於主流藝人的「賣點」。
長年協助搖滾樂團設計演唱會與專輯企劃,米妮曾多次赴中工作,也經常和「台派」色彩濃厚的音樂人合作,她坦言「我太可以理解兩方的想法,已經沒什麼情緒了」。米妮自認是台派支持者,從不避諱政治議題,不過西進中國一事對她而言,只是種商業選擇,重點是「大方承認你為何而去,選了就別後悔」。

另一名經紀人蔡淨彤(化名)帶領的樂團在串流平台上享有多首百萬點閱名曲,但在近3年間,他們前往中國演出的次數只有個位數,全是數百人等級的小型場地。對蔡淨彤來說,中國巡演更像為了鍛鍊藝人的表演技巧,況且去過才能知道自己「會不會被誘惑」。
因為行事夠低調,蔡淨彤和旗下樂團可隨時抽身,既不怕遇上政治問題,在台灣也未曾自我局限創作和言論。她透露,該樂團收入的5成來自現場演出,其中又以「政府補助、標案」型的小型音樂祭或會展活動居多,另外5成則是串流的播放數分潤、代言收入和周邊商品。
目前台灣一年約有300餘場音樂祭,根據《報導者》統計,台灣六都加上也經常辦演唱會的花蓮縣、台東縣,有獨立音樂人登台的音樂活動至少有126場,其中40場為售票演出,比例僅3成,其餘86場背後都有政府資金,或由大型財團贊助。
政府主辦的大規模活動包含各縣市跨年晚會,以及花蓮縣夏戀嘉年華、高雄市Takao Rock打狗祭、搖滾台中、台北市大稻埕夏日節等。有財團資金挹注的活動則像是台北「TOYOTA毛毛總動員」、地產商第一大國際開發公司在台中主辦的「好日音樂野餐市集」、7-ELEVEn「高雄櫻花季」等。
音樂人們會將這些活動分級,由獨立樂團為核心設計的活動,例如大港開唱、火球祭、浪人祭等,在他們眼裡才是真正的音樂祭;其餘活動多半只是「為了酬勞」而去的商業演出。也因為純商業演出的核心並非音樂品質,音樂人用同一套歌單按表操課演出即可,表演者無法從中鍛鍊技巧、參考舞台設計,讓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層樓。
「矛盾的是,台灣音樂人就是要靠這些『不是音樂祭的音樂祭』養活自己,」蔡淨彤指出,若單純為了賺演出費,聽眾多半是隨機路人的場合,她們就降低旅宿和宣傳成本,只求固定曝光、持續累積案源;假設是能聚集大批認真樂迷的售票型活動,「賠錢也要做,盡力把舞台效果撐到最好,因為這會成為很多人第一次看見我們的現場演出、成為之後願意買票的起點。」
從小舞台一路唱到大舞台,從乏人問津的中午時段變成晚上壓軸,樂團演唱會開始一票難求,「你可以很明確感受到這群孩子在成長,」蔡淨彤強調,能夠登上的舞台愈大,代表商演機會愈多愈穩定,音樂人才有辦法真正「靠演出維生」,為樂迷提供更好的作品。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蔡淨彤會替旗下藝人設定階段性目標,「每過3到5年就有可能被新人淘汰,大家最怕演唱會賣不動了,必須事前預測風險並調整,不能用太浪漫的方式經營樂團。」由於經營策略明確,她們成功將重心維持在台灣,甚至擴展了非中文圈市場,在日韓與東南亞國家都有演出機會。
在中國以外尋找機會,是近年台灣音樂人的新課題。例如2023年在中國演出數量位居所有台灣人之冠的椅子樂團便積極向歐美開拓市場,他們成為了落日飛車、大象體操等「國際賽前輩」之後,第三組登上美國知名音樂頻道「Audiotree」的台灣樂團。
如同發專輯像發名片、上音樂祭表演是為了後續發展鋪路,在數位時代,音樂人渴望登上「非母語」的串流平台、社群媒體,成為爭取國際舞台的第一關。蔡淨彤便會時刻盯著旗下樂團的Spotify和Instagram後台數據,分析最近有哪些曲子紅到中文世界以外的國家,由哪裡開始被轉發?是否有可能出國表演?
蔡淨彤並非唯一的實踐案例。即使是長年西進中國的台灣音樂人,也有不少受訪者向《報導者》透露,他們正試著減少中國市場比重。
不過簽約多名日、泰歌手的音樂演出仲介公司「九踢文化」總監洪維寧分析,目前能站穩非中文市場的台灣音樂人都有「跨語言」性質,例如椅子樂團和落日飛車的歌詞多是英文,大象體操和另一組在歐洲受到追捧的台灣樂團Mong Tong則是純演奏音樂。

「音樂能打破語言的隔閡嗎?說實話,從市場表現來看很難。」
洪維寧強調,她合作的日本歌手青葉市子、泰國歌手Phum Viphurit在網路上都有百萬粉絲追蹤,除了演奏技巧純熟,最大推力仍是該兩國的文化廣受世界歡迎,西方或台灣觀眾都會好奇他們究竟是誰,既減少了聆聽時的語言障礙,樂迷甚至把「聽不懂歌詞」當成一種魅力──但台灣文化尚未建立起如此賣點。
台灣歌還唱不進全球市場,所以前往中國最方便,多數人眼裡這是「相對安穩」的取捨,畢竟語言門檻卡在那,在台灣也缺乏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為何陷入此困境?長期以筆名「因奉」寫作的樂評人陳延碩說明,台灣音樂市場自21世紀初受到盜版興起、日韓流崛起等影響,產值不斷滑落,直到2015年起才因「數位銷售」和「現場演出」營收回溫,此時填補上市場空缺的主力,就是2010年代崛起的獨立音樂浪潮。
然而音樂市場已進入「你聽你的、我聽我的」分眾化世代,「不可能再出現下一個像五月天一樣的巨星,」陳延碩說,但獨立音樂界在近10年內嘗到甜頭,大舉投資、開設公司,台灣市場迅速飽和,最後造就產業僵局。他認為,無法提高演出酬勞的音樂人,宛如陷入「中小企業困境」,經常落得兩頭空:行銷資本不足、作品和技術也難提升,最後只能追求薄利多銷,或靠補助撐起生計,在各自的分眾裡求生存,無力培養出更健全的產業結構。
洪維寧也呼應:「我們打的不是組織戰,一直在走非常單打獨鬥,而且土法煉鋼的路。」她指出,才華和名氣雖是一名音樂人成功的必備條件,然而音樂人若遇到發展瓶頸,想要提升自我,甚至拚個海外機會,台灣其實沒有夠多的工具、人才去輔佐他們。
洪維寧口中的「工具」意指補助。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簡妙如分析,文化部注重扶持M型化頂端的音樂界明星選手,這方向形同「重點培養有能力奪牌的運動員去國外參賽」,她能理解,補助政策必須向全民端出政績,這樣做比較快速、簡單,只是長期運作後卻造成少數先鋒掌握資源,多數人緊跟著「容易拿補助」的路徑保守行事。
產業也未成熟到人才專業分工的地步,像負責向國際市場引薦音樂人的Promoter(演出買家、發起人)和處理商業事宜的Booking Agent(活動仲介、代理商)兩名關鍵角色,台灣從事這工作的產業人士寥寥可數,造成音樂人光有作品,商業執行面卻嚴重不足。
此外,目前政府補助多集中在「錄製」作品,讓台灣每年的專輯出版量飆升,但從業人士們不一定能分食到大餅,他們紛紛掛念著台灣只「培養作品」卻未「扶持產業」。蔡淨彤強調,補助只是補上一部分資金缺口、提升作品品質,讓音樂人和團隊走更遠的輔助工具,「並不是讓你靠補助餬口飯吃。」
而在音樂人和市場推手之後,還有大量硬體工作人員、經紀人、行銷企劃支撐這產業,他們負責把音樂人拱上舞台,自身前途卻極少被關注。
簡妙如表示,從「實質薪資未增長」和各音樂廠牌的「獲利率降低」這兩點可見,補助政策下一步,應是提升這批「中間層」音樂工作者的待遇,才能吸引新人才投入,並讓既有人力進修。她期待著,台灣音樂在近年成功百花齊放後,接著必須「找到自己的不可取代性」,先從健全產業結構做起。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