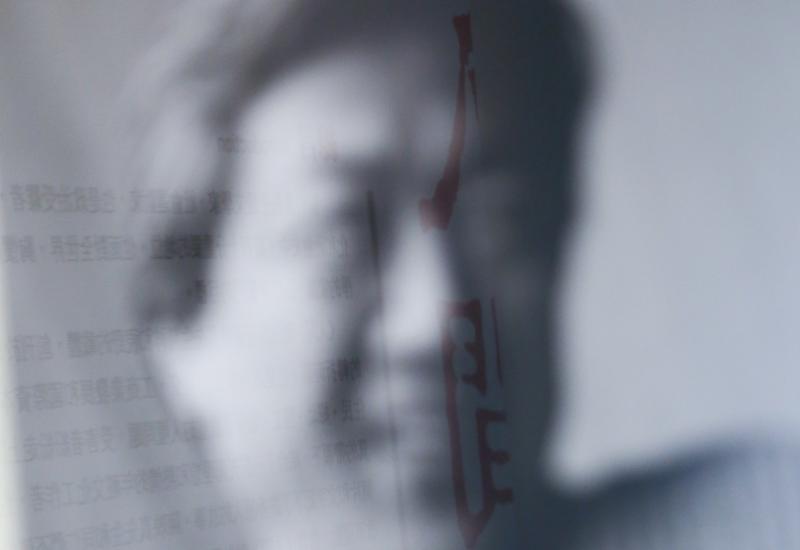影像評論

《人間》雜誌,是許多人都聽過的名字。這本由作家陳映真在1985年創辦的報導攝影雜誌,共出版47期便因財務問題停刊,但它在短短4年間所釋放的能量,卻未隨停刊而消逝;停刊36年後,針對《人間》的相關討論,從未真正停止。
從創刊前就與陳映真共事的《人間》雜誌攝影記者鐘俊陞,在展覽現場直言:「要了解《人間》是一本什麼樣的刊物,就無法不談陳映真。」
促使陳映真創辦《人間》的關鍵,源於他1983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時,接觸到美國攝影師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作品,尤其是關於日本水俁病悲劇的報導攝影。史密斯作品所展現的強大批判力道,使陳映真確信報導攝影足以穿透表象,產生深刻的社會影響。
陳映真在創刊詞中寫道:「我們相信:如果我們仔細地傾聽,深沉地注視,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的笑容和淚痕中,抓住普通人的尊嚴,發現人的意義,則人生雖然像眾生一樣的浮沉,卻有何等光輝的意義。」這也是展覽名稱「浮生」的由來。《人間》的報導對象涵蓋了當時台灣社會的各種邊緣群體:底層勞動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環境汙染的受害者,那些在經濟起飛年代被忽視的人們。
《人間》在台灣媒體史的地位幾無爭議。它見證了台灣民主化關鍵階段,至今仍因喚起社會對政治、族群問題與底層關懷的意識而聲名不墜,相關研究早已累積了驚人的厚度。《人間》被高度推崇,人們談它的理想主義,也談它的社會批判、談它替報導文體帶來的影響,更談陳映真那股近乎宗教般的熱忱。

但讓人意外的是,一本以影像為核心的雜誌,那些奠定其視覺風格的攝影工作者與作品,卻鮮少被當成主角研究。策展人蘇盈龍表示這正是策展的初衷:「我發現《人間》這麼有名,有這麼多論文,卻沒有人針對影像本身,或鏡頭背後的攝影記者做完整全面的研究。」
尋找攝影師的過程充滿斷裂與挫折。許多人在雜誌結束後便離開了攝影界、新聞界,有些攝影師已經過世,有些人的家屬不願多談,有些拒絕回顧。即便找到了人,底片也往往已經遺失或保存狀況不佳。例如攝影師張詠捷因為出家名字改為法號,直到展覽籌備的最後階段才被找到。
蘇盈龍點出《人間》這個巨大光環對個別攝影師造成的遮蔽:「如果永遠只談《人間》雜誌,我們雖然知道影像重要,卻說不出『哪裡』重要。當《人間》被拉高為一個神聖的集體標籤,個體反而面目模糊了。這對攝影師來說既不公平,也十分可惜。」
報導攝影記者常被視為「英雄」,攝影者深入險境、充滿人道關懷,期待透過影像帶來改變。而《人間》的攝影師談起工作時,更在意的是進入現場的姿態、與人的連結,以及長時間的陪伴。
關曉榮便曾提出「拍與被拍的雙向互動」這個概念,直指攝影行為的倫理核心:「照相機的鏡頭,對人本身是具有侵犯性。」面對這種侵犯性,攝影師必須先與被拍攝者建立信任關係。
他說:「你看著要拍的人,他們也在看你。也就是進到現場之初,必須要讓對方知道你是誰、來做什麼、你要怎麼做、以及這一切是為了什麼。你只能依賴這個方法去建立雙方相互的信賴。」
這種信任的建立需要時間。關曉榮為了拍攝蘭嶼專題,在當地駐留了1年4個月:「一個少數民族有獨立的語言、生產方式與生活作息,所有儀式皆隨時序變遷。我只能將工作時間布置在一年四季的輪替中,才能完整記錄他們的生命歷程。」
他也提醒:「不要相信有天才攝影家。」每一張看似自然的照片瞬間,是攝影師反覆按下快門、事後精選的結果:「一個定格的快門時機,常常會按7、8次,甚至10幾次。」
對部分《人間》攝影師來說,報導攝影的意義甚至在於放下相機之後。鐘俊陞提到,自己到了現場之後,拍照反而變成「副業」,更多的時間是投入組織運動,協助被報導的社區居民進行抗爭。他說,本來要做報導,「沒想到我蹲下去10年⋯⋯就是組織他們抗議。」這種介入式的報導與關曉榮強調的長期蹲點形成互補,都超越了單純的攝影記者角色。

這種強調功能性的攝影定位,讓觀者看展時不禁思考:當40年前在雜誌上刊登的照片,被放置在美術館牆上,本質是否改變?
《人間》的影像,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審美而拍攝的,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稱它們是用來揭露社會不公、記錄邊緣群體、喚起讀者行動的工具。關曉榮便曾強調:「作為雜誌,它是一個媒體,所以攝影在媒體上面它不僅僅是攝影,若沒有印刷媒體的傳播,再偉大的美學也是自我封閉。」
然而當這些照片進入美術館,與觀者的互動語境便發生了某種質變。資訊傳遞變成美學凝視,社會行動的一環轉為獨立的藝術物件,原本雜誌集體的傳播力量被拆解為強調署名的作品。策展人蘇盈龍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把它當成作品來看,可是其實他們當時不是以藝術創作為目的,在拍這些影像的時候,是在做一種記錄。」
1980年代的讀者翻開《人間》,看到的是「正在發生」的苦難,帶有強烈的急迫感。多年後,這種緊迫感是否還在?攝影史研究者陳佳琦也提出類似的思考,當初想要透過影像的力量呼籲大家關注社會議題,「那個其實目的性已經不太一樣了,比方說像是礦工的問題,這個可能在台灣已經比較少見到了。」
正如藝術家兼攝影評論家瑪莎・羅斯勒(Martha Rosler)曾提出的批判,美術館的展示往往會剝除影像原本的社會脈絡,將貧困轉化為審美的對象。當悲苦的紀實影像被掛在美術館潔白的牆面上,觀看的框架便已質變,隨著時間推移,苦難被磨成了藝術,當年的『不義』成了今日的『歷史』,前者召喚行動,後者只能召喚回憶。
但蘇盈龍認為這也是契機:「以前我們看雜誌會有文字、會有整篇報導,現在單純看影像,是不是提供了另一種再回頭去看、重新認識議題與影像本質的機會?」
展覽創造了新的脈絡,從攝影史與台灣社會發展對《人間》影像的重新評價與認識。例如這次展覽選入顏新珠、蔡雅琴與張詠捷3位女性攝影師,凸顯了過去在男性主導的報導攝影場域中,經常被忽略的女性視角。

面對「工具轉藝術」的矛盾,關曉榮在座談中拋出更根本的宣告:「其實我反對攝影的作者論。」
他解釋自己並非否定攝影師的貢獻,不同的攝影師在視覺語言方面肯定有個人的特色,但是,「報導攝影為了誰?不是為了攝影的作者,最重要的應是被拍的人。」他舉《人間》第37期《讓歷史指引未來》專輯為例,報導中大部分都是資料照片,許多具強大感染力的照片甚至是匿名的。「這就是我反對作者論的理由。」
當強調「被攝者核心」的報導攝影,被美術館賦予「作者身分」展示,矛盾在所難免。攝影史研究者陳佳琦也坦言:「當我們把它(人間雜誌的照片)做成展覽放在美術館,其實是帶著一點點的衝突或矛盾。」
展覽設計對此做了一定的回應,部分作品以原始底片重新放大輸出,部分則直接以雜誌內頁掃描呈現,讓觀眾同時看見影像的原初狀態與傳播狀態。
蘇盈龍解釋:「報導攝影不是只有單張照片才是作品。被印刷在雜誌上時,意義就已經存在。」這種雙軌顯示策展團隊是有意識地在處理這個矛盾,沒有假裝報導攝影可以順順當當地「升格」為藝術,而是讓轉化的痕跡留在展場裡。
雖然這樣的做法會讓某些觀者覺得,這些照片又被放回其工具意義無法跳脫的框架,但或許也暗示著,紀實影像的意義,始終無法脫離其媒介脈絡。

鐘俊陞在展覽現場說的一段話或許是最好的註腳:「歷史可以告訴未來,當年採訪所拍攝與報導的內容,40年過去,許多本質問題其實並未解決。」他進一步指出:「不管是少數民族、環保或人權等各種問題,許多都還存在,不斷發生。」
當年鏡頭下的主角如今安在?被揭露的問題找出解方了嗎?從這個角度看,這些照片並未完全失去時效性,「浮生」展覽不只是歷史回顧,也是一張對當代社會的檢視清單。
展覽說明寫道:「在《人間》創刊40年之後,策劃這樣的一個研究與展覽是必要的,目的是為了向新的年輕世代,盡可能忠實地呈現這群以陳映真為首的台灣報導攝影先驅者們的活躍事蹟、抱負與成就。」
我們或許無法完全還原當下的時空,但透過「浮生──《人間》中的報導攝影」,我們得以在不同脈絡下重新凝視這些影像,不只思考「觀看」的意義,更思考如果這本雜誌從未停刊,《人間》精神仍在,今日的台灣還有哪些被隱沒在黑暗中的角落,等待被揭露、記錄與改變?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