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初開始在台灣Facebook社群中,無數的性侵犯與性騷擾事件從政黨、職場、校園、娛樂、藝文領域的黑暗角落被陸續揭露,進到主流大眾的視野,猶如一場大規模的集體創傷,人們彷彿一夕之間發覺表面光鮮亮麗、道貌岸然的背後,對他人身體界線的試探與侵犯,長期被整個社會默許與忽視。
2017年起,這波譴責性侵犯、性騷擾行為的全球性別運動從美國興起以來,許多關心此議題者問道「為什麼台灣沒有#MeToo?」在如今台灣終於迎來遲到的#MeToo,並持續延燒的此刻,我們嘗試回到這場運動之前人們的經驗,並探究周遭為何沉默、又有什麼微小的力量在2023年前就慢慢累積?而這場運動又該走向何方?
「就像是永久被壓下來的一個咒語,我們早就沒有寄望這件事會有結果。」
在6月初台灣#MeToo風潮開始逐漸擴散以前,蕪安(化名)完全沒有辦法想像,20年來糾纏她的一段年輕時代的暗影,能夠有浮現大眾視野的一天。
一則300字不到的Facebook貼文,敘述關於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與女學生之間的傳聞,與她的記憶裡的細節疊合:山上研究室、提醒女同學小心、站不出來的受害者、旁觀者無盡的自責與無力感⋯⋯。
那幾乎就是當年大學同學親口向蕪安吐露的遭遇:「跟那個(Facebook貼文)場景描述一模一樣,天黑了以後整棟樓都沒有人,在只有兩人的研究室裡面⋯⋯」當事人冷靜地像是說著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初次聽聞此事的同學們難以置信 ,「落差太大,如果我們不了解這個同學,根本不會相信。」
他們是陳芳明剛來到政大開啟台灣文學課堂的首屆學生,陳當時是最耀眼的學術明星,海外黑名單的被迫害經歷、對現實的關懷以及講課風采,在保守的校園中,猶如平地一聲雷,深受學生愛戴,每週五的課堂盛況空前,教室甚至擠滿了大批前來旁聽的社會人士。
「她說所有可能性都想過,沒有用,跟我們講的時候已經消化了很久,就只是抒發而已,其實並不希望我們做任何事情。」
蕪安説,當事人剛開始向信任的學姊與師長求助時,碰到的就是一連串質疑(「妳覺得老師為什麼要這樣?某某人沒有比較漂亮嗎?會不會妳有暗示什麼?」)與軟釘子(「可不可以去包容、理解、原諒老師?然後自己小心一點」)。
「在我們文化裡,拒絕非常失禮,更不用說強烈的反抗,而對方又是自己的老闆或老師。」蕪安說出長久以來,各領域權力關係不對等下,在文化與社會框架中,悖離「完美被害者」難以啟齒的幽微經驗:
「不像性侵或暴力,沒有留下傷口,但最可怕是,一長串的試探過程:今天拍妳的手沒有躲,拍拍肩膀,也不躲 ,偶爾抱一下,妳也不躲,那能不能再往下?一直在往下試探,降低戒心。當事人可能還在想,是不是誤會什麼?甚至自我質疑。身體界線的感受本來就沒有明確標準,當下感到不舒服,如果沒有強烈反抗,她好像感到自己也有責任。」
畢業後,當事同學像逃難般遠走他鄉,徹底遠離原本認真耕耘的一切,到國外重新開始另一段人生。
即便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同學的經驗像看不見的傷口,長久刻在蕪安心裡,難以癒合:
「這麼多年來,這是很痛苦的一個結,沒有辦法處理,甚至談它都覺得很痛苦。對我們來說,他是這麼有意義的一位老師,卻做了這麼恐怖的事情,我們有一種很分裂、集體被背叛的感覺。」

2023年的台灣,#MeToo運動終於衝破沉默的高牆,一個接一個受害者的字字血淚,從政黨、職場、校園、娛樂、藝文場域的幽暗之處振聾發聵,進到主流大眾的視野,使人們彷彿一夕之間發覺那光鮮亮麗、道貌岸然的表象後面,無數的性侵犯與性騷擾事件恣意橫流。
在大眾還沒準備好聆聽之前,訴說的意志已如暗潮,一波波浪拍打上岸際。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中,只發出空蕩的回音。
作家吳曉樂親身見證並加入這股「前#MeToo」浪潮。
「2016年我碰到了那件事後,剛好有位朋友在美國,說那邊有一個叫做#MeToo的社群運動,我們就想說在台灣是不是也應該做一點什麼。」她口中的「那件事」,是今年6月初受害者證言首次萌發之際,才在《人選之人》編劇簡莉穎揭露自身性騷擾經驗的鼓舞下,多後終於在Facebook公開「傷害相對小」的事件──被當時任職《端傳媒》評論主編的曾柏文邀約上車,在私密空間裡的語言試探。
儘管已出版一本廣受好評的小說,然而身為剛出道、除了腦海中的故事無可憑恃的年輕作家,面對掌握策劃與邀稿決定權的媒體主管,考量未來職涯機會與話語權的不對等種種因素,這個經驗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無法訴說也無處安放。
「那時候我試圖在同理他(曾柏文)像是一個低潮的人,可能很疲倦然後做了不太對的表態,你的腦袋會斷掉,想要建立一條線,連結他的公共形象,會覺得你的經驗一定是出錯了,不應該是這個樣子,所以那時候我就把這件事情放在心裡,也不太敢跟別人講,因為我很害怕一旦跟別人講,別人會覺得我是不是哪裡也有問題 ,怎麼會跟一個男生晚上11點在車上聊了一個多小時?」
吳曉樂說出無論情節輕重程度,在權勢不對等關係下的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普遍都會經歷的錯愕─合理化─自我懷疑─噤聲過程。
直到有更多周邊的朋友,不約而同遭受類似經驗,他們於是決定在Facebook成立「如果你也聽說」粉絲專頁,在連地球另一端的美國#MeToo正在混沌不明的摸索階段,就嘗試讓這些經驗現身在公共平台中。
「結果完全大失敗!」吳曉樂說,當時整個社會與當事者都還沒準備好訴說與聆聽,反挫排山倒海而來,包括冤枉無辜者疑慮、不具諮商專業背景、如何承接受害者的質疑等等,這個可謂台灣首次回應#MeToo的行動戛然而止,折衷後轉型成「性暴力小學堂」,以資訊性的知識內容,面對性騷擾/性侵害中隱微的禁忌經驗。
除此之外,2019年吳曉樂還在網路中從自己的日常經驗出發(在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睡著,一名男人的手拿起她的頭髮嗅聞),蒐集在種種生活場合中──從家庭、校園、職場,從公共到私人空間「身為女性,在社會中的不愉快」。她將短短幾天獲得的數百則留言,整理為共筆的雲端文件檔案,網友留下的真實心聲,至今超過20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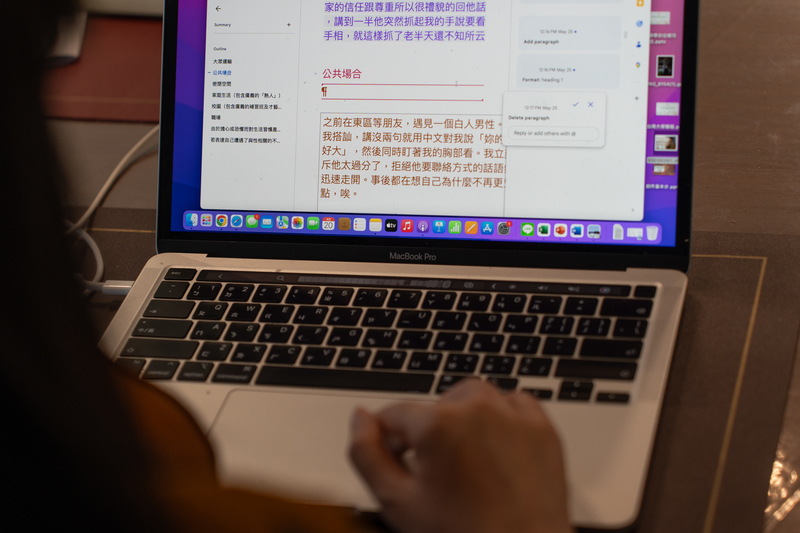
我們隨時隨地都活在被侵犯的恐懼,甚至被侵犯還要被檢視「有沒有引人犯罪的理由」,更糟的是被侵犯的人還可能會被評論「長得這樣誰要摸啊」等等言論,女人成長之路真的一點都不容易!(Eliza Yeh)
「我覺得2023年不能夠說是(#MeToo)大爆發,因為其實已經有很多次小小的累積,就像地震一樣,可以持續感應到的東西,」吳曉樂強調,除了她在社群媒體共同參與或自發的行動,2021年藝人「雞排妹」鄭家純策展的【38號樹洞】性騷/性侵真人故事信件展覽,也是如今受害者現身之前,隱藏在風平浪靜下的洶湧伏流之一。
「為什麼台灣沒有#MeToo?」
對於在此之前投注極大心力思考與實踐女性主體經驗的吳曉樂而言,這個問題縈繞不去。
「那時候想了很久,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性犯罪或者是性暴力絕對不會比較少,那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受害者)出來?我個人的理解是,因為我們是一個重感情的社會,很多時候我們會把傷害搓成別的東西──某一種大家吞得下去的東西,譬如說『他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啦』、『他只是那時候情緒不好』 ⋯⋯我們是一個很鄉愿的社會。」
吳曉樂直言,自己當年遇到的不舒服經驗後,安靜許多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考量對方有家庭有小孩,「大家都不講,所以這一切就累積成今天這麽長一串,這是台灣社會的特殊現象。」
同樣的問題,從2020年時,也困擾著長年關注性別議題的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王曉丹: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造成「2017年以降,台灣於這波譴責性侵犯、性騷擾行為全球性別運動中消音沉寂的現象」。
「我們快速從威權轉型到民主時代,威權時代極權者決定一切,在民主時代的正當性來自專業界線,用法律與制度節制行使權力的方式,可是整體社會對於權力的正當性範圍沒有明確意識,職場性騷擾、權勢性侵都是逾越專業界線,有權者用權力達成想做的事,大家也沒有意識到權力/身體的界線,瀰漫著『大局為重』文化,崇尚表面的理想形象,所以《人選之人》著名對白『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成為一個重要破口,讓受害者有力量說出那些長久以來沒有被看到傷害。」
王曉丹形容,台灣這波遲來的#MeToo運動,猶如對於瀰漫整個社會的「假掰文化」的一記重擊。

近年來常擔任公部門性平委員的王曉丹,在第一線的觀察中也看到,即便擁有進步的法制規範,性平議題仍困在形式主義的窠臼中,離整體文化的改變仍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有時參加性平會議很無奈,許多單位只看好操作、好評鑑的硬體或量化數字,例如廁所的男女比例,『性別主流化』往往淪為口號。」
「我們只在定義行為,卻非常欠缺理論的討論。性在我們的社會是很難在公共領域展演的事情。我有guts(膽量)介入別人身體的界線,表示我有權力,不只是滿足情慾,更是一種權力操演,把被侵害的人變成一個『性客體』,練習到順暢,即使別人知道,也不敢反抗,受害者只能不知所措,受傷也不敢講,」王曉丹表示。
「法律可做一些事,同時也篩選掉更多經驗,法律需要證據、無罪推定、有一定程序,一旦你的事實無法成為事證,或是你的事證無法進入程序,真實就沒有辦法被司法呈現,失去正當性,這個經驗更難啟齒。」
王曉丹觀察,目前台灣的#MeToo屬於善惡對立的「真理控訴」──指出某個做出壞事的惡人,以及受到侵害的受害者;而下一個階段,需要進展到更深入層次的「文化控訴」,使整個社會意識到,最終目標是要反對其背後的權力結構,以及把他人當成性客體的文化。
吳曉樂從6月初揭露自己的經驗後,信箱每天湧入讀者私訊,向她吐露從輕微性騷擾到家內性侵的各種#MeToo遭遇,並尋求建議與協助管道。在繁重工作與身心壓力下,每晚應接不暇的訊息,使她多次動念要「撤」,然而看到許許多多因為階級與資訊落差而不知如何是好的呼求,有法律系背景的她仍然撐著,充當接線生,為不同情境的網友提供轉介管道。
「用一個很有年代的說法──我很像是『Yahoo奇摩知識+』。這些工作,應該是由國家來告訴大家怎麼辦,悲哀的是,可能政府也不曉得這是什麼。沒有一個中心或專線,能夠提供受害者指引,從學校、職場、親密關係、家內性侵等狀況該怎麼辦。現在像是一個醫院突然要迎接大量傷患,可是連最基本的檢傷機制都還沒有,」吳曉樂說。

這也是現階段#MeToo之火之所以大規模延燒不止的關鍵,它填補了從社福到醫療,從司法到警政等維繫社會安全運作的天秤中,巨大的空缺。不斷疊加的受害者聲音匯流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洪流,控訴著人世間律法無能、體制也束手無策的罪行。
「我覺得很難過的是,來找我的這些年輕人,為什麼身邊沒有人可以講?我會問他們,我這麼遠,要不要去找身邊的人?他們說已經講過了,旁邊的人可能給一個很打擊的答案,有些時候就是家人,說你怎麼那麼的傻、那麼的蠢⋯⋯。會發現在跳出來說之前,都不知該如何去定義這些事情,整個機制並沒有去容納這樣子的人。」
14歲的時候,吳曉樂在台中出過一場嚴重車禍,將近3個月不良於行,在醫院清創的過程使她終生難忘,甚至比被車撞的當下還要痛。現階段#MeToo的過程,對她而言就是受傷後,要面對的清創劇痛。
「護士拿著大棉花棒狂刷混雜著血與泥沙的傷口,我媽在旁邊看我痛到已經快昏迷了,說不要這樣,護士說不行,現在不如此,一旦傷口開始癒合,沒清乾淨的髒東西被包進體內,以後更麻煩。現在我們就在這個狀態啊!(性侵害之後)說出來的二度傷害,包括社會的不諒解與疑惑:『為什麼當下不講』、『為什麼不反抗』 或者『是不是圖什麼』 ⋯⋯台灣社會是一個很會逃避痛苦的社會,我們很容易為了不想要承擔痛苦,然後導致日後付出更大的代價。」
在憑藉個人力量,承接還不敢或不知如何訴說自身經驗網友的同時,吳曉樂彷彿重新經歷了一遍十幾年前車禍後,傷口長出新生皮膚的過程:
「要經歷長出新的皮膚的過程才是困難的, 不只包括受害者,其實加害者身邊也要有人,因為不管再怎麼樣,他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我們不可能永遠把這些加害者排除在我們的社會之外。 」

「讓受害人被療癒之外,讓加害人也有機會反省,這個社會可以讓他繼續活動,不是永遠就社會性死亡。」
就像他將事件說出口得到新生。
今年6月2日自我揭露9年前遭知名八九民運人士王丹性侵未遂,其後開記者會、至地檢署提告。傷口積鬱已久,更早前,李元鈞也想過對大眾訴說,時局卻難。2014年太陽花運動剛結束,王丹在任清大教師期間和學生走得近,李元鈞坦言,「我不可能一回來直接說,這個人在美國想強暴我,那時候的氛圍根本不可能,也快接近大選。如果那時候說,會被弄到爆炸,輿論壓力下一定是我最弱勢。」
更令他有苦難言的是政治圈的特殊性。
「政治工作這麼敏感,如果知道你會記錄、告發,大家會對你打上問號,」曾任議員助理的他說,政治圈沒有祕密,性騷擾吹哨者不像一般企業能低調處理,若想保全組織形象,就得忍下來。李元鈞解釋,其他圈子人才流動相對快,「可是政治文化這種東西是累積起來的,新陳代謝沒有那麼快,累積下來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大局』,大家會盡力維持住、不讓它崩塌。」但這波浪潮讓他看見發聲有被善待的可能性。
同時,他也憂心台灣#MeToo會步上歐美社會的後塵:
「我很擔心互信基礎會瓦解,大家對受害人的信任程度會降低,那對真正受害的人來說,是另外一次的傷害。再來就是加害人,可能會找到另一個群體,建立另一套論述,去捍衛自己的正當性。」
從王丹案看來,海外華人社運圈已造成新一波分裂跡象──年輕的「白紙世代」要求正視性壓迫,和王丹同輩的「八九世代」,則看重中國民權運動的存續和發展,言論對抗已在Twitter延燒。這些效應是李元鈞始料未及的,但他無意否認王丹對民主運動的貢獻,也不希望「取消文化」造成更大對立。
李元鈞一再強調,大眾別拿他當標準來要求其他受害者,「我很怕大家覺得受害者就是要恢復成這樣。好像你都說了,就應該要走出陰影、要好起來,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一輩子的陰影。我可以這樣說,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這樣說,希望大家能溫柔地對待這些人。」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