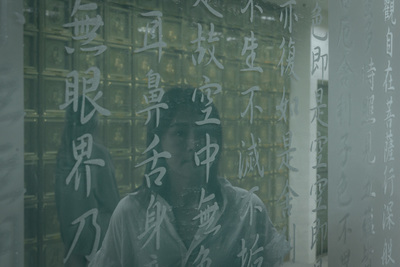主流自殺防治的框架,讓遺族受制於被管理的自殺風險對象,關係只剩下對活著的交代。在此背景下,遺族如何能真正坦露自己、相信社會上有人願意傾聽並理解他們的感受?又該從何學習接納自我的方法?
各國自助團體的出現,揭示遺族對於被貼上「高風險」標籤的不滿。近十年,台灣也陸續有遺族在公領域發聲,或以實際行動來籌組線上、線下的遺族社群,將個人傷痛轉化為群體養分,藉同儕互助、經驗者們彼此扶持,共同習作艱難的喪親課題,也讓更多人看見遺族複雜的情感和豐富的生命樣態。
1993年,18歲的李沐芸,在學校接獲姊姊自殺離世的消息。
喪親之後,她開始穿姊姊的衣服、用她的化妝品;甚至在自責時,想起姊姊手上的胎記,李沐芸將自己的手燒傷,只為「變成她、替她活著」。
姊姊離世的陰影籠罩家人,回憶那段日子,李沐芸形容如「行屍走肉」,從台北護理學院(現為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休學,找份工作勉強求生;下了班,每晚她需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青春心靈從此禁錮。
「研究所每堂課都在自我探索,分析哪個想法是我、哪個想法其實是她(姊姊),就是一個切割的過程。我開始想,如果這是她的,那我還要不要保留?我要重新開始,還是要繼續?如果她的(想法)已經變成我喜歡的,那好像留著也沒關係,不是非要改變不可。」
在校園裡,她相識恩師林綺雲。一次林綺雲聽說李沐芸遭遇後,反應是大哭,心疼李沐芸事發多年都沒人可傾訴。老師的同理、讓情緒迸發,對李沐芸來說像是示範,讓她知道「悲傷」是被允許的。此後,林綺雲常帶李沐芸演講、訴說失去姊姊的事並支持她投入自殺者遺族研究,在敘事與轉化的過程,逐步釋放傷痛記憶。
2008年,李沐芸出版《我是自殺者遺族》一書,這是台灣第一本以自殺者遺族立場,探討生命價值的書,書名以簡單的直述句,展現對遺族身分的肯認,也期待這個真實的「我」,能被他人理解和看見。
至今近20年,李沐芸研究、出版書籍、投稿文章,也上廣播電視,將個人經驗化為助人養分,為遺族群體發聲。她認為,自殺這件事對遺族來說是很殘忍的,從目睹事發現場、非自然死亡的遺體,再到做筆錄、驗屍的過程,「都要家屬去做,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只能人家說什麼就照做。還有,要帶著寫有『自殺』的死亡證明,去辦各種行政流程,這很痛苦,那兩個字對家屬來說,看一次就痛一次。」

李沐芸最早開始陪伴遺族的工作,是在馬偕紀念醫院的自殺防治中心。該單位於2005年,由時任精神科主任劉珣瑛成立。他們服務企圖自殺者、也關注遺族,李沐芸當時擔任遺族的個案管理師。
曾任馬偕自殺防治中心主任、現為馬偕安寧療護教育示範中心主任的方俊凱表示,在那背景下,做自殺防治的人很多,但「做自殺遺族(關懷)的人非常少」。馬偕試圖補充這個不足,將遺族列入服務對象,開辦針對該群體的心靈照顧計畫、提供悲傷輔導,也辦理「遺族說故事團體」。
其中,說故事團體尤其特別。方俊凱解釋,這是他從美國自殺防治學會、死亡教育諮商協會等國際單位舉辦的研討會中認識的「團體治療模式」;2005年底,他將此模式移植回馬偕試辦,至今仍由同仁每年持續運作。
方俊凱說,說故事團體立基於「建構主義心理學」的理論架構,希望達到治療性目的,協助遺族透過敘事、回饋和思考,重建被失落瓦解的生命意義,「每個參與者會在家準備好自己的故事,再到台上講20分鐘,台下的觀眾要像看電影,不能打斷或評論;在故事說完後,才分享自己看到什麼、想到什麼、感受到什麼,但不可以問問題。」
說故事的療效在於,「講完故事、聽完大家的回應後,我們才會要講者訂題目。本來講者對於他要講的故事,可能有一個設定,但他在講的過程、腦袋在想的時候,還有他講完之後,感覺可能就不同了,往往他們會說我本來的題目是什麼、現在它變成什麼,這過程就是建構式治療在講的『重新建構』。」
不過,團體基於心理健康的治療架構和目的,對遺族重回日常的幫助,仍然有限。方俊凱說:「在團體內,成員不會有太多互動。可能他們在中場休息時,有閒聊、認識,或者結束後有其他聯絡,慢慢自己變成支持團體,那就是非架構式的了。」
但方俊凱所謂「非架構式」的關係建立,反而是李沐芸更為在意的重點。她關心遺族在醫療體系的「治療」框架之外,能否維持一般人際互動,在生活當中是否能得到社會網絡的理解和支持?這個在意,讓她希望透過同儕自助的方式,尋找遺族陪伴的不同路徑。

自殺失落的悲傷,可能很漫長,李沐芸明白,陪伴遺族需要長時間投入。
2022年,李沐芸成立「社團法人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持續至各政府與民間單位,分享遺族的經驗和故事。透過倡議與投書,她努力傳達「悲傷是無處可去的愛」的觀念,並表示遺族真正需要的幫助,是去學習如何面對這份情感。
李沐芸強調,儘管遺族在悲傷調適時,可能需要專業醫事人員的協助,但他們在生活中遇到的根本問題,是「不被容許好好悲傷」。
她指的是,遺族因悲傷剝奪的情況、自殺與精神疾病汙名,以及被政策當作自殺防治對象等各種因素,使得他們的情感和處境,很難自在地表現出來。在此情況下,身邊的人對待遺族,若只是一味要他們面對失落、走出悲傷,其實是無法理解遺族的真正困境。
運用協會資源,李沐芸製作並出版繪本《他選擇離開,我們⋯⋯》,描寫遺族遭遇自殺失落的過程、悲傷時的情緒反應,也呈現他人可能對遺族造成傷害的話語,並提供療癒建議。繪本用多樣色彩呈現,希望遺族悲傷不只有灰暗,也讓該群體的故事,更接近大眾視野。
巧合的是,李沐芸提倡「悲傷是愛」的觀念,也是日本遺族在凝聚社群力量時,呼喊的口號。
日本上智大學社會福利學部特聘教授岡知史,關注該國自殺者遺族自助小組,並進行質性研究。他提到,日本政府在2006年實施《自殺對策基本法》,各地方政府依此法案,撥款資助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為遺族建立支持小組。
然而,日本遺族對政府這套以治療為出發的服務,同感不滿。2008年,專屬遺族的同儕團體「全國自殺者親屬協會」成立,岡知史寫道,有超過1,300名自殺者家屬參與。
日本遺族家屬串連的團體,強調三個新觀點,分別是:與悲傷共存(Living with Grief)、悲傷是我們的(Grief is Ours),以及悲傷是愛(Grief is Love),主張「即使遺族感到悲傷也沒有問題」。
社群的發聲,受到其他領域的關注響應。其中,前NHK新聞總監清水康之,後來成為遺族支持和自殺預防的社會運動家,他先後參與「全國自殺者遺族綜合支援中心」的成立,也創辦「自殺對策支援中心Life Link」。前者主張提供遺族「完善的生活支援」,因為自殺的發生,可能源於個人或家庭的債務狀況;事發地點,也經常使家人涉入公共或私人的賠償問題。因而,跨專業協作有其必要,除了醫學和心理健康範疇,遺族也需要法律與經濟支援,面對事後就學、就業和人際關係變化,調適過程,也考驗教育系統與社會資源的因應。
數據推算外,調查也呈現實際訪問結果。好比有56.4%的家屬,感覺到自殺汙名,認為警察和醫療機關的應對,為遺族帶來二次傷害。另外,若亡故者為家中經濟支柱,隨著時間推移,生者可能會對家庭財務感到擔憂。
在社群支持方面,79%的遺族表示,他們知道家屬有自助小組聚會可以參與,45.6%的遺族在調查當下正參與聚會、25.2%則是曾經參與,他們回饋:
「透過聚會,我感覺到解脫,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經歷類似事情的人。」
Life Link將調查現況作為政策建議的白皮書,提交給日本政府。依據全國自殺者親屬協會的網站所示,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當中,目前至少有一半的區域存在相關自助小組、聚會的社群,參與者不約而同地表示,希望自己的經驗也能幫助別人;另外,還有律師協會,專為遺族提供法律方面的專線諮詢。

在台灣,10多年前失去母親的朱妍安,也正持續打造陪伴遺族的支持團體。
2018年,朱妍安創辦「隙光精神」,從遺族訪談開始,到製作介紹影片、辦理聚會,再到經營實體空間⋯⋯這些行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媽媽自殺了,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我也參加過馬偕的團體,結束後,還是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
她憶述事發後狀態:「每天光是要吃飯、可以睡得著覺,都很困難。」比起談論喪親的失落悲傷、進入心理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朱妍安也同意剛成為遺族時,更需要的其實是務實資訊。比方說,政府有急難救助、紓困方案,喪親3個月內的家屬若符合條件,得申請以支持喪葬、傷病或生活方面的開銷。
每個家庭情況不同,她盡可能探索關於遺族與自殺相關的知識和資訊,初衷是想為自己找答案,也分享給其他需要的人。朱妍安和夥伴歸納整理,發展成隙光精神每年必執行的工作項目之一:辦理「關懷課程」。這是任何想了解遺族的社會大眾,皆可參與的實體課,內容分為知識與實作兩大部分,前者談論生者的悲傷歷程、不同失落階段的需求等主題,後者則涉及情緒覺察、自我照護、關懷方式和注意事項等。
隙光精神志工吳正華說,身為遺族,參與課程讓他收穫很多。比如,有項活動是有一個人拿著一壺很重的水,其他人必須在不能說話的限制下,找到方法去幫助承受重物的主角。就像遺族有個說不出口的重擔,旁人想幫忙,「如何不要憑想像,先入為主地行動,而是試著觀察和同理。」
吳正華認為,「在這裡,我感覺我們是朋友,不是誰要諮商誰,」精神和心理治療是另一種管道;在社群裡,想要的就是「你跟我一樣」。
朱妍安說,陪伴遺族沒有想像中困難,只是大家一起練習,再一次好好地吃飯、睡覺和生活,讓他們知道:
「悲傷可以慢慢去經驗也沒關係,不一定要符合生活本來要他成為的樣子。」
她分享,曾有位喪妻的男性,夫妻倆過去常一起爬山,後來他不再爬山了。朱妍安和夥伴邀請他再次上山:「第一次,真的很難過,他到每一個地方,拿著太太的照片自拍,那一天,我們整趟都沉默。」但是第二次、第三次,他開始在路上說笑,也帶朋友一起來,「才發現真正的他,是一個很搞笑、很幽默的人。」

每一次自殺發生,就有一群人成為遺族。
一年年下來,朱妍安總會「看到新的需要」,又或者課程上完,有參與者想來團體當志工,於是志工培訓的工作也不能停下來。
但自殺者遺族是「被迫成為的身分」,在陪伴其他遺族的同時,朱妍安也需要持續面對自己身為遺族的事實,和自殺失落帶來的課題。
她提到,母親離開時寫了遺書,其中一句話是:「因為妳長大了,所以媽媽可以放心地離開。」這成為朱妍安的惡夢:「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辦法過生日。我會想,是不是我不要長大,她就不會走?」深深的自責,她無法輕易忘記。
對吳正華來說,要能消化自責感,代表著,「要理解逝去的親人,某方面來說,就是接受他的決定、接受自殺真是人生的選項之一,但這極違背我原有的價值觀。我會想,如果要接受並理解自殺的選擇,是不是就不該阻止自殺行為呢?想去對抗自殺,扭轉自殺現象的努力,是否終究只是控制欲的展現?」
「如果你說自殺是可以阻止的,那是否真的表示,我們遺族做得不夠,才沒能阻止家人的離去?這麼一來,我們自責的理由,不就成立了?」他問。
成為遺族5年,吳正華說,這個身分帶給他很多「思維上的矛盾」,但他認為,即使思考自殺議題非常費力,卻是很難閃躲的課題。他盡量讓自己從這身分當中找到施力點:
「減少受害者,拯救其他受苦者,這是成為遺族後,我的正向動力之一。」
每年母親忌日,朱妍安都會為自己安排一趟旅行,回去跟媽媽一起住過的地方。朱妍安將這天名為「心想日」,意思是「在心裡好好想念的日子」:「我會好好哭、好好想念她,我知道我的每一滴眼淚,是因為我們的愛還沒有說完,而我不想要因為她做了這個選擇,就讓愛消失。」
她說:「雖然媽媽用我不理解的方式離開,但我覺得,愛應該要比她做的這個決定,再更偉大一點;我們之間的關係和連結,比她做了什麼決定還重要。所以,即便她讓我很生氣、很受傷,但我會告訴她:『我還是很愛妳、我理解妳,只是如果有下一次,請妳不要再這樣做。』」
「要知道你可以活下去,也許你現在不這麼認為,但你真的可以。」
- 減少詢問遺族事情「為什麼」發生,自殺的成因多重且複雜,任何單一回應,是簡化亡者和遺族經驗的回答,可能讓遺族不知所措。陪伴者或可和遺族一起回憶逝者、對他們的故事展現更多好奇,因為逝者會永遠存在遺族心中,遺族很難將他忘記,甚至害怕忘記對方。
- 若想關心遺族又擔心說錯話,請記得無聲的陪伴也是一種方式,只需讓對方知道邊有人、不用獨自面對。若不知如何陪伴對方,可直接詢問,讓遺族提出他希望的互動方式。
- 自殺發生後,從辦理後事、處理遺產、死亡除戶等大小行政流程,對遺族而言可能都很陌生;回到日常生活,有關亡者的遺物整理、住宅清潔乃至基本起居,可能也需有人照應,這些都是陪伴者可以詢問並幫忙的。
- 可和遺族相約,做對方原先就有興趣的事,或是帶他一起培養新技能,因遺族並非只有「倖存者」這個身分,還有豐富的生命歷程、多種的社會角色,只需身邊人保持耐心,和遺族一起發現更多可能性。
- 若遺族需要外部專業介入,可陪同他們尋找資源、向外求助。心理師表示,不用害怕和遺族一起前往諮商室,這讓專業者可以理解遺族,同時也能提供陪伴者建議。從不同的位置,一起給予遺族適當的關心。
資訊來源: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理事長李沐芸、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祕書長李曉芬、沐昂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陳柏任、盼心理諮商所所長呂伯杰
波頓在1970年代經歷兒子自殺離世,隨後創辦了該國最早的遺族支持團體之一The Link Counseling Center。近幾年,她在遺族論壇Alliance of Hope上發表文章,表示因為兒子的自殺,每年母親節都讓她很痛苦,但是,波頓仍珍惜與兒子在一起的時光。她寫道:
「是他教我敬畏(revere)生命,了解它的珍貴和脆弱,並能珍惜每個當下。在母親節這天,我意識到正是苦難,讓人類彼此相遇、不再陌生,生命透過這寶貴的親屬關係,重獲意義。」
失落的痛苦,可能讓陌生人彼此相遇,產生新的連結與力量。
Alliance of Hope的創辦人沃克(Ronnie Walker)受訪表示,她設立遺族論壇時是60歲,一人經營。17年來,這個公開的英語論壇,有各國民眾註冊,至今已累積26,000多名成員和70位志工,成為一個自主營運的生態系;任何人在此貼文、發問,會無時差地受到會員或志工的關心與回應。
論壇之外,她也經營部落格和電子報,「我們每個月大約會發到3~4篇文章,」累積的內容,都成為重要知識,「曾有一位波蘭母親寫信給我們,說當地沒有太多支持系統,想請我們授權讓她翻譯部落格文章。我告訴她沒問題,只要註明出處,」沃克說,光是翻譯上的合作、交流,就可以讓更多人得到幫助,她認為台灣或許也可以這樣做。
自殺失落是全球議題,很多人都在經歷。朱妍安曾在隙光精神的粉絲專頁,收到來自馬來西亞遺族的私訊,想找人談談先生的自殺,以及此後如何陪伴孩子。馬來西亞直至2023年才將自殺除罪化,汙名與避忌更加艱難。朱妍安和夥伴透過電話、視訊,一直與這名馬來西亞母親保持聯繫。
只是,不少遺族都要等到事發至少10年後,才有辦法將自殺喪親一事說出口,而目前遺族的同儕支持管道,在台灣多集中於北部,朱妍安期待有更完善的支持環境,看見遺族的需要,讓他們不用再長時間受苦。
朱妍安說,衛福部翻譯了一份「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但放在網站上,要自行下載:「不是每個人在事發當下,都能馬上知道或找到(這個資訊)。我覺得政府其實可以在當事人會碰到的單位,無論是警察局、醫院或學校,有一份這樣的手冊或文件,即時給遺族,讓他們在遇到時,不會那麼不知所措。」
即使陪伴與安慰,無法輕易讓悲傷消失,但朱妍安說,「人的需求很相似,找到認同與歸屬感,相信自己被愛,」這份相信要能發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經歷,旁邊有人這樣對待你,讓你知道自己值得活在這世界,才有可能去長出真正的樣子。」她的語氣平緩而堅定:
「我覺得人在受傷時,可能會變得很可怕,不小心傷害到自己,也傷害到別人。但就是需要有人不斷告訴他們,你是被愛的、你是被愛的,我不會放棄你。」
從受苦到助人,或許這些遺族中的行動者,為的就是有天能有更多聲音,願意對他們、對失落的遺族們,這樣說。
遺族關懷
- 衛生福利部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
- 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 社團法人台灣遺族親友關懷協會
- 社團法人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
- 隙光精神
-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 FB社團自殺者遺族
- 國際論壇Alliance of Hope
- 日本組織全国自死遺族総合支援センター
自殺防治
-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 24小時安心專線:1925
- 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 張老師專線:1980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