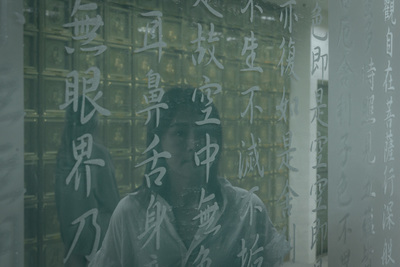自殺作為非自然死亡,涉及醫療、檢警單位介入,讓遺族的失落和哀悼,被迫進入公共領域。從事發、出殯到重回日常生活,遺族需要經歷哪些和社會領域互動的環節?過程有哪些情境?可能引發怎樣的感受?又如何影響遺族對自身遭遇的看法?
6年前剛進入博士班就讀的林佳,得知父親於家中自縊的消息。當時她配合員警調查,令她難忘的是警方要求她和家人在警局觀看監視器畫面:「我非常害怕,怕看到我爸吊上去的場面。我跟弟弟去看影片,要播的時候,我緊緊抓住弟弟的手。」
影像會出現什麼?未知的恐懼攫住姊弟倆,直到播放結束,才知道根本沒有駭人的畫面,監視器只拍得到家門外面,警方播放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家屬確認,沒有外人進入,排除他殺的可能性。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18條:「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也就是說,碰到自殺這類非自然死亡的情形,會觸發刑事偵查流程,檢警單位必須調查,以釐清亡者死因。
員警Y(化名)表示:「無論現場是什麼狀況,我們都要先假設是他殺。」因此,調查初步會判斷是否有外力、外人介入?現場是否留有遺書?而死者身上有無外傷?外傷是否為人為?
警方會派出偵查隊、鑑識人員和員警到現場,拉上封鎖線、勘察環境、拍照或蒐集物證,確保現場跡證不受汙染、降低證據滅失的風險。另外,也會調閱監視器,向報案人、亡者的親友等關係人,詢問和製作筆錄。最後,檢察官會請法醫檢驗遺體,確定不是他殺後,才會發給家屬「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能夠開始辦理後事。
從調查開始,到遺體檢驗完畢的過程,稱為「司法相驗」。遺族從事發後,到為親人辦理後事前,必須配合上述各方調查往返警局、醫院或殯儀館等地;若自殺發生在家中,調查期間家裡會拉上封鎖線,回家等於回到命案現場。
員警Y說,調查時面對家屬,「要先判斷對方有沒有事先幫當事人保險,還是當事人生前有沒有就醫、吃藥、跟誰處得比較好,都要去問,這是必走的程序。如果不是他殺,我把筆錄給你看都沒關係,因為自殺不是犯罪。」
林佳回想:「雖然可以理解警方立場,但那個當下,我們真的滿不安的,不知道自己會面對什麼,在場也沒有其他可以陪伴或支持你的角色。」
其他遺族也表示,有時警方的詢問,讓他們感覺自己被當作「嫌犯」;即使當下再悲痛、不安,都只能靠自己。
Y對此回應,調查當下若真的遇到哭得比較厲害、處在震驚發抖狀態的家屬,警察能做的,是給對方一杯水,讓他緩一緩,再進行筆錄;或者,他們會詢問當事人,是否有其他親友可前來陪伴;如需特定性別員警來溝通,或是其他需求,都可以提出來,「因為我們也知道,發生這件事是很遺憾的,」他說。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翁立思表示,通常遇有自縊情形時,「警察跟我們,都要確認當事人真的明顯死亡、家屬也不願意急救,我們才會放著(維持原狀)。但若家屬有要求,救護人員都會協助剪掉繩子、留下繩結(作為證物),然後幫當事人移至地面或床上,走完急救流程。」
然而,林佳表示,當時她的父親是單獨在家中離開,後續依遺書和監視器推測,時間約在中午左右;警方發現時已是下午,他們先通知母親,其他家人才輾轉得知。林佳說,最初到現場的警察和消防隊,未將父親從繩上解下、急救與送醫,而是「直接保留現場,並拍攝照片。」
Y說明,警方一般不會主動移動大體,除非在公共場合,鑑識人員到場之前,為避免驚動群眾、受媒體關心,才可能先將遺體覆蓋。另一名員警施嘉承解釋,「採證完,就能移動(遺體),」通常是等葬儀社來幫忙處理。
無論如何,林佳與家人的遭遇,讓他們感覺,好像家屬只能當無頭蒼蠅,他人怎麼說、就怎麼配合。
再後來的後事辦理,林佳說,由於父親和家人都沒有宗教信仰,傾向從簡,刪除了禮儀業者提出的告別式布置花籃、法會道士等項目,業者竟說他們「很不孝」、「很冷血」。這不合理的對待,與隨之而來的情緒成本,最終由家屬自行承擔。

依據一般治喪流程,禮儀公司普遍會設定基本的服務項目,從禮儀師的配置、遺體接運、豎靈安靈,到各式用品準備、告別式會場的人力設備,再到最後火化與晉塔,根據儀式繁簡、會場規模和用品差異,可能提供不同價位的「套餐」,方便家屬選擇。
在非自然死亡的類型當中,自殺尤其特殊,不少遺族都曾聽聞民俗傳說,宣稱自殺者的亡魂會在枉死城內受到懲罰,例如不斷地重複自殺,最後才接受審判,進入地獄。「打枉死城」這項儀式,是由法師率領「破城」、解救自殺者,不用在枉死城內繼續受苦。
有遺族受訪時表示,手足自殺時,父親因為心疼孩子,能做的法事都做了,花費近30萬元。
這種厚葬的現象,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授陳增穎認為,一方面可能是出於對信仰的虔誠,相信法事都要面面俱到,才是對家屬好;同時,傳統儀式有教化生者的目的,民俗上是要藉著儀式發揮嚇阻作用,讓生者不敢效仿當事人的自殺行為。
但另一方面,過多的儀式安排也可能是喪葬業者向家屬進行「恐懼行銷」,意即,業者藉家屬對自殺禁忌的恐懼,促成服務的販售。陳增穎認為,也許因為家屬也內化認為自殺是不好的,才讓業者的推銷奏效。
有遺族就曾困在禁忌裡,並為此自責:「媽媽過世後,我對留在家裡的東西感到害怕,害怕習俗說的晦氣、不吉利,也害怕想起死亡。我在房子四周擺鹽巴祛邪,這麼做的同時,心裡很羞愧,羞愧自己害怕自己的母親。」
無法參透的神祕,分化了遺族與逝者。林佳說:「我很討厭聽人家說『自殺會下地獄』,或是『自殺的鬼魂怨氣很重』這類的話,我爸爸沒有怨氣很重,他只是過得很辛苦,用這樣的方式結束一生,我相信他值得好好地休息。」
林佳和家人最終沒有為父親舉行告別式,而是依照父親遺書,電話通知了幾位他的軍校同學。入土時,有20名左右的同袍,來到軍人公墓為父親送別,她細細描述那天畫面:參與者們手捧砂土,依序將它灑進樹旁放有骨灰的淺坑當中,工作人員最後將餘土填平,一位父親的老同學指揮所有人列隊,向父親敬禮。
即使不相信宗教與靈力,回到現實生活,社會眼光與傳統禁忌,對遺族而言,仍真實得難以迴避。
林佳表示,自己和家人當初唯一做的儀式是「招魂」,也就是在法師帶領下,前往事發現場、呼喚亡者,引導祂回到家人身邊。這個儀式的用意,是為了避免親人的魂魄在外流浪,成為「孤魂野鬼」。
林佳之所以同意進行這項儀式,並非相信這個說法,而是為了要「做給鄰居看」:
「我跟我媽本來覺得不必去,但我弟覺得要去,原因是鄰居可能會介意我們沒有去做事後的處理,(給他們)帶來不好的影響或困擾。為了讓他們安心,特別去招魂。」
自殺的特殊性,讓遺族面對親人的逝去,在純粹的哀悼外,還多了一層「社會關係」要去在意。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張翠華指出遺族的普遍經驗:「假設你的家人在家中自殺,鄰居可能怪你讓房價下跌,它跟一般死亡不一樣。」她就遇到遺族說,事發後,鄰居對他們的態度變得冷漠,而有些遺族乾脆搬家。

這三層面的意義是,遺族可能在過去的生活經驗中,覺知到社會大眾對自殺行為有特殊的態度,又因為自身成為遺族後,實際經驗到被歧視和偏差的對待,綜合這些外在負面結果,將它們內化為自我評價,甚至是對自己的歧視。
遺族在汙名的作用下,成為了「演員」,努力在社交場合扮演正常人,難以本著真實的自我與他人相處。久而久之,他們可能在社會中變得退縮,斷開和家人、朋友的社群連結,減少解釋、澄清自己狀態與處境的壓力,致使失去原先建立的人際網絡,在哀慟中更失去了關係的支持。
至於遺族面對的社會汙名和自我汙名如何交織,陳增穎坦言不易分析。但她想起一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在1980年代執行的傷痕實驗(Scar Experiment):實驗中,研究人員請受試者看著鏡子,並在他們臉上畫逼真疤痕,接著告訴他們,必須帶著這傷疤去和他人互動。事後,研究人員詢問參與者感受,所有人都表示他們在互動中受到了歧視,可是,他們不知道研究人員在互動開始前,已將他們臉上的疤痕去除。
這個實驗,揭示了個人的內在信念,如何影響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感受。陳增穎提起傷痕實驗的用意,是想鼓勵遺族不要陷入「自證預言」,也就是預期自己會遭受汙名、歧視,而果然感受到歧視,並低估自身改變境況的能力。
但林佳認為,傷痕實驗忽略了人的預期就是由社會眼光學來的結果;因此,遺族會產生受汙名的預期,也就代表這樣的歧視未曾從社會上消失。
陳增穎分享近期投入的調查,主題正是希望了解社會對自殺的認識程度,並討論自殺與汙名的議題。她在問卷採用了「自殺看法量表」,詢問受試者認為自殺行為是高尚的、獻身的、勇敢的、孤獨的、迷茫的、孤立的、不道德的、令人難堪的、膚淺的還是愚蠢的?從現階段得到的回應來看,最多人認為自殺是孤獨的、孤立的,最少人認為它是不道德、膚淺或愚蠢的。
2023年,張書森、陳映燁等人的研究揭示,在1,087名台灣成年人的全國電話調查中,表示願意幫助自殺風險者的人數比例為56.5%。研究者指出,具有協助意願者,較不會將自殺行為視為是個人選擇,或對此產生誤解。
上述兩項研究顯示,台灣民眾對於自殺行為,或許有愈趨中性的理解。不過,陳增穎提醒,認知、行為與態度之間,並不是必然一致;換言之,人們對自殺有更多認識,不等於汙名與歧視就不會發生。
回顧初衷,多年下來的心理諮商訓練,讓陳增穎很在意活下來的人、受過傷的人,能否維持好的生活品質。她說自己不是遺族,但會開始自殺遺族研究,是因發現學生是遺族,希望透過研究,讓學生有「說出口的機會」。她感性說道:
「我想記錄遺族生存的過程,重新建構他們的故事,讓他們知道其實你走過來了、挺過來了、成長了,這很不容易。」
陳增穎對遺族的關心,確實被看見。在第一篇研究發表後,一名陌生遺族來信,自願受訪,請她替他書寫生命故事。這讓陳增穎非常感動,知道自己的角色有價值。
遺族關懷
- 衛生福利部自殺者親友關懷手冊
- 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 社團法人台灣遺族親友關懷協會
- 社團法人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
- 隙光精神
-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
- 彰化縣生命線協會
- FB社團自殺者遺族
- 國際論壇Alliance of Hope
- 日本組織全国自死遺族総合支援センター
自殺防治
-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 24小時安心專線:1925
- 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 張老師專線:1980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