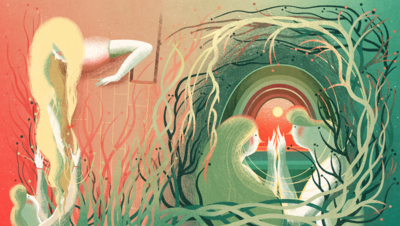童話篇

童話未必只是幻想,它也可以是我們理解人權與正義的起點。
在《格林童話》的光譜中,主流敘事多數描繪年輕、貌美、純潔的主角透過婚姻、神力或幸運之助,翻轉人生困境,正義終獲伸張。若從人權視角來看,通篇充斥著性別刻板、美醜二元、善惡二極和不人道刑罰觀的《格林童話》,許多故事可以說是當代人權的「反面教材」。然而,在交織浪漫與暴力、歌頌歧視與酷刑的童話文本中,卻有篇異數,它既沒有王子、公主、後母或巫婆等票房保證,也沒有愛情、禁言、咒語及暴力等熱血主題,但它歷久彌新,堪稱當代人權觀念的先驅。你猜到了嗎?
對了,就是〈不萊梅城市樂手〉(Die Bremer Stadtmusikanten)!它是源自中世紀德國下薩克森地區(Niedersachsen)的民間傳說,被格林兄弟文學化潤飾後納入1819年《格林童話》版本的第27篇。故事敘說四隻被人類社會視為「無用」動物──驢、狗、貓與公雞──的遊歷,牠們因為年紀大、無法再勞動,將被主人遺棄或宰殺。牠們各自逃離家園,途中相遇後決定結伴前往不萊梅,想當城市樂手自謀出路;牠們雖沒有明確的計畫與步驟,卻充滿了生存的渴望與鬥志。途中牠們在森林中發現一間被強盜占據的小屋,藉由機智地合作(由驢疊上狗、貓與公雞,一起站成高塔並發出驚人叫聲),成功嚇跑強盜後,進入屋中享用餐食、安頓下來。強盜試圖回來,但又被牠們的聲音與聯合行動嚇退。最後,這四隻動物決定不再前往不萊梅,而是在森林中的小屋中安居樂業,快樂地過著屬於自己的晚年生活。
乍看之下,這不過是德國民間傳說中一則溫馨幽默的動物小品。但若我們轉換角度,從當代國際人權法──尤其是《世界人權宣言》與後續的《兩公約》──加以對讀,就會發現這段歷程,不只是童話的奇想,更幾乎是一部「以動物之名的人權啟蒙教材」。它表面上描繪的是四隻邊緣動物的冒險歷程,蘊含的卻是一場關於弱勢者的尊嚴、生存、自由、平等以及「為權利而奮鬥」的深層敘事。我們就來重讀這篇《格林童話》中最具國際人權精神的異色經典。
故事一開始,曾為主人經年累月打拼的每一隻動物,都因年老、失去勞動力而被其主人判處「經濟性死亡」,淪為即將被棄養或宰殺的弱勢族群:驢子再也馱不動穀物、狗追不到獵物、貓抓不了老鼠、公雞不再能準時報曉。牠們無法再為主人提供經濟上有用的勞務,主人因此認為牠們必須被淘汰,餵點飼料都嫌浪費,連苟活下去都不值得。牠們的生命價值,完全由其生產力而決定。
這則經典童話,表面上是四隻動物的故事,但實質上運用了擬人化敘事,深刻反映出人類社會如何對待那些因年老、疾病或意外而失去勞動能力的經濟弱勢者與社會邊緣人。故事中的動物,如同被社會淘汰的人類,因不再具備生產價值而被其主人(即社會)無情地拋棄或面臨被犧牲的命運。這則敘事的核心意義,正好體現了《世界人權宣言》與《兩公約》的精髓:無論任何處境的弱勢者,皆應擁有基本的尊嚴與人權,並理應受到社會的保障。
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是二次戰後國際社會對人性尊嚴與自由平等的集體承諾。儘管它只是一份不具法律拘束效力的宣言,但被譽為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份普世人權標準,深深影響各國憲法、法律與後續國際人權公約。每年的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正是為紀念這份宣言的誕生。
弱勢者的人權保障,從來都是國際人權的核心課題,也正是〈不萊梅城市樂手〉與《世界人權宣言》的匯流主題。該宣言除了自由、平等、參政等權利外,特別納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奠定了對經濟弱勢者和社會邊緣人的人權保障基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舉幾個例子,如該宣言第25條規定了人人享有維持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的權利,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以及在遭遇經濟困難時的保障。第23條闡述了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有免於失業的保障;同條也規定了同工同酬與結社權,這有助於消除勞動市場中的歧視,並賦予工人集體力量,特別是經濟上較為弱勢的勞動者。再如,第22條承認了「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受個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需之經濟、社會及文化各種權利之實現」,這為建立社會福利體系、提供失業救濟、疾病津貼、養老金等機制提供了國際法理基礎,旨在保護那些因年老、殘疾或其他非自願性原因而喪失勞動能力或陷入經濟困境的人。後來制定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也繼受了以上所有這些保障內容,進一步具體化,將這些原則轉化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要求締約國採取積極措施予以實現。
對照〈不萊梅城市樂手〉,相信所有看過故事的人都會認同,這些年邁的主角們,不但值得活下去,也應該更進一步享有上述結社自由、失業救濟、疾病津貼、養老照護及退休保障等,來維持一個失去勞動力後的尊嚴生活;這不是施捨,而是他們應得的權利。差別僅在於,童話不是用冷冰冰的條文,而是用有溫度、有感情的故事來潛移默化,滴水穿石澆灌我們這些人權觀念──而這也正是我認為有些童話比起教科書,更適合作為法律啟蒙教材的緣故。
耶林的思想在當時引發巨大共鳴,他挑戰了傳統的、更為靜態的法學觀念,把法律還原成一場場活生生的奮戰與行動。他呼籲,「權利唯有透過捍衛它的意志才能實現。」他看到,法治社會不是靠條文撐起來的,而是靠無數個願意挺身而出的小人物,一次次為自己的正當權益據理力爭,聚沙成塔累積而來。他強調,沒有信念與行動的法律,只是一個空殼,而捍衛權利則是一種公民的道德義務,不是自私的爭利行為。也正因如此,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成為近代人權法發展的啟蒙文獻之一。
在人權史的長河中,《為權利而奮鬥》是一則醒鐘。它提醒我們,人權不是抽象的名詞,而是每個人、每天、在生活中選擇挺身而出、說「不」的行動累積。從耶林的時代到今日,每一次對不公不義的反抗、每一次對剝削壓迫的拒絕,都是對這句話的實踐:
「如果你不為你的權利而戰,你就不再配擁有它。」
說一下個人經歷。我生平第一次聽到這本書名,是大二時在台灣大學法律系的課堂,聽到一位留德民法大師的引介,令我耳目一新;在台灣更早之前的白色恐怖年代,即便只是提倡「為權利而奮鬥」,都是驚世駭俗之舉。但我當初完全沒有想到,耶林與格林,以及他們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兩部名著之間,會有什麼密碼連結?其實,《為權利而奮鬥》的精神,恰好也藏在〈不萊梅城市樂手〉這則動物寓言裡。故事中驢、狗、貓和公雞等四位主角,全是社會邊緣者。他們年老無用,將被原來的主人遺棄,失去庇護與生存資源,處境就像現代社會中被市場淘汰的老工人、無力發聲的貧民、或因年齡與疾病而遭社會排除的人。但他們並沒有就此等死。他們積極選擇離開、串聯、合作,主動踏上一條從未被允許的冒險之路:前往不萊梅,當城市樂手。
這不是被動怨嘆,是主動求生;不是止於空想,而是付諸行動。故事中沒有天賜、幸運或神仙之助,他們也沒有等誰發慈悲來拯救,而是靠自己分工合作、設計行動、智取房屋並獲得重生。動物主角們沒有法律扶助、也無寫入憲法的基本權利可伸張,但他們用行動證明:即使最邊緣、最弱小的角色,也能捍衛自己存在的權利。這些都在在呼應耶林所說的:「人權不是恩賜,而是奮鬥得來的。」其實,我們當今所習以為常的各種社會福利、退休保障、工會結社與勞動安全等制度,從來都不是有權者的施捨,而是歷代無數像驢、狗、貓、雞那樣沒沒無名的小人物,一次又一次奮力爭取的結果。每一次拒絕沉默的行動,都是為權利而戰的延續。
童話沒說他們最後是否真成為樂手,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沒選擇沉默與屈服,而是以決心和行動拒絕「命運的判決」。這正是耶林所呼籲的法治核心──權利,不會自己發光,必須有人點燃火種。透過這場動物的集體出走與奮戰不懈,我們看到一場無聲的法律實踐:沒有法條,卻有尊嚴;沒有法庭,卻有正義。他們讓我們相信,即使是最邊緣的生命、最弱勢的個體,只要不放棄奮鬥,就能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為自己開闢出一塊可以安身的所在。一則短短童話能夠承載這麼多人權底蘊,你說它不是異數嗎?
大多數《格林童話》的發生地,你想導航也導航不到,因為地點設定多具有普世性或模糊性(某個遙遠的村莊、森林、王國或城堡),以便讓故事能更好地跨越地域限制,激發讀者的想像力與投入感:任何一片森林都可能是小紅帽遇上大野狼的場景,任何一座中古歐洲城塔都可以想像是長髮公主的囚禁處。但〈「不萊梅」城市樂手〉和〈「哈梅恩」的捕鼠人〉(吹笛捕鼠人)則是少數例外,故事的發生的具體地理位置就明白寫在篇名裡──你現在用GPS導航得到的地方。
這段動物旅程的預設終點「不萊梅」(Bremen)並非偶然選擇,而具有多層隱喻意涵。首先,對於故事中的四個主角而言,不萊梅代表的是一個象徵性的自由空間,牠們在原社會中被拋棄、視為無用,但仍渴望前往一處能重新獲得認同與尊嚴的地方,透過樂手身分進入社會。在牠們的想像中,這座自由城市是牠們重拾自我生命價值的場所,某種形式的烏托邦或庇護所。但為何偏偏是不萊梅呢?
其次,作為漢薩同盟重要的港口、工業城市和貿易中心,不萊梅的經濟活動非常活躍,工業革命後更湧入大量勞工,伴隨而來的是勞動條件惡劣、貧富差距擴大、失能失業欠缺保障等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使得保障勞工和弱勢群體的社會政策主張,在不萊梅備受青睞,加上當初作為高度自治城市,其保障弱勢的政策,也比較容易實踐。直到今日,不萊梅仍長期由偏向勞工保障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組閣執政。這一切,其來有自。

雞生蛋、雞生蛋。是不萊梅催生了童話,還是童話造就了不萊梅?如今,雖然不萊梅的正式市徽仍是「聖彼得之鑰」(Schlüssel Petri),但童話中那四隻堆疊動物(驢底、狗中、貓上、公雞頂)的經典形象,早已成為這城市最鮮明、最親民、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徵。你若到不萊梅,可別錯過老城區市政廳旁的城市樂手青銅雕像(1953年由雕塑家Gerhard Marcks所作),摸摸驢的前腿,帶來傳說中的好運。不萊梅市政廳(Town Hall)和羅蘭雕像(Roland on the Marketplace),已於200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在漢薩同盟自由市的歷史脈絡中,羅蘭雕像連結的正是這座城市的自治與自由。
順道一提,格林兄弟在1819年首度將〈不萊梅城市樂手〉收錄到《格林童話》,200週年之際,不萊梅於2019年舉辦了一場盛大隆重、為期3天的學術研討會,各領域專家學者齊聚一堂,主題焦點即是探討「這則童話如何反映現實人類社會中的文化、歷史、社會互動,以及弱勢群體的處境」。
從以上敘述可知,〈不萊梅城市樂手〉不只是一則童話──它從頭到尾都可以當成是一個闡釋權利本質的法普教材。不過,站在《刑法》角度,卻有個特別有趣的故事情節,值得一提:這四隻結伴同行的動物夢想家,前往不萊梅途中發現一間「被強盜占據的房子」,並巧妙地將強盜嚇跑,進而安居於此。故事中動物們侵入強盜住宅的行為,大快人心,但從擬人化來看,阿驢、阿狗、阿貓及阿雞等四人的行為,在《刑法》上有無可能構成侵入住宅罪的共同正犯呢?
先說共同正犯問題。假使阿驢們該當侵入住宅罪名,他們會構成《刑法》第28條規定所稱「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的共同正犯關係。侵入強盜住宅是他們共同的犯罪計畫,彼此之間,主觀上出於共同的決意,客觀上具有分工合作、角色分配的共同行為:個頭最大的驢子墊底,用前腿搭在窗台上當支架,依序堆疊狗、貓,雞再飛上去,聯手製造出前所未見的怪異形體和震耳欲聾的巨大噪音,終究嚇走強盜,簡直就是完美組合。可以說,故事中四位行為人之間的關係,如果構成犯罪的話,根本就是教科書等級的共同正犯範例!
然而,在〈不萊梅城市樂手〉的故事裡,房子原本屬於誰、真正屋主人在何方,其實並未交代清楚;我們只知道強盜們占據了這間房子,但他們顯然不是合法擁有、使用或承租這間房子的人。他們雖然實際住在裡面、剛好住在裡面,但從《刑法》角度而言,他們不是合法的居住權人,因此,他們也不是「有權反對」阿驢們進入房屋之人。因此,對於強盜而言,如果有人違反他們意願硬闖這間房子,也不會侵害他們的住居權──因為強盜自身根本就沒有這個權利!
不過,房子總是有人的吧?!阿驢們鳩占鵲巢,還是可能違反那個不知所在的「真正屋主(阿鵲?)」的意願啊,我們該替阿驢們擔心嗎?放心!本條屬於「告訴乃論之罪」(《刑法》第308條第1項),也就是要等犯罪被害人提出告訴,才會具備追訴要件,啟動追訴程序才有意義(《刑事訴訟法》第232條)。無權住居的強盜不是本罪的被害人,也不是告訴權人,沒資格提出告訴;至於原屋主阿鵲嘛,既然連到故事結尾,世上到底有沒有阿鵲或他究竟去哪了,都還音信杳然,那我們也不用杞人憂天,替阿驢們傷這個腦筋!
童話未必總是關於奇幻、魔法、愛情或婚姻。它也可以是邊緣生命發聲的平台,是弱勢群體追尋尊嚴的寓言,甚至於是我們理解人權與正義的起點。
〈不萊梅城市樂手〉是格林兄弟筆下最少血腥暴力、性別偏見和階層歧視的故事之一,但卻傳遞了最深刻的人權觀念。我們在這則故事裡看到,無論你是誰──哪怕是像故事中老驢、病狗、落毛貓、破嗓公雞處境的人──你都享有生而為人的生命價值,也都有追求尊嚴與自由的權利。而這不正是《世界人權宣言》及《兩公約》所渴望實現的國際人權圖像嗎?特別是在當前全球庇護、難民、貧富差距、老齡歧視、經濟弱勢與社會邊緣化問題愈加受重視之際,〈不萊梅城市樂手〉無疑提供了我們重新反思當代社會人權議題的文化路徑。
人權,不該只在法庭上實現;它也可以,甚至應該,在故事中被想像,在文化中被培養,在教育中被傳遞。而童話也可以是那扇通往普世人權的祕密之門。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