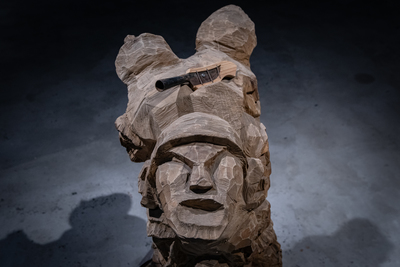2025年10月25日,是台灣社會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80週年之際,重新迎來睽違25年的第一個「光復節」國定假日。但與往昔威權時代的慶祝氛圍不同,今日的「光復節」與「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早已不再是單一的勝利敘事,而成為一面折射歷史矛盾的多元鏡子。有人質疑,戰時與日本同為一國的台灣,為何要慶祝「抗戰勝利」?有人不解,明明能守著「戰勝國史觀」,又何必承認自己曾是戰敗者?就連中性、單指戰爭結束的「終戰」一詞,如今也能引發輿論對立,成為中國國台辦見縫插針、甚至將在北京高調舉行「台灣光復80週年」統戰活動的政治煽動題。
然而,在如此分歧的歷史認知與世代經驗之下,台灣人對「戰爭」的記憶該如何延續?《報導者》訪談了國史館館長陳儀深、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理事長朱家煌,以及多位高中教師,從國家敘事、歷史保存到教育現場,共同討論戰爭結束80年後的此刻,台灣社會如何重新理解自身在戰爭中的位置,並面對記憶的斷裂、繼承與重建。

2025年9月7日午後,廖淑霞坐著輪椅,在旁人協助下,緩緩地到了菊花布置的祭台之前,以日語向台下的出席者致意:
「戰後80年的現在,更多關於戰爭的記憶正快速流逝,我們要求的不是金錢的賠償,也不是日本政府的道歉,只是希望我們能和其他經歷過戰火洗禮的日本人那般,得到一視同仁的平等對待。」
這天是《舊金山和約》簽訂73週年前夕,這個國際文件是日本政府放棄對台澎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的依據。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此日在旗津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舉辦「二戰台灣戰歿者慰靈暨和平祈念儀式」,不僅邀請曾參與二戰的台籍日本兵、遺族和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會長何麥克(Michael Hurst)參與,分屬軸心國與同盟國的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長奧正史、美國在台協會(AIT)高雄分處長張子霖(Neil Gibson),也都代表出席。
超過90歲之齡的日本海軍特別志願兵陳金村、高座少年工葉文懷,以及破百歲的陸軍軍屬楊馥成,都坐在第一排貴賓席,聽著廖淑霞說話──他們在80年前,不過是青春無憂的少年少女,卻被戰爭捲了進去。身後不遠處,則有20餘名高中生與這些將青春獻給戰火的長輩同處一個空間,看著肅穆的悼念儀式舉行,這才真正理解與發現:在課本上提到的那場戰爭,我們(台灣)是侵略國(戰敗國),「原來台灣有戰俘營,囚禁的是盟軍。」
一場戰爭,多種認知記憶。1945年的戰爭結果,為這座島帶來具有不同生命經驗和語言的統治者,也改變了台灣人的國籍,而這個社會對於戰爭歷史記憶的認知和認同,因為前後政權戰時的敵對關係與戰後戒嚴,斷裂、模糊曖昧,至今仍爭執不休,並在2025年的夏天再度引發密集議論:總統賴清德的「終戰」談話成為反對陣營批評的箭靶,稱其「媚日」;而美國在台協會特別點出「戰爭前後的各項文件都未決定台灣最終地位之說」,也引發廣泛爭議。

此外,當立法院今年(2025)5月三讀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台灣光復節」睽違25年後以「台灣光復暨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之名再次回到國定假日之列時,民進黨祕書長徐國勇稱「沒有什麼台灣光復節」,讓國民黨立委忍不住怒嗆。
「台灣光復節」的取消和重啟,就是意識型態的角力。2005年,在「台灣光復60週年」慶祝茶會上,時任總統陳水扁對於因實施週休二日而取消光復節在內的7個國定假日時,曾如此解釋:台灣社會對使用「光復」有不同意見,對許多政治受難者或被迫害者,情感上是無法接受的,大家應將心比心。
「過去在威權統治之下,由少數獨裁統治者所詮釋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存在,並不是因為它代表事實的真相,而是因為它背後的政治力量。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壟斷或操縱歷史的詮釋,」陳水扁表示,對光復節這個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紀念日,台灣社會有必要重新思考與檢討,賦予在歷史上更客觀與正確的定位,這才是政府訂定任何紀念日應有的態度。
在假日之外,陳水扁甚至態度強硬,對於「光復」一詞遭扭曲提出警示:「假如把『光復』等同於『回歸』、把『光復台灣』變成『回歸中國』,部分台灣人士發動所謂的『投降法』還不夠,還特別跑到中國跟人家一起慶祝,甚至說出『台灣再光復』,甘願要還給、送給中國,這才是『台灣光復』最大的悲哀。」
這段整整20年前的談話,竟也成為今日的預示:中共將在北京舉辦「台灣光復80週年」紀念活動,其目的是「捍衛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的勝利成果」,並再次強調要維護「二戰勝利的成果」及戰後國際秩序,即是確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歷史和法理事實。而有部分台灣人則響應這個紀念活動,赴中參加。
一個光復,不同解讀,各種利用。
當台灣戰後的國際地位,及因白色恐怖而形成的斷裂,而讓戰爭歷史在台灣社會缺乏認知的一致性和認同的延續性,甚至因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產生分裂時,我們要問:是否有讓戰爭歷史記憶延續下去,以從中得到反思、教訓,乃至於形成共同體的可能?又或者,建立更多元、更多樣的談論歷史的視角與取徑?

如同賴清德於終戰紀念日的社群發文受到在野黨和部分媒體攻擊一樣,國史館也因為使用「終戰」二字成為箭靶──為了紀念戰後80年,國史館舉辦多場活動,包含「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但部分媒體、網友強烈抨擊代表國家歷史論述的國史館竟然使用「終戰」一詞,甚至連中共國台辦發言人都公開指控國史館:「刻意淡化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殘暴,抹煞抗戰的正義性,並歪曲事實、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既是對歷史的無知,更是對全民族奮鬥犧牲的褻瀆。」
對此,國史館館長陳儀深甚至得在記者會上解釋,「終戰」的字面意義就是戰爭結束(the end of the war),是中性名詞:
「這樣只看標題就攻擊,雖然反映了社會分歧、政治對立的現實,但我們認為是不必要,對我們也是不公平的。」
接受《報導者》訪談時,陳儀深對此攻擊提出了一套解釋。在他看來,「終戰」之所以會成為媒體和輿論焦點,是因為今年是終戰80年,中共格外重視,並喊出了「三個80」的政治口號──抗戰勝利80、反法西斯戰爭80,還有台灣光復80──而這套緊密論述扣合著中國宣傳論述,即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所言,包括《開羅宣言》等二戰期間的國際文件,「要求日本把從中國所竊取的領土包括台灣歸還給中國。」
「戰爭不只是飛彈大砲攻擊而已,戰爭時還要考慮到外交,要找你的盟友一起來打群架,不是只有我們和敵人雙方打架而已,」陳儀深表示,這些包圍戰爭歷史的論述,和近幾年習近平加緊對台策略有關;歐美民主國家則紛紛通過「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地位」的國會決議,以阻絕中國扭曲歷史的作法。
針對中國刻意曲解二戰時期的國際文件,美國在台協會也於9月公開批評中國試圖扭曲《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舊金山和約》,並強調二戰相關文件未決定台灣的最終政治地位。
國史館為終戰80年所舉辦的紀念展覽「亮光與暗影:1945年前後的台灣重要史料微型展」,便以《開羅宣言》為起點展開,呈現《開羅宣言》制定過程中各方對戰後台灣歸屬的討論與思考。「《開羅宣言》只是戰爭期間的意向的表達,戰後情勢就已經不同了,」陳儀深表示,從道德上來看,這些國際文件留給台灣人民一個選擇的機會,至於今年包圍著《開羅宣言》而起的爭論,他則認為,美國所謂的「台灣未定論」是說給北京聽的,因為台灣仍擁有自己的主權,也應該能討論自己的未來。
國史館今年以「終戰」為主題,對戰爭歷史與台灣戰後的國際地位舉辦多項活動。不過爬梳過往紀錄,國史館過去並未在8月15日舉辦紀念活動,主要談的多是「抗戰勝利」,但在2005年戰爭結束60週年的出版品上,印有「終戰」二字。這樣的用語轉變,大致反映出2000年後台灣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變化:陳水扁執政時期曾以「終戰」為題發表談話;馬英九上台後,則強調「抗戰勝利」;蔡英文任內未對此多作表態;直到賴清德執政,才再次發表「終戰紀念日」感言。
值得注意的是,曾擔任過台籍日本兵的台灣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此前在1995年的終戰50年時,也是強調抗戰勝利。待政黨輪替後,他才於終戰70年之際對日本媒體表示,戰時的台灣和日本「同為一國」,自己當時也曾以「日本人」的身分為祖國而戰。
陳儀深表示,陳水扁執政後,由張炎憲接管國史館,而國史館的歷史研究與文獻,才慢慢將中華民國史挪到以台灣為主體的狀態,也開始讓兩種史觀併置。這兩種史觀,逐漸在他這個戰後世代疊合、具現。
1954年生的陳儀深,童年時常聽父親提到「降伏(こうふく)之後如何如何」,受到黨國教育的他不明所以,總以為這個詞彙就是學校裡教的「光復」,「因為台語發音類似。」一直到成年後,對於台灣歷史產生覺醒,他才明白:前者是站在日本的立場說話,後者是站在戰時中國的立場說話,兩者南轅北轍,各自代表不同的生命經驗。
陳儀深的父親是日本軍伕,曾被派往海南島,卻因眼疾提前返台而撿回一條命。他記得,出身南投名間鄉的父親,總說那是「帝爺君」(玄天上帝)的保佑。年輕時,陳儀深只是把這些話當故事聽,並不以為意,而父親對他加入國民黨,也沒有太多意見──這正是戰後台灣家庭的常態:兩種記憶,兩種立場。直到晚年,父親才透露自己的看法:「(二二八時)抵抗國民黨的人很勇敢。」
「你不可能叫我父親說『抗戰』,他就是日本兵啊,抗自己嗎?台灣人沒有抗戰經驗。」作為歷史學者,陳儀深深知國民黨在中國的八年抗戰非常慘烈,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怎麼說這都不會是同代台灣人的生命經驗。
「(當時)台灣人就是戰爭的棋子,我們不是下棋的人,有什麼資格談勝敗呢?」陳儀深表示,台灣人在當年是日本的一部分,跟著侵略作戰,結果戰敗。所以國民黨代表在台灣接受日本降書時,才出現明明是戰敗國卻又立刻成了戰勝國的尷尬局面。

不過,這個「光復」時刻,也是許多台灣人所期待的。陳儀深解釋,戰爭結束後,台灣有不少知識分子因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而感到歡欣,渴望迎接「祖國」,因此接受了「光復」的說法。例如在二二八事件中帶領民軍對抗國民黨政府的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就在「光復」之初因歡迎祖國的心理,加入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國史館為終戰舉辦的展覽中,也展示了多份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日記與文件,證明當時的確有不少人期待光復。例如,38歲的台南醫師吳新榮,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後,興奮得如同少年般蹦跳,還跑到河邊脫衣跳水,起身後對著水面大喊:「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今日起,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然而,吳新榮之後卻因二二八事件入獄。
不只吳新榮,台灣日治時期台灣議會民主運動者林獻堂,也與部分士紳於1945年10月25日到機場迎接國民政府首任駐台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並至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參加受降典禮,還針對台灣「光復解放」發表談話。但之後,林獻堂也因二二八事件對「祖國」感到失望,最後遠走他鄉。陳儀深表示,台灣知識分子當年確實期待光復,但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因缺乏現代性與治理能力,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使這些台灣菁英陷入困境,也因此改變了他們的立場。
而這也是陳水扁在台灣光復60週年慶祝茶會時所提:「光復節」對某些人而言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也象徵著洗刷中國在列強的欺壓之下所遭遇的各種屈辱,但對台灣人民而言,「光復」卻是傷痛與苦難的開始,伴隨來的是二二八事件的殘酷鎮壓、清鄉、白色恐怖,以及長達38年世界現代史上最久的戒嚴統治之一。
「即使到今天,還有許多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心中的傷痛尚未能完全撫平,而威權統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與族群的緊張關係也還沒有完全消弭。」陳水扁當年指出,在這個時候刻意的去凸顯「光復」這個具有特定政治含意的名詞,不但無助於台灣內部的團結,更與整個社會所強調的「台灣優先」的主流價值背道而馳。
「其實歷史是活的,不應該這麼死板,」陳儀深認為,對於「日子」我們可以有很多角度的認識,例如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那天也是10月25日,那同一個日期是不是也可以同時當作中華民國的國恥紀念日呢?他進一步表示,我們可以針對「日子」做更多的歷史補充跟討論。
作為國史館館長,陳儀深也提出了「和解史觀」的看法,主張我們既應該正視並細談對日抗戰的歷史,也應重新挖掘當時台灣人的經歷與聲音:
「中華民國在台灣,或是中華民國台灣,是我們現階段的最大公約數。站在國家歷史的角度,當然要各方面納進各個族群、群體的歷史,因為這些也都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陳儀深進一步補充,因為台灣是在解嚴後、全面民主化後,才透過檔案和口述,慢慢收集、檢視過去的歷史記憶,不像其他民主國家可以有一貫性的歷史,而現在是逐漸凝聚的狀態:
「當然,只有不同政治立場的互相包容跟尊重,才能走向『和解史觀』。」

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理事長朱家煌從小在高雄鹽埕區長大。日治時期的高雄是糖廠與軍需工業的重要基地,承受著盟軍的頻繁空襲,他那來自澎湖的阿公,甚至被迫疏散回望安島以躲避轟炸。然而,出生於1972年的朱家煌,在學校所接受的卻是以抗戰為核心的史觀,認知中的敵人是日本,這與祖輩的真實記憶完全衝突。
「我爸爸是戰後出生的,沒有戰爭經驗,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父母都跟鄰居講日語。」朱家煌解釋,戰後他的阿公阿媽也不敢談日本時代的事情,因為當時的統治者是與日本敵對作戰的政權,更別提台籍日本兵了:「在那個年代,他們在課本裡、在社會意識中,都被視為漢奸。」
戰爭的歷史記憶,正是這樣在台灣世代之間造成斷層。即使朱家煌上了高中、大學後,慢慢明白事情並非課本所述,也在中年後投入關懷老兵協會的工作,但卻不知道自己家族和戰爭的關係,直到近年,翻找阿媽抽屜裡的檔案資料時,才發現原來家族中也有台籍日本兵。
「大概在民國60年代,阿媽有幫我曾祖父的兄弟,向日本厚生勞動省申請償還薪資儲金。」朱家煌的曾叔公,曾經幫日軍開運輸船,他的薪資被存在台灣銀行裡,但戰後被國民黨政府凍結而無法領取,只得向戰時的祖國──日本──提出追討。
日本於1951年與同盟國簽訂《舊金山和約》,正式結束戰爭狀態,並放棄對台灣及澎湖諸島的主權。隔年,日本又與中華民國另行簽訂《中日和約》,其中第三條明定:台日之間的財產與債權問題「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理辦法」。換句話說,台籍日本兵在戰時被積欠的薪資及軍事郵政存款等,理應由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透過「特別處理辦法」協商處理。
朱家煌表示,台灣總督府在戰後曾將台灣兵的徵召名冊交給陳儀,但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來說,反共抗俄才是重點,對於台灣的戰爭債務清理並不放在心裡,「和日本斷交之前,日本政府曾數次要求國民黨政府推動特殊處理辦法的進度,但國民黨政府都不理。這是日本人欠台灣的錢,國民黨侵占日產後,何必要吐出來讓日本人去賠台灣人?」
朱家煌認為,台籍日本兵真正的債務人,其實應該是中華民國政府,因為那筆錢早已在中華民國政府手中,「所以,像王育德這些人為台籍老兵爭取補償所發起的抗爭,不論怎麼告,最後都只能輸。」

戰後,日本陸續創立《恩給法》及《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等援護法》等法律,但給戰時軍人、隨軍文職人員及其遺族的各種補償卻只限於日本籍,因此台籍日本兵及遺族就被排除了。
1975年,在明治大學教授、語言學學者王育德的帶領下,針對台籍日本兵及其遺族補償問題,展開一場社會運動。10年後,相關法律陸續在日本通過,凡台籍前日本兵的遺族或戰傷病者本人提出申請並獲認可者,每人可獲得200萬日圓的特定弔慰金。
至於懸而未決的台籍前日本兵積欠薪資與軍事郵政存款等「確定債務」問題,日本政府也於1995年決定以債務金額的120倍,也就是依據1952年發還沖繩人存款的「沖繩方式」進行償還。然而,該方案並未考量戰後薪資水準與物價變動,因此日本政府單方面的決定,引發許多抗議與反彈聲浪。
「即使我們曾經以日本人的身分為國家奮戰,但日本政府仍在戰後以喪失日本國籍為由,不合理地將我們排除於撫卹與恩給的對象之外,讓我們的身心蒙受了無限的痛苦。」
在旗津舉辦的二戰戰歿者慰靈祭上,廖淑霞如此控訴。她說,戰爭期間存放在日本郵局內的薪資及其他款項,戰後全數遭政府凍結,直到半個世紀後,這筆所謂的「軍事郵便存款」才終於得以解封領取,「但我們辛苦的等候了50年,最終得到的金額,竟只相當於當時日本公務員半個月的薪水而已。」 「面對如此不合理的對待,我們雖然大聲抗議,但那些充滿苦楚的聲音,仍然被完全忽略。」廖淑霞不平地表示:「這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屈辱,即使多年過去,胸中的忿懣仍難以平復。」
「很多人問說,為什麼不乾脆當個戰勝國就好,何苦要承認自己是戰敗國?但歷史的事實就是:台灣屬於戰敗的一方。」朱家煌說,無論當年台灣是打贏還是打輸,畢竟都捲入到了戰爭裡,既然有這種經歷存在,就有保存記憶的必要:
「應該記住說當年為什麼會捲入這場戰爭,而戰爭結束後,我們有沒有去用心去撫平傷痕、或收拾戰爭引起的後遺症?」
朱家煌認為,戰後國民黨政權將台灣視為戰敗國的殖民地來統治,沒有妥善處理戰爭遺留下的問題,任由戰死海外的台灣兵遺骨無人收殮,倖存者的創傷也未被正視。更嚴重的是,在長期戒嚴之下,經歷過戰爭的人無法坦然說出自己的故事,也沒有機會被記錄,導致歷史記憶出現斷裂。
「雖然有人留下日記,也有戰友會的回憶錄被印出來,但這些資料都不會被圖書館收藏,家屬也可能覺得沒價值就丟掉了。所以那些紀錄很少被保留下來,這也是我們現在很痛苦的地方,沒有辦法好好重現那段歷史,」朱家煌感嘆。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政權之下,台灣至今都不曾像歐美或日本那樣,主動尋找與收集戰歿者遺骨,或將戰爭結束的日子訂為國定紀念日,公開舉行追思與慰靈儀式。這也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對這段歷史難以處理,索性擱置不管的態度。
當我詢問朱家煌對此有何意見時,他立刻回答:「所以許昭榮才要自焚啊。」
因政府對台灣人戰爭經歷的漠視與偏移,讓曾是台籍日本兵、同時身為政治犯的許昭榮,長期為台籍老兵的權益與這段歷史的保存而奔走,並推動為台籍老兵──包括為以日軍身分參加二戰,或者戰後被迫走上國共內戰、甚至韓戰戰場的台灣人──建立紀念碑與紀念公園。
儘管在許昭榮等人的不斷努力下,這群台籍老兵最終如願在旗津海岸邊,由民間籌資建立了無名戰士紀念碑,並爭取到政府承諾建設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但這一過程並不順利。除了政府對於紀念公園的建設始終消極,許昭榮也批評,無論是國民黨還或是民進黨執政,執政者都未曾真正重視老兵權益,不僅迴避「台灣歷代戰歿英靈」歷史定位,也不曾舉辦國家級的追思或弔祭,還讓約4萬位台灣先靈在海外流浪60餘年,這都讓許昭榮失望不已。
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總統宣誓就職當天,為了反對高雄市議會執意欲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更名為八二三紀念公園,也對現行國軍退輔制度偏袒外省老兵剝削本省籍士兵表示不滿,79歲的許昭榮選在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前在汽車裡自焚死亡,並留下遺書:「我依據自己的意志,以死抗議台灣執政者長期對『歷代軍人軍屬台籍老兵』之精神虐待。」
為了完成許昭榮的遺願,在他去世後的隔年,「台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終於落成,並首次舉行「秋祭台灣兵」儀式。此後,民間團體也持續在每年舉辦終戰紀念活動,延續對台籍老兵與戰爭犧牲者的追思。朱家煌說:
「如果你對戰爭沒有記憶,那就不用談什麼和平。沒有經歷過戰爭,就不會意識到和平的重要。這就像空氣一直存在,我們平常不覺得它珍貴,但是一旦經歷過沒有空氣的時候,就會明白那是多麼幸福的事。」
這些年,朱家煌經常帶團前往沖繩參加慰靈祭,觀察到日本許多與戰爭歷史相關的城市,都設有和平紀念館或資料館,並在紀念日舉行儀式、動員學生參與;學生會以撰寫學習單、摺紙鶴、寫祈念紙條等方式投入,「這是一種文化傳統。就算學生對戰爭感受遙遠陌生,也能透過這些行動慢慢體會戰爭的殘酷,進而理解歷史。」朱家煌感嘆:「可惜的是,台灣在這段歷史教育上的實踐,幾乎為零。」

今年的二戰戰歿者慰靈祭現場,特別出現了一群高中生。 「我覺得讓學生能與這些80年前的少年少女見面,真是太好了!」彰化縣溪湖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高珮華表示,為了讓自己在知識上有所刺激,也為了更好地面對教學現場,她親自參加了終戰80年的慰靈祭。在主辦單位的鼓勵下,她還召集了同校師生,一同前往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參加儀式。
參與的多是高一、高二學生,他們對這個歷史議題原本感到陌生,準備也不多,但在課堂上的引導與討論後,仍有26名學生主動報名。
高珮華笑說,同學們參加慰靈祭之前的想像是類似清明掃墓,不料卻是一場莊嚴的儀式,這讓他們心理產生不同感受,「體感上是輕鬆的,但心靈上卻是沉重的。」過程也讓學生們頗有收穫,像是他們原本不認為歷史記憶很重要,但在活動開始前參觀紀念館,聽了講解,才知道這些參與戰爭的台灣兵有各種不同的光譜,又如何帶著理想性走過白色恐怖時期,而後爭取撫卹卻遭遇種種困境。
「但他們最震驚的,是發現我們曾屬於侵略國,而且台灣竟然有『集中營』,營裡的戰俘還在台灣進行基礎建設工作。」
高珮華指出,學生們在慰靈儀式現場與台灣戰俘營協會負責人何麥克對話時,才得知學校鄰近的員林曾設有戰俘營,而南邊的斗六市過溝國小也曾被當作戰俘營使用:「知道戰俘營存在的這件事,影響了他們的世界觀。」
高珮華出生於1990年,是九年一貫教育的第一屆。她清楚記得,當年歷史老師發的筆記上寫著「抗戰勝利」,課堂上也使用「台灣光復」的詞彙,「我當時沒有辦法反思,這到底是關於哪一個主體的敘事。」直到踏入教育現場、教授公民教育後,她發現:如果沒有歷史感,沒有對一定程度的歷史敘事的理解,許多公民概念就難以真正闡述,像是國家主體意識、國家認同的意涵是什麼,以及國家認同為什麼重要。
「當然,如果只是為了應付考試,這樣的知識已經足夠了。」她說:「但學生沒辦法進一步思考,如果沒有國家認同,會怎麼樣?而我們這個主權國家在面對世界時,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高珮華進一步指出,當討論更深層的問題時,這些問題最終都會回到根本的提問:我是誰?我在哪裡?她強調,這些問題關乎我們擁有什麼樣的敘事,以及哪些歷史記憶能支持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的共同經驗。
不過,就現代的歷史科老師而言,教學上已經沒有史觀混淆的問題。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陳一隆自2006年開始執教鞭,就已是台灣史脫離中國史且獨立成冊的時代。就他的記憶,高中課堂上的台灣史已不再帶入「抗戰勝利」的觀點,「20年前,伍佰的《空襲警報》就已經入題,問的是:誰轟炸台灣?」
1974年的陳一隆讀的是工科五專,不太受到黨國意識形態影響,也沒有「史觀」的困惑,直到上了大學與研究所後,才被台灣主體的文史啟蒙,從而銜接到教學現場。不過,以醫科、理工為志向的多數台中一中學生,未必對歷史有興趣,甚至認為這些內容不夠「當代」。因此,陳一隆認為,課本如何談史觀,與學生如何認知歷史甚至提出自己的觀點,並不會有直接的連結。
至於光復節再次放假一事,陳一隆表示,學生只會想著放假很好,不會理解為什麼放假及其背後的目的。

新竹中學圖書館主任、歷史科教師黃大展坦言,1971年出生的自己是在「抗戰史觀」中長大,儘管大學讀了歷史系,對於台灣史已有認識,卻沒有辦法清楚感受到自己和歷史的連結性。因此,如今教書時,他才會刻意將在地故事與在地經驗,與學生個人及歷史進行連結。
「不過,即使學生知道我們當時是日本殖民地,卻不見得能搞得清楚台灣屬於哪一陣營、是誰轟炸台灣,更不用說去了解我們當時是為誰而戰、為何而戰。」黃大展認為,學生並不具一定的同質性,他們對歷史的看法,不是因為受了什麼樣的教育,而是他從哪裡來,他們的認同,也和自己家族背景有關。
黃大展會派給同學一個寒假作業,請他們做家族訪談,訪談父母或阿公阿媽,詢問他們過去的生活經驗;有些同學會寫家族前輩的遷移,有的會寫躲防空洞經驗,有的會寫二二八。他認為,要讓同學對歷史有感知,就要讓他知道這些過去和自己身邊的人有關,才會產生感覺。
例如,這些年黃大展在投入新竹中學校史工作,就整理了過去戰時體制的狀態,題為:「戰爭底下沒有人是局外人」。舉例來說,竹中有個名為張棟蘭的台籍英語老師,二戰期間便被動員到南洋擔任翻譯官;(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第4回的畢業校友陳增嶽則當過日軍軍醫,還留下過一張與新幾內亞原住民合照的照片,而黃大展在整理校史時也曾問陳增嶽的兒子,但他卻表示父親其實不曾談過當年的經歷,「我想,大概就跟陳千武的《烈女犯》一樣,他(陳增嶽)可能經歷太恐怖的事,所以不願意說出來。」
黃大展的用意是讓學生知道,戰爭並非與他們無關,而且,戰爭狀態底下掙扎的人,其實和大家都有聯結的。在他看來,歷史課的真正目的,不僅是讓學生建立歷史知識,而是能否對那個時代、各場戰爭建立主題性的理解,尤其在現在的108課綱中,歷史、地理、公民已被整合為社會領域,「而社會領域有共同的目標──讓學生成為現代公民,懂得如何面對當下與未來。」
「但我自己覺得台灣對戰爭記憶沒有那麼在意,國家也沒有一個日子紀念或談述這段歷史。即使是光復節,我認為在台灣要好好談終戰或光復,也是困難的事情。」
黃大展坦言,即使自己已經夠認識台灣史,並從台灣主體來思考,看了迷你劇集《聽海湧》和紀錄片《由島至島》後,仍受到不小衝擊:「我本來覺得在戰爭體制下被壓迫者都是受害者,但從這些作品發現,台灣人有可能是共犯跟加害者,對我來說是個刺激。」
「我就會想,陳增嶽不願意說出自己在新幾內亞的經驗,會不會也是有個不願回顧,也不想讓別人知道的經驗?」黃大展表示,歷史課本只是呈現一種觀點,但人的多樣性、多元性和處境,乃至於人性,都是應該被拿出來討論的。他認為,而每個人所知的故事跟經驗中,都可以找到對話跟互動的空間。如果只是從終戰或光復這些概念去討論歷史,去問這是誰打誰的戰爭,那麼人都會陷在自己的立場與觀念裡,討論就卡住了。
換言之,在現在高中教育現場,無法完全依賴課本。因為,除了公民課裡的國家認同外,歷史課本的部分也談論的戰爭、轉型正義與人權侵害的議題,像是二戰時期的國家動員,以及不同群體的戰爭經歷,高珮華認為,有些課外資源勢必得走到教室外才能接觸到,與「歷史人物」實際接觸,讓他們可以看見、聽見。
9月7日的二戰歿者慰靈祭結束前,溪湖高中的師生們排成數列,依序走向祭台獻花。對他們而言,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並沒有隨著儀式結束而畫上句點,而是展開──回到學校後,他們打算找出鄰近的戰俘營,進行田野調查。因為他們已知道,歷史離自己並不遠。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