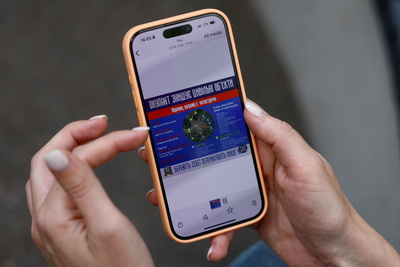獨家專訪

2025年11月19日,就在美國正式提交「28 點和平計畫」、試圖施壓烏克蘭接受和談條件的前夕,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的「公民自由中心」(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主席馬特維丘克(Oleksandra Matviichuk)飛抵台灣。她不僅拜會副總統蕭美琴,同晚更首度發表公開演說,試圖以烏克蘭歷經革命、混合戰乃至全面入侵的經驗,一一回應台灣社會的種種困惑:戰時女性的角色、青年政治冷感、「民主富二代」是否有為民主而戰的意志、怎麼在抗戰同時回應讓烏克蘭社會憤怒的貪腐問題,以及該如何看待「不抵抗侵略的和平」與面對假訊息泛濫的溝通之道。
訪台期間,馬特維丘克也再次接受《報導者》獨家專訪。這是繼今年(2025)3月基輔之行後,我們第二度與這位人權鬥士深度對話。這回,她不僅想和台灣讀者分享戰時堅持人權調查的信念,更深入剖析烏克蘭社會如何面對恐懼、自身回應絕境的策略,以及為了生存,人們究竟還能做些什麼?
「我們在台灣常聽到一些聲音,說我們不該為戰爭做準備,因為這對我們的鄰居而言就是挑釁。根據妳的經驗,我想知道該怎麼回應?」在演講會場上,一名30多歲的智庫研究員,困惑地向馬特維丘克(Oleksandra Matviichuk)提問。
「如果你的鄰居已自行決定你不該擁有權利、自由和民主,你無論怎麼想、怎麼對國際展現自己、甚至如何自我稱呼,對那個鄰居都無關緊要。」她隨後分享一則她在蘇維埃時代讀過的俄文童話:
「書上的山羊困惑地問大野狼『為什麼你要欺負我?』、『為什麼要殺我?』山羊不斷想找到真正的理由,但不耐煩的大野狼,最後只回答:『你唯一的罪過,就是我餓了。』」
公民自由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來,馬特維丘克與團隊至今已記錄超過9萬件在俄羅斯侵略行為下的戰爭罪受害個案——而童話中狼與羊的對話體悟,也正是她從這9萬多份犯罪證據中所得到的結論。
自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與頓巴斯戰爭爆發以來,公民自由中心系統性記錄俄羅斯在侵略與占領地區造成的政治迫害與戰爭罪;2022年俄軍全面入侵後,這項記錄工作更進一步擴大為全國性的戰爭罪證據庫,試著為國際審判與未來的轉型正義奠定基礎。
「我自己就採訪了數百名從俄羅斯囚禁中倖存下來的人。他們告訴我自己如何被毆打、強暴、塞進木箱、手指被切斷、指甲被拔掉或鑽孔、生殖器遭受電擊⋯⋯知道這些細節後,你就能明白他們面對的生存危機有多麼急迫。領區數百萬人活在灰色地帶,沒有任何工具能捍衛自身的權利、自由、財產、生命與摯愛。」
「(對他們而言)俄羅斯的占領,絕不只是換一面國旗那麼簡單,而是強制失蹤、酷刑、性侵、否認你的身分、強制收養你的孩子、過濾營與萬人坑。」
馬特維丘克及團隊建立的記錄與建檔機制,其開創性不僅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之一,也讓她擁有理解極權者行動邏輯的關鍵資料庫。
繼今年3月拜訪基輔後,《報導者》此回再次在台灣獨家專訪馬特維丘克。她不僅分享戰時堅持人權調查的信念,更希望與台灣讀者談談烏克蘭社會面對戰爭的恐懼、自身應對絕境壓力的策略,以及為了生存,人們究竟還能做些什麼?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妳剛描繪了以《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為基石的和平體系如何崩解。這套二戰後為防範戰亂而建的機制,眼下正處存亡關頭,世界的動盪與衝突將接踵而至。在此情勢下,你們對戰爭罪行的記錄還有什麼實質作用?正義真的會被伸張嗎?
馬特維丘克(以下簡稱馬):記錄是絕對有必要的──因為「記憶」最多只會保存三代,但在這三代人之後,唯有被「記錄」(documentation)下來的東西才能真正留存。
俄羅斯耗資數十億美元在全球建構資訊網、推銷他們的敘事,為所有暴行辯護,並假裝在烏克蘭發生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俄羅斯不會得逞,因為這已是人類史上被記錄得最完整的戰爭。光是我們的資料庫,就有超過9.1萬筆戰爭罪行的證據。身為人權律師,我們建檔不只為了留下國家正在遭遇的歷史,更是為了正義。
即使法律目前還無法起到立即性的作用,但我仍相信這只是暫時的。譬如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混亂,但人類在戰後仍有辦法恢復法治秩序。所以當機會重現之時,我們要呈交國際法院的,才不會只有眼淚或空話,而是有憑有據的清楚證據。
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坐在原地苦等機會從天而降,而是從現在就開始啟動法律程序。當我與其他國家的總統、政府成員、國會議員交談時,我發現大家仍是以紐倫堡大審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即納粹戰犯,只會在納粹政權崩潰後才受到審判。
誠然,紐倫堡經驗是上世紀的重要里程碑,但那也立下了一種準則式的成見,暗示「正義是屬於勝利者的特權」。不過時代已變,正義應是基本人權而非特權。這也是我們如今面對的歷史任務,我們必須進一步推動國際準則的進步,讓正義的實踐,不再受限於戰爭何時或如何結束。
好消息是,今年6月,烏克蘭和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簽署了歷史性協議,將設立針對俄羅斯侵略的特別法庭,在戰時即起訴普丁及其親信。這是革命性的概念,讓我們看見了更多可能性。
我們也運用數位工具重建犯罪經過、蒐證,甚至與占領區民眾溝通、指認施暴者。過去因證據難存,戰時正義難以伸張;如今,新科技則將挑戰這項舊常態。
報:但威權侵略者也正掌握新技術。在台灣,人們對真相的力量與罪行紀錄漸失信心,事實的影響力,似乎已不及資訊操縱與極權宣傳?
馬:這是普遍現象,也不只僅有台灣或烏克蘭如此。我明白有些人們只會等到炸彈落在頭上時才能意識到戰爭早已發生。但戰爭不僅限於軍事熱戰,還有完全沒有邊界限制的資訊衝突,在這個非實體的戰場上,敵人的目標就是入侵他國公民的心智。
現代極權者雖然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但他們推動共同的敘事,試圖呈現民主是軟弱、無效的,威權獨裁則是強大且充滿效率的。他們攻擊人權、言論自由、法治、普世價值,試圖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用犬儒主義和冷漠來毒害人們。
不幸的是,這種戰術確實有效,因為人們在數位世界中花費愈來愈多的時間,開始完全失去與現實的連結。他們變得極易受到外部操縱,失去了辨別謊言與真相的能力。現況是,來自同一個小群體的人們對現實不再有共同的認知。而沒有共同的現實感,我們就無法採取共同行動。沒有共同行動,我們如何保護自由、家人、國家、民主?
這是一個全球性挑戰,我稱之為「後知識時代」──當人們不再重視知識,與其尋求醫師的專業判斷,大家開始更傾向聽從網紅、部落客的建議,他們會想:「如果你真的這麼聰明,怎麼會沒有數百萬粉絲追蹤你?」同時,人們也開始要求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比方說吧,流鼻水時誤信跳繩能治病,或許還不至於害死你;但若罹患癌症仍信偏方,最後的代價將極其慘痛。而這,就是全世界正在面對的問題。

報:正是因為這種全球性的亂局,包括在台灣的許多人,開始不信任民主,甚至質疑這種體制無效。
馬:這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在已開發的民主國家,這一代人是從祖父母那裡繼承了民主,他們未曾經歷奮戰與犧牲,充其量僅是民主的消費者,將這一生來即有的人權視為理所當然。
因此,他們無法真正理解生活在俄羅斯、中國或前蘇聯意味著什麼──那是失去投票權、言論自由,甚至無法選擇摯愛的生存狀態。
對他們而言,自由或許僅是「在超市挑選起司」。正因如此,他們才能輕易地以自由交換經濟利益、民粹口號或虛假的安全感,反正一切都只為了自己當下的舒適。許多人繼承了民主卻不解其價值與意義,這是其一。
其二,民眾憤怒,是因為民主並不完美。沒錯,民主制度確實處處面臨挑戰,也有責任解決社會不均等問題。人們有權憤怒,但在抱怨的同時,大家仍得意識到自己仍須肩負兩項任務:保護民主,並完善它。
因為我們別無選擇。不完美民主的替代品,即是威權政權的地獄。而威權同樣無法解決大家憤怒的問題,唯一的差別在於:那裡的人們,連抱怨的權利都沒有。
報:妳也有對民主動搖信心的時刻嗎?
馬:有句名言這麼説:
「我們不能對民主失去信心,因為它是唯一對人有信心的制度。」
讓我解釋:我身處基輔,飽受俄羅斯飛彈與伊朗無人機轟炸,背後更有中國助俄規避制裁、替他們進口戰爭所需的關鍵技術。更別提北韓提供的上百萬枚砲彈與軍隊支援。
我們正目睹威權集團成形,其共通點是否定權利、將人民視為控制標的;反觀民主制度,它雖不完美,卻仍視人權與自由為最高價值,此點不容妥協。
自由世界的存在本身即是對獨裁者的威脅,危及其權力基礎。畢竟,身而為人,即便是威權體制下的公民,也有追求自由的本能。
馬:我非常憤怒,就像其他數百萬名烏克蘭人一樣。我們不是富裕的國家,但所有人都在為抗戰付出:老人捐出微薄的退休金,人們拿出最後的積蓄幫助傷者、流離失所者和軍隊。我們每個人都有親友、同事自願從軍,保衛家園和我們共同的民主選擇。因此,面對貪腐事件,我真的非常憤怒。
最後,我們成功捍衛了反腐敗機構的獨立性,也因此它們今日才能有效運作,這正是民主力量的最佳證明。
這種力量非常重要。我承認烏克蘭的現況遠非理想,畢竟這還是一個處在戰火中、民主轉型尚未完成的國家,而政治改革即使在和平時期都極其困難,更何況戰時。但我們仍努力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烏克蘭的韌性並非來自中央集權,而是來自地方民主、言論自由、公民能動性與基層自組織。我們的韌性建立在一個信念之上:每個人的努力,都至關重要。
報:妳是什麼時候建立起對人權工作的信念?
突然間,作為一個學生,我發現自己身處在「歷史人物」之間。他們都是了不起的人,言行一致,高尚、誠實、勇敢。因為挺身對抗極權蘇維埃機器與蘇維埃帝國,有些人被殺害,有些人被監禁,還有人被送進精神病院強制治療。你不難想像他們承受過什麼苦難。
但他們從未放棄。正是這些人深深啟發了我,也讓我走上法律之路。
我之所以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從短期來看,這些人在1960年代的抗爭努力似乎都失敗了,他們遭到鎮壓,事業、生活與家庭都被摧毀。但今天,當我們能從更長的時間尺度回望就會明白:烏克蘭之所以在蘇聯解體後有機會恢復獨立、成為獨立國家,正是因為1960年代的那些人們曾經戰鬥。
這正是你我都深知的那個道理:所有的努力都很重要。我們的生命很短暫,可能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成果;因為生命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但對歷史來說甚至不及一秒。然而,所有努力依然重要。這就是歷史教給我們的事。
報:這讓我想起在基輔附近一個村莊的對話。那個村莊是新建的收容聚落,專為國內流離失所者而設。我拜訪了一對夫婦:妻子曾被俄羅斯軍隊俘虜,在占領區待了數月,遭受許多痛苦;丈夫則在前線作戰,現已退役,腿部受傷。那對夫婦就在我面前,為是否應與普丁談判和平協議展開辯論。妻子非常堅定,認為必須戰鬥到底,因為她深知正義對她有多重要;丈夫則說:「我真的累了,我已經無法再戰了。」
馬:我能理解他的感受,因為大家都累了。但我們沒有疲憊的餘裕,因為這場戰爭具有種族滅絕的性質。
請容我說一句,2014年普丁占領克里米亞和東部地區時,烏克蘭也完全沒有機會收復領土。在那之後,我們曾與俄羅斯兩次簽署和平協議,那麼俄羅斯如何利用那段時間?俄羅斯把這些占領區變成強大的軍事基地、當作下一次發動侵略的平台;俄羅斯為新一波制裁做經濟準備;俄羅斯生產彈藥;俄羅斯強制徵召占領區的烏克蘭男性加入俄軍;俄羅斯規劃入侵並在2022年2月發動全面戰爭⋯⋯所以,如果你的鄰國是一個擁有核武與軍事力量的強權,並早已決定要侵略你,那麼你怎麼想,對方根本無關緊要。
我想再次強調:在這種狀態下,就算你再怎麼懇求和平,也不會有用。我當然始終支持對話,但政治家有責任為自己的國家準備B計畫。像是如果對話無效,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必須能夠保護我們的孩子、家人、家園、自由與國家,因為不會有人來拯救我們。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義務」。
報:我知道有人向妳說明過,台灣也有一些團體因看見戰爭的殘酷與傷亡,因而主張「不計代價的和平」。妳會如何回應這種立場? 馬:這是恐懼的語言,也非常符合人性。但在親身記錄了過去12年俄軍在占領區的暴行之後,我可以向你保證:無論你是支持俄羅斯、保持中立還是反抗,作為被占領者的你,都可能面臨綁架、監禁、酷刑甚至殺害的命運。因為在侵略者眼中,你的生命毫無意義。這就是占領的本質──它絕非換一面國旗而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們見證了強迫失蹤、酷刑、強姦、否認身分、強制收養孩子、過濾營和萬人坑的無數證據,這就是現實。
讓我用畫面說明:我相信許多台灣人還記得布查(Bucha)慘案的可怕畫面。當俄羅斯軍隊試圖包圍基輔時,我們沒走。等到俄軍被擊退後,我們立即前往布查等曾被占領的近郊地區,卻目睹平民屍體橫陳街頭。
我們看見居民陳屍自家花園、亂葬屍坑裡堆滿雙手反綁遭槍決的男女,還有車內攜子逃亡卻慘死的平民家庭──很遺憾,俄軍不在乎政治立場,他們用槍砲坦克掃射,純粹以殺戮為樂。因為在占領者眼中,生命已毫無價值。
有些人可能很天真,以為只要投降就沒事了,或許認為:「戰爭太可怕,接受占領雖然不合法,但至少比較不痛苦吧?」錯了,占領並不會減少人類的痛苦,它只會讓痛苦變得不可見,甚至更加殘酷──占領往往不是痛苦的終點,而是開始。
我想再說一次:以烏克蘭為例,即便是那些自以為自己從不談政治、不主張民主人權、所以認為自己沒理由被戰爭罪波及的人,他們最終的結局,也都死在俄軍占領區的酷刑地下室裡。這非常悲哀,但我理解人性:在面對危險現實之際,感到恐懼,是合理的人類本能。
然而在感到恐懼時,我們仍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首先該做的就是果斷行動,但這總是知易行難,因為人們還是會怕、不情願離開舒適圈,所以不願採取行動改變現況。
我能理解並同情所有感到恐懼的人。但真正的勇敢絕非無所畏懼,而是那些雖懷恐懼卻能克服自己,堅持做正確事情的人。

報:但當有人指出不和平的現況並主張積極應對時,卻常常反被指責是「挑釁者」或和平破壞者?
馬: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灣和烏克蘭人都讀過《哈利波特》,還記得那條潛規則吧?「絕不能提起佛地魔的名字」。
或是像是那個小孩子的遊戲:當鬼要抓到你了,只要雙手抱頭喊聲「我在家」,就沒人能碰你、也不會輸。
小孩子的遊戲當然可以這麼做。但很抱歉,我們都已不是孩子了。
你無法拒絕現實。即便你不提佛地魔,但當黑魔王決意發動攻擊時,他仍會現身於此。侵略者根本不在乎你的想法或感受。
報:我們都知道《哈利波特》。在台灣與國際社會中,中國或許一直像那個佛地魔──人們不能提中國的名字。但過去4年的戰爭改變了一些事,烏克蘭社會現在如何看待中國在這場戰事中的角色?
俄羅斯就像中國的代理人,負責執行骯髒的任務。對這些威權獨裁的軸心國而言,烏克蘭並非最終目標──試想,北韓對我們有什麼利益?他們只是把烏克蘭當作工具,意圖打破既有的國際秩序,並植入自己的威權願景。而這樣的願景其實並不新鮮:無非是復辟「弱肉強食」的舊邏輯,彷彿只要握有軍事力量與核武,就能為所欲為。但這對世界上所有人都極其危險,毫無例外。
沒有人是局外人,即便是那些發動侵略的國家本身,它們的公民最終也會被派上戰場,只是為了證明國家的「強大」。這正如蘇聯在阿富汗所做的,也如同俄羅斯如今所為。成千上萬的俄羅斯士兵在烏克蘭白白喪命,他們不是為了孩子,也不是為了家庭,只是因為普丁決定讓他們去死。
那個所謂的「新世界」對絕大多數國家及其人民都充滿危險,甚至對那些自認為「強國」的菁英也同樣如此。因為所謂的「強大」是一種必須不斷自我證明的狀態;一旦站上這個價值體系的高位,就必須持續展示自己總能變得「愈來愈強」。
這正是為什麼,不講法治、人權、正義,由力量決定一切的「強者主宰」的世界秩序,必然是一個更糟、沒有法治、只有暴力的世界。而這些威權國家正集體把我們推向大規模暴力的時代,這是一個極為危險的趨勢。

報:最後,我想問一個關於我們上次見面時看到的畫面──這是今年3月,我在妳辦公室拍的照片,牆上的這些東西,對妳而言代表什麼?
馬:左邊是一張登機證,上面寫著從基輔機場飛往「和平」。那是2023年,澤倫斯基總統舉辦的一場活動,他在那裡向我們報告他的和平計畫。我是公民社會的代表,其實我很少被邀請參與烏克蘭官方會議,因為我們經常批評政府。但那次,總統辦公室邀請了我。
那場國際會議在基輔的伯里斯皮國際機場(Boryspil International Airport)舉行。它是一座因戰爭而停止運作的機場,在全面戰爭爆發後,那是我第一次回到那裡。當時,主辦單位發給我這張機票──從伯里斯皮飛往和平。我拿到它的當下,眼眶是濕的,因為這張機票提醒了我:和平⋯⋯那正是我渴望恢復的生活。
那是一種你不必害怕暴力的生活:可以安排每天的行程、可以去工作、擁抱所愛的人、和家人吃晚餐、在咖啡館與朋友見面。而現在,這樣的正常生活已經不存在了。
右邊的是書籤。我們用被俄羅斯非法拘留的平民照片製作書籤,提醒人們仍有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被囚禁在俄羅斯。書籤上的QR Code連結到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
報:其中有妳自己的朋友嗎?
馬:有。我的好幾位朋友和同事都死在俄羅斯的監獄裡,其中包括烏克蘭記者維多利亞・羅什奇娜(Victoria Roshchyna)。她年輕、才華洋溢,曾獲得多個國際新聞獎,勇敢得令人難以置信。在家鄉淪陷後,她決定前往俄軍占領區採訪,試圖揭露俄羅斯在被占領領土上的行為,阻止假新聞與錯假資訊,因為她相信這是記者的責任。
然後,她失蹤了。後來我們得知她被俄軍綁架、遭受酷刑,並被非法運送到俄羅斯本土,在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關押。我們也知道她沒有接受任何醫療照護,獄友說她的體重最後只剩30公斤。但我們仍不知道她究竟如何死去。
失蹤6個月後,當俄羅斯終於歸還她的遺體時,我們發現屍體上有可怕的酷刑痕跡,且多個內部器官──眼睛、大腦與部分氣管──都不見了。
那是我的同行、烏克蘭記者羅什奇娜。她相信真相能改變世界。我不認為她天真。我至今仍相信,真相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
報:朋友死去、戰火無情、每天都有空襲,但這4年妳從未停下。為什麼能在戰爭與死亡的風險下持續工作? 馬:因為我明白,「奮鬥」(struggle)是人類最有效的生存策略。
奮鬥,會給你活下去的機會。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