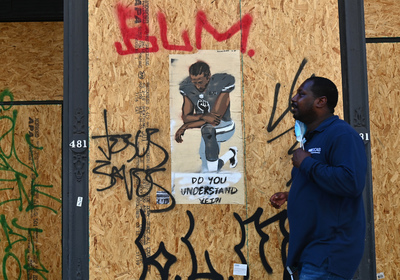週六現場【Long Game】

趕在《F1電影》(F1)上映的一個星期前,我就先預訂了上映第一天IMAX規格的門票,因為從創新的觸覺回饋預告片、大咖雲集的原聲帶陣容、片商鋪天蓋地的宣傳,我知道它會是今年(2025)夏天重振電影工業的重要一役。
結果,它也沒有讓人失望。
如同先前專欄提過,疫情期間,Netflix的F1紀錄片影集《Formula 1:飆速求生》(Formula 1: Drive to Survive)將該影集34%的美國觀眾轉化成F1的車迷。也讓F1終於打開他們覬覦已久、但原本就有NASCAR、IndyCar兩大傳統賽車體系瓜分的美國市場。如今,車手們依舊「飆速求生」,但熱度總無法複製疫情期間全球隔離在家的「有利」大環境,紀錄片影集所帶給F1新手車迷的入坑紅利也大概消耗殆盡。自2022年賽季在美創下平均每場賽事119萬人收視的高峰之後,2023、2024賽季的收視陷入停滯,因此亟需一批新血車迷的加入。
除了《Formula 1:飆速求生》持續製作之外,讓大家重返電影院,享受IMAX、ScreenX、4DX、Dolby Cinema等特殊規格下的極致聲光效果,這招聽來老套,卻在F1、電影院與投身電影製作的Apple公司通力整合下,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全球上映首個週末就達1億4,400萬美元(約新台幣41.6億元)的總票房。可別小看這短短3、5年的間隔,就流行文化來說,這是個每3、5年就更迭的時代,期待在疫情期間不知電影院為何物的COVID世代裡,再培養出新一代的影迷與車迷。

幾乎無窮盡的影音串流平台上,運動紀錄片的數量已經多到連我這個運動狂熱分子都無法消化完,待看片單上晾著一部又一部的運動紀錄片,還沒跟上新一季的進度,一個星期後又有新的運動紀錄片上線。
運動紀錄片之所以如此蓬勃發展,就是運動組織、片商與串流平台理解到運動敘事的魅力──原本運動比賽結束就結束了,但故事卻可以反覆、甚至從不同角度來說。成者為王的運動世界中,在只有現場轉播的線性媒體年代裡,冼拿(Ayrton Senna da Silva)、普魯斯特(Alain Prost)、舒馬赫(Michael Schumacher)、維泰爾(Sebastian Vettel)、韓密爾頓(Lewis Hamilton)是車迷唯一需要知道的名字;但串流運動紀錄片的年代,《Formula 1:飆速求生》裡可以讓哈斯(Haas)這個小車隊的前總監史丹納(Guenther Steiner)一躍成為車迷新偶像,也可以讓角田裕毅莽撞與口無遮攔的「人設」成為全球共識,更可以創造出無數隊友、宿敵間的戲劇張力。
《Formula 1:飆速求生》的出現,讓10年前可能默默無名的後段班車隊與車手,頓時得到相同的曝光甚至成為幾集的主角;《F1電影》則更進一步,與其說車手、總監在電影中客串,倒不如說是電影劇組、布萊德・彼特(Brad Pitt)為了增加電影場景的真實性而闖入了他們的世界。
運動電影是個奇妙的類型,一方面是虛構或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劇本,但又希望背景脈絡愈真實愈好,但在題材敏感或是授權金的問題下,運動電影未必能有真實的球隊或運動員相襯。
《大聯盟》(Major League)、《往日柔情》(For Love of the Game)不只有克里夫蘭印地安人隊(現更名守護者〔Cleveland Guardians〕)、底特律老虎隊(Detroit Tigers)加持,傳奇播報員優克(Bob Uecker)與史卡利(Vin Scully)的獻聲,更增添這些電影的真實性;《泰德・拉索:錯棚教練趣事多》(Ted Lasso)的陽光、正能量,讓虛構的瑞奇蒙隊(AFC Richmond)可以在場上與英超豪門曼城(Manchester City)對戰;熱血、謀略的《超級選秀日》(Draft Day)讓NFL用整套官方規格,相迎凱文・科斯納(Kevin Costner)擔任正港克里夫蘭布朗隊(Cleveland Browns)的總經理;但既牽涉毒品又黑暗的《挑戰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艾爾・帕西諾(Al Pacino)與卡麥蓉・狄亞(Cameron Diaz)就僅能在虛構的邁阿密鯊魚隊(Miami Sharks)裡勾心鬥角;以球團與球員勞資爭議為背景的《十全大補男》(The Replacements),也只能讓基努・李維(Keanu Reeves)在虛構的華盛頓哨兵隊(Washington Sentinels)帥一番了。

《F1電影》儼然就是一部F1賽事的官方衍生劇,所有出現的圖騰、人物、設定,都讓這部電影像是2023年賽季的平行宇宙。在F1全力配合下,虛構的APXGP車隊可以在賽道旁擁有自己的車庫、布萊德・彼特、丹森・伊卓瑞斯(Damson Idris)可以在國歌儀式中並肩維斯塔潘,更可以在頒獎台上在羅素(George Russell)身旁大噴香檳,各車隊總監們也在設定好的場景中大談策略與奚落APXGP車隊的表現,當然更少不了「F1之聲」克羅夫特(David Croft)在電影中的激情導覽。
真實的運動賽場與虛構的電影文本交錯,《F1電影》也非好萊塢運動電影首見的情況。2005年電影《愛情全壘打》(Fever Pitch)男女主角吉米・法隆(Jimmy Fallon)與茱兒・芭莉摩(Drew Barrymore)就闖入聖路易紅雀隊(Saint Louis Cardinals)主場,與終結86年貝比魯斯魔咒(Curse of the Bambino)的波士頓紅襪隊(Boston Red Sox),一同「見證」他們的愛情故事;電影製片商20世紀福斯影業利用同集團《福斯電視台》轉播世界大賽之際,安排兩位主角進入球場內擁吻,並重新撰寫劇本,給了男女主角提早擁有的幸福結局,連賽事主播巴克(Joe Buck)見到此景,都只能驚愕地留白。好萊塢的亂入,讓《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大罵大聯盟官方「忝不知恥」,憑什麼讓與球賽無關的演員出現在場上,還讓片商恣意取景,汙染了棒球史上最神聖的一刻。

時代變了,可不是嗎?儘管劇情「避輕就重」地忽略了讓死忠車迷跳腳的一些規則與細節,但可沒什麼人抱怨布萊德・彼特出現在神聖的頒獎台,甚至還讓羅素成了活動布景──《愛情全壘打》再褻瀆,可沒有讓奪冠狂喜下的瓦瑞泰克(Jason Varitek)刻意被安排晾在一旁。
所以,不論您看到的F1賽事轉播、《Formula 1:飆速求生》、或是《F1電影》,其實都是F1的多重宇宙,而這樣的魔幻場景只可能隨著《F1電影》的成功而更加普遍,未來可能看到更多運動現實與虛構交織而成的文本。
「什麼?」 「電影是虛構的?」 「您確定?」
當大量在電影裡置入的Tommy Hilfiger店裡擺賣APXGP車隊的各式衣服時,這支「車隊」可是比今年的阿爾卑車隊(Alpine)更有存在感,不是嗎?
《F1電影》上映時間的高明算計,讓其上映一週後的熱度,得以完美地延續到本週英國的銀石賽道(Silverstone Circuit),那正是75年前開啟F1紀元的伊甸園。
過去與未來交錯,虛構與真實交融,F1與Apple打了這多重宇宙裡完美的一仗。
運動,是一種文明的演進,在規範與框架之下,將野性的競爭與衝突升華為力與美的技藝。
運動,也是一種經濟的刺激,隨著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資本巿場發展,串接庶民消費與高端精品。
運動,更是國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交鋒,在集體榮光共感底下,不斷思辯競技最核心的精神與意義。
運動的社會性,與社會的運動性,是一場永恆的「長盤制」(Long Game),人類的愛恨情仇,喧囂歡愉,當代價值,將天荒地老戰鬥與論證下去。
Long Game,《報導者》的運動專欄,由研究專長為運動社會學、流行文化與媒體觀察的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美國職棒MLB球評陳子軒執筆。本專欄榮獲第23屆卓越新聞獎「新聞評論獎」。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