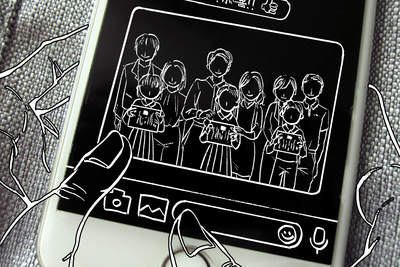大專心輔保衛戰之1:心理師篇

近年大學生自殺事件頻傳,校內的專業輔導人員被賦予重任,要防止遺憾再度發生。但走進心理師們的工作現場,卻發現困難重重──不合理的薪資待遇、身分定位不清、行政業務龐大、學生狀況複雜⋯⋯像一支投資匱乏又頻繁換人的球隊,卻期待選手能燃燒熱情,神通廣大守下每個出局數。
2014年,為維護學生心理健康的《學生輔導法》誕生,如今正是通盤檢討的時間點。本文從實務困境出發,看見在調降師生比、增加人力之外,還有哪些結構問題該搬上檯面?什麼是讓學生和助人工作者雙贏的方向?
蜷縮在諮商室沙發上,小杰(化名)哭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不久前,他人在學校頂樓,路過職員察覺不對勁,通報校安人員,眾人費一番力氣才將他拉下。在大學服務2年的諮商心理師天宇(化名),發現小杰似乎在找什麼東西,便想遞出橄欖枝打破僵局。
「是想要你的包包嗎?」對方終於點頭,至少有回應了。
天宇把包包往前推,只見小杰摸出一樣東西,迅速往懷裡藏。心理師的警示燈亮起,天宇趨前把手拉開一看,「他拿了一把美工刀,我當下就奪刀啊!再往後退一步,我也會怕!」
面對愈來愈複雜的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心理師被推上第一線,「他們期待心理師發揮功能,好像心理師來了就沒問題,但大家都一樣無助啊,」天宇無奈地說。
美國作家沙林傑(J.D Salinger) 在《麥田捕手》裡寫:
「幾千幾萬的小孩,附近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就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來,我就把他捉住。」
但當危機個案大幅增加,人手不足又缺乏資源的心理師們,如何抓住搖搖欲墜的少年?
2020年,台灣大學一週內發生3起學生自殺事件,點燃學生心理健康的討論。據教育部統計,2016年到2020年,各級學校學生自殺通報人數皆大幅增長;其中,大專校院從256人增加至2,359人,整整是5年前的9.2倍。
與此同時,大學裡的諮商需求也節節攀升。已有20年資歷的廖聆岑,是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簡稱心輔組)元老級的心理師,最直接感受到趨勢變化和工作量的衝擊。
她印象深刻,大約在2018、2019年,成大還未增聘新人力進來,心輔組彷彿修羅場一般。「超級崩潰,一週接十幾個(個別諮商)家常便飯,但工作品質太糟糕了,所有心理師都呈現快要burnout(倦怠、過勞)的狀態。」

翻開成大近年資料,106學年度來諮商的學生有5,934人次,到110學年度成長至7,086人次,5年增加近2成。廖聆岑解釋,這與心理衛生議題去汙名、求助意願提升有關,但學生議題確實也變得更複雜,情緒困擾的狀況更多。
愈是困難的個案,愈需要資深心理師的專業來承接。但像廖聆岑如此資深的年資,在大學裡實在太少見。
大專校院心理師的流動率高,在圈子裡已不是新聞。
曾在前段私立大學服務的心理師佩珊(化名),回想剛到學校時的光景:「我進去,先是兩個人走,之後又陸陸續續走,剩下我一個,就變成我最資深了。」她說,當時的同事都待了5、6年左右,看似穩定,但這年資也正好是大專心理師離職的高峰期。
大家都離開,佩珊只能接下諮商中心主管的任務。去年,她自己也轉換跑道成為行動心理師,正好待了6年,「我出來之後就是一直接案,相對來講CP值是高啦,只要做個案(諮商),收入也不差。不能否認,現在單純在諮商所的心理師愈來愈多了,大家都離開學校了。」
近年諮商所如雨後春筍開設,光台北市就約80間,台灣目前有近3,000位執業的諮商心理師,10年前只有800位左右。根據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全聯會)2020年的調查,不隸屬特定機構的行動心理師,視口碑和接案能力,月薪從2萬多到10萬元不等。
剛畢業的心輔新鮮人願意在大學練功累積實力,但是中繼站很難成為終點站,薪資水準低於市場行情和身分不受保障都是重要因素。
張河(化名)在國立大學擔任心理師5年了,他說,新進專任心理師的起薪是45,000元,包含本薪和專業加給;每晉升一級,可加薪1,000元左右,十級便封頂──換句話說,薪資天花板約落在55,000元,而這也是許多大學的常見作法。
此外,絕大多數的大學專任心理師,都是一年一簽的約聘僱人員。張河說,約聘的問題還在於年資帶不走,假如心理師想從A校換到B校,年資得歸零重算,意味著薪資和休假又回到菜鳥狀態,很難吸引資深心理師,「要是這樣,我就乾脆跳出去了,反正都要重來了,我幹嘛還去你那邊?我就去累積一個新的市場(指行動心理師)。」

大學裡還有另一大困境:即使人手不夠,心理師還要做諮商以外的事情。
《學生輔導法》中有所謂「三級輔導」的概念,初級範圍最廣,以全校學生為對象,依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篩選需要被關注對象,三級個案相對少,但情況複雜、風險高,更須加強資源連結。高中以下的學校,初級由全校教職員共同投入,二級給校內輔導室,三級則靠縣市教育局或國教署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承接。
在大學,實務上心理師卻要統包全部三級的輔導任務。
每週平均安排8~10小時個別諮商,是心理師最可見的核心職能,加上相對隱形的晤談紀錄工作,被稱為「直接服務」。
但他們的工作內容不止於此──「初級」有推廣心理衛生的講座工作坊、「二級」要評估學生狀況開案、「三級」得連結可使用的系統和外部資源⋯⋯有時候,加上值班遇上緊急危機事件,處理下來,可能再耗掉半天到一天時間。
在私校服務2年的諮商心理師Jack(化名)說,自己很幸運,近年在少子化趨勢、校方經營不易下,仍未刪減專任輔導人力──或許是看見眾多社會新聞報導青年心理問題、學生諮商需求持續上升,且狀況更複雜了。
相對地,Jack被要求支援其他學生活動和行政業務, 寫計畫、做核銷在所難免,但連學校辦運動會,他也得幫忙當工作人員。文書庶務繁瑣,非屬心理師專業,也不跟心輔直接相關,且原先已滿的行程表卡得更死、更沒彈性。
在他工作的地方,學生較少主動來使用資源,因為大多數人要在外打工,沒時間諮商或難以持續;但走進諮商中心的,往往是更複雜的個案,可能是特教生,或來自脆弱家庭。Jack坦言,「Hold一個就要花很大的心力,他們的社會支持大多都是低的,」因為家庭功能不彰顯等複合因素,才使學生來到這裡。他們不習慣或不曉得該如何求助,一旦出事卻最嚴重。
當大量學生的諮商需求未能被消化,什麼樣的資源配置,才能讓人力真正運用得宜?

量能不足,導致多數學校都設下6~8次的諮商次數限制。雖視個案狀況可提前結束或延長,但當學生展現的議題日趨複雜,需要長期諮商的比例也愈來愈高。
坐在清華大學諮商中心的辦公室,王道維比劃著電腦螢幕解說。2016年接下主任的他,本身是物理系教授,在理工科老師佔多數的清大,為了和其他老師溝通,他在新購的諮商系統加入統計功能,分析校內需求及服務量,用數字找出真正的現象與問題。
數據發現,清大過去10幾年來,學生使用諮商比例的確逐年增加,反映需求迫切。但從2019年起,即便心理師值班的時數持續增加,學生使用比例維持在7%左右,和全國青少年的憂鬱症盛行率差不多,表示校園的心理健康暫時進入穩定狀態。
清大學生初談後到正式諮商療程約要等待1~2個月,為什麼排這麼久?統計也給了答案。清大諮商中心大概有30%的時數,用在長期諮商(指一年晤談9次以上)的學生身上。
王道維解釋,清大目前申請諮商可晤談到8次,比許多學校的6次還多,但面對高危險或特殊的學生,也會延長諮商時數。「如果你不花那麼多時間,這些人可能後來會出問題。等到大家看到,就已經上報了,當然不希望它發生。」
採訪時,不少學生反映,希望預約後至少能在1到2週內能安排到諮商,認為一旦超過2週,中間發生太多事,當初困擾的狀態也改變了,不確定是否還需要晤談。
對此王道維回應,「如果1、2週後覺得OK了,代表他是有方法的,我們甚至應該鼓勵學生,尋求更多方法來提升自我的心理健康。」諮商中心在量能有限下,應該提供更多自我心理照顧的基本知識、告訴學生怎麼找其他資源求助,把有限的服務留給嘗試過一段時間、還無法克服的同學,更能發揮效益。
王道維用醫療公衛相比,「不是大病、小病都來醫院,當然希望小病可以自己盡量避免,戴口罩減少感染,多做運動,預防絕對比後來的處理更重要,這是一級輔導應該強調的。」清大也預計開設線上心衛課程,讓相關知識成為更多學生的基本常識。

成大也有相同的困境,於是在2017年增設初談機制。心理師廖聆岑回憶,過去直接開始正式諮商療程,把心理師的時段都卡住,想約的人就大塞車。有了初談後,可先掌握學生狀況,區分輕重緩急,「有點像是急診的檢傷分級:比較危險的,趕快優先幫你排;需要讓他們等的同學,可以教他們怎麼照顧自己,我們也會安心一點。」
即便校內心輔單位已想方設法,讓學生都能盡量使用服務,但每當自殺事件發生,最先被檢討的還是心理師。
「他明明有在諮商中心談,但是心理師接不住他,是不是你們輔導無效?」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常務理事林上能表示,這種說法是對諮商工作的誤解。現於點亮心燈諮商中心服務的他,在學校待了8年、曾任高中輔導組長,陪伴許多青少年度過低谷。
林上能解釋,學生帶著累積20年的身心議題而來,面對結痂的傷口,不可能驟然撕開。
「我們要先清創,重新敷藥,等傷口慢慢長好了,能夠活動了,才有辦法重新訓練他的能力,這都不是一蹴可及,」林上能說,心理師雖經過專業訓練,但也要時間逐步建立信任關係,與對方產生連結,無法直接跳過。
特別是當學生已有自殺意念和企圖,得先做危機處理,緩和個案情緒,「進入到醫療療程,有理智的時候,才真正正式進入心理諮商,」林上能解釋,直接告知引導、傳授理念是教育,不是諮商,正因一般教育處理不了,才需要心理、精神醫療等專業工作者一同合作。
「自殺也不是單一因素造成,有的時候,真的就是時間點,正好在我們接觸到的時候,才真的發生問題。」

不只是外界對心理師有期待,心理師的工作特性,也常讓他們面臨自我期待落空的懷疑。
張河一路讀輔導諮商,想成為幫助個案「好起來」的人,「當我實際去接觸、去實習,跟個案談話的時候,我才發現,為什麼他們就是不改變?我做了很多,怎麼他們就是一樣?」
面對湧上的挫折感、找不到工作的成就感,張河從一次次的督導和自我覺察中,看見自己的限制:「就像醫師吧,有時候以為這個手術沒辦法救回他,但他活過來了;有時候以為做得很完美,可是病人卻走了。我能做的只是一個中介的、催化劑的角色,但是他們怎麼變,變成什麼樣,不是我能決定的。」
他近期也負責一位頻繁做出自殺預告的學生,最嚴重時,張河已問好時間地點,考慮要通知里長和警察,同時聯繫個案的親友、老師、精神科醫師及社政單位,串聯周邊的系統安全網。
「網子能補的大概就是這樣,真的有破洞,或他要割破出去,那就是他的選擇,我沒有辦法壓著他。」話雖如此,張河發現學生的自殺意念真的減低了:「他(說要自殺)的時間一直往後延,你就知道他有點鬆動,不是那麼強烈。」
已經在大專待了5年,張河仍不時感覺自己做得不夠好。這種時候,他喜歡看學生的意見回饋表,有次同事告訴他,學生在Dcard特別留言推薦,「我就去把這個對話截圖下來保存,有點挫折的時候,看這些東西把自己拉起來。」
林上能說,圈內人普遍身心壓力過載。很多人會說心理師要懂得自我調適,但他認為,當人們出現心理危機,經常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環境需要改變:
「當環境對心理師不友善,心理師要如何為個案發聲,撐出足夠的空間跟時間呢?」
拮据的資源,正反映大多數學校對心理輔導的不認識及不重視。
王道維說,就算資源豐沛的頂尖大學,往往也想優先追求排名、提升研究能量,例如聘外籍老師提升國際化程度,或買研究硬體設備,「投資在心理輔導當然有,頂大經費也絕對不是問題,只是以前沒有參考標準,沒有預期要花那麼多在輔導上,所以就是要一點、給一點。」
為了爭取校方支持,王道維攤開數據說服。他分析,來諮商的學生中,15%有自傷、自殺意念,以每週250人次左右的諮商量,等同一週內有30~40人可能處在危機狀態。「這些學生沒有出事,就是諮商中心在做的事。大部分人看不到我們在做什麼,是因為他們沒出事;如果我們什麼都沒做,早就不是這樣了。」

但王道維也清楚,不是所有學生都會來求助,仍有黑數存在,再怎麼做都有漏接的可能。目前清大諮商中心的服務時段,使用率已超過8成,量能趨飽和,若想容納更多學生、縮短排隊時間,就得再增加投入。
清大校方得知這些資訊後,重新規劃經費,為聘任心理師支出更多人事費。此外,明年(2024)也將建新大樓,擴充諮商中心空間,讓更多學生可以得到即時的服務。
無獨有偶,成大在近2年也增聘了2位專任、6位兼任心理師,並在2022年底落成3間新的諮商室,終於緩解過去人力和空間都很吃緊的窘境。
成大副學務長兼心輔組長余睿羚坦言,多數學校認為把錢放在諮商的投資報酬率太低,看不到績效成果,也難以對外宣傳。這樣的心態,讓《學生輔導法》規定的人力樓地板變成天花板,只求達標就好。
余睿羚表示,目前成大增聘的人力不是終點,新上任校長很注意學生心理健康,兩人幾番討論後,希望能往1:700的專業輔導人員師生比目標邁進。她說,法規只是平均值,從過往頂大頻傳自殺來看,成大學生的需求很可能更高:
「從實務端再往上推,怎樣才是比較夠的量能、比較積極的輔導?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路。」
不只是量的增加,余睿羚也希望根據學生狀態來聘更合適的人。她解釋,每個心理師的特質、技巧、學派都不同,假如精神疾患比例增加,可考慮加入臨床心理師;外籍生人數多,得更完善外語諮商。此外,也希望聘行政專員,來處理各種庶務。
余睿羚想著,如果心理師能把更多時間拿去排案,同學們就更有機會被接住。「但這是滿奢侈的想法,特別是在公立學校的結構底下,要專門一個人來做行政不容易,還在努力中。」
既然法規標準往往成為實務上的天花板,要為校內心輔爭取更多空間,修法便是不能輕忽的戰場。
林上能表示,早在2014年《學生輔導法》立法時,就有立委提出1:800、1:900的想法,如今大環境惡化,學生更需要協助,絕無讓步的道理。
至於師生比怎麼評估才合理?林上能提醒:
「要分析歷年來學生的主訴議題、waiting list有多長、晤談量、每個心理師平均的負荷量。」
林上能表示,必須從學校特性和學生需求來思考,有些學校即便高出標準,實際運作仍是超載。他也呼籲,教育部要有考評機制,來檢視各校的統計和量能,確實編列需要的經費。

種種困境是否有解?這次《學生輔導法》修法是個契機,但降低專業輔導人員師生比、補足人力只是最基本,林上能提醒,應該趁此時全面檢討各種制度性問題。首要是組織編制和人事的正式化,讓心輔在校內可以「名正言順」。
他建議,應將各校的心輔中心提升為一級單位,不再隸屬於學務處,才有更充裕的經費、話語權與專業自主權;心理師也要朝向正規聘僱。針對人事成本太高的質疑,林上能提議,可以逐步增加正式聘僱比例,加入升遷考核機制。「大家正向競爭,學生才會有好的被服務品質。不然你永遠就是約聘,有時候薪水還不會增加。」
但這些改革都需要教育部確實的督促,林上能直言,不是學校沒達標就抽掉補助,而是要積極輔導,「大學自主」不該被拿來當成袖手旁觀、迴避責任的擋箭牌:
「學生在學校裡面,是我們最好可以幫他們的時機了,很多人到大學成年,才有機會脫離受傷的家庭或社會環境的不利,獨立自主,這不就是學校的社會責任嗎?」

前陣子,Jack有位學生在家中吞藥(overdose),幸好最後平安無事。可學生已在外全職實習,評估又有再自殺風險,要怎麼幫忙連結更多資源?
醫院先做了自殺通報,當Jack聯繫自殺防治中心時,仍在分派個案管理員的階段。對方說,個案既然還在學,最後還是交給學校追蹤。Jack鍥而不捨,打電話到學生住處附近的衛生所,諮商也都爆滿。
「我不可能跟學生說,案滿了,你再等一下⋯⋯最後還是學校自己要吃下來,說穿了就是外面人力也不足啊!」 Jack深刻體會,如果學校不把重擔挑起來,學生也沒有其他去處了。
受訪最後,他在鏡頭那端語重心長地說,「大學可能是這學生最後一個可以賦能的階段,如果因為我們自己的情緒耗竭、工作疲勞,在這裡把他放掉了,我沒辦法想像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升學主義下,我們作為一個人需要的能力,在之前沒被建立。到了大學,漸漸要走向自立之路,很多人才有機會重新思考我是誰,開始療癒自我的旅程。」
作為助人工作者,Jack真心希望這些年輕人,有機會被多拉住一下。他說,如果資源能再多一點、偏見能再少一點,那就好了。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