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年拉警報的內外婦兒急五大科之外,今年(2025)包括台大醫院在內,首度把神經內科也納入「人才招募困難科」,紛紛加薪留人,台大第一年住院醫師每月加薪2萬元,第二至六年住院醫師加薪2.2萬元。但住院醫師招募起跑後,神經內科門可羅雀,最新一年神經科一招率僅有80%,呈斷崖式下滑。
其中,大幅提升急性缺血性腦中風預後和存活率的24小時內取栓手術,被認為是「嚇跑」年輕醫師的原因之一。這項每年健保給付達5.95億元,原本神經內科、放射線科甚至心臟內科相關科都趨之若鶩、又效果顯著的醫療服務,為何成為壓垮神內人力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台灣腦中風學會理事長陳龍認為,「最困難的不在於導管操作,而在於術前判斷與溝通。」醫師必須在分秒必爭的時間內評估病人是否適合手術、排除禁忌症,並向家屬清楚說明風險。以雙和醫院為例,去年(2024)完成約120例動脈取栓術,但實際經評估的病人是好幾倍。
中風病人送到急診後,在第一線評估、守住「黃金時間」的重責,幾乎全落在神經內科醫師身上。
「病人一到急診,我們就得立刻趕過去,」大林慈濟醫院神經內科醫師邱孟祈形容,這場與時間的賽跑,從接到電話那刻就開始,「急診醫師通報後,我必須在10分鐘內出現在急診室。」
台灣每年腦中風新發生數約3萬人,是台灣第四大死因。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內科部副主任張谷州形容,早些年各科醫師都不想收腦中風患者,因為沒有好的治療方式,只能給他一張病床。
直到1997年陸續有積極性的治療發展,2002年健保核准rt-PA血栓溶解劑、2015年開放EVT的取栓術給付,腦中風治療進入新紀元。
臨床上,rt-PA與EVT被醫師代稱為「一號」與「二號」治療,台灣神經學學會祕書長、台大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蔡力凱則把兩種治療比喻為「通樂」與「通條」,前者是把rt-PA藥物注入血液中以疏通阻塞的血管;EVT則是將取栓導管深入血管,直接將血塊移出,適用於「大血管阻塞」的病人。依據阻塞位置與發病時間綜合評估,必要時兩種療法可同步進行。
「治療的進展下,現在能替腦中風患者做的事情太多,」張谷州也以「很幸運」形容自己有幸能參與到台灣血栓移除的時代。
取栓手術必須經過一年的培訓、取得證書才能進行,目前執行的科別主要是神經內、外科和放射線科,共有6個學會可進行訓練和認證,包括台灣神經學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腦中風學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醫學會、中華民國神經放射醫學會、社團法人神經外科學會、台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治療醫學會。目前全國取得資格、可以執行取栓的醫師僅有224人。
因為rt-PA和取栓治療效果頗佳,2023年健保署放寬給付適應對象,發布新聞稿強調,參考國際實證和臨床指引建議,取栓術由原先「限前循環在發作內8小時內使用」,延長至「24小時內」,預估一年約新增565人次受惠;同時rt-PA給付對象也由發病「3小時內」延長至「4.5小時內」。原本是德政一樁,沒想到,卻引發神內人力擠壓的骨牌效應。
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長、台大神經部主任鄭建興直言,適用病人中風急性時間拉長,就代表可以治療的病人變多,年輕住院醫師逐漸受不了,「因為值班都不用睡覺,病人會一直來。」
「(2023年)健保署對取栓術放寬給付是一個滿大的轉折,讓值班變得難值,」一名嘉義市區域醫院醫師透露,目前重度急救責任醫院的標準,需要有神經科醫師24小時提供急性腦中風的評估,但人力向外流失,標準愈來愈難達成,神經內科醫師沒辦法填上值班數,只好由急診醫師來負責。
《報導者》取得腦中風學會提供的資料顯示,施打rt-PA血栓溶解劑,2023年放寬對象前平均每月為437件,放寬後為556件,成長了27.2%。取栓術申報量3年內則從2,106件數成長至3,334件,成長了約1.5倍;特材的申報量也從3,237件成長到5,642件。以2024年來說,光腦中風健保就支出626.32百萬點,花費將近5.95億元在腦中風取栓上。
健保對取栓術相關給付其實不算差,基本技術點數為45,059點、「顱內血管抽吸取栓裝置」點數122,698點、「顱內血管抽吸取栓裝置」點數為82,999點,還有其他收治病人和轉院獎勵等。健保署之前表示,一個血栓病人健保給付平均大約300,000點。但是,其中治療評估費用僅有3,000點。
蔡力凱指出,缺血性腦中風的病人,大約100個中就有10需要打rt-PA、15個需要取栓,這兩項治療占了大約五分之一,「但是一個病人不是只有一個醫師在治療和處理。」以台大為例,會先由急診醫師和護理師進行檢傷分類和一般醫療處置、神經內科值班住院醫師進行會診評估、影像科團隊執行腦部影像檢查、CALL當天待命的主治醫師討論決策,如果確定要做取栓,還要召來取栓團隊進行,團隊基本成員包括取栓醫師、護理師、放射師和麻醉醫師,手術後由加護病房團隊進行後續照顧,前後經手醫護至少超過十餘人。
「當醫療團隊們投注這麼多心力,是不是有被制度等價對待及回報?不同工有不同酬嗎?」蔡力凱指出,但各家醫院有不同分配機制,撥補比例差異極大10~70%,代表有部分醫師花了一個小時評估並擔負了診療壓力下,換算僅獲得不到300元的補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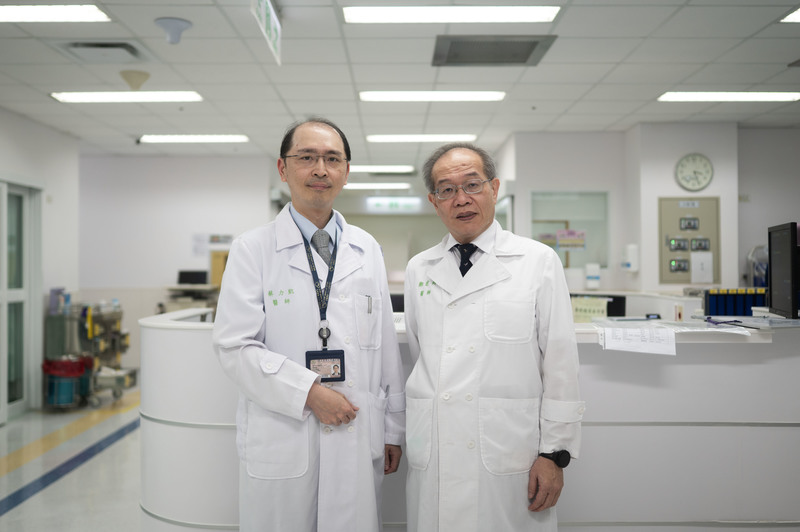
不只是溶栓與取栓照會神經內科醫師,神內是「會診」最多的科別之一,意識不清、頭痛、癲癇、不明原因的異常神經學表現都照會神內,蔡力凱自己就隨身攜帶一個神內專用的神經功能檢測包。他舉例,在急性腦中風使用抗血栓藥物阿斯匹靈(Aspirin),比以往也更複雜,需搭配其他藥物,第一線醫師往往得回頭請教神經內科──醫學進展對病人來說是好事,但複雜度提高,加重照會量與決策壓力。
除了給付分配問題外,高風險科別的壓力和醫療糾紛,是另一個人力流失的因素。
看到患者康復固然有成就感,但也難免出現預後不佳的患者。以取栓手術為例,有6.4%出血的副作用風險,手術前醫師會判斷腦中有哪些死掉細胞、活著細胞,搶救苟延殘喘的細胞,但所處的血管較脆弱,如果把塞住的血栓突然移除,血就會沖到血管脆弱的地方,產生大出血。
邱孟祈就曾經遇過出現併發症的患者,「預後都不好,就會愈做愈挫折!有時候又遇到醫院評鑑的壓力,熱情就會慢慢消退。」
若又遇到家屬責怪和壓力,心灰意冷離開的醫師非少數。博智博睿診所院長陳炳錕就以「重症逃兵」自嘲。他曾在醫學中心一人値了半年的rt-PA班,一次夜診時替一名左側肢體無力的男性施打rt-PA,一切看似順利,不料數小時後,病人突然呼吸心跳停止,急救過程出現大量出血,最終,病人仍未能挽回生命,家屬責怪:「都是你害的!人是好好的走進醫院,為什麼會這樣走了?」這起事件成為他難以抹去的記憶,熱愛功能性神經學的他,最終選擇從醫院出走。
蔡力凱也遇過病人在治療後發生出血併發症,「但以當時的病人狀況,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通常還是會這樣治療。」醫學本來就有不確定性,醫師很努力去照顧,但總是會有不如預期的時候。「治療風險對醫師心裡掙扎、波折、不被肯定,當承受不住心理壓力就離開,導致人力不足、其他人崩盤,」他感嘆。
有的醫院去年神內團隊走了一半的人,瞬間值班量能就少了一半。而一個醫院人力不足,影響的是一整個地區治療的量能。尤其六都以外的縣市,大醫院原本就比較少,當一、兩家醫院人力出問題,緊急醫療系統就會翻天覆地的影響。
神經內科醫師流失,導致夜間、假日沒有人力輪值,腦中風患者送進來沒有醫師進行評估判斷,嘉義長庚成為嘉義地區唯一後送醫院。嘉義縣衛生局醫政科科長林淑華說:「網絡間11間醫院都把患者外轉,長庚醫院得負責自己院內重症個案,還必須協助其他醫院診斷,人員就會burn out。」
林淑華表示,縣衛生局已再協調分流,嘉義市患者優先往嘉義基督教醫院,雲林北港則送往台大雲林分院,藉由分工分流減少第一線的壓力。張谷州認為,當時嘉義長庚的事件,不是基於患者治療的需要而轉院,是照護的需求,各醫院應該更詳細盤點更重視整理人力問題。
嘉義取栓警報事件也顯示,目前各地區在急重症人力不足下發展出的「區域聯防」,區域不能只以行政區畫分,而需要以生活區擴大聯防。
以取栓為例,人力更高度集中於北部地區,約有一半的取栓醫師分布於台北區(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金門縣、連江縣)及北區(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雙北地區有16家醫院能全天候提供溶栓與取栓治療,醫師資源密集。陳龍指出,「我們甚至曾經派醫師跨區支援到宜蘭、苗栗,這就是現實人力的緊繃狀況。」
「你們怎麼看待未來發展?」蔡力凱問年輕神內醫師,收到的答案是:「我擔心自己值班值不完,就算到了4、50歲,可能還在值班。」
蔡力凱觀察,年輕醫師傾向至不用值班的醫院和診所就職,願意以神經內科當作志願的醫學生、住院醫師也愈來愈少。
儘管健保署針對取栓術給付和分配立即做出調整,但顯然年輕醫師未必買單。衛福部每年給神經科固定容額為51名,往年滿招是常態、報到率也在9成以上,但今年一招率首度下滑到8成。
台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神內醫師王署君也感慨,這兩年人減少特別明顯,「北榮固定容額4名,往年是17名醫學生搶4名額,但今年只剩下6人來面試。」這還不是最慘,中南部醫院幾乎找不到神經科住院醫師。
當住院醫師數減少,無疑直接增加主治醫師工作量,值班數增加下,又留不住人。不僅住院醫師招收率下降,蔡力凱憂心,完訓獲得專科執照比率也創新低──當住院醫師受訓第4年後進行專科考試,歷年都可以維持在9成以上,近年完訓率創下新低達到84%。
緊急醫療人力明顯出現斷層,留下來的醫師憑著信念、熱情苦撐,邱孟祈說,像大林慈濟醫院就沒有住院醫師,「若是我值班,一條龍全包辦。」他回憶起,有次晚上凌晨1點接到電話,在急診開始評估、接著取栓,直到早上6點將患者送進加護病房;他回到宿舍洗漱後也睡不著,緊接著回醫院查房、看門診,「但那天的門診,後面根本不知道是怎麼結束的。」

腦中風治療是劃時代的躍進,但這是建立在高度人力支持下的成果。蔡力凱擔憂,「現在價值撐不起勞動力時,問題到臨界點就會爆發,而這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也不希望時代進步,卻因人力不足讓我們(治療)走回頭路。」
除了合理的給付外,醫師也認為,應在醫療糾紛、跨科支援等面向建立完整制度,才能同時維持專業人力與腦中風治療的品質。
陳龍從腦中風學會角度著手提出解方:
- 效仿婦產科的生產事故救濟,給予手術執行者及患者更充足的保障,減輕第一線醫師的心理壓力和負擔。
- 在神經內科醫師人力不足的地方,考慮由急診醫師經過相關訓練後一起加入一線評估中風病人是否適合接受溶栓及取栓的治療。
- 給付制度更充足,可效法美國將神經學細分分為兩大類:一般神經科(General Neurology)和腦血管神經學(Vascular Neurology),讓從事腦血管治療的醫師獲得合理回報,同時年輕醫師更清楚自己清楚要從事的醫療面向。
陳龍強調,「救一個腦中風,救的是全家人。」緊急醫療單靠砸錢沒有用,除了醫院要支持、各科別要配合,更重要的是回歸政府建立完善的制度來解決。
張谷州也認同,腦中風未來或許會走向更多的跨科合作,除了溶栓及取栓是特定處置,後續照顧屬於內科共同一起承擔,別讓一個專科孤軍奮戰。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