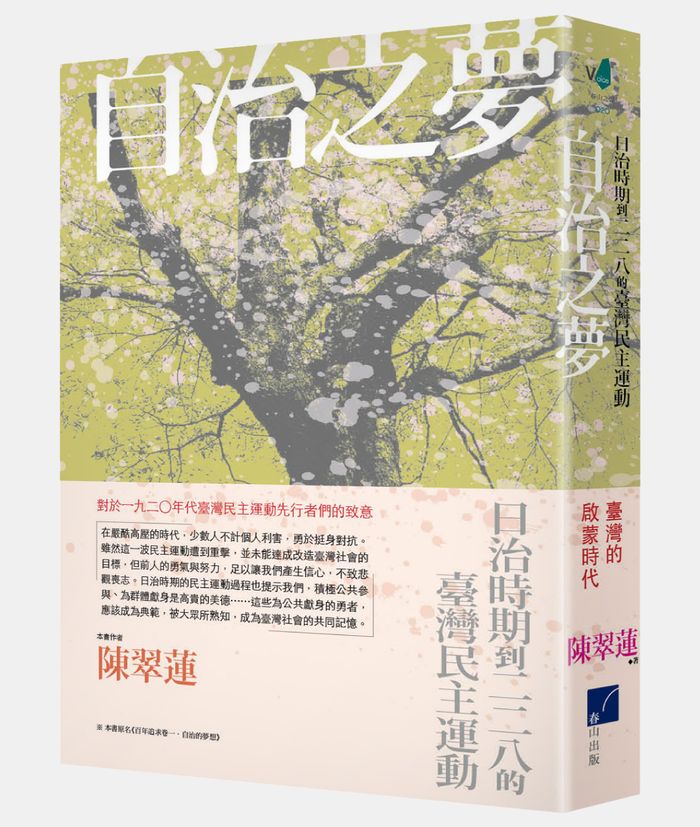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第四章部分書摘,經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1920年代日本在台統治進入穩定期,已在帝國牢牢控制下的台灣,為何會出現政治社會運動?
在那個台灣識字率只有3.9%的年代,解放的思潮影響著蔡培火、林呈祿、林仲澍等台灣留日學生,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們與本島仕紳如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相互奧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藉由文化運動傳播新的文明價值與各種理論啟迪大眾,同時也成立政黨,以組織之力要求民主與參政權。
雖然內部有路線與理念之爭,外面有統治者步步緊縮,後期更面臨了戰爭與東亞秩序變動的壓力,以及二次大戰後新統治者毫不容情的斲傷;然而,從1920年到1947年,這近30年的時光可說是台灣的啟蒙時代,「台灣人」意識在這段期間內形成,對於自由、民主、人權與自治等概念的理解,也逐漸根植人心而成為共同的追尋。
長期研究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戰後台灣政治史的學者陳翠蓮,書寫那個年代積極公共參與、為群體獻身的勇者,希望他們的身影被大眾所熟知,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本書原名《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
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不到30年,不但克服熱帶疾病與髒亂,並展開全台的基礎建設,西部鐵路、南北港口、都市下水道、農業水利設施逐步完成。台北、台中、台南已是道路寬敞、整潔有序的進步都市,農業發達、工商繁榮,台灣總督府志得意滿地向西方各國宣傳,台灣是成功的殖民典範。
不僅日本政府自誇,新崛起的台灣第一仕紳辜顯榮也這麼附和:
若以公平的眼光來看,觀察帝國領台以來至今30年的治績,我台灣島民實在是地球上各國之中最最幸福的人民之一。看看對岸支那便知。
支那在清朝被推翻、建立中華民國至今,動亂相繼,號稱共和政治,實則各省軍閥橫行,爭權奪利、重斂苛稅。與之相比的話,我們台灣如何呢?全島土匪一舉廓清二十多年來,一次戰亂也沒有,全島一片和氣洋洋的昇平景象。如此幸福的人民,世界何處可尋?
簡言之,台灣現在的富庶要比前清時代增加數十百倍,事實可證,台灣人民生活已大幅改善。 ──(尾崎秀太郎,《辜顯榮傳》)
然而,物質生活的滿足,這就是台灣人所追求的全部嗎?
1920年7月,林呈祿、彭華英、蔡培火等人創刊了《台灣青年》雜誌。1922年4月以後改為《台灣》,由蔡培火返台籌募資金成立公司,東京本部由林呈祿接任編輯兼發行人,支局設在台灣文化協會創辦人蔣渭水太平町住處。這兩刊都是月刊型態,訂閱者多是知識分子,最高發行量不過3,000部。
為了因應島內政治與文化運動的推展,並擴大讀者群,1923年4月發行《台灣民報》,以半月刊方式出刊。東京方面黃呈聰、黃朝琴二人出力最多,台灣方面則有蔣渭水加入,報紙總批發處就設在蔣渭水大安醫院隔壁。《台灣民報》以淺顯漢文出刊,從半月刊、旬刊、又改為週刊,至1925年7月,發行量突破一萬部,與當時台灣第一大日報《台灣日日新報》發行量18,790部相較,並不遜色。而爭取自東京移回島內發行、由週刊改為日報,則成為台灣政治運動家們的主要目標。
192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至此,從改革訴求、運動團體到宣傳機構一應俱全。參與其中的葉榮鐘這樣形容: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裝抗日的三大主力。若用戰爭的形式來譬喻,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外交攻勢,《台灣青年》,包括以後的《台灣》雜誌、《台灣民報》、以及日刊的《台灣新民報》是宣傳戰,而文化協會則是短兵相接的陣地戰。
《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這一系列報刊做為「台灣人的喉舌」,除了宣傳政治社會運動外,更重要的是深入探討台灣文化問題,推動文化改造運動。
《台灣青年》創刊號上,林呈祿所撰的〈新時代台灣青年的覺悟〉一文,對日本統治下的物質文明提出批判:
台灣的物質進步,是以內地人為本位的進步,是殖民地母國本位的經濟政策,是與台灣人精神進步無關係的跛腳的進步。
人類是追求理性的、精神的動物,並非以物質生活的滿足做為唯一的目標。如果只滿足於物質生活,那人類與動物園內的動物有什麼不同呢?又與耕作用的牛馬有什麼差別呢?
擁有高級智能與理性,是人類與與動物最大不同之處。追求完全的文化生活與精神自由,則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區別之處。 ──(林呈祿,〈新時代に處する台灣青年の覺悟〉)
100年前,台灣青年就已經明明白白揭櫫台灣人所追求的目標:台灣人不僅希望物質生活進步,更要求擁有精神文明、自由與尊嚴的生活方式。
1920年底,蔡培火在《台灣青年》上發表了一篇〈台灣島與我們〉,文中這樣說:
我們台灣人置身於這無盡的天然寶庫,眼底盡是偉大山河景色,豈能無動於衷。我們決不能悠悠閑閑,無所作為,台灣是帝國的台灣,更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
啊!我們台灣人是這美麗寶島的主人翁,各位應重視此事,做為島主的我們,應共同努力,使同胞得享安樂幸福,必非夢想! ──(改寫自蔡培火,〈我島と我等〉)
文章一出,《台灣青年》首次被日本當局禁止發售。顯然,統治當局已嗅到文中所傳達強烈的政治氣息。雜誌雖被禁,「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卻成為日後政治運動最響亮的口號。這篇文章中所暗示,台灣人應不分人種族群團結起來,抵抗外來強權宰制,爭取當家作主的機會,這種「做自己主人」的企圖,從日本時代延續到戰後,成為百年來台灣人追求的夢想。
在此之前,清國統治者稱島上的人民為「台民」、日本政府則稱之為「土人」,台灣人只是被統治的客體、落後的土著。島上的人民則以祖籍漳州人、泉州人、廣東人自稱,島民的認同仍是遙遠的祖宗移居之地「唐山」。
經過近代國家日本的統治,1920年代的台灣社會因交通、通訊等設施,語言、報紙等媒介,島民開始出現近代性的群體認同。但是,這個群體認同並未被整合進總督府大力宣傳的「日本」國家,相反的,因為遭受歧視與差別待遇,知識分子明明白白體會到「我們與日本人不同」,我們是「台灣人」。「台灣人」這個自我命名在此時出現,透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宣傳,一再被使用、傳述,不斷被強化。於是,「台灣人」,一個以台灣全島為範圍、以腳下這塊土地為認同、標示著「我們」的這個主體認識出現了。
配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推展,〈台灣自治歌〉這樣主張:
蓬萊美島真可愛,祖先基業在。 田園阮開樹阮栽,勞苦代過代。 著理解,著理解, 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 台灣全島緊自治,公事阮掌才應該。(台語發音)
島民自稱為「台灣人」,並且要求「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自治」,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日本政府對「台灣人」這樣的自我命名感到不舒服,試圖將之去除。總督府指示官方媒體不再使用「土人」衊稱島民,改為「本島人」,但自我認知已被喚起的人們已不再甘於殖民者所給予的名字,他們要自己選擇名字。黃呈聰驕傲地說:
《台灣日日新報》同意改為本島人,過去雖稱為「土人」,現在已經改正。並且說明,土人是指土著人,本島人是本島居住的人,土人這個稱呼引起反感,現在改為本島人,應該比較合適。
但我們則主張稱為台灣人比本島人更好。其一,若在內地稱本島人,沒有人知道是指台灣人。其二,本島人就是指島上所居住的人,像是沖繩人也可以稱本島人。所以,我們主張稱為台灣人,不論到什麼地方都容易明白。 ── (改寫自黃呈聰,〈台灣人的名稱〉)
島民相當堅持,久而久之,連日本人的報紙、官方文書也使用「台灣人」的稱法。如此一來,「台灣人」不僅是自我命名,也成為別人對我們的稱呼了。
不過嚴格說起來,日本時代所稱的「台灣人」,與現今台灣人的範圍並不相同。當時所稱的台灣人是指漢人及行政區內的原住民(熟蕃),並不包括山地原住民(生蕃)。日本統治者採取「漢原分治」政策,使雙方各在不同行政體系下被管理,缺乏接觸的機會。因為缺乏互動接觸與共同生活經驗,也就難以產生「我們」的想像與情感,這正是殖民統治的後果之一。戰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了類似的統治手段,例如設立山地管制區,把原住民圈養起來,禁止漢人自由出入,遂行控制。
台灣人要做為自己的主人,先要有「人的自覺」,文化運動就是一種「自覺運動」,《台灣民報》中不斷如此闡述:
燦爛的歐洲現代文明,是由於全歐洲人的自覺,在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四五百年間,所建造出來的。事實上,歐洲近代史可以說是一部「我」的自覺史。
文化運動是一切運動的基礎,在全體民眾還未完全覺醒以前,任你社會運動家如何叫嚷社會改造,任你政治運動家如何鼓吹民權伸張,也不過是做一場空夢罷了。欲使社會運動甚至政治運動能夠有效實現,非得借文化運動之力,叫醒全體民眾不可!而文化運動的目標,正是要喚起全體民眾的徹底的覺醒。 ──(改寫自《台灣民報》社論,〈文化運動的目標〉)
100年前,台灣的文化運動者就已經努力宣揚人文主義,喚起台灣人覺醒,不甘再像動物一般受人役使、像奴隸般受人壓迫。他們不斷提醒民眾,要自覺「我是人」,要有獨立人格、要被尊嚴地對待、要過自由的生活。
蔡培火在報刊上說,他長期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就是「人格的做成」,「人格是辯真偽、別善惡、定行止的總體能力」,是做為人類的基本條件,沒有了人格,失去基本尊嚴與能力,就失去了生存的權利。所以他說,「文化運動即是人格運動」,要喚起台灣民眾的自覺,使其人格不受束縛、不被壓制,不再逆來順受、麻木不仁。
1920年代前後,日本知識分子間流行「新康德哲學」,包括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東北帝大、高等學校都陸續設立哲學系,探討新康德哲學。因為,此派哲學對19世紀以來西方急速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矛盾現象頗為關切,更對科技發明、產業發達後所造成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現象產生危機感。新康德哲學提倡精神文明與文化價值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抵擋物質文明對人類精神腐蝕的良方。這樣的哲學思維,正符合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他們也急於尋求解救社會過度物質化、功利化的精神力量。京都帝大的桑木嚴翼、朝永三十郎等人移植了這個德國哲學流派,成為日本學院派的「文化主義哲學」。
1918年,日本思想團體「黎明會」成立,第一回演講就邀請了哲學家左右田喜一郎演講「文化主義的理論」;接著又由桑木嚴翼演講「文化主義與社會問題」,文化主義成為大正民主時期最流行的哲學思潮。
這些日本哲學家們強調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推崇自由、獨立的人格能夠抵抗物質腐化,抵抗專制壓迫。自由的人格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基礎,是真善美文化的源頭。而且,文化主義與自由、平等、和平等價值具有親近性,可以抵抗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官僚主義的壓迫。這些主張,稱為「人格主義」、「文化主義」。
台灣知識分子也承襲了這些日本國內所流行的哲學思維,其中以陳逢源做為代表。他在《台灣》第三卷第三期發表〈洞察晚近世界潮流〉、第四卷第二期又發表〈做為人生批判原理的文化主義〉等文章,闡述「人格主義」、「文化主義」。陳逢源是台南人,1893年生,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熟讀康德哲學之餘,他進一步將此運用在政治論述中。例如他以人格自由原則對照台灣統治現狀,指出台灣總督府明顯侵犯台灣人的生存權與人格權,因此主張撤除對台灣人的種種束縛,包括廢止砂糖原料採集區域制度對經濟權的限制,廢除保甲制度、匪徒刑罰令對於基本人格的侵犯,禁止日本同化主義對台灣文化的歧視等等。
覺醒自己為自由人、具備獨立人格,這樣的台灣人才有資格談論台灣文化。接著,文化運動者們描繪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台灣文化。
日本時代,雖然許多政治運動者都抱持某種「祖國情懷」,但他們認為,晚清閉關自守,國民長睡不知世變,方遭遇割地賠款之辱,因此對於中國文化評價不高。他們主張,世界文明不進則退,所謂「中華輝煌文化」早已成過往,以漢民族為主的台灣人,不積極從事文化運動不足以自救。
尤其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改革有成,即便如此,日本國民全體仍舊兢兢業業於「攀登文明階梯」。東方新興帝國全體國民尚且努力仿效西方文明、力求進步,做為帝國征服新附領土下的台灣人,又怎能不加緊腳步、奮起直追?
但是,急起直追並不是一味模仿日本文化或西方文化,而是應該追求豐富多元、兼容並蓄。林呈祿認為,要開發本島文化,除了革除陋習、吸取新知之外,最重要是「去除種族的憎惡之念」,「因種族差別挾憎惡之念,則失去新時代文明人的資格。」王敏川也指出,把東洋道德、西洋器物對立起來的說法是不對的,忠孝節義並非東洋人所獨有,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亦採西洋道德來教導人民:
我們台灣人不可隨聲附和,一味排斥西洋文化,而應該善取不同的精粹。又如東洋文化中的道德,像仁愛的觀念,也應當尊重,發揮東方文化的長處。
文化運動是不可滿足於現狀的,最重要是創造的精神,我們不但不應滿足於東洋文化,就是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是!不滿足才有創造的精神,才會得到豐美的成果。 ──(改寫自王敏川,〈從事文化運動的覺悟〉)
黃呈聰更提出「多元混雜」的主張,他認為台灣文化的現狀,本來就是一種揉和了漢人、台灣人、日本人的「混雜文化」,往後更要擇善學習、調和創新出更優越的文化:
我們台灣有自己固有的文化,更要選擇外來文化優良的部分加以調和,以打造成台灣特種的文化。
並不是盲目模仿,就可獲得高等的文化。必須能創造特種的文化始能發揮台灣的特性,促進社會的文化向上。執意傾向中國、或傾向日本、或傾向西洋的生活模式,是無益的。而是要擇其最善、有益的部分,加以融合,方可促進社會進步。否則,終歸只陷於混亂的狀態。 ──(改寫自黃呈聰,〈應該著創設台灣特種的文化〉)
受到世界思潮的鼓舞,1920年代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們胸懷大志,以世界性的眼光自我期許。《台灣》雜誌創刊號的卷頭詞〈台灣的新使命〉就指出,做為「地球之一部分的台灣、人類之一分子的島民,應急起直追適應新時代,啟發精神的、物質的文化,從而貢獻於改造世界的大業」。
像這樣自我期許的文字,不斷出現在台灣人的報刊中。例如林呈祿強調,開發台灣文化並非只是為了個人的目的、350萬人所構成的台灣,或日本帝國的台灣,而是「做為世界的一部分的台灣」的觀念來開發台灣文化,涵養公共的精神。王敏川以「雄飛天下,興世界文明民族,貢獻人類之進步文化」期許於台灣青年。1920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上,蔣渭水的致辭更是廣為周知,他認為「台灣人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所以要奮起,達成使命。
但是,自許擔負著世界和平任務的台灣人,文化上卻甚為落後。醫生出身的蔣渭水自我檢討之餘,如此描述台灣人的「症頭」:
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思慮不遠、缺乏講求衛生、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爭眼前小利、智慮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全無朝氣。 ──(蔣渭水,〈臨床講義〉)
知識分子們希望過改造台灣,首先指出台灣主流文化活動中的反智性與落後性。
1921年11月《台灣青年》刊出台南文化人王開運的文章〈就普渡而言〉,指出普渡活動是迷信行為,一來使子孫陷於迷信,二來鋪張擺場、費錢財,三來珍饈鋪排敗壞、罔顧衛生,無一有利。此後,民報系列不斷刊出文章批評民間信仰活動,尤其1924年前後,火力更加猛烈。因為,這時期正巧許多民間迎神賽會活動接連進行,包括台北市稻江慈聖宮建醮、桃園景福宮建醮、迎城隍、迎媽祖、迎王爺的賽會不斷,又極盡鋪張,《台灣民報》因此炮聲隆隆,毫不留情地批判。黃呈聰等人指出,將禍福吉凶祈於鬼神,是反智、愚蠢的行為;民眾張羅祭品浪費錢財,不如用於濟貧。蔣渭水則認為,殖民政府袒護廟宇做醮委員、勾結特定紳商。
他們也質疑,總督府面對迷信行為,不但不加以開導教化,反而以公權力配合廟會活動,甚至任由大小官員出席祭拜捻香,此種鼓勵台灣社會沉迷於此的做法,不知是何居心? 他們擔憂,在殖民政府的縱容,台灣紳商、廟祝委員們的共謀下,台灣社會被集體麻醉,成為「迷信島」:
台灣自風景上來說,是美麗島,自風俗上來說,卻是迷信島。我們在台幾乎每日看見所謂善男信女,有的捧著香爐、提著紅燈,有的抬著神輿、捧著香枝,前頭必有吹打⋯⋯希望官廳,與其傾力於文化運動的親臨監視,寧可多用一點工夫於撲滅迷信。更希望御用仕紳們,不要假借迷信做為巴結當局的手段,希望言論界少鼓吹迷信。最要緊的是,希望同胞不要久久執迷。
民間流行的戲曲歌仔戲,也是文化運動者批判的對象。他們認為歌仔戲的內容敗壞社會風氣,因為劇中歌詞多淫蕩、挑撥男女邪情;演員表情多猥褻、對白淫穢;男女演員素無文化、人格卑劣,甚至多不良分子,誘惑良家子弟墮入淫邪。為了使戲劇達到「寓教於樂」、「移風易俗」的目標,文化協會成員竟然自組劇團,播演「新劇」。1925年7月,南投草屯青年成立了赤峰演劇團;1926年11月,新竹地區文協人士成立了新光劇團;1927年又有星光劇團、民聲社等劇團成立。可惜,這些富有「文以載道」任務的文化劇,與大眾娛樂、民眾情感格格不入,未能引起共鳴。
日本時代知識分子所推動的文化運動,流露出菁英主義的傾向,無法接納文盲社會的庶民文化。這與今日廟會活動、民間戲曲已被視為台灣文化特色,情況已大不相同。
台灣文化運動追求三大解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婦女解放。1927年1月30日的《台灣民報》第142號所刊載〈台灣解放運動的考察〉這樣說:
數年來台灣解放運動發生的順序,是由民族的解放著手,而漸進入無產者解放,而後婦女的解放運動。⋯⋯台灣解放運動第一個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提高台灣文化的內容,就是台灣人民族解放的準備。要先充實人民程度、提高知識水準,才能要求與日本人同等的權利、平等的待遇。第二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就是正式的民族解放—自治的運動。
以後出現的無產青年,旗幟鮮明,是階級色彩明顯的階級運動。⋯⋯為農民解放的農民組合運動,事事為了擁護農民的階級利益⋯⋯工人階級的解放運動也已經興起。
婦女解放運動最後發生,諸羅婦女共進會、台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已經是不可看輕的女子解放先驅。 ──(改寫自〈台灣解放運動的考察〉)
早在1920年8月,彭華英就已經於《台灣青年》發表了〈台灣有婦女問題嗎〉一文,點出東洋社會,尤其是台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之必要。此後,《台灣民報》大量討論婦女議題,批評台灣社會的父權結構,買賣婚姻、嫺婢制度、續妾制度等等都是對女性的歧視與壓制。文化運動者如黃周、黃呈聰、王敏川等人,也公開主張「有責任感的自由戀愛」、提倡女子教育、培養謀生能力、經濟獨立,進而廢除娼妓、改善婚姻制度、改造社會、追求男女平等。
因為文化運動的啟蒙與倡議,台灣各地出現許多婦女團體,1925年起,彰化婦女共勵會、諸羅婦女協進會、宜蘭婦女讀書會、高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苗栗婦女讀書會、台南婦女青年會、台中婦女親睦會等在各地陸續成立,以改革社會陋習、追求婦女地位向上為目標。其中最活躍的是彰化婦女共勵會,會員約40多人,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召開例會,學習漢文、日文、羅馬台灣話文,安排進步女性演講,並組織體育會,號召女性注重體能訓練、鍛鍊強健體魄。諸羅婦女協進會成員有30多人,不定期舉辦演講,鼓吹女性覺醒。
儘管這些時代女性想要呼應時代、掙脫牢籠,試圖與男人一樣站上講台表達心聲,但是,當她們鼓起勇氣上台時,仍然要面對抱著看好戲心態的運動同志與喧譁笑鬧的男性聽眾,輕薄起鬨、品頭論足,實在讓人氣結。
即使如此,1920年代的婦女運動,終究出現了活躍新女性。張麗雲,號群峰,廈門集美女子師範學校畢業。1920年6月,她在《台灣民報》發表〈我所希望於台灣女界者〉,認為台灣男性為求解放而奮起,但台灣女性卻仍在酣甜睡夢中,因此提出9點期望,鼓勵台灣女性們打破舊習、向真理前進,可說是台灣女性解放的宣言。此後她積極在民報上發表言論,也應邀演講,推動婦運不遺餘力。1929年2月3日,張麗雲與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書記胡金碖結婚,在婚宴邀請函中聲明:「我們的結婚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被《台灣民報》推崇是「前所未有的聲明」、「新時代男女結婚的參考」。
1926年2月,葉綠雲以「玉鵑」為筆名,在《台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並簡介世界各國的婦運成果,引起矚目。葉綠雲是台北人,1908年生,因母親改嫁,改名謝玉葉。雖然家境清苦,卻堅持上學讀書,在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期間,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台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台北無產女青年。1925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籍。她輾轉到上海,獲得同是大稻埕黑色青年翁澤生的幫忙,進入上海大學,並在翁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她改名謝志堅,並以謝玉鵑為筆名,在《台灣民報》上密集撰文,筆調尖銳、頻頻與傳統文人打筆仗。1926年秋天,她與翁澤生結婚,但也與同為共產黨同志的潘欽信展開複雜的三角戀情。
蔡阿信據說是台灣女性在公開場合演講的第一人。她生於1899年,自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後,返台服務於赤十字醫院,是台灣第一位女醫生,1924年與彭華英結婚時,連官方報紙《台灣日日新報》都大幅報導。1925年,她到台中開設清信醫院,1928年又創辦產婆學校,為台灣社會培育超過500名以上的助產士。
蔡阿信不僅醫術受到肯定,也成為成功的職業婦女典範,1930年底,《台灣新民報》舉辦台灣五州七市議員模擬選舉,以1,444票獲得最高票支持。蔡阿信事業成功、社會聲望高,對她的夫婿彭華英造成極大壓力。彭華英雖是活躍的社會運動家、最早的婦女解放主張者,仍舊無法克服外在與心理的障礙,兩人的婚姻以離異收場。戰爭時期,彭華英進入中國華北發展,另娶一女伶再組家庭。阿信則在1938年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再前往加拿大,但她的日本籍身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遭到行動限制,直到1946年才返台。不久又目睹二二八事件,選擇逃離故鄉,一生坎坷,客死加拿大。
1920年代,隨著文化運動與知識啟蒙,台灣社會大眾被喚醒,從菁英的反抗擴散為工農階級運動。同時,受到來自日本國內與國際思潮的影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抬頭,反對陣營內部逐漸出現思想對立、路線衝突,台灣社會運動不知不覺中已走到轉型的十字路口。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