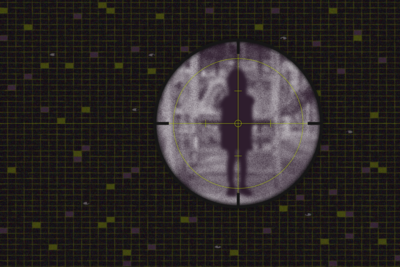台灣#MeToo運動至今滿兩年的此刻,相關議題已從大眾的關注中退潮。被害人回歸各自的生活,一度消聲匿跡的加害人,又是如何看待被指控的犯行?藝文界#MeToo事件中,最知名者當屬2023年攝影家謝春德被揭露20多年前長期性侵與猥褻未成年兒少,引發軒然大波,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隨即發表公開聲明暫停與其共同製作的演出。今年(2025)初,謝春德接受《典藏》雜誌團隊訪談, 對外公開表示,台北地方法院的一份裁定書已「還他清白」。
真相,隨著時間消散;責任,在法律規定的20年追訴時效結束後,毋須承擔。兩年前一字一句的證言,還剩下多少重量?《報導者》獨家專訪謝春德案被害人梁梓筠及其母莊月嬌,記錄這段日子以來她們的心路歷程,以及追尋公義的未竟事宜。
梁梓筠站在北投櫻花大廈12樓的頂樓,2000年初期就讀國中的她,第一次有了往下跳的念頭。
充滿細節的文字,描述出具體的空間、動作、對話,像是一台不帶感情的冰冷攝影機鏡頭,記錄下地獄般的景象。
「我那時候(被謝春德性侵)是飄起來的,感覺自己有點像是攀升的攝影機,從第一人稱視角切換到第三人稱視角,從上面往下,看著這一切。」
「北投。黃銘哲畫室和我在公園旁十樓書房相距500公尺。果然繼續夜酒,水美溫泉會館和新光員工訓練所中間狹窄的巷口,以後成為『食神』的阿嬌,蝦仁羹和炒米粉是如此美味⋯⋯」
阿嬌的長女梁梓筠,下有兩名妹妹,當時就讀國小的她就要承擔起長女的義務,在假日或放學時協助父母繁忙的生意,除了洗碗、備料,還要外送食物到熟客家。鄰居與顧客每每見到她靈動的大眼與天真的笑容,總會稱讚好像廣告裡可愛又漂亮的女孩,想要認作「乾女兒」。
父母忙於營生之餘,梁梓筠也受到街坊鄰居許多照顧,到鄰居家如同在自家般自在地畫畫、看書,在彼時人情緊密的溫泉小鎮猶如「同村共養」般受到大人寵愛,包括已是熟客的林文義。「第一次送食物去給林文義的時候,他的女性友人第一次見到我,就說我長得很漂亮,」梁梓筠回憶道。
目前移居台東池上,經營預約制餐廳的莊月嬌也提到,「她(梁梓筠)常常說,『媽,我要去找阿姨』,林文義不一定會在,但是他那位朋友都住那邊,我就會說,妳去啊。」
蟄居北投的作家及其友人,就此為這個勉力求取溫飽還債的平凡家庭,帶來命運的轉折,在藝文圈緊密交織的人際網絡中,也讓當時正處於創作能量高峰的謝春德打開一扇門,日日夜夜接近剛國小畢業的梁梓筠。

謝春德從1970年代起就活躍於攝影、藝術與廣告界,莊月嬌則出身礦工家庭,成年後經歷一連串婚姻、經濟等現實磨難,兩人來自截然不同社會背景,在2000年初期於北投偶然相遇,發覺彼此對飲食美學的品味、土地上的庶民氣息,皆有著超越常人的執著與熱愛,一拍即合之下,合作開啟數家創意台菜品牌。在還不時興無菜單料理的年代,就以充滿巧思的精緻套餐掀起極大的注目。
謝春德和阿嬌夫婦一家人成了好友之後,又認識了阿嬌夫婦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儼然走進浮沉台北藝文圈30年、從未曾細看過的另一個族群面向;阿嬌的單純、樸實、堅韌、牢牢著根於生活,相對於清談觀念理想、激辯雅俗高下的飛花殘絮,更讓他發現另一種動人的能量。 (謝春德說)「阿嬌看起來土土的,是道地台灣小姐,但很奇怪,她的作品竟那麼抒情,像散文詩。」 阿嬌跟「食方」餐廳的員工都稱謝春德「謝老師」,我問阿嬌為什麼,阿嬌很自然地回答:「因為他是老師啊!」 在阿嬌眼中,謝春德有過人的洞察力,又能一直保持絕對的信心和耐心對人不厭其煩、諄諄善誘。「他看出我自己所不知的我,對我的信心比我對自己的信心還強,這大大幫助我突破自我。另外,他脾氣好好,總是那麼溫和,這是我最佩服他的。」
然而,在事業高峰的底層,42歲的莊月嬌正經歷外人無從得知的心靈風暴:「我個性很強勢,當時與(一開始經營北投小吃攤的)第二任丈夫離婚,同時背負3間餐廳──阿嬌的店、食方、嬌食──的營運壓力,幾天沒辦法睡覺,以前不知道哭是什麼,我不能倒下來,因為我是家中的生活與精神支柱,我如果哭,(女兒)會覺得她們的天塌了。每天早上7點就開始關在房間,聽到小女兒去上課──匡的關門聲,我爬起來就哭。」
2010年,食方、嬌食相繼歇業。表面原因是經營者的財務糾紛,實際上,當大女兒梁梓筠透過謝春德人脈,到台北讀明星國中,學業卻一落千丈,經追問後,女兒首度吐露在謝春德工作室被性侵,餐飲事業剛起步的莊月嬌不敢馬上撕破臉,只能「一直在想辦法要怎麼去抽身」。
「他(謝春德)的政商關係太好了,我女兒小學畢業,他都有辦法把她的戶籍遷到樊曼儂、許博允家,讓她去讀仁愛國中,所以我知道要找時機,一定要把證據拿到手。我一拿到證據,就把食方馬上結束掉,搬去宜蘭,這中間的煎熬⋯⋯。」
在兩人合作的那些年裡,表象的風光底下,莊月嬌暗自思忖要如何取得那些不堪的「證據」──謝春德拍攝梁梓筠的裸照。
「他要我給他拍照,拍我的胸部,當我衣服脫掉的時候,他會一直摸我的乳頭,摸到起小疙瘩,他覺得這樣才很棒,拍拍拍拍之後他就會勃起,他會試圖想要我幫他打手槍,但是我不要,他把褲子解開,他一邊摸摸摸摸……手一邊在那邊(下體)弄弄弄弄……之後再拿相機拍拍拍拍拍……然後再摸摸摸摸摸弄弄弄弄弄弄,『妳看,很大、很硬,妳摸摸看、妳摸摸看』,我說不要。」
梁梓筠重述到台北市中心就讀仁愛國中後,寄住在謝春德工作室樓上房間時,被其性侵及猥褻的情形,那裡是她週一到週五放學後的居所──中山北路一段33巷食方餐廳正對面,週末才返回北投的家。
如同母親,她也過著月之暗面的矛盾人生。 在被猥褻拍攝性剝削影像的房間樓下,白天的工作室如同藝文沙龍,年輕藝術家、音樂家、經紀人環繞,談論高遠的藝術哲思。梁梓筠放學後謝春德會帶她去看表演、看電影、參加藝文活動,「許多知名藝文人士的小孩都常常來謝春德工作室混在一起,那群大哥哥、姊姊們真的在各方面形塑我。因為我以前在家裡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沒有想那麼多,只知道身為大姊、女兒、學生,該做的事情就都要去做,但沒有去想過生而為人,我可以有什麼選擇?」

經過20多年的漫長歲月,梁梓筠對於母親第一時間「妳是不是在說謊」的回應,已經釋懷,「任何人都一樣,接受這個訊息需要很多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不想要場面尷尬、也不想一片空白,一定會先問,是真的嗎、還是開玩笑的?我那個時候不懂,會覺得說謊要有個好處,說這個謊沒什麼好處欸!」
談起2023年中女兒公開此事後的衝擊,莊月嬌大笑三聲後,形容是「地獄」,「大概吃了半年的鎮定劑」,母女之間種種不足為外人道的誤解、悔恨、情緒張力,那是她20年前獨自扛下3家店的經營壓力之後,此生第二次哭出來。
「現在時代不一樣,我們真的要感謝#MeToo,她講出來之後,(網友)攻擊我、說我是共犯,什麼都沒關係,活到這個年紀,現在已經練就金剛不壞之身。我並沒有想要怎麼樣,但是應該還我的,你就應該要還我一個公正!」
從囿於傳統封建觀念而噤聲,在文化霸權下低頭隱忍,到無畏人言,訴求遲來的責任與真相,這位母親20年來的心境變化,彷彿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對於兒少性侵害態度的轉變,終於緩緩打開黑箱裡的禁忌,照進一絲微光。

「我跟當事人(梁梓筠)說,追訴權時效會像一座山一樣,把我們擋住,」律師邱顯智表示。他於2024年初卸任立委後,與過去一同打關廠工人、洪仲丘、太陽花等人權司法案件的戰友劉繼蔚,開始協助謝春德性侵案,「另一座大山是證據,因為性犯罪通常只有加害人跟被害人,很難取得堅實的證據,但不代表不能驗證真實性,包括當時聽聞的人、當事人的身心反應,都可以從調查中釐清。她所述細節與前後脈絡都經得起檢驗,我相信她!」
事實上,長期關注校園性侵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早在2019年協助處理台南狼師張博勝案橫跨兩校十多位受害人,即意識到很多都有時效問題,倡議立法院修法「刑法關於對兒童性侵害之犯罪行為,應增訂追訴期之例外規定,自被害人成年時起算,並訂溯及既往之條款。」
從2022年開始,立法委員開始提出性侵害案件追訴期的修法問題:該年8月,范雲提出台中某國中老師權勢性侵案(黃紀生案),應將未成年性侵被害人追訴期自成年起算,並對權勢性交未滿14歲者加重其刑;2023年7月,時代力量黨團呼籲除性平三法修法,應修正《刑法》延長兒少性侵追訴時效;2022年9月、2024年3月,國民黨則分別有林奕華、洪孟楷提案有關追訴期停止計算的《刑法》第83條修正草案,考量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恐未能辨識自己遭受侵害,或是不知如何行使權利,亦或是迫於與加害人巨大的權力不對等,導致當下難以求助之情形」,因此對未成年人犯相關性侵害案件,追訴期應自被害人成年後才開始計算。林奕華版草案甚至參照德國《刑法》78b規定,兒少性犯罪追訴期從被害人滿30歲才開始計算。
2025年以來,則有包括新竹縣警官吳文進被指控長年性侵家族女性,因超過追訴期而繼續任職警界。被害人在制度中求助無門的相似境遇,凸顯對於幼年受性侵害者的「結構不正義(structural injustice)」──超過時效,事實的真相便不必深究,加害者也無需承擔任何罪責,也因此近年來無論所屬政黨,立法者罕見地對單一議題展現共識,認為現行法律亟待修正。
「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解,其實是因為時效消滅,案件根本沒有開啟,而不是真的司法已經還他清白了,但是他(謝春德)就會去詮釋說,是我的當事人亂講,司法形同為加害人背書,真的啞巴吃黃蓮,」邱顯智說。
在協助梁梓筠走上司法過程中,律師團一再向檢方與法院強調,應該至少要開啟調查,例如江國慶案縱使超過追訴期,檢方還是可以經過周密的實體調查做出129頁的不起訴處分,確認事實曾經發生,是因為時效限制所以(冤案發生時任國防部長)陳肇敏不起訴,「對當事人來講,這個公道很重要,當年的一個小女生成年之後長出力氣、勇敢說出來,應該要得到社會支援、得到國家的支援。」
「在《性騷擾防治法》第14條第2項,就有考量未成年人難以尋求司法的協助,規定被害人可以在成年後3年內提出申訴;除此之外,像《民法》有關拋棄繼承的規定,實務見解也認為在小孩成年之後可以自己決定,」邱顯智解釋,《刑法》卻沒有考量兒少性犯罪被害人難說出口、往往需要許多年才能對外求助的特殊性,與其他犯罪「齊頭式平等」的追訴權時效規定,使許多早年遭受性侵害、如今已成年者陷入結構性困境。
在現存法律制度窮盡一切而找不到出路時,邱顯智巧合地發現處境相似的被害人──2006年修法前的未成年性犯罪只有20年追訴期,提出的釋憲案已被憲法法庭受理,經過當事人(梁梓筠)的同意,他和劉繼蔚以及實習律師黃守鵬,毅然加入兒少性侵追訴期釋憲案行列,於2025年7月2日寄出釋憲聲請書至憲法法庭,請求就同⼀標的「112年度憲民字第384號」案件併案審理,正式以謝春德性侵案挑戰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主張《刑法》第80條有關追訴權時效的規定違憲,並建議大法官「促使⽴法機關考慮延長追訴權,或將追訴權之起算點設於受害者成年後」。

在揭露謝春德犯行的這段時間,梁梓筠已與前夫離婚,目前獨立帶著女兒在池上生活,三代女性於兩座山脈中照應著彼此。
8歲的女兒,將母親經歷的現實磨難看在眼裡,童稚的眼光中,是孩子對父母本能的崇拜:「受傷害會變強嗎?會變得很好嗎?我也想要跟妳一樣。」
梁梓筠如此跟女兒解釋:「小時候我有一個乾爸爸,我國中的時候去住這個乾爸爸家,住在他家的時候被他性侵。」女兒問她,性侵是什麼意思?「我說性侵就是他把生殖器放進我的性器官裡面,沒有經過我的同意發生了性關係,他侵害了我在性這件事情上面的權利──還有很多妳自己的權利需要保護,包括智慧、身體、自由,我就是不要妳像我一樣受傷害。我免費幫妳交學費,這堂課不用再上了。」
截稿前《報導者》聯繫上謝春德,詢問對於被害人的指控是否有需要澄清與說明。他表示不想多談,不希望對方受到二度傷害,重點是台北地檢署已經不起訴,對方律師繼續提告到高檢署,被駁回後再提到地方法院,被駁回又不可抗告,「所以也不是只有時間的問題,包括所有的證據,我的證據都有拿給律師,律師都有拿給檢察官跟法官。」
謝春德強調,他在「一個很大的冤情裡面」,其實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法律有其公正性,但外界卻一再質疑。「每一個人心裡都有一把尺,但是那個尺在哪裡,我再怎麼講,每一個人都用他自己的尺來丈量,那我就不想再提了,因為會水落石出,這個事情,法律的程序已經走完了,司法也給我公正了。」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