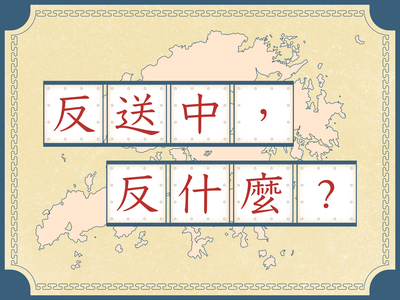這是個正在被傾倒的城邦,一國兩制被破壞,催淚彈與各種監控的恐佈壟罩此城。城裡的他/她們本來都有很好的人生,但過往生活被政治介入和打亂後,他/她們選擇告別原有人生的軌跡。
無論是商業大狀(香港對「大律師」的俗稱)轉進為年輕人辯護,或大學教授轉進入中學生罷課現場的流動學堂對話;又或是攝影菜鳥拿起DV進入示威第一線帶回前線訊息⋯⋯跨世代香港人無法抉擇橫在眼前的命運,當中不少人把自己丟進一個更大地、超越個人富貴幸福的意義裡,建構香港的公民意識,為此城香港繼續搏鬥。

見到Lawrence Lau──劉偉聰的第一面,是在香港東區裁判法院,我們坐在媒體區聆聽他為一名31歲,在家中被蒐出防毒面罩跟眼罩,曾參與8月13日機場示威的社區工作者辯護。「這些器具是中性的,可以用來防身,和平的人會用,暴力的人也會用,不能因為被起訴人買這些東西就指控他;暴動罪罪名嚴重,他沒案底,大學畢業,奉公守法,社區服務多年,職業良好⋯⋯」一襲西裝,道地英式英文,帶著自信和幾分貴族氣息,Lawrence在多次與控方律師交手後,庭上的法官允許了當事人被擔保。
港大畢業、留學英國,擔任律師近25年,總愛伏案讀書的劉偉聰大概沒想過,會在50歲的中年,站出來為一群被國家力量不成正比檢控的年輕示威者站上法庭,青年們被拘留48小時後,義務律師們在短時間內研讀個案、為其奔走。大狀的人生還在轉,劉偉聰要出來競選11月香港的區議員,選區是中產階級聚集的九龍塘又一村;從不喜歡政治到出來參與政治,他說,反送中運動把民主這個事情「打」了出來,他們必須為良知站起來,因為「只有法治沒有民主,社會是沒有辦法穩定的。 」
(以下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呈現。)
1997年回歸時我30歲,那時幾乎心碎了,香港很擔心回歸後的香港無法保有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文化與法治。97之後,原本英文比中文(普通話)使用率多的香港法律界,開始改變,因為香港跟中國的互動增加,中國相關的官司變多,中文也一天比一天重要。
2000年初期,我曾代表一個有強烈官股色彩的中資企業打官司,他們對於法律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概念。這間公司因為調動一位懷孕的員工到深圳,很明顯地調動職位。但根據香港法律,若員工懷孕,你不能無理由地隨意調動她的職位或工作地點,這是為了保護她的權益。
這間公司除了明顯地任意調動她的位置之外,也向香港稅務局寄出他們解僱該名員工的文件,於是,這位女士向香港法院提出告訴,指控公司無理解僱。這個大公司來找我,要我幫他們辯護,但在這個案子上,明顯的解僱文件與證據讓這間公司不會打贏官司。但公司裡的資深管理階層很直接的跟我說:「通常我們寫給官方的文件都是虛應故事,不是認真的。」他們並不清楚自己寄出的文件是有公信力,是代表公司,結果他們執意上訴, 或許在中國他們可以任意扭曲法律,他們想要開除你就開除你,甚至不會給你應有的資遣費,但在香港不是。
這些年,我對香港是採取一種respectable detachment(敬而遠之)態度。因為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社會與法律等系統對我們來說,是完全外來的,我們應該跟他們保持距離。我不一定接大僱主的案子,反而,97後我常常代表那些來香港打黑工或是從事性工作的大陸人打官司。我比較傾向幫受檢控者打官司,不喜歡代表控方,因為我一直不信任政府的起訴權,我覺得有的時候他們會用國家力量壓迫無辜的人。
雖然我無法說回歸這22年來,國家力量壓迫無辜的人的情況有沒有增加的趨勢,但是在這個夏天看起來,很明顯是有的。這個暑假,政府變得相當暴力,他們用很多的方法,包括法律來限制人民的自由。
香港有《公安條例》,第18條和第19條定義了「非法集結」和「暴動」,但這個法令的門檻很低,法條解釋空間變得太大,被視為人權落後的法條,但以前的政府不會用輕易的使用這些條例,不會趕盡殺絕,比較包容。而林鄭政府「嚴正執法」的態度,讓很多年輕人輕易地變成了犯人。

今天早上在裁判庭裡,控方指控這位年輕人因為在亞馬遜(Amazon)網站上買了豬嘴(防毒面具)跟眼罩等東西,就說這些是暴力示威者使用的東西,證明他是暴力示威人士。但我跟法官解釋,這些東西暴力示威者會用,但和平示威者也會為了保護自己而使用,所以這些器具是中性的,並不能因為被起訴人買這些東西就指控他是暴力示威者。
控方現在做的就是把這些證據轉向有利自己的一方,企圖引導法官相信被起訴人就是暴徒。這就是一開始就把這些年輕人都以有罪的方式來看待。
其實我開始接受這些年輕人被控的案件,原因有兩個,第一點,大律師公會有一條規是說,如果你有時間、有能力還有這個案子的價錢合理,你必須接下辯護。第二,就是因為這是正確的事。雖然我可能會失去一些承接其他案子的機會,但我不在意。
這幾年來我開始覺得自己有點用處,不再單單只是要賺錢,我以前沒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幫社會,現在透過幫助年輕人,覺得自己有用了。
香港逐漸不一樣了。其實是很可悲的,政府透過法律機器來針對這些年輕人。很多年輕人仍天真的相信法律是公義的,但是他們可能不瞭解,法律不能單獨來看。單單司法獨立是不能實現真的公義的,只有法治沒有民主是沒有辦法穩定的,這幾個東西是互相依賴的。反送中運動把這個事情「打」了出來,法律是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民主議會、民主政府跟法治社會是互相扶持的。
目前的區議員多半是支持政府以及北京的,大多是保皇派和親建制派,不論是民建聯(香港建制派最大政黨)或是自由黨,都是很傾向自己的利益;其實五月分《逃犯條例》有小幅度修改,原本以香港商界人士組成的自由黨是反對修例,但當政府修改讓智慧財產權、勞工等跟商業有關的9項犯罪不會被引渡時,自由黨放棄了大眾的利益,轉向支持政府。
若香港變成向深圳那樣,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我被迫變成中國內部的維權律師那種狀態,隨時會被消失三、五年時,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勇氣再站出來;但我同意勇氣是會被鍛鍊出來的。這些年是這樣的。
我對香港的未來是悲觀的。在大時代的洪流中,香港的未來可能正在消亡,你問我這是不是垂死的掙扎?我想我會說,我不是在垂死掙扎,我是站起來體面地迎擊(decent fight)。

59歲的許寶強眼神炯炯,隨著處於戰鬥狀態,採訪這天,香港中學生與大學生已開始全港串連罷課活動,學生們用自己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這不是許寶強第一次見識到學生罷課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當學生罷課,時任嶺南大學教授的他只好把教室搬到運動現場,沒想到「現場一百多位學生都真的好想要懂,他們的眼睛都在跟你的對話。」
在那之後他就明白,是教育把學生跟時代隔開了,把社會脈絡與歷史脈絡隔開了。學生只有體感過才知道自己要什麼,是社會真實的情境才能叫學生主動思考。這個衝擊了在大學教了25年書的他,許寶強之後離開大學,他在灣仔「富德樓」的文化空間裡,開了「流動共學教室」,與教師或社工等職業的成人一起共學,再由這些成人學生將共學的概念傳播出去。這次反修例的「罷課不罷學」裡,他又風塵僕僕,一只揹包進到罷課現場,教起這群有無數疑問但眼睛發亮的中學生們,實踐他自己說過的「教育就是社會運動」這句話。
(以下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呈現。)
我2017年離開嶺南大學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全球教育環境的變化,讓大學內的管理主義愈來愈重,除了讓教育的空間變窄,學生可以主動學習的彈性少,愈來愈壓抑,大學只是一個在乎世界排名遊戲規則的地方。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在雨傘運動裡的經驗,加速我離開的想法。最近中學生罷課的活動從2014年那時就開始,只是當時規模較小。我們在學生佔領的金鐘辦了連續四、五天的「流動民主教室」,我現在在做的「流動共學」的概念也是當時那樣發展過來的。流動民主教室裡有義工有老師有學生,大家一起討論、互動,那是我連續教學25年來經驗最好的幾天。
當時我的感觸很深,會反思自己在大學上課的時候學生為何無法吸收,聽課都不專心,是不是有什麼隔閡?要學生看我們以前看過的,我們覺得受到很大啟發的精典著作,想把好東西教給他們,但後來發現,只能從20幾頁的英文材料一直砍頁數,後來連兩、三頁對他們來說也太重了。
依賴過往經驗的我們,不懂得怎麼教好變化中的本科生(大學生)。
但是傘運時,我在添馬廣場上教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思想,討論權力跟暴力間的關係,其實跟我們在課堂上講解的方式一樣。但現場一百多位學生都真的好想要懂,他們的眼睛都在跟你的對話。在那之後我就明白了,現在的中學、大學,把學生跟時代隔開了,把社會脈絡與歷史脈絡隔開了。但是正在經歷運動洗禮的學生身在其中,他們會想要了解現在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次的運動裡,有學生到機場示威或是在哪裡被警察困住,或是因為地鐵站暫停營運沒有交通工具搭乘,回不了家,最後家長開車去接他們。這個其實是家長去接小孩子放學回家的感覺,因為學生跑到街上認識真正社會的面貌,他們正在學習。家長或社會也許不是這樣想的,但是這是一個各方要重新被理解的過程。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因為現在的政府跟社會太久沒有思考跟學習,現在已經拒絕接受不同立場的意見,所以問題沒解決、又累積了新的問題。
現在學生發動「罷課不罷學」,其實我認為社會看到的重點應該是在「不罷學」,而不是「罷課」。學生在廣場,在街頭上碰見真正的問題之後,我們(教師)要做促進他們學習的中介者,不要再把自己當做提供知識的維基百科。這對我們反而是好的機會,把阻礙他們學習的牆打開,高牆外的學習會很不一樣。
最近我進到中學校跟學生討論到漢娜鄂蘭對暴力(violence)跟權力(power)概念的分別。當有人以武器施加暴力,要你屈服,就像是現在香港警察違法使用武力令人害怕,這種武力有沒有合理性?有的警察會說因為示威者使用暴力,所以警察要使用更強的暴力,試圖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但一個政府的權力來源是要用武力支持,還是必須努力用民心所向的合理性來治理,這是要去思考的。當我們先不去講誰對誰錯,而是試著這樣談,學生便能反思現在社會的狀況。

又或是跟學生談,為什麼大家覺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問學生:政府已撤回《逃犯條例》,不再推了,是否還是缺一不可?他們回答說,因為政府可能會翻臉不認帳,用各種理由重啟《逃犯條例》的修法。
又或是要釋放被捕示威者這一訴求,他們跟我說大部份示威者都沒有犯法,所以應該被釋放。但是我反問:你們說是大部份的人沒犯法,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沒犯法,那我們對於觸犯法律的人怎麼想?在這樣的難題下,我們就接續討論,其實律政司可以用這次運動具有「公眾重大利益的理由」,先不對示威者提控訴,等到獨立調查報告出來,律政司再判斷。
但幾年前你跟學生談這些沒有人理你,但現在他們學習很快。因為整個時代都在逼學生來思考這些問題。
當學生帶著各種問題與好奇來到你的面前,你在回應他們之前,應該要先讀懂他的問題。就像是一個好的木工,要開始製作傢俱之前必須要判斷這塊木頭的木質適合什麼樣的工法。教學也一樣,你要先認真聆聽他的問題。如果你先用成見擋住了,認為他在找你麻煩,那這個學習的機會就完蛋了。
現在這場罷課的運動跟5年前也不一樣,這次不像2014年幾個單位一起,所有大學中學集中在添馬公園四、五天,NGO講者在那裡集體講課、交流。這次不一樣,每間罷課的中學或各別大學,會互相到對方學校裡面演講。如果依照政府說法,我們辦罷課不罷學,每家學校都有外國勢力進去。這很麻煩,也根本不可能,所以對我來說是莫名其妙的。
人的主體性是最重要的,但不論是外國勢力控制或是指控大家是港獨,都是抹消了香港人的主體性。
香港其實有一種市井文化,它包含了義氣、樸素與平民等元素,這些不是今天才有的。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實用主義或是說情感都是一直存在的。像是周星馳電影《功夫》裡的豬籠城寨,其實就像是我在旺角長大的社區一樣。平時大家都有自私一面,但只要有問題的時候,大家都會站出來。只是在運動這個被提升出來,讓民眾把情緒轉進到公共政治裡。

《用自己方式的時代》、《手足》還有《Trial and Error》三部長度6分鐘到10分鐘的影片,是由33歲的導演廖潔雯在這3個月時間裡,從一開始只有簡易的口罩、在示威現場撿到的簡陋頭盔裝備開始,與夥伴一起冒著抗爭前線的槍林彈雨所記錄下來的反送中運動紀實。因為拍攝題材與角度的獨特,台灣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也在8月特別播出這三支片子,讓台灣民眾可以更瞭解這次運動的面貌。
「我想傳達出最真實的訊息,讓人們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什麼拍片計劃、群募方案、更沒有生涯規劃,2014年時,28歲的廖潔雯就一路被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大小社會運動牽引著,當人們被捲入漩渦裡,她選擇拍出那場漩渦,看清漩渦的模樣。於是,她離開了原本傳媒公司幕後工作,走出攝影棚、離開安全安靜的辦公室,在前線吸入大量的催淚瓦斯,時常上吐下瀉。她說自己要用攝影機保護那些年輕人,把現場傳遞出去。
(以下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呈現。)
2014年以前,我一直留意社會運動的發展,但最多就是去遊行,不會去參與運動或是做些什麼。我之前的工作都是在報社跟電視台的幕後,做的都不是做記者跑到現場的工作。
我在電視台的時候學了一點拍攝的技巧,所以2014年在雨傘運動的時候,關心金鐘現場的情勢發展,在黃之鋒跟示威者衝入公民廣場的那一天,我拿了家裡的小型數位相機就跟朋友到現場去拍。我認為那是香港很重要的時刻,應該要被記錄下來。在那之後,我離開了電視台的工作,跟朋友借了比較好的攝影裝備,就從傘運開始拍攝社運的紀錄片。
我自己拍攝的方式是近距離方式,跟著現場運動的狀況走,讓不在場的觀眾有置身現場的感覺。像是第一支《用自己方式的時代》裡,不同示威者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傳達反修例的訊息,我就在旁邊拍他們在做的事,有的人會用A4紙印出傳單派(分發)給大陸人傳達香港人反對逃犯條例還有五大訴求,有人用普通話解釋給遊客聽香港警察如何濫權,還有一些人會唱中國國歌來吸引大陸人注意。
還有一個最有趣的,他們會用手機的AirDrop傳送訊息給隨機的人,讓訊息可以透過他們自創的方式,傳達出去。這跟這場無大台的運動很像,大家利用自己的方式、不同的創意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和理非用和平的方式示威,勇武派用衝撞的方式,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第二支影片《手足》就是記錄勇武派的抗爭細節,我們幾乎是把自己融入示威者之中,他們蹲下我們就蹲下、他們走我們就走。因為我們靠得很近,所以可以看得到他們之間的互動,除了肩並肩互相照顧,也有看到他們吵架,口罩後頭的他們大聲說出想法,彼此互相溝通。就像一般的朋友、手足一樣,會有爭執也會互相幫助。
有幾次我們都還可以看到橡膠子彈打到旁邊,所以我很多時間都在比較後方,不敢走太前。
那次在拍的時候,就連我們也被他們示威者照顧。在最初期時我們戴著N95口罩,沒有辦法防催淚瓦斯,那些示威者還會叫我們快走。但其實裡面有不少年紀比我還小的女生,她們比我們還勇敢,都站得比我還前。
在拍《Trial and Error》的時候我們本來只是想拍佔領機場的活動,但後來在機場巴士站的時候發現氣氛很緊張。因為一直有謠言說警察會開始武力清場,大家都很害怕。我就開始把兵荒馬亂的狀況拍下來,也跟著他們的決定移動,有的人要搭巴士離開,有的人要用走的,也有人決定要留下來跟警察拼。那時我跟示威者一起從機場走到靠近機場的港鐵站東涌。
5年前我們播放雨傘運動的紀錄片時,傘運已經結束,大家看了紀錄片才發現原來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幫助學生,讓他們很感動。但是因為反送中運動變化的速度太快,還有網路上有好多謠言,讓大家不知道什麼是真是假,所以現在我出去拍了之後,故事畫面夠的話,我會儘快剪出來。
會有這樣想法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個故事,是說有一位前線示威的女孩買麵包的時候錢不夠,然後陌生人給她錢買。這個故事被很多人知道之後,大家就開始捐錢開始買食物兌換券,好像募集了有十幾萬。但是我覺得大家搞錯方向了,前面的人需要的是人的支持、不是物資。
買那些食物券讓我感覺他們只是在買「贖罪券」一樣,想要消除自己讓這些年輕人在街上被警察暴力對待的罪惡感。所以我就趕快把拍好的素材剪出來,把訊息放出去。
像《手足》那支影片我有兩層意涵,第一層的我想要傳達的訊息是讓觀眾知道他們其實很需要支持,他們不是無敵的戰士,面對全副武裝的警察還有警棍跟槍彈,他們是相當脆弱的。第二層就是希望讓香港人自己反思,他們到底應該是買物資給他們還應該要表達更多實際的支持。看到這支影片的香港人無論在社會的什麼位置上,都可以幫助這些冒著巨大風險為了香港的前途在前線衝撞,但年紀只有14、15歲的年輕人。
但有時候我也會感到到灰心,很多朋友會傳網路上未經證實的訊息給我,像是約好要出去拍的那天已有謠傳說醫院準備要接受大量傷者,警察要開始大抓捕。或是網路上有人說有南亞裔的人混入示威者準備搗亂,要無差別攻擊等等的。因為這些謠言大家就不敢出去支持前面的人,不敢出去拍,我覺得很不好。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樣,我知道我更應該到現場,除了快速的讓社會知道正確的訊息之外,攝影機也可以保護示威者。運動需要民間每一個人的力量,就算是你只有一台DV,你也可以在現場拍,因為攝影機可以保護那些年輕人。我們要監督警察,不能讓他們亂來。
明年我希望可以進到新聞媒體裡當正職的記者,用另外一種方式記錄跟傳遞訊息。但是我自己紀錄片的工作也會一直進行下去,尤其是在這個運動沒有結束之前,我不會停止的。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