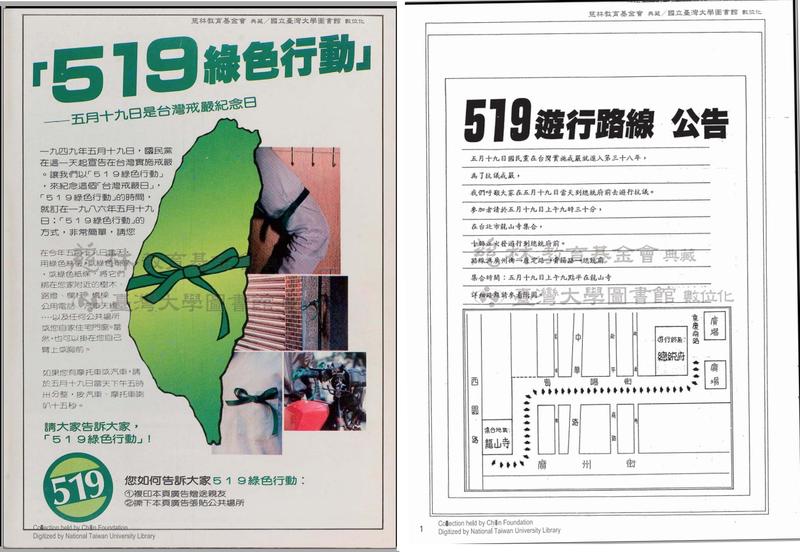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業為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的翁稷安,同時也是大眾文化的愛好與研究者,他在《我的世紀末:九〇年代混音帶》一書中,以自己的個人青春記憶為經、政治與文化變遷為緯,仿錄音帶形式分成A、B兩面,收錄1980年代末至千禧年前,形塑台灣社會與作者生命的關鍵碎片。
翁稷安將解嚴前後台灣社會所釋放的巨大能量,比喻為神話中「伊卡洛斯(Icarus)的啟程」。當時瀰漫著進步是理所當然的氛圍,人們渴望飛得更高更遠,卻忘了翅膀的脆弱,最終迎來無數理想的崩解。唯有回探那些轉錯彎的地方,正視伊卡洛斯墜落的教訓,才能在下一次升空時,順利抵達。
本文摘自聚焦當時公領域之喧囂與失序的「A面」部分章節,由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和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談起解嚴前後台灣政治,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最關鍵的現象,莫過於在威權行將崩潰之際,人們一次又一次在街頭聚集,表達對體制的不滿,並與公權力發生或大或小的衝突,當時媒體常用「示威遊行」、「自力救濟」、「上街頭」等詞彙來描述這些抗爭。台灣民主運動是百年以來不曾間斷的追求,80年代末的社會運動,可以視為70年代美麗島事件遭到壓制後的延續,然而,在這份連續性之外,80年代的街頭運動仍有其獨特的屬性:它往往從與民眾切身相關的環境保護議題出發,進而激發更廣泛的民主訴求。此起彼落的示威遊行,在台灣大小城市和鄉鎮的街區展演與動員,將不滿轉化為抵抗,讓抽象的理念逐步凝固成具體的信念。在世紀末的台灣,人們樂觀地相信,這些逐漸穩固的理想,將成為日後不可撼動的民主基石。
當年還只是小學生的我,雖說勉強可算是時代的親歷者,但始終未曾察覺到自己正處於歷史的轉折。30多年過去,腦海中關於80年代末台灣街頭運動的記憶,除了一些新聞片段(且多半是充滿暴力渲染的畫面),更多的印象則是與父親緊密相連。
在激盪的時代裡,父親和母親都是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父親出生在嘉義的農村,中學時就離家到台南念書,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直接前往台北找工作,從此在「異鄉」安身立命。近幾年阿公阿媽相繼去世,台北更已成為爸爸的「故鄉」,鮮少回嘉義。母親是外省第二代,祖籍安徽合肥,一個她一生從未踏足的地方,實際上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她念大學夜間部時,白天在泰灣出版社半工半讀,在那裡認識了父親。
生長在一個本省和外省結合的家庭裡,父母截然不同的背景,使我深切體會到台灣民主引以為傲的「寧靜革命」,從不曾真正寧靜。父母之間或激烈的爭吵,或沉默的冷戰,政治的喧囂吵雜,一直是家中恆常的聲響。
對於政治,從年輕到現在,父親充滿熱情,心態上近乎狂熱,但還不至於影響到日常生活。我不知道若以「世代」的視角出發,父親是否具有代表性(又或者究竟誰有資格代表整個世代)?但每當我看到台灣解嚴前後街頭運動的新聞畫面或影像,那些跟在領導者身後,從未被鏡頭好好對焦,更不曾被報導,歷史敘述只會輕輕一筆帶過的支持群眾時,我就會想起父親。
我出生的隔年,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有記憶以來,父親就是黨外運動堅定的支持者,家裡總有幾本用牛皮紙包起封面的禁書,不時會出現看完得特地藏好的黨外雜誌。雖然父母小心翼翼做好各種防護,但也不知是疏忽或默許,我偶爾還是有機會可以偷偷翻開這些神祕的出版物。以我有限的閱讀能力,看看圖片,猜猜標題,胡亂拼湊出那個朦朧模糊的世界。父母並未嚴格禁止,也沒有責備,唯一一次例外,是某次我不知看到報紙標題還是雜誌封面上,斗大的「二二八」三字,我不解其意,從前後文推斷這三個數字指的似乎是日期?沒想太多,隨口問父親這三字的意義。父親臉色一沉,沒有解釋,只是口氣嚴肅地叮嚀:「千萬不要去學校亂說。」這是我第一次具體感受到「禁忌」的存在與壓力。
父親其實多慮了,這些書籍或雜誌,毋須明說,就算小孩也能感受到附著其上的沉重,知道那是不能向外人透露的祕密。更何況裡面出現的人事物,每一個都是新聞裡嚴加抨擊的萬惡之首,「必然會為國家帶來危難,為社會製造禍亂」。 生性怯弱的我,自然沒有向任何人提及的勇氣。這些禁書禁刊就像是「不存在的存在」:在暗處流通,供人閱讀,傳遞著觀念,成為沉默大眾理解台灣政治的養分,卻無法保證大眾能打破沉默。
事後回想,母親會允許家裡出現這些禁書禁刊,或許也正是將之視為「不存在的存在」──將政治和生活切割,只要父親的投入不會影響日常的平靜,那就睜一隻閉一隻眼,視而不見。
然而,在社會力量逐漸壯大,威權體制的控制力面臨挑戰的80年代末期,公領域的對峙,正一點一滴滲入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召喚著人們的關注與投入。此後,私領域無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任何人都無法再躲在歲月靜好的溫室裡,假裝外界的紛擾「不存在」,和自己無關。
在不影響白天工作和下班後家庭責任的前提下,父親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去參加街頭的抗議活動,我沒有和父親一起上街的經驗,不太確定他在街頭的模樣,猜想以他有些人來瘋的性格,即使不衝到隊伍的最前線,應該也不會只甘於遠遠旁觀。正因為媽媽和我都瞭解父親的個性,哪怕他再三強調只是跟著人群看看熱鬧,會注意安全,但隨著台北街頭抗爭的熱度不斷升高,我們還是愈來愈不安。
媒體對遊行的報導又總是一面倒地負面,將示威群眾描繪成「暴民」,整座城市也因此被形容為隨時可能爆發游擊戰的戰場。媽媽很難再假裝無所謂,從起初淡淡的抱怨,逐漸演變成與父親激烈的爭吵。這些爭吵包裹著母親的恐懼,擔心在現場氣氛的鼓動下,父親會不會一不小心變成執法機關眼中的「暴民」?畢竟任誰心中都沒有把握,公權力會不會突然發狂,將人民當成敵人,變身為殘暴的屠夫。
「寧靜革命」是史家後見之明的歸納,在威權體制依舊頑強的年代裡,與之對抗,就是革命,或至少是帶有革命意味的行為。「寧靜」與否,則是沒有人能說得準的運氣。1987年的解嚴當然是重要的宣示和象徵,但那條自由與人權的底線是否真的被劃下,仍屬未知,沒人能臆測或信任所謂黨國高層的盤算,更無法確保走上街頭是否能安全返家。
父親參加的街頭示威中,引發家中最激烈爭吵的,是1988年的520農民請願運動。他出發前應該想不到這場遊行會演變成如此激烈的對抗。遊行的訴求無涉敏感的政治議題,單純是農民上街表達對於政府計劃大規模開放美國農產品的不滿,在解嚴後的自由氣氛下,感覺就只是一次單純的人民表態。沒想到,長期處於重工商、輕農業的劣勢下,一向無聲、順從的農民,壓抑的憤怒竟在這天一夕爆發。從台北車站出發至中正紀念堂,不算長的一段路,沿途多次上演警民衝突,立法院、警政署和城中分局三地成為風暴的中心。
遊行隊伍於中午集結,下午2點多抵達立法院中山南路的大門口,群眾要求「到立法院內小便」,未獲警方同意,立即引爆第一波劇烈衝突,現場罐頭、石頭、磚塊齊飛,不只民眾投擲,警方也不甘示弱拾起石頭、磚塊擲回,並逮捕民眾。沒想到逮捕的行徑激起現場群眾更大的憤怒,包圍警政署和城中分局,要求警方放人,場面數次混亂,警民多人受傷,一整天下來送往台大、馬偕和仁愛醫院急診治療者超過100人。民眾包圍分局,和警方一路對峙到次日凌晨,才在憲兵隊以大規模人力壓制下遭到驅離。
面對這麼激烈的暴動,主流媒體自然持批判立場,認為有不肖分子混入其中,操弄單純的農民。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尤其是學界。不少大學教授在受訪時都指出台灣農業的困境,指責警方的執法過當和報復行為。更有學生自發來到現場,試圖調停,卻同樣遭逮捕。 這場農運,意外地為日後的學運埋下了種子。
學農業出身的李登輝總統在當天聽聞農民上街抗議,就表示「心情很不好」。事件發生後,他於隔日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與會官員皆主張嚴辦,甚至有首長認為茲事體大,為防止類似狀況再度發生,日後若判斷情勢相同,「似應考慮局部實施戒嚴」。記者在報導時刻意隱去該首長的身分,僅強調「此一主張未為李總統所接受」。
520那天,父親傍晚下班後,先送母親與我回家,就直接趕去現場,沒有在家吃飯。即使當時消息傳遞不如今日迅捷,但街頭接連多起衝突,新聞也有報導,爸爸絕對知道現場不可能平靜,冒然前去聲援,多少有點風險。那天直到我入睡前,父親都沒有返家,屋內瀰漫著母親的焦慮和不安。隔天清晨,他才終於回到家。我當然是早上醒來後才知道的。父母之間應該已有過一番爭吵,當下我所面對的,是父親疲倦的神情,以及家中因父母冷戰而來的沉重氣壓。
可惜的是,數十年的時光沖刷之後,一家三人的記憶都已模糊。父親早已忘記當時堅持前去的理由,母親也記不得那晚的心情。後者可能比較好猜想,那是以埋怨和憤怒包裝的不安和擔心,畢竟彼時只有室內電話,人與人之間無法即時聯絡,電視台也不像今日24小時播放,時段一過就變成彩色條紋訊號。走上街頭,就等於與日常世界割裂,像被丟進常人無法觸及的競技場,只剩下周圍由陌生人組成的群眾,以及從對面牢籠裡放出的威權巨獸。也許從結果來看,80年代走上街頭抗議的人們,多數如父親一般全身而退,但這絕非必然,而是僥倖。
即使知道現場開始暴動仍要前去的父親,面對的是無法拒絕的呼喚吧!父親的家族世代務農,但到了他這一輩,多數人已離開故鄉,轉往城市打拚,從事其他工作。父親國中離鄉,與農地的交集僅止於童年的幫忙。這也在他心底留下某種矛盾──「農人」成為他未曾真正經歷、卻又根深蒂固的自我認同。那一夜,他或許覺得自己正代替故鄉的人們站在街頭,與公權力正面對峙。如同那些被主政者視為「暴民」的抗爭者,內心也都覺得自己背負著某些人的未來,懷抱著使命感,才會犧牲生活的平靜,加入街頭抗議的隊伍。
正是因為這些沒有在歷史留下名字的平凡「暴民」不斷衝撞,才能一點一滴鬆動威權的禁錮。第一線衝鋒的永遠是少數,而當走上街頭的代價不再昂貴時,就有愈來愈多像父親這樣的「追隨者」、「旁觀者」加入,匯集成沉默而巨大的民意。
曾叮囑我不要在學校提及二二八的老爸,開始忍不住帶著還只是小學生的我,去一些抗議活動現場,像是鄭南榕自焚後在士林廢河道新生地設立的靈堂,或1990年初中正紀念堂的野百合學運。我始終不明白父親帶我去的動機,是覺得民主的教育不能等?還是一時沒地方可以安放小朋友?膽小的我,早已被媒體形塑的形象洗腦,身處現場只覺得害怕、局促不安,只想趕快回家,完全不覺得自己在參與或見證歷史。心底對父親的抱怨,遠多於對運動的感動。
無論如何,進入90年代後,雖然不見得所有「自力救濟」皆如此,但的確有愈來愈多示威遊行的現場,已呈現出可以帶小孩同行的氣氛,逐漸洗去革命式的日常斷裂,以體制內改革之名,重新與一般人的生活接軌。
鄭南榕的大名,常常在家裡出現。他主編的《自由時代》雜誌,不時會出現在爸爸的床邊。對於三不五時不想一個人睡,跑去賴在爸媽床上的我,這些雜誌也間接成了我的枕邊讀物。這當然是玩笑話,我沒有那麼早熟,《自由時代》也沒有那麼輕鬆,至少對小學生來說,滿滿的字,看起來就好嚴肅。比起來,另一本黨外雜誌《民進》雜誌更吸引我,因為裡面會出現漫畫。
我對《自由時代》最深的記憶,是有一次看著版權頁那一長串「某某時代」的名稱,好奇地問爸爸:「這些都是這本雜誌的名字嗎?」只見爸爸露出微笑,默默點頭,沒有解釋太多。雖然對《自由時代》認識有限,但我知道爸爸很欣賞總編輯鄭南榕,常去參加他舉辦的抗議活動,也會特地跑去聽他演講,只要提到這個名字,爸爸眉宇之間總流露出欽佩。
1989年4月7日,當電視報導鄭南榕自焚的消息,螢光幕裡冒著黑煙的大樓、焚燒過後的焦黑房間,以及用紗布和黃布包裹、抬上救護車的傷亡者⋯⋯,每段畫面都令我震撼與驚慌。我當然知道政治抗爭背後總伴隨風險,否則也不會和母親站在同一陣營,一起責備上街頭的父親。然而,直到鄭南榕以身殉道,我才真切意識到這一切的重量──那是以生命為代價的付出。鄭南榕的新聞喚起我心底最深的恐懼,懼怕的不單是死亡,而是如果有一天,父親也和他的英雄鄭南榕一樣,該怎麼辦?
會有這種聯想的,不只我,還有更瞭解父親的母親。鄭南榕的去世,使父親激動難平,母親則再三告誡、想方設法,不讓父親衝動上街參加抗議。書店繁忙的店務充分發揮了牽制的作用。5月19日鄭南榕出殯遊行,因為是星期五,父親無法參加。遊行當天一早,先在士林廢河道設置的鄭南榕靈堂前舉行入殮告別式,下午1點半出發,4點接近尾聲時,隊伍來到總統府前廣場,警方早已擺放蛇籠和拒馬嚴陣以待。突然間,青年詹益樺衝向前方,點燃身後背負的汽油包,撲倒在蛇籠上,火勢猛烈,兩、三分鐘不到的時間,詹已燒成一團焦黑,享年32歲。放學回家的我,看到新聞,第一時間打電話到店裡給媽媽,確認爸爸整天都在店裡,沒有出門,才鬆了一口氣。
沒有參加遊行,爸爸仍抽了一個晚上到廢河道的靈堂祭拜,並帶我同行。開書局後,我們家三人的生活形態幾經調整,逐漸定型,爸爸晚上先開車帶我回家,由媽媽看店,打烊後她才會回家。顧我的這幾個小時,是爸爸一天中少數能自由支配的時間; 去祭拜鄭南榕也是趁著這段空檔。
爸爸完全可以讓我一個人待在家,但他沒有那麼做。那晚他神色凝重,我不敢多話。到了現場,氣氛肅穆。現場應該有放音樂?來來往往的人也不少,但在記憶裡,一切都靜得出奇。也不知是出於擔心還是想獨自憑弔,爸爸並沒有帶我進靈堂,要我在外頭稍等。一人在陌生的環境,又不敢直視遺體照片,只能低頭盯著地面,時間不長,卻度秒如年。終於,老爸回來了,我正想開口抱怨,一抬頭就看到他紅紅的眼眶。對孩子而言,父母的眼淚是件大事,尤其幾乎不曾在我面前落淚的父親。我不知該說什麼,一路沉默,也沒跟媽媽提起那一晚的事。

去野百合現場的那次,倒比較像是散步。散步是爸爸的嗜好,從上班族時期延續到開店後,不曾間斷。偶爾他也會帶上我,這樣的活動持續到我上了國中、進入青春期,那時大人再也叫不動我了。那些散步的夜晚,我總是又愛又怕。爸爸在家裡扮演白臉,負責陪小孩玩耍,媽媽則是管教擔當。這並非刻意的分工,而是性格自然形成的秩序:爸爸外向活潑,媽媽內向拘謹,我介於兩者之間,可能更接近媽媽一點。
爸爸對逗弄小孩很有一套,只要有小孩聚集的場所,他很快就會成為孩子王。能和他下班後四處閒晃,黏著他不放,是一種近乎寵愛的幸福。只是他討厭一成不變,總會創造出各種新的「冒險」,像是闖進夜晚無人的植物園或青年公園,或一時興起變更路線,走到離家有點距離的龍山寺或中正紀念堂。怕事、只想和父親在家附近晃晃的我,每次都努力想把那個一股腦向前衝的他拉回,結果皆以失敗告終,只能跟著他,一起走進不知地上是樹影還是鬼影的公園小徑。
那天他趁著媽媽在店裡,只有我和他在家,拉著我出門。我沒有想太多,以為這只是一次平凡的散步,可是愈走愈遠,也愈來愈覺得不對勁,心想我們的目的地該不會是這幾天新聞一直播報的那座紀念堂,爸爸口中的「中正廟」?果然,遠方出現了那藍白相間的塔尖。只怪自己太大意,早該從爸爸出門時興奮的神情察覺不對。
中正紀念堂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爸爸有陣子迷上攝影,留下不少一家人在那裡的合照,是全家週末短暫出遊的常見選項。但那天的紀念堂和我印象中完全不同,大廣場擠滿了年輕的人群,空氣中瀰漫著難以形容的氣氛,交雜著緊張、興奮、疲倦、恐懼、憤怒、自信、迷惘⋯⋯。潔白的建物,高掛著布條,上面的大字對小學生的我來說有些難以辨識。勉強拼湊,內容不外乎父親痛罵那些「老賊」時說過的話。那時父親常和我談政治,除了二二八之外,幾乎無所不談,特別是重大的新聞事件,最常用的「教材」是《自立晚報》裡魚夫的漫畫,以及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專輯。這次他沒有再交代不要在學校談這些,除了放心我的怯懦之外,那時關於老國代的新聞早已撲天蓋地,不再是禁忌話題。不過,爸爸倒是特別告誡我,不要在外婆家講這些。這道理我當然懂,不懂的是,為什麼他在媽媽面前總是毫無保留地長篇大論,完全無視她深鎖的眉頭。
不知道是因為爸爸只帶著我在活動的外圍繞繞,還是剛好在日期上錯過,或只是我不敢東張西望,我對那朵「台灣野百合」的雕塑沒有留下記憶。我只記得現場那些年輕學生的友善,對著我這個一看就搞不清楚狀況、滿臉驚懼的小學生,這些大哥哥、大姊姊都露出了笑容,其中一、兩位還和我簡單攀談了幾句,怕生的我趕緊躲到爸爸身後。我感覺得出來,眼前這一小群年輕人,因為這個亂入的小鬼,獲得片刻輕鬆,緊繃的神情鬆開了,短暫回到他們原本的模樣。最明顯的是,他們對爸爸的態度不再提防,畢竟應該不會有線民帶小孩來蒐證吧?他們和老爸閒聊了幾句,接受了他的加油。看著他們的友好互動,我卻只想趕快回家──這次可不同於鄭南榕那次,我回家一定要和媽媽告狀!
1990年可以視為台灣街頭運動轉折的起點,它延續了80年代草莽的活力,也逐步走向體制內部的規訓。上半年野百合學運結束沒多久,接著就是反軍人干政的登場。5月,當具有軍人身分的郝柏村將要接任閣揆的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全國輿論譁然,野百合學運換來的改革似乎將付之一炬。
立法院首先成為戰場,李勝峰、朱高正和陳水扁3位立委都發言表示反對,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或許是日後加入新黨的國民黨立委李勝峰的發言,他認為這次提名決策實為「黑箱作業」,軍人組閣不僅違反民主潮流,也和蔣經國極力避免軍人干政的理念相背。幾名在旁聽席的大學生也高舉著「你郝我不好,反對軍人干政」等字樣的布條進行抗議,和警衛發生衝突,導致議事一度中斷。主席梁肅戎用麥克風對旁聽席喊話:「各位是大學生,我們很尊重你們,希望你們尊重國家的制度,遵守秩序,取下布條。」卻遭到學生反嗆:「你們都不尊重制度,憑什麼要我們尊重?」梁只能宣布散會。
到立法院抗議的學生,以「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的名義,聚集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然而這次的能量已大不如前。許多民間團體持觀望態度。最後,由少數社運團體組成的「全民反軍人干政聯盟」,加上學生,動員將近3、400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與三月學運(野百合學運)近萬人的盛況相比,社會支持度明顯有別。此外,股市在郝即將接任閣揆的消息傳出後,連日長紅,顯示至少部分工商界人士和投資人視此為利多,甚至學生內部也出現是否有必要大力反對的雜音。
反軍人干政的遊行於5月20日下午1點45分在中正紀念堂誓師出發,在各方動員下,約有萬人參加,繞行中正紀念堂四周主要幹道。記者稱「這是台灣地區解嚴後首度出現最大規模的政治性抗議遊行。也是台灣最大規模知識分子走上街頭抗爭的行動」。遊行以「和平非暴力」為訴求,但因為參加群眾背景複雜,指揮人員也難以約束,不時發生零星衝突。
反軍人干政的最高峰,發生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的5月29日。相對於議場內議事干擾的平和,場外則陷入激烈對抗。抗議群眾準備了汽油彈,據現場記者報導,當天至少投擲引爆了10至11枚左右。前兩枚約在中午投出,後來又陸續有零星投擲,甚至焚燒沿路車輛。汽油彈之外,示威群眾也以大量石頭、磚塊和彈弓攻擊警方,警方則以強力手段回應,台北市警察局長廖兆祥下令出動霹靂小組緝捕滋事民眾,並派出大量警力和噴水車。
「軍人干政」看似涉及大是大非,但其背後更牽涉權力與權位的運作。執政者李登輝讓郝伯村以「整頓治安」為由組閣,藉此瓦解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對國是會議的干預,並誘使郝柏村交出軍權,「將國民黨軍隊變為國家軍隊」。他鐵了心要把郝柏村送上閣揆的位置。
郝柏村上任後,立即著手延伸並強化《集會遊行法》的各種管制。先是內政部出來宣示加強管束集會遊行的決心,要求申請單位配掛明顯標幟或臂章,並須事先向警察機關報告參與人數。也禁止抗爭者蒙面、戴帽子或面具,違者視同妨礙警方蒐證。
他在上任後的第一次治安會報中強調,日後只要違反《集遊法》,治安機關應秉持「暴力行為,現場逮捕」的原則。
在郝柏村「治安內閣」的定調下,街頭示威被視為治安問題,並延續「暴民」論述,強調抗議行為必須以「合法」、「和平」為首要原則。
隨著政黨政治日益步上軌道,體制內的選舉對決,吸引了更多的關注,當「凍蒜」取代了「抗議」,體制外的「自力救濟」,也就逐漸失去過往的能量。之後台灣街頭還是不時有人上街,無論訴求為何,最後往往淪為選舉的算計。90年代成為民進黨重要領袖的許信良,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長期列名於海外黑名單,1989年偷渡回台遭判叛亂罪,1990年獲李登輝總統特赦出獄。同年5月21日,他在記者會上表示:「暴力是手段,不是目的」,如今台灣「人民的力量已經很強大,不用暴力就可以改變一切」,極力撇清民進黨的「暴力」形象,以爭取執政的機會。此話看似言之成理,卻也與過去的街頭示威劃下明確界線。
日後台灣的街頭依然喧囂,台北街頭仍是提出政治訴求的重要舞台。然而,當街頭與立法、行政、選舉等多條路線並行時,街頭已不再是過去那樣的街頭。
以反軍人干政運動為界線,爸爸就很少再參加街頭示威了。一方面是生活的變化──父母從上班族轉為一家小書店的老闆,從朝九晚五的員工變成從早到晚顧店的老闆、老闆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街頭示威逐漸轉化為選舉造勢。80年代的街頭能量在90年代產生了質變和量變。
父親仍會努力在店務繁忙、母親抱怨之間,偶爾硬擠出時間去參加選舉造勢晚會或遊行,只是,參與這些「體制內」的活動,風險與心境已大不相同,甚至連結束的時間都有精準的安排。
父親和他同輩的許多人一樣,漸漸淡出了街頭;而我與同世代的人,對街頭的印象則更為模糊。不管是父親還是我,我們或許仍會為了選舉而熱血沸騰,為了某些議題與人在現實或虛擬世界爭得面紅耳赤,但要像解嚴前那樣,帶著幾分革命色彩去挑戰或否定體制、走上街頭自力救濟,似乎已經是遙遠的過去。
改變從來只能依靠行動,而非精巧的論述,或寄望於體制內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保障。尤其是民主、自由、人權等當代普世價值,衡諸歷史,無一不是人們用行動、乃至鮮血和生命爭取而來;它們也從未安穩,不時被有心人想方設法地鬆動、扭曲、否定。這些價值得來不易,卻可能因人們的冷漠與鬆懈而迅速消逝。
有學者指出,民主與自由是在國家與社會兩種力量互相牽制下,所構成的、如奇蹟般存在的窄廊;人們必須像路易絲.卡洛爾(Lewis Carroll)《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裡的紅皇后,不斷奔跑,才能維持在原地。
父親那個世代在青春年華承擔了奔跑的責任,而我們這一代,多數人卻視現狀為理所當然,不是忘了繼續奔跑的義務,就是跑錯了方向;有的袖手旁觀,有的甚至沾沾自喜。於是那條窄廊數度瀕臨崩解,讓少數人辛苦代替我們扛下奔跑的責任。直到近20年後的21世紀,台灣街頭再度風起雲湧,不同世代的人重新聚集,重返立法院外的道路,並赫然驚覺:那所謂街頭的「平和」、那消失的「暴民」,其實不過是我們對未來的盲目期盼──一場自我欺瞞的幻夢。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