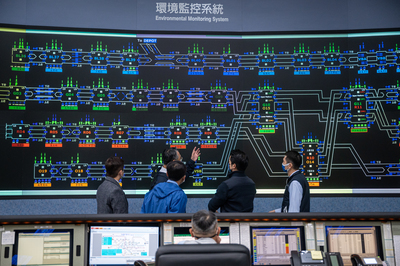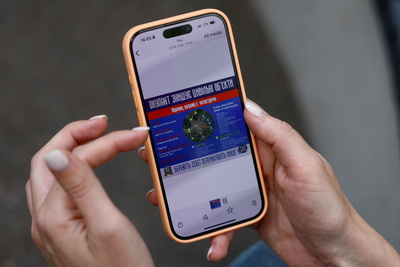當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產生衝突時,台灣是否已有足夠準備?近期網路上頻傳「檢舉可疑路人」的貼文,並持續引發論戰與誤會,導致因政治分裂的社群媒體更加極化,甚至成為有心人士發動「認知作戰」的養分。
這些臆測如何產生?公開拍攝交通要道、政府設施和民眾臉孔是否為間諜行為?《報導者》接觸一名遭遇爭議的當事人,並透過多名軍事界、法律界、精神醫療學界的專家視角,分析這場正席捲台灣社會,目前仍不見盡頭的互相攻伐風波。
搭捷運一邊看健身影片卻被懷疑是中國間諜,健身教練黃瑜萍從未預料過這件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更忍不住心想:「會不會對方剛好讀到類似文章,內心真的很焦慮,覺得我很壯,看起來很可疑,剛好誤會了,才不小心動手?」
6月15日下午,黃瑜萍剛結束訓練,累癱在捷運座位上,反覆回味自己當天舉重成功的影片,竊喜著表現不錯,此時一名年約20多歲的女性路人突然伸手擋住她的手機螢幕,「妳是台灣人嗎?還是中國人?」一邊質問她是否在拍攝捷運車廂,並作勢要奪走手機。
黃瑜萍回應「我是高雄人,搬來台北工作」,對方又發抖著追問她的生日、星座、血型。兩人的對話時間不到3分鐘,僅是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到下一站古亭的短短距離。因為黃瑜萍必須趕著下車,她既無法向對方確認「為什麼懷疑我?」也來不及安撫對方情緒,究竟她被懷疑在偷拍或是間諜,黃瑜萍一頭霧水,心裡只留下恐慌的種子。

在親身面對爭議之前,黃瑜萍雖看過不少類似的網路貼文,但從未深入瞭解,「以前看到那些討論和影片,我覺得應該大多是造假,有人在刻意散播假資訊,想營造我們『台派』都很不理性的形象。」
「『當我面前可能有一名中國間諜,我要如何處理?』沒有人平常會想過這個問題,所以當下她應該只是憑本能,希望馬上做點什麼。」當這位素昧平生的路人對黃瑜萍產生質疑,黃瑜萍抬頭看向對方時也驚覺,竟是一名年輕、看起來文靜又緊張的女生。
隨後,當黃瑜萍在社群平台Threads上公開闡述此事,希望和網友討論,甚至找到那位女生聊聊,網友們卻不領情,大量留言進攻謾罵:一派人戲謔地説「台派不意外」,也有「自己人」認為她是假帳號,刻意在製造分裂。但對黃瑜萍而言,她只想解開這場誤會,並向網友抒發「我們不該這麼做」的心情。
這些「誤會」近期頻頻發生。有網友看見一名中年婦人在菜市場直播時,湊上前大喊「六四天安門」希望阻止,隨後有一名自稱是她兒子的帳號出面澄清,「我媽媽只是在和朋友討論要買什麼菜。」
日前民進黨立委郭昱晴也在Facebook上發文,自述在公園遇到一名「鬼祟男」疑似用手機拍攝周遭的孩童與家長。郭昱晴未曝光該名男子的個資,畫面也以馬賽克處理,她自認重點在呼籲民眾需留意在公開場合拍照時,角度應避開未成年人,因此該男雖已在現場回應「我只是在自拍」,郭昱晴仍發文公審其行為;隨後該男的「友人」回應反擊不滿,該男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澄清,當天晚上郭昱晴才刪文道歉。
還曾有網友發文指稱,他親眼目睹空軍新竹基地外有3名「中國情蒐人員」,一人拿望遠鏡、一人持長鏡頭特寫拍攝戰鬥機,第三人在後方牽著腳踏車保持警戒。但隔天該網友就刪文道歉,他說明警方到場調查後發現,持相機者只是剛下班的攝影愛好者,另外兩位民眾則是單純好奇而駐留現場。
在各項案例中、進入正式調查程序的僅有二例,正是引爆這波爭議的第一案。5月26日,一名家住台北市松山區的52歲中國籍配偶遭警方逮捕,原因是她經常在抖音和小紅書直播台灣街道和小學生放學,內容清楚拍到孩童臉部,被現場家長阻擋後仍不停止直播。
台北市警察局當天回應,雖然該女供稱「只是分享台灣的生活和風土民情」,但因拍攝已涉嫌違反《刑法》妨害祕密罪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台北市社會局裁處;另有一名台灣籍的25歲女子也因為相同原因遭家長報案提告。
對此,一名國安人員向《報導者》說明,近期中國社群媒體上正流行直播台灣街道,相關影片的點閱率皆不俗,此類型影片若拍攝到路人正面並公開上網,會視影片內容斟酌是否涉「妨害祕密」,營利使用則可依「侵害肖像權」辦理;若被拍攝的對象屬未成年人,則為《兒少法》處理範圍。
但該人士強調,從事上述行為「不代表一定犯法」,假設記錄路人拍照行為的「檢舉者」在網路上影射對方是中國間諜,檢舉者甚至可能涉《刑法》妨害名譽。

拍攝影像之後,用途是否涉及商業利益、誹謗或公然侮辱,以及被拍攝者的年齡,這些條件都是衡量路上「公開拍人」犯法與否的依據;那麼記錄台灣街道,甚至軍事設施和關鍵基礎設施周遭的地貌,又可能碰觸哪些法律爭議?
目前台灣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中,以《國家機密保護法》及《要塞堡壘地帶法》和本現象關聯性最高,但《機密法》僅限政府文件,《要塞法》只匡列22座軍事基地,目前傳出的事件都未涉及這些敏感資訊。國防部長顧立雄於6月25日赴立法院備詢時也回應,軍事迷拍攝軍機起飛並不違法,但若特意拍攝營區內機敏處所,有偵查行為,「足以影響軍事營區安全,就會構成違法。」
不過官方說法難以安撫民眾疑心,近年國際衝突中頻傳的滲透案例,已成為網友們的焦慮來源。例如今年(2025)6月,烏克蘭對俄羅斯發起「蜘蛛網行動」,烏克蘭特務人員潛入俄羅斯境內後,用無人機空襲多座俄方空軍基地。去年(2024)9月以色列也曾對黎巴嫩的軍事組織「真主黨」展開突擊,先在真主黨成員使用的BB Call呼叫器裡預埋微型炸彈,最後遠端引爆,炸死多名真主黨高層。
而在情報戰、間諜滲透領域,中國共產黨經驗老道,他們的做法在歐美稱為「沙粒」 (Grains of Sand)戰略,意即安排大量情報員,在各領域隨意蒐集看似不起眼,卻有潛在價值的情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發行的《戰略學》一書,將資訊作戰定義為「模糊的,游移於明確攻擊和威懾之間,游移於平時和戰時」;另一本中國官方著作《軍事情報學》則明白寫著「情報的價值,取決於它對使用者的實用程度」。
何謂實用程度?外界無法窺探,加上中國長期對台進行軍事層面的灰色地帶騷擾,於「個人層面」則慣用身分可疑的民間人士騷擾香港移民、海外台灣組織,並蒐集民主運動者的個資。各種實際案例交織後,匯聚成陰謀論的土壤。
前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台灣防禦協會理事長陳彥廷對此分析,不論是拍攝台灣馬路或敏感機關,以軍事角度來看,「其實中國不需要用這種做法收集情報。」陳彥廷說明,諸如隧道高度、橋梁寬度等數據,在台灣網路上也能輕易查到,「在各國都有衛星的年代,Google Maps上的比例尺比用相機拍現場更準。」
以最具軍事價值的攻擊目標──軍營、陣地和政府機關為例,許多地點早已被中國建檔,解放軍在內蒙古興建了模仿總統府所在地「博愛特區」街道的巷戰訓練場,也在新疆沙漠中打造疑似蘇澳軍港的飛彈靶場;今年4月解放軍展開「海峽雷霆─2025A」軍演,更公布了模擬高雄永安天然氣接收站的影片。
陳彥廷認為,派遣特務以留學、觀光為名混入台灣民間親自拍攝資料,既太招搖,對解放軍來說也缺乏效率,況且近來傳出爭議的地點都並非「高價值目標」,由於解放軍追求短期決勝負,攻擊它們並非首要任務。至於民眾擔心被拍攝後搜集個資,陳彥廷也直言,「非政治人物、軍事將領的普通人資料對解放軍而言,沒有價值。」
「陰謀論永遠不會有結果,我們能做的就是在感到焦慮時,多想幾秒。」
陳彥廷表示,國家安全和情報戰等詞彙對大眾而言十分神祕,再加上兩岸局勢詭譎,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難免引發臆測,此刻保持冷靜並理解法律,比個人實施檢舉行動更重要。

為了解決長期曖昧難解的民眾拍攝爭議,國防部還新訂《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即將於8月1日上路。該條例設計各項管制措施,定義何謂「重要軍事設施或軍事機關之駐地」,可望將過去的灰色地帶明文化,界定出合法、非法拍攝之間的界線。國防部參謀本部聯合作戰計畫處處長董冀星補充,未來若因訓練需求,必須臨時劃定限制區域,軍方會在45天前進行公告。
以今天(7月9日)開始的漢光演習為例,董冀星說明,民眾拍攝軍人、軍車的運輸過程,或者在公開場合進行的訓練,都不屬於禁止範圍;唯有民眾出現長時間記錄的「持續性」,或不斷記錄特定人物、裝備的「針對性」,國防部才會通知警政與國安單位調查。董冀星表示,只要拍攝地點不屬於管制區,民眾也不違反兩項規則,「不涉及違法或國安問題。」
國防部最新說法為過去的灰色地帶定錨,法律上或許已有解答,但如何舒緩台灣的內部紛爭?近年醫界同樣關注由安全威脅衍生的資訊焦慮(Informational Anxiety)現象。
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吳易叡長期研究醫學史、精神醫療領域,他便指出,當前台灣承受著中國軍事演習與外交孤立等多重壓力,加上社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變得焦慮是可以理解的:
「最大的傷害,是心理上信任機制的瓦解。」
由於社群媒體必須不斷吸引用戶「黏在螢幕上」,平台方會透過程式演算法加強熱門話題,並鼓勵網友即時互動,這些因素都加固了陰謀論的土壤,甚至讓有心人士更容易發起「認知作戰」。吳易叡分析,網友們的負面情緒,以及憤怒感、羞辱言行都會被社群平台上的討論放大,在俗稱「同溫層」的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影響中兩極化。

醫學專家看待認知作戰的角度是:在心理上容易形成「現實的錯亂感」。吳易叡解釋,人們變得難以分辨「哪些是真實經驗?哪些是受操弄的資訊?」久而久之,事物的真相不再受重視,或失去可供檢驗的客觀標準,因為人們開始懷疑原本具有公信力的媒體、由政府發布的官方訊息,只相信自己熟悉的消息來源。
安全威脅在前,缺乏健全討論的社會隨之分歧,並衍生出「標籤化」現象,這在吳易叡的研究中並非罕事。他舉例,歐洲中世紀流傳黑死病期間,猶太人被懷疑在井中下毒,造就大規模獵巫浪潮;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引起東京大火,也讓當時的日本人急著找出「讓社會秩序崩潰的代罪羔羊」,許多韓國移民(在日朝鮮人)首當其衝,歧視至今仍深藏日本民間。
更近一點的案例則在台灣COVID-19疫情初期,一名家住中部的白牌計程車駕駛被歸國乘客傳染,成為首例死者並造成後續群聚感染,當時台灣網路上稱其為「防疫破口」,出現撻伐浪潮。吳易叡認為,群眾在極端狀態中為了迅速「保護自己」,往往會過度簡化、分類敵我。他也對此提出警語,歷史上各國社會面對「威脅感」時,剛開始容易過度放大焦慮,但後來可能轉向消極,甚至否認,並對政策失去批判力道。
來自同樣受俄羅斯威脅的北歐地區,挪威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Lars Svendsen)則在《恐懼的哲學》書中提出一定義,他認為,人們總懼怕生命中的重要事物被摧毀,「例如自由、尊嚴、健康、社會地位,乃至性命」,因此大眾不只為自己,也為親近的人們擔憂,而當其中任何一項要素遭受威脅,「恐懼便是自然反應」
2023年史文德森又出版《希望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Hope,暫譯),其中一章闡述他對國家安全的看法:「抱持希望,將為你的行動生活建立一個框架,讓你明白必須做什麼,以及不應該做什麼。」史文德森更直言「不抱希望就不會失望」只是缺乏邏輯的推託之詞,唯有因希望行動,才能增加實現該目標的可能性。
史文德森主張,恐懼並非最適當的選擇,因為「恐懼極少讓我們對『恐懼的對象』有所認識」,一旦人們對風險產生執迷,危害可能勝過恐懼的對象本身。他更寫道,當個人或社會基於恐懼採取自保行動,這過程中產生的焦慮,通常是「反映自己的脆弱」多於「我們所懼怕的現象」。

不論群眾擔心間諜滲透,或有心人士向這股恐懼見縫插針,在各界專家眼裡,「對國家安全的陌生心理」或許正是脆弱根源。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所長黃丞儀解釋,在台灣的民主化歷史中「反對軍人干政」是對抗國民黨威權的主要訴求,同時獨裁政權也不樂見民眾太了解國安議題,在此背景下,早期民主運動者都將打破蔣家軍事統治視為首要任務,「前人對軍事非常警戒、非常排斥,當時大家擔心的是,武裝力量將威脅台灣民主化。」
尤其出身軍界的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在1990年接任閣揆,多家媒體皆表態「反對軍人組閣」。而台灣在歷任總統軍購案遭阻擋、漸進式廢除徵兵制等歷史事件後,社會對軍事的冷淡態度於2013年洪仲丘案達到高峰,最後廢除了長期存有人權疑慮的軍事審判制度。
直到2014年發生太陽花運動,台灣社會對國家安全的思維開始翻轉,視「中國滲透」為現在進行式。黃丞儀指出,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更多民眾看見中國的極權野心,如今被稱作「亡國感」的焦慮正式興起,然而台灣尚未建立起對國家安全的新想像,制度上曖昧不明、個人可做的準備也尚未普及,導致恐懼無法有效被化解。
針對疑慮,黃丞儀主張「辨別哪些行為真正危害國安?」是重中之重。他舉例,桃園機場常發生斷電、漏水等工安意外,還曾經傳出中國網軍擾亂航班資訊的陰謀論,不過水電工意外剪斷電線只觸犯「公共危險」,以現行《刑法》便可處理,「當事人造成社會大眾不便,於是國家必須以刑法來處理。但即使發生在機場,在證據不充分的狀況下,恐怕還是不能恣意上綱到國安問題。」
「最關鍵的要素在於,該犯罪『是否有破壞自由民主憲政之虞』,」黃丞儀說,假設投票所的電纜在選舉投票日被剪斷,妨礙了民主運作,才能上升至國家安全問題;所有的國家安全問題都會牽涉到人民心中的恐懼,當恐懼的總和壓過民主政治的一切,那就離制度崩壞不遠了。
黃丞儀提醒,即便是面對中國入侵的當下,一旦台灣境內發生有國安疑慮的犯罪,法院仍須以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的司法審查標準,不能因為「國安案件」就忽略證據法則,自動傾向有罪推定,擴張法律條文的解釋。另一位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蘇彥圖也強調,「國安問題不應該依靠人的判斷,必須建立制度保護。」
蘇彥圖說明,二次大戰前夕納粹德國追緝猶太人,或美國在1950年代因蘇聯滲透引發全國恐慌,掀起大規模檢舉潮的麥卡錫主義時期,都可見民眾成為無視法律的「Vigilante(自發性執法者)」試圖揪出社會中的「非我族類」,這些先例留下相同結果:「無法有效解決國安威脅,反而製造了更多社會問題。」
蘇彥圖表示,當民眾處於壓力中,不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也無人提供解決方案時,「自然會產生Vigilante傾向,但這種焦慮對國安往往是最不好的狀態。」他擔心,人們在慌亂中無法保護自己,更遑論進行社會對話,唯有先冷靜面對問題,才能開始改變。
至於法律能否跟上兩岸風險升溫的速度?蘇彥圖認為,政府必須制定有效預防滲透的法律工具,同時向民間說明「現在發生什麼事?」或許這作法會遭民眾質疑緩不濟急,但以現況觀察,中國問題將會長期存在,唯有建立制度,透過不同的法律判例持續修正它,才能健全民主政體的防禦韌性,「這過程不應該是民主的弱點,而是強項。」

當中國威脅來到眼前,台灣內部尚未做好準備,導致焦慮與陰謀論橫行,陳彥廷正致力扭轉現況,他常在民防課堂上詢問聽眾:「你家的巷口有幾支監視器、最近的消防栓和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在哪裡?郵差都幾點來按門鈴?」能完整回答者卻寥寥可數。
這些問題都是建立安全意識的基礎,陳彥廷直言,台灣以治安名列全球前茅為榮,但民眾也因此忽略「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他建議:
「第一步可從觀察住家環境做起,了解什麼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和『異常』。」
「如果你家附近有一間變電站,晚上10點你看見一名穿著工程服、手拿工具,無法辨認身分的人靠近,你會怎麼做?」這是陳彥廷會問聽眾的第二題,多數人都選擇上前拍攝、報警,甚至直接攔住對方,接著陳彥廷會問第三題,「如果那個人只是忘記帶識別證的台電員工呢?」聽眾此刻通常會語塞,反射性地忽略了事前查證的必要性。
這和「郵差幾點來?」是相同意義,陳彥廷說明,除了正確認識中國滲透的可能性,掌握生活周遭的「正常」運作,也有助於民眾分析現況,進而減少焦慮。即使真的遇上「異常」發生,「大眾的任務絕不是去判斷異常者的身分,審判他犯了什麼罪、行為帶著哪些疑慮,猜測背後是否有幕後黑手。」陳彥廷強調:
「異常不等於有問題,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通報。」
政府有責以法律回應國安問題與民眾疑慮,讓人們面對異常時知道該做什麼,並且願意相信制度。陳彥廷指出,這些不起眼、看似徒勞無功的努力都是在加強「心理韌性」,重要性絕不亞於硬體建設。
陳彥廷說,兩岸維持在雖有實力差距、但落差不至於讓中國可趁隙侵略的平衡中,將是未來的長期課題,台灣必須兼顧心理和硬體準備。他形容這像辦保險,「人們買醫療險、壽險時都不希望會用到,但你還是會買,」靠保險減少後顧之憂,也得在生活學習避開風險,「做好持續過每一天的心理建設。」
這對黃瑜萍而言,保持平常心已是日常作業,她經常問自己和朋友看了新聞後「在害怕什麼?」是害怕因戰爭失去生命、房產或股票,還是家人?她認為,每種恐懼的準備方法都不同,前提是先面對它,「當你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只能盲目想逃時,恐懼就會一直跟著你。」
身為兩個小孩的母親,黃瑜萍自認抱持「每一天都好好過生活,不為戰爭焦慮」的正面態度,目前她最害怕的情況反而是「看見其他同胞正處於焦慮中,我卻無力改變」。黃瑜萍不希望留給孩子一個剩下恐懼的社會,「為了守護自由,所以我們必須先犧牲自由,這點我無法接受。」
尤其是黃瑜萍為此發文,希望提醒網友冷靜後,不少人卻質疑她「為什麼要說出會傷害台灣人團結的事」,即使黃瑜萍貼出自己參加社會運動、罷免投票的證據,仍無法止息聲浪。但黃瑜萍不後悔自己寫下這段經驗,「至少還是有人願意認真討論,我也為此重新整理了自己的心情。」
事發半個月後回想當下,她笑說:「我練這麼壯,那位女生還敢伸手擋住我,我覺得她很愛台灣這個國家,才會有勇氣去做這件事。」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