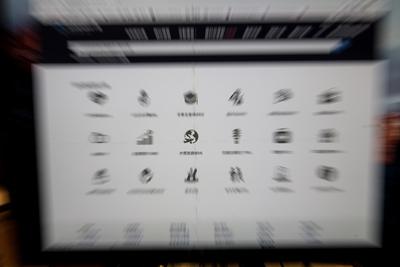週六現場【法律人追劇】

(※本文含《教宗的承繼》、《秘密會議》劇透,請斟酌觀看。)
2025年4月21日,教宗方濟各(Franciscus)溘然長逝,舉世哀悼。方濟各本名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義大利裔阿根廷人,是天主教史上第一位來自南美洲、出身耶穌會(Societas Iesu)的教宗,與前任來自德國的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個性迥異,價值觀更大相逕庭。
耶穌會是為回應宗教改革的衝擊而成立的男修會之一。許多人或許對於耶穌會感到陌生,但如果提到於明朝與徐光啟等人翻譯《幾何原本》等書的利瑪竇,以及在清朝擔任欽天監監正與協助製造紅夷大砲的湯若望、南懷仁的事跡,相信多數華人都不會陌生,他們都是當年耶穌會派來傳教的修士、神父。
2013年2月,本篤十六世以年事已高、健康欠佳為由,突然宣布退位,這是近700年來首位在世的教宗辭職,震驚全球。2013年3月13日在選舉教宗會議的第五輪投票中,貝爾格里奧以三分之二多數票獲選為教宗。貝爾格里奧選擇「方濟各」為名號,彰顯他效法亞西西的聖方濟各(Sanctus Franciscus Assisiensis)關懷貧弱、謙卑服務的精神。
方濟各接任後,始終以簡樸、開明作風示人。無論是教廷財務制度的改革,對犯下性侵害罪行牧師的嚴懲,對同性戀的寬容,與其他宗教和信仰的對話,或在全球議題上為難民、貧窮與氣候危機發聲,他都展現「與世界同行」的牧靈精神,被《時代》雜誌(TIME)譽為「人民的教宗」(The People's Pope)。

2019年在Netflix數位發行、根據本篤十六世與方濟各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教宗的承繼》(The Two Popes),由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飾演本篤十六世,強納森.普萊斯(Jonathan Pryce)扮演方濟各,兩大英國傑出男星精彩對戲。劇中探討兩位牧者在信仰、人生上的掙扎與友誼,例如本篤十六世自責未能阻止教會醜聞蔓延,貝爾格里奧則深陷過往於阿根廷軍政府時期的愧疚陰影,質疑自己能否肩負改革使命。
貝爾格里奧為何會有此愧疚陰影?讀者從我在〈從《1985年阿根廷》到《我依然在此》:台灣轉型正義的時代意義與未竟之業〉一文中的說明,即可知悉阿根廷自1976年進入長達8年的軍事統治時期後,軍政府開始大規模且殘酷的高壓肅清,至少有8,000多人被強迫失蹤。此時貝爾格里奧擔任耶穌會的阿根廷省省會長,他被指控與「骯髒戰爭」期間軍方綁架兩名神父的事件有所牽連。
雖然貝爾格里奧在此期間曾收留過很多反抗軍政府的年輕人,但這兩名神父遭受酷刑折磨而死,貝爾格里奧卻未公開發聲。這樣的指控,讓誠信正直的貝爾格里奧一直懷有負疚之心。即便成為至高牧者,依舊會悔恨與自省──正是神聖職權與凡人性情的拉扯,讓電影中的教宗形象格外鮮明。
影片中兩位靈魂人物被巧妙塑造成光譜的兩端:本篤十六世是基督信仰的原旨主義者,緊握教理正統與理性思辨;貝爾格里奧則化身傾聽街頭心聲的牧者,主張教會應該順應時代變革並沾染人間塵土。一個是學院派,尊崇傳統,愛好古典音樂;另一個是改革派,深入民間,熱愛足球與探戈。兩人在彼時醜聞籠罩的梵蒂岡,展開一場又一場關於傳統或進步、罪惡或寬恕的辯論交鋒。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曾獲邀對當時世界最大的企業組織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進行長達18個月的調查研究,從中累積眾多關於企業經營管理的案例分析。日後,杜拉克在《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一書中,藉由他與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CEO、長期任職通用汽車董事長的史隆(Alfred Pritchard Sloan, Jr)之間對話的內容,告訴讀者企業組織的用人之道。
當杜拉克發現史隆與眾主管只為了任用一個零件小部門的技工師傅之職,卻花了數小時討論時,不禁提出疑問。史隆答道:請你告訴我,哪些決策比人的管理更為重要?我們在做好人事決策方面犯的錯誤比較少,不是因為我們會判斷人的好壞,而是因為我們慎重其事。史隆同時強調:「用人的第一個定律就是那句老話:『別讓現任者指定繼承人,否則你得到的將只是次級的複製品。』」
「現任者指定繼承人得到的是次級複製品」?確實如此,人都會挑選跟自己同類型的人。企業組織領導者的選任是如此,宗教領袖的繼任何嘗不是。然而,從《教宗的承繼》中,卻可以發現本篤十六世在與貝爾格里奧的深度對話中,明知他的性格、觀念與行事作風跟自己完全不同,卻屬意他成為接班人──因為本篤十六世知道,只有貝爾格里奧這樣的人才能為彼時的天主教與教廷開創新局。這種大智慧,顯然不是多數人所能企及的。
當然,在天主教會的神學體系中,教宗作為聖彼得的繼承者,始終被賦予至高牧者與信仰權威的光環,已有一套運行千百年的教宗選任制度,並不是由現任教宗指定接班人。
教宗跟其他地方的主教一樣,原本是由教區裡的神職人員和教友達成共識後選出。樞機(主教)團在1059年被指派為羅馬主教唯一的選舉人團後,自此教宗選舉權人明確化。而經過1268年至1271年的選任程序卡關,以致宗座多年出缺,教宗額我略十世(Gregorio X)於1274年第二次里昂大公會議進行期間頒布法令,規定樞機選舉人在選舉期間應被鎖在一個用鑰匙上鎖的房間裡,這奠定了今日教宗選舉以閉門會議召開的形式。
依現行制度,為避免教宗選舉受到政治干擾,樞機團於選舉投票期間,不得離開選舉地點西斯汀禮拜堂,並且統一住在同屬梵蒂岡境內的聖瑪爾大之家,直到選出新任教宗為止。會議規定包含新任教宗需有至少三分之二的支持票才可當選;投票方式為樞機團每一人代表一票,在宣讀誓言後將選票投入票箱,內部宣讀後,對外結果將由教廷燃燒選票通知群眾。若無人當選,會燃黑煙;若煙囪冒白煙,則代表新一任教宗已誕生。
運作近千年、以閉門會議進行的教宗選任制度,由於每次僅有百餘人左右的樞機主教在場,有關於推選教會精神領袖的過程,難免披上神祕的面紗,外人難以一窺堂奧。各樞機主教真的是秉持良心投下神聖的一票?這些神職人員都只追求精神層面的信仰,沒有追逐權力(位)的慾望?有沒有搞小圈圈、派系爭鬥的情形?有沒有如同現實世界的拉票、換票等政治行為?

2024年上映、由雷夫.范恩斯(Ralph Fiennes)主演的電影《秘密會議》(Conclave),講述一場沒有明顯熱門人選的教宗選舉。這部電影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讓觀眾們得以窺見梵蒂岡這個神聖殿堂中的密閉世界,以及天主教會如何選出領袖的神祕過程。由於樞機主教們一生難得有機會參與教宗選舉,據說在方濟各過世準備推選繼任人選前,許多樞機主教還藉由觀看《秘密會議》,以了解、學習教宗選舉過程中所需注意的事宜。
雷夫.范恩斯這位演技精湛、獲獎無數的知名演員,在《辛德勒的名單》裡飾演一名納粹戰犯,在《英倫情人》中化身伯爵,在《007》系列電影最近3集扮演接下軍情六處的負責人(代號M),在《哈利波特》系列電影裡是令人聞風喪膽的佛地魔,到了《秘密會議》中則成為樞機主教團長,擔任教宗選舉秘密會議的主席。
范恩斯在劇中飾演紅衣主教勞倫斯,原本已多次向教宗請辭團長之職,只想單純做個牧者,卻被教宗認為適合擔任管理者的職位,而加以慰留。在整部電影中,雖然這位過世的教宗只有出現「躺著」的鏡頭,但他早已看出教廷可能因自己的繼任人選選舉產生紛擾,遂以其超群的智慧與隱藏的謀略,運籌帷幄,深刻地影響著往後的這場教宗選舉。
原來,在秘密會議正式開始前,有心人士早已展開各種布局,在幕後進行許多的政治操作和權力角逐。會議一開始,出現了幾個熱門人選,有的持改革立場,希望推動教會進入新時代;有人堅守傳統,試圖讓信仰回歸純粹。在這場神聖儀式的幕後,埋藏結盟、角力、計謀層層交織,甚至有人不惜以抹黑對手的方式達成目的,真相與謊言交錯,連勞倫斯都無法置身事外。
一開始,勞倫斯並無意競逐教宗職位,只想要讓自己所支持的自由派代表當選。然而,幾輪投票後,熱門樞機人選陸續發生醜聞事件,讓身處在漩渦核心的勞倫斯不得不行使職權,甚至違反規定而進行蒐證。這些參雜了自身職位權力與政治立場的行為選擇,讓他遊走在自己的信仰邊緣,當選的呼聲卻是愈來愈高。
勞倫斯終於放下對道德的執念,在熱門人選陸續出局的下一輪投票中,寫上了自己的名字。此時卻發生一場突如其來的爆炸攻擊,將彩繪玻璃炸出一個洞,陽光灑了下來,穿過塵土瀰漫,落到在壁畫前倒下的勞倫斯身上。這道近乎神諭的光,像是一道照亮會議晦暗的純粹的光,讓信仰破除權力的迷思,重新回歸主的正道。
最後當選教宗之人,就是一個心靈純淨的牧者、毫無野心,而且其特質隱約有著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暗喻與「男女平等」的宣示。在這個秘密會議的選舉規定裡,只有男性能參加投票和擔任候選人。而這個新教宗彰顯著人類生理性別的多樣性,意味天主教會的走向寬容、性別平權與多元可能,讓人不得不佩服原著與編劇的卓絕功力,也難怪可以一舉奪得第82屆金球獎最佳劇本獎、第97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
在這部改編自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同名小說的電影中,秘密會議是在全然封閉的情況下進行,參與投票的樞機主教們與外界完全隔絕,無法接收任何新聞或訊息,這與真實的選任過程相符。不過,事實上樞機主教之間不得彼此交談,也不被允許進行任何形式的競選活動,是導致選舉過程長短不一的原因之一。這說明電影中樞機主教之間結交聯盟、私下交易等衝突場景,雖然強化了故事的懸疑感,卻與真實歷史是有差異的。
導演愛德華.伯格(Edward Berger)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儘管秘密會議被視為「一種古老的宗教儀式」,他希望讓觀眾看到其中的「現代性」;同時他也指出:「我們把他們放在神聖的地位上,但當你靠近看,你會發現他們也有手機,也會抽菸,也有和我們一樣的煩惱、缺點和秘密。」這也難怪一群樞機主教們在抽菸閒聊後離開時,觀眾會在地上看到一堆菸蒂的場景。

教宗被天主教會認為是耶穌在當今世界的代表,自中世紀起即擁有超乎西歐世俗君王的精神地位。《教宗的承繼》與《秘密會議》卻揭開了這層神聖面紗,呈現出教宗作為「人」的真實樣貌:他們同樣背負個人情感、歷史包袱與道德掙扎。
有人說基督教歷史其實就是西方文明史,這當然是過於簡化和絕對化的說法。不過,天主教在西方文明發展中,確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在中世紀,天主教不僅是宗教信仰,更是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核心。而法學發展,就是深受基督教影響的領域之一。
在古代社會,神職人員往往掌握著對神聖文本的解釋權,而《聖經》或其他文本常常被視為法律的基礎,神學中的正義、公平等道德倫理觀念,也對法律的價值觀念產生影響。法律條文如同《聖經》一樣,都需要解釋與詮釋,據此發展出的「法律釋義學」,又稱「法學方法論」, 它探討抽象的法律規範如何被解釋,並適用於具體的個案。
迄今為止,文義、體系、歷史及目的解釋等解釋方法仍被認為是法學方法論上的重要基礎。而當代最具爭議的解釋論上問題,就是應否採行原旨主義(Originalism)?這主要是《美國憲法》解釋的一個概念,與其相對的則是「活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主張。目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由派與保守派之爭,主要就是源自其對憲法解釋方法上的根本性差異。
原旨主義者主張應該以「通過憲法時」的制定者原始含義或原始理解,來解釋和對待憲法,也就是根據「立法者的本意」解讀法律文本,他們反對隨意運用全新的解釋理論來重寫憲法;「活的憲法」論者則認為即使憲法本身沒有正式修改,其內含也應順應新形勢而作出調整和演變,亦即解釋憲法時應隨著社會的需要而發展,並為政府治理提供更為靈活的工具。
美國原旨主義的興起,源自於對1960、1970年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墮胎合法化、保障刑事被告人權等系列判決有關,說穿了其實是為了《美國憲法》和政治話語權的爭奪,同時也為任命聯邦法官的政治競爭上發揮重大影響力。而這種原旨主義與多元民主之爭,也出現在宗教界,無論各教派,大都存有回歸到原始教義或基本原則的思潮。
天主教的原旨主義,可以被理解為:重視對《聖經》的字面理解,並視為唯一的權威;強調回歸宗教經典和原始教義,拒絕世俗化和現代化;原旨主義思潮與政治運動結合,試圖以宗教原則來重建社會秩序。在《秘密會議》中,就有保守派的樞機主張回歸傳統,使用拉丁文,教宗只能由義大利人擔任,以及其他族群的人不該被委任為主教等;甚至當選舉過程中西斯汀禮拜堂遭到抗議民眾以炸彈攻擊時,還有人慷慨激昂地主張要對異教徒開戰。
在這些說詞當中,有不少是出於政治競爭上的考量,更多的則是出於對世俗化和現代化的抗拒心態。誠如論者所說:當代宗教領袖該如何定位自身使命?在科技主宰、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教會與其他宗教或世界該建立何種對話?當改革浪潮衝擊傳統價值,平衡點該立於何處?而每個追尋信仰,或僅僅試圖理解信仰的人,又能從中獲得怎樣的啟蒙?
這種既要因應改革浪潮又要守護傳統價值的情況,當然不會只出現在天主教會。而天主教會「關起門來」,在神聖殿堂以極為神祕過程選出教宗的方式,似乎與現代社會講求透明、公開與監督的價值觀背道而馳。然而,這種儀式或許是觀眾最著迷的,也正因為其神祕的宗教色彩,而得到信服與接納。
現代社會能夠順利運作,仰賴的是人對他人的尊重、具有理性,社會制度能夠保障個人的安全與基本信賴。可惜的是,無論哪個國家、社會,幾十年來的民意調查卻一致指出:從政府、企業、媒體到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被公眾信任的程度一直快速滑落。這是個欺騙的時代。面對這種信任危機,許多人提出的解方是:公共事務全盤透明化。
劍橋大學名譽哲學教授、英國科學院前院長昂諾娜.歐妮爾(Onora O'Neill)所寫的《信任的力量》一書表示:人們不斷地鼓吹公共事務要全盤透明化,卻忽略了真正關鍵的問題,應該是如何減少詐騙的行為。她在這本將自己於《BBC》著名「芮斯講座」(Reith Lectures)節目的講稿整理而成的書籍中指出:「科技可以輕易而有效率地傳播資訊,也可以廣泛散布錯誤或惡意誤導的資訊。也就是說,有些公開化和透明化可能對信任是不利的。」
誠哉斯言!正如歐妮爾教授所言,如果我們要重建信任,必須減少欺騙和謊言,而不是減少隱密性,保持隱密而不透明未必是信任的大敵,透明化與公開化不該是無條件的。我一向倡議司法人員應該多與社會溝通對話、最高法院廢除保密分案並常態化開庭、各級法院法官事務分配與分案規定的公開透明化,也認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公開播送法庭活動,卻也堅持評議祕密應該徹底執行、法庭活動應該適度地保持儀式性與神聖性。
目前台灣各級法院的合議庭法官在判決前,會進行評議,討論案情。評議過程正如教宗的選任般,通常是封閉的,以確保法官們能暢所欲言,不受外界干擾,而且在判決確定前均不得公開。唯一的例外是憲法法庭,它讓司法院的廳長、研究法官、助理及行政人員等人參與評議,這是援用以前大法官會議開會的模式。
如今憲法訴訟案件既然已經訴訟化與法庭化,並採行言詞辯論化與判決主筆制,實不宜援用過去大法官會議開會需有行政人員在場速記或筆記的模式。這背後涉及的不僅僅是評議祕密,避免資訊外洩影響公眾信任而已,更重要的是大法官如何減少其書面作業、強化言詞辯論與評議效率,以提升其審判效能,俾以受理並妥速審結更多攸關憲法爭議的案件,從而善盡憲法維護者的職責。
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而言,它的審判效能、裁判品質與社會影響力,遠遠超過台灣的憲法法庭。該院法官在評議時,只有9位大法官在場,自不可能出現台灣大法官審查會所謂的「速紀錄」;如果有訴訟文件遞送的需要,再透過聯繫行政人員提供,由座位靠近門邊的最資淺大法官來應門、負責收受文件,因此,這位大法官有最貴、最資深門房之稱。在評議決定出主筆大法官後,大法官彼此之間主要是以書面來交換意見,而非開會逐句、逐段共同討論判決的文字內容。主筆大法官在綜合各方意見並修改完之後,成了最終對外公布的法院判決。

司法院在研擬「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草案時,原本有意仿照憲法法庭的評議模式,讓行政人員可以進去會場協助處理各項行政作業事務。我以前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運作模式及自己實際進行過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經驗,表達不同意見,才有如今「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41條「原則不行、例外可以」的規定。
我於《國民法官法》施行前在台北地方法院擔任審判長的一場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時,仿效比利時陪審制的作法,不僅於評議時採取祕密投票的方式,而且開票後當場立即銷毀投票單,如此即可避免個別國民法官的投票決定為他人所知悉。
比利時曾受法國統治,這種評議方式可能受法國法的影響。在法國重罪(參審)法庭的投票規則中,每一位職業法官和參審員都會領到一份蓋著重罪法庭印戳的空白票,上面印有下列字樣:「本著我的榮譽與良心,我的意見是……」。職業法官與參審員在自己的票上寫上「是」或「否」,票上的內容不得讓其他人看見。每一個人把寫好的票疊好,交給審判長,由審判長投入票箱。票箱在啟封統計之後,表決單應當立即燒燬。
比利時、法國參審法庭這種評議過程的運作模式,與《秘密會議》中樞機在投票前會發出「主基督為我作證,祂會論斷我,我將選出我認為符合天主旨意,應當獲選的人」的誓詞,以及開票後立即燒燬的作法,非常雷同。我想這應該與比利時、法國都是以天主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甚至天主教曾長期被法國列為國教有關。
台灣民主轉型後,司法公信一直不高,原因有待深究。長期關注民眾法意識的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王曉丹在〈司法意識與司法信賴──權威、感知與正義觀〉一文中指出:西方法律傳統起源於中世紀的教皇革命,與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傳統具有緊密的關係,之後的路德革命確認了個人神聖不可侵犯性,並確保了凌駕於個人的法律權威;我們一心嚮往的西方社會(例如美國),一直致力於司法神話的建構,透過新聞、影視、小說、公共論述等,不斷再現司法正義的形象,因而確立司法權威,在民眾心裡屹立不搖,成為穩固的社會共識。
台灣作為華人社會的一環,「愛民如子的父母官」、「日斷陽、夜斷陰」的包青天形象,反映出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的特色與司法神話。雖然包青天式的正義觀與司法意識未能完全契合當代社會的法治理念,且當代法官的審判權限來自於人民的授權,不應該再有「父母官」高高在上的心態;但司法的本質是剝奪人民生命、自由或財產等權利的合法暴力,其權威的基礎往往來自於「神話」。王教授告訴讀者,唯有在理解司法與人民於文化認知及情感框架的差異之後,創造新司法神話,不信賴的社會基礎方能有所轉變。
如何創造新司法神話?這沒有簡單的答案。源自基督教文化的刑事司法觀,孕育出正當法律程序、合理懷疑、司法的被動性與超然性等刑事訴訟理念,正是創造現代化司法神話的基礎。另外,在強調司法公開透明化的同時,保有一定程度的祕密性、神聖性與儀式性是必要的。其中關於評議祕密一事,已如前述。
在神聖性方面,世界上有許多地方的文化傳統,將法律認為是「神意的表現」,美國社會依其信仰手按《聖經》作證或宣誓,伊斯蘭社會則是按《古蘭經》宣誓作證;甚至2009年1月13日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依慣例在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的引領下宣誓就職,卻為了歐巴馬調換了某句誓詞中字詞的順序,因為擔心宣誓是否有效的問題,而不得不慎重其事地在隔天重新宣誓一次。
華人社會的玉皇上帝(天公)、媽祖、城隍等宗教信仰原本也都一定程度反映在司法文化當中,清末民初繼受西方法制時,卻因過度追求世俗化國家,立誓與盟約等傳統文化完全未融入政治與司法體制中,以致證人在法庭作證時完全不帶有宗教意涵。如今已難以翻轉這種法庭立誓模式,但由於證人「具結」義務與「結文」內容不夠白話,法官仍可適度加以曉諭,使其知悉「具結」即相當於在神明面前發誓,從而提升其敬畏心,避免虛偽作證而使人蒙冤受屈。
台灣社會日常的廟會、每年的媽祖繞境活動盛行,政治人物更是逢廟必拜,這代表宗教信仰迄今仍深入人心。而許多的廟宇或城隍都帶有審判善惡的功能,如今強調多元寬容、人權尊重的司法當然無法再融入神判儀式,但仍可借助宗教以發揮調解糾紛的功能。
對於天公、城隍信仰素有涉獵的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黃傅偉即指出,城隍、地藏王菩薩等神明不只處理人死後的世界,也處理陽間民眾事務的不公。民眾在陽間司法體系受到的委屈,或對司法人員的不信任,常寄望透過城隍等司法神祇,以洗刷冤屈或作惡救贖的機會。
這說明民間信仰可以作為審判外尋求正義的一種價值觀,在推動修復式司法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DR)的操作上,輪迴觀、因果報應等信仰有助於讓加害者面對真相、承擔責任,並讓被害者有機會放下、寬宥對方,成為促進關係修復的媒介而定分止爭。2025年間7月間台南地區有一爭訟事件,當事人雙方都不願意前往對造律師事務所簽訂協議,某日雙方律師在台灣首廟天壇偶遇,遂提議改選法院或天壇簽約,雙方都選擇了後者,最後即在天公的見證下簽訂和解契約,成為一段佳話。
至於在儀式性方面,以國民參與審判為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宣誓辦法」明定法院應使宣誓場所莊嚴隆重,以提升國民法官執行職務的使命感。我在前述主持的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時,即特別重視宣誓、儀式的重要性與神聖性這件事情。
另外,在製作國民法官流程圖簡報檔中,我特別製作一張「法庭旁聽注意事項」,並交代通譯於中場休息時投影呈現,內容為:「國民法庭法官是受全體國民的託付,依據《國民法官法》規定,行使審判上的權力。基於對國民主權的尊重,國民法庭法官蒞庭或退庭時,在法庭之人均應起立(遵從法警人員口令);除了急事須及時處理之外,入座後不要隨意走動。感謝您的配合。」
當時某位旁聽這場法庭活動的民眾在Facebook寫下回饋意見,表示:「這種審判工作的沉重性,不透過言詞,而是藉由國民法官親身實踐的參與及溝通,以其參與整個儀式後的心態轉變(類似神話學的英雄旅程),作為司法資訊的強力傳播者……。」我想,這或許是創造新司法神話的一種呈現方式。
最後要說明的是,雖然本文建議可以適時將信仰作為審判活動的媒介,但司法人員仍應意識到保持宗教中立的問題。因為作為政教分離國家的執法者,應避免認同特定宗教;即使僅是輔助說理,援引宗教經典,哪怕只是名稱而不是教義,還是能免則免。而這二部電影告訴我們:即便理念不同,真誠對話仍能在鴻溝間架起橋梁。在政治極化與民粹主義盛行的當代社會,司法人員應學習方濟各謙卑服務並順應時代變革的精神,深刻了解民瘼之所在、誠實面對案件與當事人,並積極與社會溝通對話,這或許才是提振司法公信最需要的智慧。
法律人也追劇?當然,只是他們不會在法庭上告訴你而已。有的法律人不僅愛追劇,更希望解讀及探討影視作品中的法治文化意涵,並讓司法改革可以更加通俗易懂。
《報導者》在週末開闢「法律人追劇」專欄,邀請曾以《羈押魚肉》一書獲得金鼎獎的台灣高等法院法官林孟皇、雲林地方法院法官王子榮等法律人執筆,每月一篇與讀者相見。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