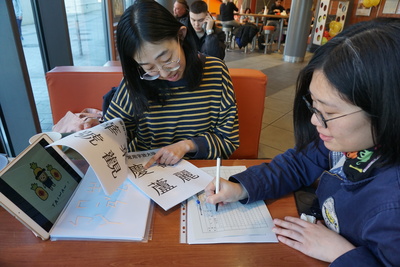2024年總統及立委選舉後,台灣政壇再度出現2000年時的「朝小野大」局面,近一年來朝野立委衝突不斷,立法權與行政權強烈對峙,因而捲動史無前例的立委「大罷免潮」,截至2025年5月14日已有30個選區罷團宣布第二階段送件並達法定門檻,現由各地方政府選委會查對中。台北市長蔣萬安主張「倒閣」之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及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則強調應該「罷免總統」。
從罷免立委、倒閣(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到罷免總統(立法院對總統提出罷免案),牽涉的憲政法治層面相當複雜,《報導者》擬訂10個問題,邀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張峻豪、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蘇子喬、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3位學者專家回答,希望協助讀者釐清憲政法治層面疑問。
以下是與罷免立委、倒閣、罷免總統相關的憲政體制10問及學者回答。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張峻豪(以下簡稱張):

大部分民主國家對於罷免行政官員或國會議員都比較謹慎,《中華民國憲法》則是在公布實施的時候,就納入罷免權,這當然與孫中山有很大的關聯性,所以我們的《憲法》上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這四項權利。制憲者其實也比較謹慎,創制與複決另以法律定之,所以我們看到後來會有《公民投票法》,可是罷免是直接透過「憲法保留」的概念,寫到《憲法》裡面,所以有了一個幾乎獨步於全球的制度。
在當時中國大陸識字率不高的大環境下,制憲者還是認為罷免權是一項重要的權利,思想非常先進地將罷免放入《憲法》,因此我一貫主張,必須對於《憲法》上的罷免權予以尊重。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蘇子喬(以下簡稱蘇):

歐美國家在談參政權或公民權的時候,最主要談的是選舉權,再進一步延伸強調的是公投,就是創制權與複決權。罷免權在國外所講的參政權裡面是比較次要的,就是剝奪職位。
很多國家雖有地方層級的行政首長跟地方議員的罷免,可是在全國層級、人民直選總統跟國會議員,就很少有罷免權。
這必須先說明學術名詞「強制委任」與「自由委任」。強制委任意思是指民意選出國會議員,他一定要代表民意,做不好就可以罷免他;可是民主政治的常態是國會議員仍有一定獨立判斷的空間,不見得完全是選區的代言人,這就是自由委任。
民主國家認為地方首長或地方議員必須完全代表民意,做不好或不符合民意就可行使罷免權;但全國性的國會議員則不只是代表民意,更有考量全國人民利益的含義,況且國會運作並非單一議員就能主導,不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決策者角色,因此在國會議員的制度中很少有罷免制度,而是以定期改選的方式課予政治責任,檢視是否仍獲得多數民意支持。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以下簡稱林):

地方首長有點像是地方的總統制,首長握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多數國家都會設計定期改選,若做不好要提前罷免,還具有正當性;但民意代表並沒有獨立的行政實權,在議會內是集體合議制,任期上也不會有限制,只要民意支持就能一直連任,用罷免在任期期滿之前拉下來就比較沒有正當性。
但即便是行政首長罷免,其他國家也相當罕見,只有相當極端的情況,通常都會跟首長對地方重大開發案態度轉變有關,才有機會被罷免。
持平而論,從《憲法》第133條條文:「被選舉人得由原選區依法罷免之」而言,其實制憲者期待是回到被選舉人與選民之間的代表性關係,也就是他表現得怎樣,他有沒有辜負選民的委託;後續訂定的法律在技術層面上,恐怕卻讓制憲者的初衷受到破壞,尤其是現在馬上就能夠利用這一套制度來處理三黨不過半問題,導致選民檢視的不只是被選舉人的個人表現,這個是制度層面上需要檢討的地方。
但反過來說,藍白立委目前在立法院的表現,其實也加強了這個制度的負面效果。藍白立委透過多數席次,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修正案,都一概地想要用立法權來凌駕(行政權)的時候,反而更加添柴火、彰顯這個制度的效果。現在的「大罷免」已經脫離原選區,變成說罷免某某某就等於罷免傅崐萁,形成選民對一個政黨投下不信任票,這個會是接下來觀察的重點。
蘇:《選罷法》第75條第一項規定,公職人員「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到底不得罷免的意思是不能罷免提案,還是不能為罷免?這個爭議點在2020年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時作出解釋,是不能為罷免投票,換言之,就是在當選後,即使未滿一年也可以開始進行提出罷免案前的動員動作。
林:選舉跟罷免都是民意的反映,選舉是正面反映,通常是兩個候選人以上,我喜歡誰我就支持誰;罷免是負面民意反映,我反對誰就拉下誰。罷免並沒有不行,都是一種制度的選擇,但罷免可能會讓社會頻繁政治動員,若有其他制度設計,或許可以考慮不用罷免。
任期開始多久後可以罷免,要跟任期長短一起考慮。如果任期短如2年,那或許不太需要罷免;如果把任期拉長超過4年,然後讓罷免容易一點,這也可以考慮。不過綜合各國經驗來看,定期改選仍比罷免來得好一點。
台灣立委過去任期是3年,後來修憲改成4年。台灣總統任期是4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韓國總統任期是5年,不得連任。可見任期長短、連任限制跟罷免都是一種選擇,很難說誰好誰不好。

張:我們已算是愈來愈成熟的民主國家,雖然我們有愈來愈激進的罷免制度,但是我從來不覺得罷免會形成一種龍捲風的浪潮。也就是說,在每一次選舉完,是不是大家都會進入到罷免的這種情況,我其實是保留的。
現在過於激進的罷免門檻,只要25%選民投下同意票就可以罷免,最有可能造成的問題,其實是未來這些代議士或是行政首長的表現會愈來愈動輒得咎,對於選區裡面可能比較高度爭議的法案,或者是鄰避設施,反而會不敢做決定。我覺得這個才是真的要思考罷免所產生的負面效果。
蘇:罷免門檻其實很主觀,因為全世界有罷免制度的國家已經不多,日本、韓國地方議員或地方行政首長的罷免制度,門檻都不太一樣,要件也不太一樣,很難說找到一個客觀的、大家公認的標準。
就我個人的主觀觀察,2016年底修法降低罷免門檻之後,罷免案變多了,就代表提議人認為比較容易通過。所以我個人會覺得,目前的罷免門檻確實是有點偏低,因為現在的罷免規定之下,確實會造成被罷免通過的人,他的通過票數是低於當選票數的,我覺得這個是不盡合理,像陳柏惟他的當選票數比罷免同意票數多了2、3萬票,我認為25%的門檻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
此外還有投票率的問題。通常全國性的選舉投票率高,罷免的投票率相對較低,不是「大罷免」的話,投票率相對更低;但如果罷免票數需要高於當選票數,門檻難度又太高了。所以我覺得標準不太容易訂定,我目前也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客觀的答案跟標準。
林:台灣目前罷免門檻的設計是中間難度,不會非常容易,但也非遙不可及。很多人的印象可能來自於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罷免案,只是韓國瑜一選上市長就要選總統,最後成為罷免教科書般的特殊案例,難以作為標準。
衡量其他罷免案例,會有兩種狀況:單一選區如立委通常是兩大黨選舉,兩方激烈競爭之後常見一方險勝的結果,但過去被成功罷免的立委只有陳柏惟一席。複數選區如議員,因為一個選區內當選多個名額,會造成只要其他反對陣營聯合起來就能罷免最高票當選人,最低票的當選人當然也更容易被罷免;不過觀察直轄市議員的罷免結果,桃園的王浩宇雖然罷免通過,但高雄的黃捷就沒有成功。
至於罷免門檻應該要更嚴格還是要再放寬?要看實際上的方案,若改成非常容易,那會造成政治過度動員,無法支持;要調高到幾乎不可能罷免,那也不好──如果一個制度在現實狀況幾乎不可能發動,那絕對是個壞的制度,應該朝廢除來思考。

張:我自己在東海大學看著中二選區從罷免到補選,然後還有一個再選,整個過程裡,地方上其實只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斷在傳達仇恨值。罷免是投仇恨票,讓選民更討厭這個被罷免的對象。這個選區好像就一直是在選舉,這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罷免制度,民意代表在選區的經營變成不是要把餅做大,會形成只是去鞏固我的支持者;對於那些討厭我的人,跟我對立的人,我是不是需要去開拓他呢?可能不需要,因為任期就4年而已,而4年裡都在忙著防禦罷免。
我個人研判未來政治光譜的極化現象或者是對立會愈來愈嚴重,也就是選舉已經很對立了,再加上罷免又加添柴火,未來負面投票、負面選舉的狀況會愈來愈明顯。
但正面來說,政治極化已經是全球現象,造成現有政黨認同度一直降低,台灣已經有這樣的現象,我認為未來會持續下降,已經從4成到3成5,甚至現在已經掉到3成,有學者做的資料已經降到2成多。
政黨認同度不斷下探的結果,容易造成第三勢力的出現。若加總歷來政黨票的比例,會發現藍、綠跟第三勢力,不管是民眾黨或是其他第三勢力,其實是三分天下。我認為這個狀態會愈來愈明顯,所以我不會講說,罷免一定是對民主不利,而是說現有政黨支持度都下降,那未來可能有一個新的第三勢力出現,產生一個新的寄託,只是現在暫時還沒有出現更新的第三勢力。
反面來看,罷免不要講是仇恨動員,但可說是一種負面的動員。罷免投票是「一個人的武林」,基本上提案的人要不斷說被罷免人的壞話、說這個人多不適任,那被罷免人要去為自己辯護,而不是要跟另外一個人競選。
「不是去講誰比較好,而是說我沒有那麼壞」,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負面選舉、負面投票或負面動員,我覺得這會造成政治的極化現象變得更明顯。一般民主國家沒有把罷免制度作為一個普遍制度,有可能是考慮到這個因素,避免造成政治極化。並不是說一般選舉就沒有極化現象,但選舉中至少還有一些政策議題的論辯,然後展現自己的優點跟別人去相互競爭。
林:雖然我認為罷免民意代表不見得是一個好的設計,但台灣這次的大罷免潮不能當成單純的罷免,必須搭配立法院過去一年的脈絡來理解。
我觀察台灣政治30多年,從沒看過台灣政治如去年(2024)的情形,國民黨和民眾黨立委的表現是沒有要跟民進黨溝通,屢屢在國會直接沒收討論程序。藍白陣營完全否決對方陣營跟司法的正當性,不斷批評對方是「綠共」、「獨裁」,指控本應獨立的司法是對方的附庸,這些行為只能理解成是要把民主的正當性摧毀。即便是在2000年到2008年扁政府朝小野大的時代,當時甚至擁有多達三分之二國會席次的國民黨都沒有這樣做。
過去罷免都是針對個人,但這次大罷免針對個人的好惡被稀釋掉了,而是針對藍白立委過去一年行為的全面性反撲。因為在台灣目前的憲政制度設計下,行政權無法主動解散國會,才會陷入僵局,大罷免才會很弔詭地成為唯一反制的手段。
老牌民主國家的政治癱瘓其實不罕見,但民主政治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必須要找到妥協的共識,而其前提是不完全否認對方的正當性。遇到政府失能,其他政治團體會開始施壓,逼迫對方慢慢妥協。
張:罷免權是制憲者設計的其中一項參政權,如果人民藉由這樣的權利改變國會席次,必須給予相當程度的尊重。只是當時制憲設計是以中國為思考,將這個設計放到台灣來實行,台灣地方小,議題擴散出去的可能性很大,已經不僅局限於地方性問題。以台中中二選區為例,當時(指2021年立委陳柏惟罷免案)已經討論到年輕人買不起房、地方派系把持政治等,這些跨區問題甚至引發全國關注,讓設籍在選區但在外生活的選民趕回來投票,這與當初制憲設計罷免權的精神是否相符,是後續必須關注之處。
此外,仍要提醒在野黨,在這次罷免過程當中,公民社會的想法與在野黨的想法差距愈來愈大,從很多面向都看得出來,如果真的因為大罷免而改變國會席次,這是最大在野黨需要很警惕與檢討的問題。
蘇:如果真的發生透過罷免權改變上一次國會選舉的結果,這個做法在制度上不能說不對,因為這就是現行制度,所以執政黨或許真的有這個動機。
不過就結果來講是不好的,因為從全世界來看,真的沒有看到有任何案例是透過罷免的方式去扭轉國會朝小野大的格局,從少數黨變多數黨。如果是總統制國家就是定期改選,遭遇僵局就是要盡可能去協商,等到下次大選才能改變情勢;如果是內閣制或是半總統制有可能是解散國會,用罷免幾乎是沒有。
我覺得這次不管有沒有真的扭轉國會朝野結構,就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罷免被認為是一個可行的手段,如果這樣運作下去,我認為後面的罷免案會不斷出現。我要強調的是,罷免制度運作之下,冤冤相報何時了?當罷免門檻不高,所以國會朝野結構被扭轉之後,另外一方找機會再發動一次,整個政治結構是很浮動、很不穩定的。
這就要回到罷免本質的討論,罷免不應該是政黨競爭之下,決定國會中席次多寡的主要制度工具。整體來說,大罷免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會是「短多長空」,如果真的藉由大罷免發生多數黨翻轉,政治極化將不只局限於選民,而是整個政壇都是如此,那種對立與仇恨將會更加白熱化。
假設大罷免後民進黨變成國會多數,或許目前的危機能夠緩和,但對長期民主來說是不是好事,還有待觀察。反過來說,若藍白在大罷免後仍維持國會多數,也不排除原本削弱民主正當性的行為會變本加厲。
作為法律人,我認為憲法法庭極為關鍵。讓司法癱瘓是威權國家常見的前兆,若憲法法庭被癱瘓,台灣選舉能否撐到2028年都令人擔憂。還好台灣還有強大市民社會動能,這跟2014年的318學運不同,當年國民黨是完全執政,公民社會都還能救台灣,現在條件不會更不佳。

張:有政治人物主張倒閣,不管動機如何,這是一個相較於罷免,可以真正透過憲政機制來解決憲政爭議的做法。可是我目前的觀察,包括蔣萬安提倒閣,可能與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比較有關係。
國民黨後來主張的倒閣是同時訴求總統下台,這是對於憲政爭議處理機制的知識不足,因為台灣是雙首長制的國家,我們就是雙元行政首長(總統與行政院長),所以倒閣案發生在行政對立法負責,此處的行政是行政院長,當然跟總統沒有關係。總統是民選,有民意基礎,怎麼能以倒閣要總統下台。
回到倒閣議題上,台灣的憲政如果可以走第一次國會重選,以後走順了之後,就會回歸到很多民主國家的常態。碰到政治僵局真的窒礙難行,倒閣後就解散國會來檢視新的民意,這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想法。
蘇:聽到倒閣被討論的時候,我是還滿樂觀其成。制度上,倒閣後總統不一定要解散國會,決定權在總統,不過台灣作為一個半總統制或稱雙首長制的國家,我們能夠解決僵局的制度設計就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立法院倒閣之後,如果總統還是任命自己人當行政院長,不解散國會,那立法院可以再倒閣,一直倒閣到總統願意接受立法院多數政黨認可的人當行政院長為止。憲政體制運作之下,立法院可以透過倒閣去爭取執政權或一定的組閣權,但這個前提是多數黨也不怕解散國會。
國會解散重選,誰在國會大選中獲得多數,就是由誰來組閣,因為這代表新的民意。如果民進黨重選獲過半數,那就是民進黨組閣,中央跟國會一致;如果還是藍營占多數或藍白聯盟占多數,那應該就是由立法院多數來組閣。
如果總統不願意讓在野黨來組閣,總統也應該要尋求綠白聯盟組閣,理想制度設計應該是這樣,誰在立法院占多數就組閣,這樣行政立法就沒有那麼對立了。這種情況之下,有可能總統跟閣揆是不同黨,那就要承擔(可能造成對立的)成本。兩害相權取其輕,我覺得國會多數黨或多數聯盟來組閣,這個運作就是解決僵局的一個方式。
林:倒閣跟大罷免的效果可能類似,但主軸不同。大罷免是針對藍白立委一年多來表現的一個整體回應,像是民意的直球對決,社會會關注在國民黨立委的表現上(因為民眾黨皆為不分區立委,無法被罷免),希望藍白能懸崖勒馬;而倒閣後若總統解散國會跟改選,就只是提前選舉而已。
回到制度面上,因為台灣行政權沒有解散國會的主動權,不然的話,解散國會重新改選應該還是一個好的方式。

張:立法院這個會期快要結束,如果真的要推動倒閣,立法院勢必得開臨時會通過倒閣案,總統若宣布解散國會,依法必須在60天內進行國會重選,時間點可能會落在8月罷免投票之前,在這段期間國會休會等待新國會產生。如果重選結果出爐,罷免的標的消失,自然就不會有罷免投票。
蘇:這是法律上要怎麼解釋的問題,倒閣之後如果真的解散國會,解散之後的國會議員不是馬上解職,是處於休會狀態,等到新的立委就任的時候才職務交接;此時罷免案還是持續當中,但如果罷免投票尚未進行,而國會已經改選完成,那罷免案基本上就被蓋掉了。
林:法律行為依照效力發生時間點來評斷,若某位立委罷免通過,中選會作出公告讓某立委失去身分,在那之後才解散國會重選,依照《選罷法》,他就不能在原選區擔任候選人;如果大罷免進行中還沒有結果,但發生倒閣並且國會改選,他還是可以參選原選區職務。
張:對國民黨來說,當國會跟總統分開選舉,對他們是有利的,因為總統選舉就會帶動國會議員選情,被稱為「花車效應」,在這樣的選舉狀況下,國民黨總統選舉這三次都是輸給民進黨,近10年來嚐不太到甜頭,所以拆開來選,對國民黨應是比較好的。
第二個重點是在學理上面,我在歐洲很多半總統制國家做過訪談,問過很多半總統制國家學者 ,他們都覺得台灣合併選舉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像奧地利學者就說,奧地利甚至透過《憲法》規定總統和國會不能一起選。為什麼?因為這兩個都是半總統制重要的憲政民意機關,一起選,選民到底要投票給誰?他們覺得拆開投票才合理。而我的長期主張也是認為總統與國會必須拆開來選舉,像是法國就隔兩個月的時間,台灣完全在同一天是非常奇怪的事。
過去的理由說要節省選舉支出,這是經濟考量,但從學理上來看,分開來選對憲政運作是比較好的,而且國會與總統彼此互相對抗的正當性,也是存在的。如果同一天選出來,總統與立委都代表新民意,當處於「分立政府」時就會有衝突;但若是不同的時期選舉,然後產生不同的民意,我覺得會有更清楚的責任政治的概念。
蘇:當總統跟立委同一天選的時候,選民比較不會分裂投票,所以總統跟國會比較不會不一致,一般認為這還是一個優點,比較不會造成朝野分立,可是不能保證如此,因為去年大選還是發生了(朝野分立)。
同時選的缺點則是國會主體性變弱,因為整個政治的焦點跟媒體鎂光燈焦點都在總統選舉,所以國會選舉的主體性會被掩蓋,在這樣情況之下小黨的能見度就更低。
此外同時選還會造成一個缺陷,例如政黨輪替時,舊總統卸任要換新總統會有4個月的空窗期,如果同一個政黨還好,就像去年一樣,政務還是照常推動;但如果是2016年的狀況(馬英九卸任、蔡英文當選),出現政黨輪替,就會有4個月的看守內閣,等於是國家要空轉超過一季的時間。
如果總統、立委分開選的話,國會的主體性就會變高,政黨提出政策議題比較會被討論,不分區立委也有比較多的宣傳空間。不過,屆時「新總統舊國會」或「新國會舊總統」不斷交錯,分立政府的可能性變高,政治衝突是否加劇也讓人滿擔憂的。
所以整體來說,總統與國會分開選、同時選都各有優缺點。
林:當初《憲法》設計的本意,應該是總統跟國會是雙核心制度,必須要同時產生。如果依照這個精神,總統、立委選舉應該還是同一天進行,較能符合《憲法》本意。但如果解散國會後依規定重新起算任期,之後很難透過總統或立委延長任期切齊,因為大法官曾經宣告延長任期違憲。任期錯開後,可能會出現更強烈的「我(總統或立法院多數)才是最新民意」訴求與壓力,政治上的攻防可能會比目前更強烈。

蘇:2006年時立法院針對時任總統陳水扁提出好幾次罷免案,當時是國務機要費,以及第一家庭問題,連民進黨內部都有聲音希望總統下台,但仍未通過三分之二高門檻。現在藍白國會席次加起來就是過半多一點,民進黨也沒有要反對自己的總統,現在要提罷免總統幾乎是不可能。
從政治觀察來看,我覺得這是為了呼應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倒閣提議,朱立倫作為國民黨領導人,必須要提另外一個方案來回應,所以提罷免總統。
但這就是一個政治宣傳跟口號,可能藉此來凝聚藍營,或是非綠陣營的凝聚力,我覺得這事情既然不太可能實現,你一直喊,到底是能夠凝聚多久?尤其是很多民眾不了解罷免總統的門檻規定,還以為罷免總統跟罷免立委是一樣,我覺得這訴求還是滿民粹的。
林:法律上只要符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在野黨想要推動罷免總統不成問題,只是會不會過而已。政治上比較有趣的是,藍白也知道總統罷免不會成功,但現在拋出罷免總統,策略上是不斷轉移跟稀釋焦點,讓目前罷免議題更加多面向與更多混亂。
張:從去年立法院開議以後,《中華民國憲法》就遭受一大堆挑戰,最後發現真的是找不到可以解決憲政紛爭的機制,來處理三黨實質不過半的問題,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所有想要解決的憲政機制全部都走不通,所以考慮修憲非常具有必要性。
尤其是三黨不過半的部分,很多學者都會主張將閣揆同意權還給國會,但我要強調,還給國會還不夠,其實大多數的先進民主、新興民主國家都會加上一些機制,譬如閣揆經由國會同意這個說法以外,還要加入假設不同意怎麼辦?因為現在很大的問題是,我解散國會,我重選以後,如果還是三黨不過半,總統還是任命民進黨籍閣揆,但是大多數的新興民主國會,要求總統一定要諮詢國會的最大黨來提名,或按照國會的比例來提名,才能達到制衡效果。
蘇:恢復立法院的閣揆同意權是重要的,1997年修憲拿掉之後,當總統與國會多數黨不一致時,就會產生問題,如果有閣揆同意權,至少會有一個安全閥。
或者這樣說,應該由國會多數黨來組閣,不是說總統就沒有權力,因為提名權還是在總統手上,他還是可以任命一個協商出來的人選,可以得到國會多數支持的人當行政院長。總統有閣揆提名權,立法院擁有同意權,兩方共同默契形成的人選,就可避免造成朝野的對立,或是朝小野大的情況。 另外是修憲讓總統可以主動解散國會,像法國總統就可以主動解散國會,可是還要有一個防弊設計,因為如果總統隨意解散國會的話,會造成總統濫權,所以要配套,即由國會多數黨組閣,所以立法院要有閣揆同意權。這些制度配在一起就變成,總統如果敢主動解散國會,那就是重選後由國會多數黨組閣,達到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平衡。
林:總統制運行得比較好的只有美國,中南美國家的總統制幾乎都是軍事政變獨裁的前階段;而內閣制又只會出現在有深厚傳統的民主國家,難以複製。所以愈來愈多比較政府研究者相信,半總統制是比較好的制度,許多國家也都是半總統制。
制度選項上,台灣的半總統制可以維持,但為了要避免這一年多來的窘境,賦予行政權、總統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應該是很必要的。假設有主動解散國會權力,或許現在的大罷免就可以不用發生。
若讓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權,需不需要把過去曾經修憲修掉的「立法院有行政院長的同意權」再修回來作為配套?兩者不必然掛鉤,如果立法院有同意權,總統必須要提名多數同意的閣揆,那就是偏向法國的半總統制;如果總統可以直接提名行政院長無需立法院同意,那就是偏向總統制,這都是選擇題。
除了制度選擇外,台灣還有非常嚴重的中國威脅,這個危機愈來愈明顯,必須納入這個獨特性思考。像現在有立委用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來質疑自己的政府,這是過去不會發生的情況。就算台灣的憲政制度修得再好,重點仍取決於政治行動者是否同意捍衛民主的邊界。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