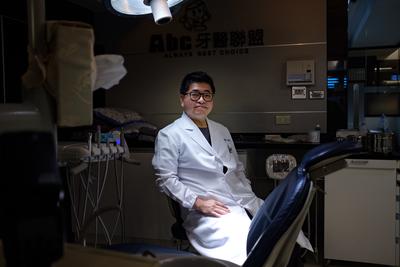讀者投書

愛滋病發現的前幾年,全球衛生界並沒有即刻動員。除了頭幾年疫情受限於高度發展國家、一開始對這個全新疾病更存在諸多誤解和汙名外,時任世衛組織總幹事對初級健康照護的關注也讓針對特定疾病的垂直手段較難獲得支持。直到1986年世衛組織成立自己的「全球愛滋病計畫」(Global Programme on AIDS)開始,到1996年在跨部門合作的需要、捐助國施壓、世衛組織失能等多重因素下成立了跨部門的聯合國愛滋署(UNAIDS),逐漸地愛滋病開始獲得超越健康部門之外的關注。2000年愛滋病被列入千禧年發展目標中(唯二列名的疾病),2001年聯合國召開愛滋病特別大會,2003年當選世衛總幹事的李鐘郁博士將愛滋病列為其政策核心,提出了「在2005年前為300萬人提供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遠大目標,展現了愛滋病在聯合國體系內日趨重要的地位。
此外,2001年聯合國祕書長安南(Kofi Annan)、世衛組織總幹事布蘭特(Gro Harlem Brundtland)等人進一步促成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2002年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則成立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PEPFAR),都為全球愛滋行動注入可貴的資源以及機制。這些豐富的資金來源,使得全球愛滋病發展援助金額即使在2008年金融風暴下,僅是成長趨緩而不致減少。20年過去,隨著愈來愈多其他健康議題進入大眾目光,包括COVID-19疫情的威脅,PEPFAR的年度預算仍然穩穩地維持在每年7億美元的高點。今年(2021)9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宣布將指派現任非洲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Africa CDC)主任、喀麥隆出生的恩肯加松(John Nkengasong)接任領導PEPFAR,將是這個重要職位首次由受援助國出身者擔任,也讓人期待這項重要計畫持續轉型進化。
除了國際組織和政府部門外,愛滋社會運動也是去除疾病汙名及推動治療平權的重要力量。在疫情首先爆發的美國,愛滋社運奠基於1970年代在性解放與同性戀去病化等戰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志運動,在去汙名化、安全性行為、乾淨針頭計畫、藥物研究開發等議題上多有突破。在南非、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更有許多爭取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可近性的成功事例。
這些運動中的人物(如曾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運動者阿赫馬 [Zackie Achmat])、組織(如英國的泰倫斯.希金斯基金會)、符碼(如粉紅三角形),都成為當今社會中重要的行動者以及政治文化象徵。運動者出身的史塔伯(Sean Strub)的自傳《死亡人數》(Body Counts)、記者法蘭斯(David France)的《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以及作家舒曼(Sarah Schulmann)今年剛出版的《讓紀錄說話》(Let the record show),都提供了珍貴而深刻的文字記載。中文資料方面,去年(2020)美國著名愛滋社運人士克萊默(Larry Kramer)過世時,《轉角國際》上登載的這篇文章則講述了克萊默與另一位重要的人物:美國疾管署的佛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在愛滋公衛政策上的重要論戰。
不過大多數的上述文獻著重在這些運動對國內政策的影響,一來健康政策主權大多仍在國家手中,而運動者的代理人(agency)身分也會受到國家區域疆界限制。但愛滋社會運動是否也對全球治理帶來影響?學者曾將愛滋社會運動區分為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從愛滋病的發現到1990年中期,社運對汙名化、政府乃至於整體社會的無視及不作為展開激烈的反抗;
- 第二個階段(1990中期到2000年中期)則大致從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發明開始。有效藥物的出現使北方國家(global north)的社運相對趨緩,卻在資源較缺乏的南方國家(global south)掀起新的戰線,這個時期的愛滋社運逐漸更關注透過跨國協作來爭取資金、藥物,更具有全球公民運動的特色;
- 2000年中期之後的第三階段則見證了運動的碎片化(frangmentation)與衝撞力的相對減弱。另一方面,許多運動者從街頭轉進國家政府與其他治理機構參與愛滋防治。
其中,1990中期到2000年中期的第二階段時期──全球愛滋公民運動逐步興盛的年代,充分彰顯愛滋病公民團體與運動者的影響力如何超越國界,對全球健康治理機制帶來翻轉。

「當時公衛界傳達的聲音都是『小心愛滋病,得愛滋病會死掉』,其背後的意涵是那些已經被感染的人就是會死掉也沒辦法了。我們的口號『正向地與愛滋共存(living positively with AIDS)』就是在反抗這樣的態度。」
擴大感染者參與的影響不只在全球治理上,今天的愛滋病相關論述以及愛滋病治療的快速發展,都受益於感染者沒有被無謂地排除遺忘。但在代表性由主權國家把持的全球治理體系中能夠做出這種空前的創舉,絕對是運動者對於感染者、公民團體、草根運動者在決策過程中參與的堅持的重要實質成果。

本世紀初全球3,000多萬名愛滋感染者絕大多數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在急需藥物治療的族群(約600萬)中則只有不到一成能夠取得藥物。2000年的世界愛滋大會在南非德本舉行,是這場會議第一次在南方國家進行,而全球愛滋社群聚焦藥物可近性議題。主辦國南非的時任總統穆貝基(Thabo Mbeki),一個愛滋懷疑論者,卻與他的衛生部長在會議上發表懷疑愛滋病真實性、藥物有效性的言論。剛成立不久的南非「治療行動運動」(TAC)則高分貝地反駁。整場會議成了雙方激烈交鋒的場域,並將可近性議題拉上了國際檯面。
感染者、治療行動運動的創辦人、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阿赫馬(Zackie Achmat)將這場會議對全球藥物可近性戰線所帶來的深遠影響稱作「德本效應(The Durban Effect)」。在接下來幾年內許多重要里程碑一一達成:世界貿易組織通過促進學名藥授權的杜哈宣言(Doha Declaration)(2001)、全球基金(2002)與PEPFAR(2003)的開始運作,以及藥品專利池(Medicine Patent Pool, MPP)機制的創設。
2002年,關注健康智財權的非政府組織消費者科技計畫(Consumer Project on Technology)的執行長樂福(James Love)在世界愛滋大會上首次提出了「藥品專利池」這個觀念,嘗試解決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價格居高不下導致許多患者無藥可用的問題。會議同時阿赫馬正進行拒絕抗反轉錄病毒藥物治療的絕「藥」抗議行動。2006年該組織再次協同無國界醫師(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一起向當時草創的國際藥品採購機制(UNITAID)提出這個建言,直接促成了兩年後世界衛生大會上的討論以及這個機制在2009年的誕生。
藥品專利池是從藥廠或其他專利持有人取得自願性授權,然後再授權給不只一家的學名藥生產商,並將學名藥販售所得一部分抽成回饋給專利持有人。這個做法除了幫助學名藥取得專利,也能促進學名藥競爭並降低藥價;而在藥物專利權複雜且愛滋病療法同時需要多種藥物(也因此涉及專項專利)的情況下,更有助減少學名藥廠取得授權的困難。目前為止,專利池已經取得13種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專利,而研究指出專利池將可以在18年內為全球節省23億美元的藥物支出,成本效益比達到43倍。
推動愛滋藥物可近性的努力是世紀之交最重要的公衛成就之一,而除了各國運動者對國內政策的積極倡議,專利池也是這場運動在全球治理層級留下的珍貴資產:不只是愛滋病,其他包括肝炎、肺結核等健康議題也因此而受益。今年默克與輝瑞藥廠都宣布將自家COVID-19治療藥物的專利釋出,也是透過這個機制。

很多時候全球層級的重大改變的發生除了社運的推波助瀾,仍需要仰賴政治意願、專家推動、地緣政治等重要因素。實際上,公民團體的倡議與實際發生的改變之間的因果關係也不是那麼容易釐清。
但嘗試分析與了解愛滋社運如何實質影響全球健康治理,並不僅僅是故意挑一個相對難坐實的角度談公民社會的貢獻。對多數人來說,全球健康治理往往顯得遙遠而與己無關。從運動者的角度,治理層級常常永遠過於遲緩被動、且善於忽視草根與街頭的聲音。但愛滋社運對全球健康治理帶來的影響,在某方面則是社會運動機構化(institutionalisation)的成功典範,在維持倡議與衝撞力道的同時,還能實質參與決策層級,對官僚體制與最高層級的論述建立和資源分配帶來改變。
對於各種議題的運動者來說,愛滋運動史都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經驗。既然他們成功過,我們也更有理由相信在正確的策略與時機下,我們的倡議有一天可以帶來類似的衝擊效應。
大疫當前,回顧過去40年來人類,尤其是感染者與運動者們,如何走過陰影的幽谷應該能給我們許多信心和勇氣。對於感染者、愛滋工作者、學者、倡議者也好,或者只是一個對愛滋不甚了解的路人也好,世界愛滋日都提供了機會讓我們追索自己所認同的族群背後的奮鬥故事與重要價值。記得這些與自己有相近生命經驗的人們是如何達成了一些也許曾經無法想像的目標。
舞台劇《血熱之心》(The Normal Heart)裡面的一段話,也許對任何人來說都能激起一些共鳴:
「我屬於一個文化⋯⋯它一直都在那裡,在歷史的長流中我們從來就沒有缺席。我們只需要大聲主張、找出那些人們、然後向世人道出我們的所想所感、道出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貢獻。」
“I belong to a culture. … It's all there—all through history we've been there; but we have to claim it, and identify who was in it, and articulate what's in our minds and hearts and all our creative contributions to this earth. … ”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