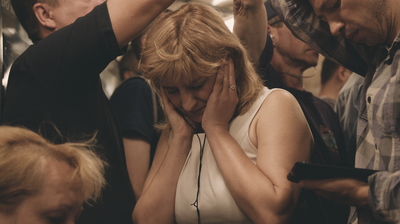辛西亞.恩洛(Cynthia Enloe),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者。最為人知的作品《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出版於1980年代末,是最早將女性主義帶入政治、戰爭、外交領域分析的學者。在她筆下,外交官的妻子、軍火廠的女工、替軍人洗衣服的難民女性⋯⋯這些曾經被忽略的身分,都在她的研究中,找到自己的聲音。
「當戰爭來臨時,女人真的可能沒有國家嗎?」在恩洛的新書《戰爭的十二個女性主義課題》中 ,她更廣泛研究不同樣貌、曾直接或間接參與過戰爭的女性,包括烏克蘭、美國、俄羅斯。本文專訪中,對於今日台灣當前的情況,從女性、戰爭、民間國防的角度,恩洛也提出許多想法與觀察。
戰爭時,還需要上班上課嗎?戰時,誰來如何維持日常運作?戰爭時,誰來洗髒衣服?
隨著混合戰概念的普遍,人們逐漸認知到,戰爭並非二元性僅有「戰爭」與「和平」組成的相對概念;而是一系列非線性的,由地緣政治變動產生的持續性衝突。因此,戰爭研究不只關乎傳統的軍事研究,當政治宣傳、經濟制裁、資訊戰,都成為近代戰爭的常見手段,不同年齡、不同性別、族群與職位的人們,如何參與或受戰爭影響,是近年興起的重要領域。
戰時暴力,戰時動員,戰時志工,戰爭裡的性與性別勞動──女性主義視角的國際關係與戰爭分析,也成為我們更加了解戰爭的途徑之一。
以《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妮莫的戰爭、艾瑪的戰爭》(Nimo's War, Emma's War: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the Iraq War)等著作聞名政治學界的美國學者辛西亞.恩洛(Cynthia Enloe),出生於1938年,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長年關注戰爭中的女性角色。
2023年,她出版新書《關於戰爭的十二個女性主義課題》(Twelve Feminist Lessons of War),大量書寫關於俄侵烏戰爭的採訪與分析,採訪包括烏克蘭、俄羅斯、波蘭、美國等,討論此時,彼地,各自相異的女性們,未曾謀面卻共時性地經驗了這場戰爭。
在地緣政治衝突不斷的今日,恩洛於本篇專訪中分享過往對於戰爭、性別與國族的研究經驗,以及對於東亞的思考。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最初是什麼讓您開始研究「女性與戰爭」?大約直到1960、1970年代,在政治與外交領域,幾乎沒有學者做過相關研究。所以我很好奇,作為先驅,您為何注意到這個角度?
辛西亞.恩洛(以下簡稱「恩」):現在回想,開始教書的前幾年,甚至寫前6本書時,我都專注在軍事研究,從未注意過「女性在政治中的缺席」。
我畢業於一所新英格蘭地區的女子大學,叫康乃狄克學院(Connecticut College)。我在那裡讀政治學。那是所很棒的大學,有很多女教授,但她們卻從未談過女性經驗。我知道她們肯定吃過不少苦,畢竟,你可以想像,1940到1950年代,一個女人想取得博士學位,肯定會碰上不少困難,但她們從來隻字不提。她們並非反女性主義,只是覺得「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後來,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念政治學博士。1960年代,你知道當時的社會氣氛,校園裡的政治氛圍濃厚,卻唯獨對女性議題漠不關心。政治系非常龐大,有近50位教授,全都是男性。我攻讀中國、日本政治,這一切都太有趣了,也沒注意到教授裡沒有一位女性。
我和另一位女同學被選為全系第一批助教,負責指導大學部課程。當時的男教授們,其實應該知道,她們正在「打破玻璃天花板」──雖然當年沒人用這個詞,畢竟這些概念還沒被發明。
我沉迷研究亞洲與非洲,殖民與軍事,卻未想過「女性」在哪裡。這是因為,一直以來我們做戰爭研究,討論的男性都相當多元:有窮人、有富人、有影響力的人、邊緣的人。當時我對被嚴重剝削的低階士兵很感興趣,以為自己已經談了夠多元的人──族群多元、種族多元──這種情況在學術界,直到越戰末期都非常普遍。
直到有一天,我任教大學的同事,他曾是越戰中的低階士兵。他替學生辦了一場工作坊,並且邀請我去。他在工作坊中提到:在越戰期間,誰幫他洗衣服。美軍會雇用因戰爭流離失所的越南女性、付她們少量薪資,請她們幫軍人洗衣服。當時我坐在那裡,四周環繞著學生,突然想到,自己似乎從沒想過,在戰爭裡「誰幫士兵洗衣服」這件事。
那一刻我想,如果從「洗衣服」這件事開始思考,戰爭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場越南對法國、對美國的戰爭、或世界上所有的戰爭,會變成什麼樣子?

「斯維特蘭娜(Svitlana)此刻正穿著她最保暖的大衣。她謹慎地將IPhone塞進牛仔褲口袋,肩上掛著背包,裡頭有護照、一些點心、筆記型電腦、兩個充電器、衛生棉條、幾件要讓孩子們替換的毛衣,以及倉皇離開前還來得及拿走的幾張家庭照片。
「她的右手,被最小的孩子緊緊抓著──謝天謝地,她已經大到可以自己走路了。她的左手,則拖著行李箱,裡面裝著得用上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的衣物。8歲的大女兒,努力在人潮裡不要跟母親與妹妹走散。在基輔的火車月台,她小小的身上掛著一個色彩鮮豔的學校書包,晃蕩著前進。
「而同一天,在華沙的月台旁,阿格涅什卡(Agnieszka)與其他波蘭女性志工司機們忙碌著。
「隨著大量烏克蘭女性難民湧入邊界,阿格涅什卡和其他波蘭女性主義者們注意到有性人口販運者正虎視眈眈,打算趁亂喬裝成歡迎難民的本地人,藉機拐騙未成年女童與女人。志工們因此迅速號召了女性司機群,為這些精疲力竭又驚魂未定的烏克蘭女性們提供交通,至少送她們平安前往下一站。」
──節錄自辛西亞・恩洛,《戰爭的十二個女性主義課題》
報:《戰爭的十二個女性主義課題》開篇故事,也是從您提到的這種女性視角開展的。以斯維特蘭娜為中心,交錯多名女性的「戰爭這一天」,描繪出俄烏戰爭初期,不同國籍、不同族裔的女性,如何被這場戰爭不同程度的影響。您是怎麼找到這些受訪者的?她們為何願意與你分享這些私人經驗?
恩:有時,人們會聽說,我是真的認真想理解女性在戰爭中的經驗,她們就會主動聯絡我。有人會寄email給我,或是在某場演講、某次會議、甚至某個書店活動上,走過來說:「妳剛剛提到關於軍人妻子的部分,跟我的生活好像。」
而我作為研究者,雖然理論上這應該是正常的,但我每次還是會感到很驚喜。我會說:「真的嗎?我們到那邊坐一下,能不能告訴我,作為軍人妻子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我永遠對願意誠實跟我談的人心存感激,那是一種巨大的禮物。
例如,她或許會補充:「作為軍人妻子,最困難的一點是我無法擁有自己的職涯。我的先生一直調動。我們錢也不太夠,因為我無法找到一份固定在某處的全職工作,畢竟我必須跟著他四處搬家。」
這些口述對我的分析都非常重要。
有時是女性主動來找我,也許是看了YouTube訪談、讀到某篇文章,也許有人把我的書給她們。她們或許覺得我會認真對待她們,而與此同時,其他人沒有認真聽她們說過這些。另外,當然,我也會正式邀請對方接受訪談。但你知道──身為記者想必比誰都懂──你得先建立信任。人們不會因為你自稱記者、我自稱研究者,就願意把艱難的生活告訴你。
例如,有些伊拉克女性在戰爭期間為了撫養孩子,進入性交易工作。我曾寫過相關主題,包括收錄她的親口證詞,我判斷可信,所以會呈現出來。但那不代表所有女性都有同樣的經驗。這類情況還需要更多研究。
一位女性的經驗可能是真實且重要的,但還不足以代表全部──無論她是家庭照護者、工廠工人,或香蕉園工人。
所以寫作者的任務也包括,我們要持續對讀者說:我們可以呈現部分真相,但這還不是故事的結局,親愛的讀者,你們要繼續尋找其他的線索。

「在海洋的另一端,露西爾(Lucile)不知道是否該為了自己剛從一家軍火製造商找到新工作而感到高興。她有一個姪子正在從軍,但至少她從不自認是美軍的啦啦隊。然而,作為在奧蘭多的一個非裔單親媽媽,她應該替自己至少不需要去迪士尼樂園從事低薪工作而感到慶幸。既然如此,為『雷神公司』(Raytheon)工作,製造軍火,是否符合她的個人價值觀呢?
「然而,隨著烏克蘭戰爭開始占據了美國的頭條新聞,露西爾找到了答案。她第一次為了自己生產的武器感到自豪:那是標槍(FGM-148 Javelin)反坦克飛彈。她看到標槍在晚間新聞中被大大讚揚。社群媒體上甚至開始流傳烏克蘭當地一個名為『聖標槍(Saint Javelin)』的迷因塗鴉,它看起來像是瑪利亞的肖像畫,然而聖母懷抱的不是聖子,而是標槍飛彈。
「露西爾想知道,在生產飛彈的工廠擔任技術員,是否某種程度上,將她與這些烏克蘭女性相繫在一起。」
──節錄自辛西亞・恩洛,《戰爭的十二個女性主義課題》
報:在書中的第四章與第五章,您探討了關於女性是否應該參與軍事化(militarization)的爭論。例子包括烏克蘭女兵、緬甸反抗軍政府的女性武裝起義者等等。這也關乎長久以來,女性主義該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戰爭」、「支持武裝行動」的道德辯論。能不能說說您的想法?
我認為任何政府,任何試圖讓國家軍隊全部只能由異性戀男性組成的政府,都是父權制的。它有兩個層面。
首先,它把一個完整的國家機構,貼上只有全是男性才會可靠的標籤。可是,事實上,我採訪過的大多數職業軍人都認為,有能力招募到愈多元的人加入軍隊,一支包含同性戀、跨性別、非裔、亞裔、美洲原住民的多元化軍隊,會愈是一支充滿力量的軍隊。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要思考,女性加入國家軍隊,是為了什麼目的?如果是希望保證女性獲得解放,它真的能達到嗎?
我們要區分兩件事。一個是,每個國家針對女性募兵,出於哪些動機?是為了促進軍隊改革與現代化、或者填補某些人力不足的職位?另一件事情是,女性參軍有哪些原因?為了延後結婚、為了逃離讓人窒息的小鎮、為了贏得社會尊重、或者是為了取得一個有保障的工作機會?不同的社群與性別身分,都有各自的考量。而這些考量,是否有助於軍隊改革?還是加速了其中的壓迫階級?
另一個事情是,反政府的武裝行動,在什麼時候能與女性主義相容?許多主張反獨裁、反殖民、反種族主義的組織,都能招募到不少女性成員,其中尤其是年輕女性。她們渴望戰鬥,因為看見對平民有威脅性的政權強化武力,決定起身抵抗;也因為不願目睹自己的男性親屬遭到政府無端殺害,而拿起武器。
只不過,大家也必須要明白,自己此刻投入,最後希望獲得什麼?畢竟過去70年間,世界各地參與起義的女性們幾乎能總結出的性別教訓之一,就是:不要期望其他目標──比如,結束殖民統治、結束種族優越論、推翻獨裁者、實現國家獨立──會「自動」帶來其他好處。
重要的是必須去問,這些女性在高度由上而下的軍事化與階級化運作的制度中,累積了哪些經驗?這些組織的領導人,在戰時與戰後對於當初自由主義的承諾是明確的、還是含糊不清的?他們對於這些女性的訴求,是否兌現?
這些起身反抗的勇敢女性給予我們的,是教導我們必須要維持長時間觀察的視角。我們本來就不應該指望「更宏大的目標」,就能帶來女性的自由與解放──因為事實證明,我們以為的「自動」,從來就不會「自動」發生。(Automatically, it turns out, is never automatic.)

「亞莉珊卓拉(Alexandra)年紀很小,她太晚出生,以至於來不及參與異議樂團『暴動小貓』(Pussy Riots)早期那些驚世駭俗的演出,她們多次挑釁了俄羅斯政府與東正教神職人員,她一直很欽佩她們的勇氣。在普丁入侵烏克蘭後,她決定,這次該輪到自己行動了。
「2月下旬,她加入了聖彼得堡的街頭的抗議。裹著厚厚的冬衣,她小心翼翼,不敢喊出『那個人』的名字,只是舉起自己手繪的標語『反對戰爭!』(NO to WAR!)當天安全部隊對和平示威的殘酷鎮壓令她震驚不已,幾個鐘頭後,她不得不丟下標語逃跑。事後,她和朋友私下討論此事,他們都出生於冷戰後的俄羅斯,沒有人知道國家將為她帶來怎樣的未來。
「塞爾維亞的萊帕(Lepa)則經歷過真正的戰爭。
「作為貝爾格勒的居民,她經歷過1990年代血腥衝突粉碎了她的上一個國家,緊接著而來的是另一個種族關係緊張,後巴爾幹的專制國家。萊帕和其他人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組織了一個性侵危機處理中心,以及女性主義反戰抗議組織。從那之後,她致力於投入女性主義反軍國主義。
「但這並不是她的一些烏克蘭女性主義朋友們此刻感受到的情緒。
「她們告訴她,現在她們正需要的是武器,尤其是重型武器。她一瞬間感到動搖──難道運送火炮將成為跨國女性主義未來團結的新形式嗎?」
──節錄自辛西亞・恩洛,《戰爭的十二個女性主義課題》
報:在中國,因為嚴格的網路審查,少數被允許談論的公共議題,是關於女性的。這是因為一胎化政策下,年輕女性已是最大的勞動人口之一。所以有時,當她們試圖進行一些小規模的網路行動,是會被部分允許的,但當然只能在特定框架內進行,儘管,這樣的例子依然非常非常少。一些中國女性主義者告訴我,最常碰到的問題是,無法知道底線在哪。有時行動會被默許,有時候卻遭強力壓制,有些人會被抓,有些人卻不會。很難知道界線究竟在哪裡。中國政府似乎就是刻意讓人們感到困惑。
同時,對於台灣議題,中國女性社群不時也會出現激烈辯論。比如,有些人會在網路上攻擊台灣人:「台灣仍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我是女性主義者,我仍然認為必要時要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即使知道她們就是在那樣的背景長大,但我仍感覺失望。在您的寫作中,也寫到了俄羅斯的女性們。您怎麼思考這些來自對立國家的女性觀點?
恩:某種程度上,如果你想用威權方式統治,就要讓人們搞不清楚你會因為什麼逮捕他們、因為什麼折磨他們、因為什麼開除他們、因為什麼讓他們閉嘴。讓人們混亂,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讓你維持權力。這是一種非常糟糕的、反民主的治理方式,會讓人陷入自我審查的狀態。
當然,得到這種回應,一定感覺很糟糕。這只是我的猜測,但對於一些在中國生活工作,並對政府持批判觀點的人來說,他們可能覺得,如果我先投誠說一些中國愛國主義的話,像是「反對台灣是一個國家」就能保護我。這就像盔甲,接著我也許有機會批評一些黨的行動。也許如果我公開談論一些中國至上的言論,黨就不會打壓我。在很多國家都是如此。
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們當然不能成為極權政府的共犯。不能為了維護自己那點可憐的空間,而發表擁護極端政權的言論。只是,你我採訪的那些人,也必須顧慮他們接受採訪當下的風險或處境。
至於團結(solidarity),未必意味著要跟對方當朋友,而是對對方的處境保持好奇。雖然我們未必總是能夠記得,但有時,光是這樣就足夠了。
報:在台灣,近期也有一些因為出面批評內閣比例性別失衡、或者立法委員發言失當的女性主義非營利組織或個人,遭到了許多網路攻擊,認為她們「厭惡男性」或者「不夠愛國」。我觀察到,在「女性主義」與「愛國」之間,似乎有著優先次序,您怎麼思考這件事?
恩:任何人,出面指責任何形式的性別歧視,都不能因為有人說她們這樣不夠民族主義、不夠愛國,就應該要被噤聲。但這真的很難,很難承受那種壓力。
即使在美國,我想應該也有很多人覺得我不夠愛國,但那沒關係,他們想說什麼都行。但我學到的是:如果我看到任何性別歧視、騷擾女性,我就必須指認出來。否則對我來說,那是最糟的事情──我不想成為讓某些男性氣質被特權化、而幾乎所有女性氣質被貶抑的整套系統的共犯。
同樣地,對於台灣,我的想法也是──使一個社會較不性別歧視,包括政治系統,包括內閣的運作,包括公共討論──使一個國家變得較不性別歧視,都會讓這個國家更強韌、更具韌性、更公平,讓更多人能參與社會。這反而會讓社會更強,而不是更弱。
報:最近很多議題都圍繞著「政治正確會讓我們變弱」。 因為很多人害怕我們太弱──我們生來就太弱了。一種常見的論述是,我們必須支持右翼的盟友,必須放棄追求政治正確,因為國家有難,同時因為我們是國際孤兒,我們別無選擇。
恩:台灣經歷了3次的殖民統治,但是,世上任何地方,即使經歷過被壓迫、被殘酷地暴力對待,也都不代表它從此就只是受害者。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有那樣的經驗:像我自己,在一個極度性別歧視的年代上學的女性,但那並不表示我的餘生都是性別歧視的受害者,我就可以逃避責任。
承認自己有能動性(agency),並不意味著我、或我的父母一代完全沒有真正作為受害者的經歷。
那是你們的一部分,但不是你們的全部。
我們都必須思考:如果我曾經被糟糕的對待過,那是否代表我從此就不需要背負任何社會責任?是否代表我這輩子都不會擁有其他人擁有的權益?如果我有某些能動性或特權,那我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
我能感受到的是:台灣人,儘管彼此之間也很多元,但在過去幾十年,你們、你們的父母,也可能包括你們的祖父母,都一直非常努力地讓台灣的生活成為真正的民主生活。而我們這裡(美國)老實說,現在也很辛苦。所以我知道,那是需要努力、需要投入、需要耐力、需要承諾的。
而我覺得──這是我,完全是身為一個外來者,非常、非常外圍的看法──你們所有人正在一起努力,做著最困難的工作:做調查性報導、維持公平的選舉,舉辦公開、甚至有時令人不舒服的辯論。持續做這些,就是台灣對世界的貢獻。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你們都已經在做了。你們想要保護自己,但也對軍國主義的思想抱持謹慎,而我們也看到很多台灣人們正在努力讓社會變得更強韌的方式。所以這不只是建議,是一種希望:
你們會努力的。你們會努力,是因為你們彼此交談、彼此傾聽、一起思考。這不是大寫的G那種「集體思考」(groupthink),而是互相聆聽、保持好奇,並且對任何想把你們塑造成單純的受害者、單純的恐懼者的人保持高度警惕。你們不會那樣的。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