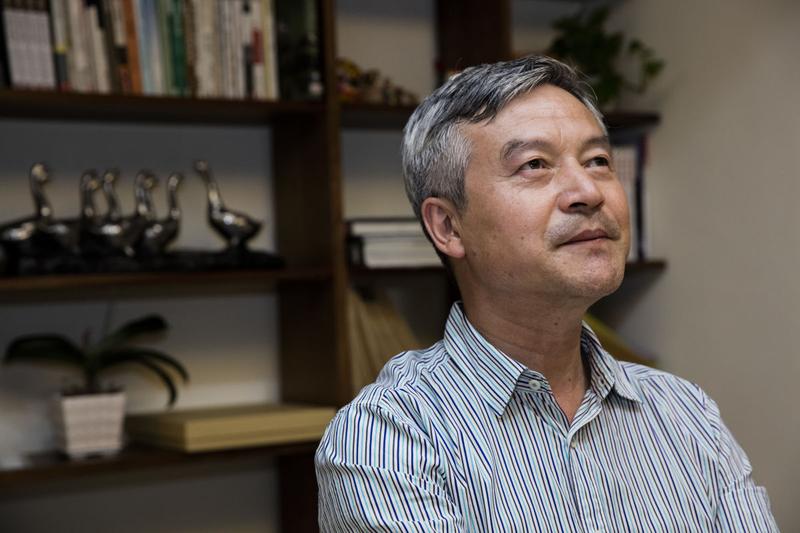張贊波專訪艾未未

中國藝術家也是導演身份的艾未未,今年8月底帶著他執導的最新紀錄片《人流》(Human Flow)前往威尼斯影展。參與此片拍攝工作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藉著此次影展機會,與艾未未進行了3次總長近4小時的深度訪談,《報導者》與張贊波獨家合作,分3個主題刊登,此為系列之三。
- 訪談人:張贊波(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
- 受訪人:艾未未(中國藝術家、紀錄片《Human Flow》導演)
- 訪談地點:威尼斯、柏林
- 訪談時間:2017年8月28日、9月6日、9月9日
艾未未(以下簡稱艾):關於劉曉波,我在Twitter上很早就有話,不是最近開始。我和劉曉波的關係始於1989年,他來美國和我有往來,「六四」發生前,他告訴我決定回國,他六四事件後被抓,我在紐約也做過一個公開的抗議示威活動,要求釋放他。
我1993年回國後,他釋放後來找我,要我為劉霞做一個展覽,我那時有一個藝術空間。他剛被釋放,經濟上有問題,和王朔做過一個對談《美人贈我蒙汗藥》。我給劉霞做了展覽,在南城龍爪樹的畫廊,展的是她的攝影,現在大家在網路上看到的,劉霞拍的一些玩偶的照片,表達她在劉曉波被監禁時期的孤寂內心狀態。
之後,我與劉曉波並沒有頻繁接觸。大約2006年,他約我來我開的餐館吃飯,我和友人在亮馬橋開了一個餐館「去哪兒」。他是乘警車來的,那段時間,便衣警察跟著他,他要去哪,就直接坐他們的警車拉他去,這倒也方便。車停在餐館門前,兩個警察跟著他,那時我還挺稀罕,是我第一次見到「國保」。我們在餐館裡吃飯喝酒,熱鬧了一番,之後他坐著警車離開了。之後我看到他的博客上的鏈接上只掛了我的名字,他覺得我做的事有趣。
《零八憲章》起草的時候,他發給我讓我看一下,提點意見,他可能是想讓我簽名,但是沒有明說。當時是草稿,其中很多部分還是紅字。有些提法我覺得不妥,我沒有回答。後來,我在國外旅行的時候聽說他被抓了,我也就在《零八憲章》上簽字了,已經是第三波了。如果他沒有被抓,我是不會簽字的,我不相信簽名這種事兒,一撥人一起,有些人我不待見。我在北京機場第一次被禁止出境,是他們擔心我會為劉曉波去領獎。在我的監禁中,我做了加州惡魔島的展覽,劉曉波的肖像作為全球著名的政治犯在其中,這個展覽現在在華盛頓的博物館中展出,展覽中觀眾給劉曉波寄出了成百上千張明信片。
他被抓後,我時常在網路上呼籲,後來他被判時我去了法院門前抗議,我們工作室的劉豔萍、石靜也去現場了。劉曉波得諾貝爾獎,我在倫敦的泰特博物館做展覽,那一天我接受了20多個採訪,譴責了中共,同時為他道賀。
我爭取的是普遍的原則,普遍的價值,那麼這個事件的普遍性,是中國政府不應該關押任何政治犯,應該釋放所有的政治犯,這是我呼籲的。
他並不是真正的受難者,真正的受難者,他的獄友李必豐在監獄裏服刑,他今天提都不提。他回避從本質上去訴說專制的惡毒,而是賣弄個人的受難狀,像個耍蛇者,通過展現和一條並不存在的毒蛇互動來表現自己的嬈勇,這確實搞笑。在劉曉波這事上,他對西方關心劉曉波的人,扮演一個和劉曉波關係深、能拿到第一手內部消息的人,造成了很多誤解。由於他遠不及劉曉波,根本無法解釋劉曉波的價值,填在劉曉波嘴裡的「我死也要死在自由國家」,這是對一位垂死的政治人物的詆毀。
劉曉波的價值不是他個人的,而是他試圖創造一個國家再生的倫理可能,《零八憲章》具有這樣的光輝,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傳統。當然,劉曉波是可爭論的,關於他的陳述《我沒有敵人》,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想找道德高度,將自己弄成甘地或者曼德拉。他們大多眼光平庸,並不能認清現實,中國不是印度,不是南非,兩處是殖民地,擁有巨大的反抗群體和使用暴力的可能。當一個沒有使用暴力可能的人談「非暴力」,那是扯淡。你根本沒有性功能,卻說不好色。中國知識分子談「非暴力」是個偽命題,你談「非暴力」,太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吧。
劉曉波「高度」了一把,說「我沒有敵人」。我說「曉波如果沒有敵人,那我就沒有朋友」,你不可能和一個沒有敵人的人成為朋友的。有人因此認為我這是詆毀劉曉波,劉曉波是他們的神,損他就是毀神。實際上沒有誰比他們自己更毀掉自己的「神」的,因為他們最終將神解釋為和他們合體,毀的是神的原則。他們是一群「借劉曉波之死為自己賣假藥的」,真正詆毀了劉曉波存在價值的人。
廖亦武說過很多可笑的話,且自己還得意。比如他為劉霞出主意,建議劉霞說自己病了,要求中國政府讓劉曉波陪同劉霞出國看病,諸如之類。這是什麼意思?是給政府下台,還是給曉波下台?劉曉波說過,死也要死在中國,不出國之類的話。一個智力和倫理水準極低的人,對西方扮演「知情者」、「密友」角色,對中國線民扮演他在德國政界有通天關係,放出諸如德國政府正在給劉曉波及家人辦簽證,還向他要了照片之類資訊。廖亦武在國外多年,外文一字不識,天天拽著翻譯四處電話,只要有人接電話就哭。他見過我三次,三次都又哭又鬧的。
後來德國和美國的醫師進入中國,給劉曉波看病。一個主權國家的犯人,認可外國醫生為政治犯看病,這是達成了某種協議和共識,他們都不想在這個問題上被輿論指責,中國希望讓他們進來看醫療條件,做出自己的評價。具體到能不能出國這就更複雜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接受這樣的情況,雖然從道義上不能不說「願意他來治療」, 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讓他出來。我調侃了梅克爾,一再地問,當她和習近平見面的時候,談及過劉曉波問題嗎?我認為沒有,梅克爾政府只是以外交照會,表達了「嚴重關注」。
廖亦武在媒體放出不真實的資訊,渲染個人在政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不懂社交媒體,扮演裝瘋賣傻的角色是不能維持太久的。我在維護劉曉波政治上的價值,他的價值不是拿諾貝爾獎,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上不具備討論人權、人的價值的能力,更別說政治眼光了。
張:談談你寫的那本自傳體書──關於你與你父親艾青的那本書,現在怎麼樣了?能簡單介紹一下你寫作的這本書嗎?它什麼時候能出版問世?
艾:關於這本書,要從我2011年被監禁了81天開始說起。在那段時間,在裡面我突然有了很多閒散的時間、空的時間。因為徹底切斷了和外界的聯繫。我坐在那裡,除了接受審訊之外,大部分時間用來回憶過去,藉以消磨時光。回憶從我出生後具有記憶的東西,包括人物、事件,一件件地回憶。一個星期之後,我就沒有東西可回憶了。我一生的記憶就像裝在一個袋子裡,被翻了個底朝天,抖兩下就全沒有,一點不剩了。那種感覺很茫然,發現自己能記憶的東西如此有限。
回憶中關於我父親的部分,更是有很多缺憾。現在我很喜歡做點記錄,但那個時候我竟然沒有向父親提過哪怕一個問題,和他相處了幾十年,竟然一個問題都沒有向他提過,我沒有問題可問嗎?還是我覺得有些問題不該問,還是其他原因?
人能問問題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進化,但這個並不是必然的。我就沒有問我父親,雖然我有無數問題可以問他,他現在早已去世,我再也沒有機會去問他,這只是後話。一直到他去世十幾年後,我才突然想起這個問題,覺得非常遺憾,再也沒有辦法得到他正面的回答了。
張:你最想問你父親的是什麼?
艾:想問的問題太多了,我最想問的是他怎麼看待自己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他在那個國家受過那麼長時間的迫害,我從來沒有問過他,我也從來沒有聽到他談論那個問題,對此我只能想像。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遺憾,當審訊者告訴我,我會被判刑十幾年的時候,他們直接說:「你被放出來的時候,你的兒子已經不認識你了。」這對我打擊挺大的,我想,哎呀,如果有機會,我應該將我的經歷寫下來,以後給我的兒子看,讓他知道我經歷的世界是怎麼樣。這樣不會讓他有我對我父親一樣的遺憾。我們兩個之間,不要再形成我跟我父親之間的那種不了解,我應該將想說的話都說出來。
後來,我很意外地被釋放了。放出來後,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是將我在裡面被監禁81天的經歷記錄下來。關於那81天,我肯定會忘記一些的,這是為什麼要儘早做個記錄,這樣做是免得自己會對此改變說辭,記錄下來就是一份確鑿的證言。我們對事情的理解取決於我們所處的角度和位置,有如在一艘船上看到的風景,隨著水的流動,風景一直在發生變化。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和對世界的認識也是這樣的,所謂的客觀性,受限於「此時此地」。
寫完我的81天,我開始寫我的父親。他生於清末,1910年,他是清朝之後的知識分子,18、19歲去了法國,回來蹲國民黨監獄,後來流亡,再後來去了延安。進京後,1957年,我出生那年,他被打成了「右派」,然後流放去了東北和新疆,一去20年,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時刻,47歲,他的創作巔峰時刻,和整整一代人,幾十萬人一起被「收拾」了。他所代表的是中國的文化的現代歷史,他個人的生存極具戲劇性,江南一個小地主的兒子,出生時難產,生出來後送給了一個農民去養,寫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詩。
作為一個反封建、反帝制、愛國、追求公平和正義的人,他的處境在中國可想而知。我以前就覺得他的經歷、他的個人史其實是和國家史、時代史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我也僅僅只是想想,那時候我並沒有從事寫作或者和文字表達相關的事,我又不是一個社會活動分子,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閒人,閒散了很多年。
張:你不是被大家稱為「社會活動家」嗎?
艾:那是後來,2005年我開了博客 ,我在上面3、4年的時間,每天在網上寫2、3篇博客,寫了250萬字。那時候是瘋了,我的全部精力都在寫博客上了,2007年我做了《童話》,08年發生了很多事,四川地震、楊佳事件。楊佳事件我就寫了幾十篇,博客上的熱度是我從沒經歷過的,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活動分子。
那個時候,我在藝術方面沒有太多認同, 2004年做第一個展覽,到今年13年,在這段時間,我做了100多個個展,三、四百個群展。我最主要的成績體現在博客上,就是我那250萬字的胡說八道,口無遮攔。後來我被關押,罰稅,監視,直到我能夠出國。我覺得我的歷史和我父親有了相近之處,成為「國家的敵人」,不同的是,我是在21世紀,有了全球化和互聯網,我有機會在輿論平台上發出聲音。
這是我的一個簡短的活動史,我的活動史和我父親的加在一起,更能說明中國的問題,它發生的變化與不變的地方。儘管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位已經明顯不同,但很多地方是沒有變的,它的極權、封建專制完全沒變,我的書是想探討個人和國家的關係。
我父親出生在1910年,我兒子生在2009年,這本書是從我父親的出生到我兒子的出生之間,100年發生的事,書由美國出版公司出版,差不多再有1年的時間能出來,大概是25萬字,寫作持續了3年。
張:聽說這本書的中文版會在台灣出版,也就是說它將跟華語世界的讀者見面?
艾:華語世界是不完整的,華語是一種被摧毀的語言,從白話之後它就跟這個國家的政治現實綁在了一起。這個政治是一個消除語義、消除思想含義的,也是一個綁架於極端審查的政治,這個語言已經被毀壞被扭曲了。
台灣像一個苗圃,保存了一些華語的苗木,但這個太小的苗圃不足以支撐一種語言所需要生長空間。這本書在中國大陸必然是禁書,它探討的是個人和權力的關係,涉及言論自由,人權等不可回避的問題,它是不能出版的。
艾:《此時此地》是「理想國」的第一本書。那個時候我已經有點敏感了,正是我在博客上正猛,2009年以前,他們要出書,審查稀裡糊塗通過了。中國是這樣的,直到你出事之前你都不會有事,什麼叫出事?就是中宣部或者出版署,有明文規定這個人的名字不能出現,這一步來得比較晚,我根本不是個作家,書一出來,出版社被迫向主管部門做了檢討,但書沒下架,後來還加印了。
艾:中國的政策很有意思,和病毒一樣,它是有階段性的,也因人而異。某個時間禁令說不能怎麼樣,之前的事他們不管。另外是權力者是有任期的,不在他的任期內他就不管。我的那本書裡沒有什麼敏感內容,是將我在博客裡的有關建築、攝影、繪畫或者文化的部分選摘了進去,沒有政治內容。
張:但這些不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嗎?你的觀點就是“everything is art, everything is politics.”
艾:中國認為的政治是敏感詞,涉及六四,領導人和國家政策,這是他們關注的。
張:但我的書其實也沒有涉及到那個層面的政治。
艾:你的書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被禁,我看不出為什麼要被禁。
張:對於我來說,這也是個謎,他們並沒有告訴我具體原因。
張:按你的類比,說我的書像趙樹理的書,那應該獲得國家級的獎項才對,魯迅文學獎什麼的(笑)。
艾:對呀,因為這個國家,很少會有一個作者去蹲點一個工地做這種紀實性、社會學的觀察和記錄,你應該得社會學的獎。文學早已經被其他學科蓋過了,考古學、社會學等等,走在了純文學的前頭。
中國是全世界修公路最多的國家,它的公路里程好像是印度的幾百倍,中國在這方面投入非常大,「要想富,先修路」。它是國家腐敗的血脈,許多道路建設都是政治性立項,在計畫內完成多少道路,是對政府工作量的衡量標準。道路工程能拿到國家資金和投入,道路工程領域的腐敗,是與開發房地產腐敗並行的領域。管理道路的權力部門,城建和路管局機構,抓一百個,一百個都是腐敗的。分段承包,層層發包,每層都會產生腐敗,它是權力集中施展的地方,腐敗也是遍地開花。
張:是的,按照你這個闡述,它看起來雖然是某一個層面的生活的紀實,是某一個社會狀況的紀實,但它最後還是會關聯到制度和體制的。這也許正是他們會禁掉我這本書的原因。
艾:你展現了一個癌細胞在顯微鏡下的狀態,它如何生長,擴散的,儘管沒有涉及到更深的層面,癌是如何得的?得了癌會不會死?實際上已經觸及到敏感區域。
張:你希望人們將你當做「藝術家艾未未」,還是「導演艾未未」?你怎麼看待紀錄片這樣一種表達手段和當代藝術的關係?你怎麼看待你的紀錄片在你的所有藝術作品中的地位以及價值?
艾:我是作為一個正常人生活,不在乎我是藝術家或建築師或者電影人的名銜,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完全不重要,因為即便是擁有這一切,你也還未必是一個正常人。對我來說,做一個正常人比什麼都重要。另外,是否參加電影節或是作品是否被認可,最終需要個人內心對自己的評價。我對自己工作的評價是,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我有機會在生活中面對現實,找到相應的語言來進行表達,並且有一定的受眾願意分享我的經驗,這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我所應該獲得的。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