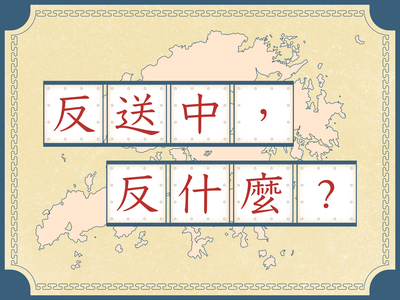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年輕人冒著遭警察逮捕、被黑社會暴打,甚至被自殺的風險參加了這場衛城之戰,挺身而出保衛香港的未來。經過半年的衝撞,近千位抗爭者被警方以暴動罪或持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起訴,讓他們必須面對漫長司法程序的心理壓力。
他們就像是上過戰場的士兵一樣,經歷過戰爭的殘酷後,心裡的傷口遠比身上的傷疤難以痊癒。這些難以承受的壓力應該要怎麼承接?這些被烙印上「政治犯」前科三個字的年輕人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在荔枝角每天上演不同的故事,有人面臨失去當教師的夢想,有人在探訪房隔著鐵窗求婚,有人錯失兒子出生的一刻⋯⋯從被捕一刻開始,我們就知道將失去,幾年甚至10年之青春和自由。身在牢籠,日子雖苦,所作之舉,無怨無悔,乃義之所至,與有榮焉。」
這是被關在香港荔枝角拘留所的反送中示威者,在11月27日對全體香港人發出的公開信。他們希望仍在外面的「手足」,不要忘了他們的犧牲。
到2019年12月16日為止,香港反送中運動參與者中,有6,105人遭警方逮捕;在978位遭到起訴的人裡,有517人被以「暴動罪」起訴、122人被控「持有攻擊性武器」、119人被控「非法集結」等罪名,其中暴動罪的刑期最高可達10年。

被逮捕人士有將近4成是在學學生,年齡大多都是落在15到25歲,也有人才剛出社會,開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司法系統無法短時間消化爆量的政治犯,有些人要在拘留所內等上一到兩年的時間,才能確認判決。而等著他們的還可能是重罪的刑期,要與殺人者或毒販等重刑犯在監獄一同服刑。
青春才要翱翔,但他們卻飛不高了。一國兩制的崩壞讓不少年輕人鋌而走險,用身體對決政權,原本應該恣意揮灑的青春,可能被鐵窗歲月給取代。他們的心理充滿著不安與恐懼。
從2016年開始,香港旺角魚蛋革命之後,就有年輕的政治犯被判刑入獄。這些年,陸續有牧師進到監所內帶領他們禱告;有立法會議員利用「公事探訪」的方式,拜訪他們,知道年輕政治犯關心社會,議員們會把從網路搜集而來的新聞資訊做成簡報帶進去,讓年輕人不需要仰賴監所內一面倒親政府的TVB新聞。如今,隨反送中運動進入的政治犯又更多,有經驗的立法會議員──如朱凱迪──進入拘留所也更頻繁,他說,年輕人待在拘留所等待漫長的司法訴訟程序,需要大量律師與他們討論案情,提供專業意見,「但在這之後,他們在面對漫漫牢獄的長夜,需要的仍是心理上的陪伴。」
除了牢獄之災的年輕人,長達半年以上,在催淚彈、橡膠子彈、強烈水柱衝擊中,走入運動,經歷城市戰場而受影響的年輕人,更是不計其數。
對麥可和不少運動者來說,他們更大的悲傷來自家人的不理解。以麥可為例,他的父母是支持政府的藍絲,雙方關係處在長期的劍拔弩張。父母看到《TVB》或《大公報》報導時,會跟著罵示威者是「暴徒」,還曾讚賞對示威者射擊實彈的警察。麥可曾離家住酒店,避免與父母無止境的爭吵,麥可說,從事運輸與清潔業的父母,每天規律的上下班「搵食」(討生活)、面對社會劇烈地變動,他們只求生活安穩,支持警方鎮壓抗爭者,「民主自由對他們來說太虛無飄渺,他們不了解我們為什麼犧牲。」
除了不理解子女的「藍黃家庭」之外,還有家長跟子女同樣站在支持反送中這一邊的「黃黃家庭」也出現問題。黃黃家庭的家長會擔心孩子抗議時站太前頭,阻止孩子上街;同時,子女也因害怕家長擔心而少了溝通,最後讓家庭關係也出現疏離、間隙。
政治的動盪滲入家庭,不少受訪的示威者表達,家人的冷漠或不理解的擔憂,讓他們感到更孤獨而徬徨。

「現在是香港的集體創傷,每個人都失去了一點東西,」臨床心理學家阿悅認為,在這次的運動裡,無論是支持反送中或是撐政府的人們,全部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從2019年6月21日到7月21日所做的調查顯示,有4成民眾認為社會紛爭是影響精神健康的原因,跟2018年相比,上升了23%,表示民眾認為反送中運動確實影響到民眾的心理健康。另外一份在10月底進行的「抗爭者精神健康」問卷調查中顯示,有36.7%的人因為警方執法而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症狀,經歷或目睹2件以上暴力事件的人,則有55%的人出現PTSD。
面對如此的集體創傷,數十位臨床心理學家組織的公民組織「良心理政」發起了「心靈照顧站」的服務,讓受到運動波及的人可以免費尋求基本的心理諮商療程。身為良心理政成員之一的阿悅在半年時間裡,一對一面談了數十位受創的年輕心靈。「他們承受著無數的惡夢,那些回憶隨時會重回他們的腦海,讓他們的身體狀態再度回到遇到暴力時的緊繃,」阿悅說,來到諮商的人們常常崩潰痛哭,她能做的就是陪著他們走完這段痛苦的過程。
良心理政裡的臨床心理學家全是義工,上午在自己的診所、醫院裡上班,空閒時就到良心理政輪班提供諮商服務。「在看診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到這些年輕人累積的情緒,」阿悅說,因為他們必須大量接下抗爭者心裡的悲痛,所以必須適時給自己放個假、透透氣,否則就算是專業的心理學家,有可能也無法承受。
心靈照顧站至今已提供超過500人的服務,但服務的初衷是為了幫助緊急需要心理支援的人而設置,所以規定只能為每一位個案提供4次心理諮商。但警民衝突升溫,導致需要幫助的人遽增,這也讓良心理政人手短缺。
「我們這種義務的心理學家人數不夠,這是很大的問題,」良心理政創辦人、同樣也是心理學家的葉劍青指出,就算有「612人道救援基金」這樣規模較大的公民組織,能夠以公眾募款的方式提供每人10次諮商療程,但能夠幫到的人數目前也不到百位。而且有的心理治療可能要為期一到兩年,所以只靠公民組織協助不是長久之計,最後仍要回歸到公共社福系統中。
「香港正在面對一次大規模的人道危機,」葉劍青如此描述香港社會的心理狀態。
雖然社會上的心理創傷理想上要回歸到公共的社福體系中,但目前的氣氛,港府與港警和公立醫院合作密切,讓大多數運動者抗拒前往,即便受了傷也不敢到公立醫院就醫,更別說要掏心掏肺把祕密說出來的心理諮商,運動者擔心一旦說出口有可能被醫院的諮商師「篤灰」(出賣),供出他們曾在哪裡破壞過商店、哪幾天丟過汽油彈等等的紀錄,這個病歷紀錄反而可能成為他們被定罪的證據。
這都讓抗爭者不願意相信任何諮商中心,寧願把祕密埋在心中。

理工大學的抗爭現場,總共與警察僵持了16日,Curry在入內一週後決定逃離理大。他與幾位年輕人佝僂著身子、雙腳以半蹲的姿勢前進狹窄的下水道中。下水道裡,有著大量的蟑螂和老鼠,為了保持平衡,他們雙手扶著汙穢的牆壁,身體有一半泡在腥臭的汙水裡。他說,在令人感到窒息的空間裡,除了稀疏的水聲以及蟑螂老鼠亂竄的聲響外,只有遁逃者急促的心跳聲。
「我一直不敢走下水道離開的原因,就是必須確定我不會死在裡面,我才敢走。」Curry在理大思考下一步的抉擇時,他都在想,這樣做會不會被逮捕?或是會不會死?如此高壓的環境讓這位年僅20多歲的年輕人急速長大,但也讓他原本的個性在短時間內出現很大的轉變。
在理大的每一天,因為無處可逃,又害怕警察衝進學校抓人,高壓讓他不斷與運動的「手足」發生爭吵,甚至爭論該如何逃離包圍時,他會以「垃圾」這樣的字眼辱罵手足。
「我以前不是這樣子的,」Curry說。
發現自己的改變之後,Curry傳了訊息問了手足們對自己的印象。而他得到的答案都是「固執」或「不聽他人意見」等負面觀感。這讓他下定決心,找了與良心理政有類似功能的心理支援組織幫忙。
他開始去上心理諮商的療程,因為他不喜歡現在的自己。
在走過運動半年後Curry才發現自己需要幫助,但高強度運動裡有很多人並沒有病識感。「隱藏在心裡的傷痕就像一顆炸彈,爆炸的時候會傷到自己,也會傷到旁邊的人,」阿悅說,社會上有很多像Curry一樣的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或是知道,但不願意尋求幫助、正視問題。
為了改變這個狀況,葉劍青與其他臨床心理學家發起了一個名為「創傷同學會」的運動,透過一些文宣和課程教學,讓民眾可以檢查自己或是身邊的人是不是受到心理創傷所苦,需不需要幫助。葉劍青指出,現在跟1967年的六七暴動很不一樣,因為當時人們對於心理創傷並沒有研究,心理學與臨床心理學並不成熟,「當時很多創傷都被隱藏起來了,」而創傷同學會要做的,就是幫助人們面對自己的脆弱,不需要再假裝自己沒事。
除了與這一代的年輕人站在一起之外,也要讓被關在牢裡與拘留所裡的政治犯們曉得他們並沒有被遺忘。朱凱迪說他與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在耶誕節前夕號召民眾,一起寫耶誕卡片寄給在荔枝角拘留所的手足們。「現在一個人可以收到超過100張,這其實對在裡面的人來說,是很大支持的力量,」朱凱迪說。

面對這次的社會動盪,大批的年輕政治犯的心理狀態,不會是幾個公民組織NGO或是臨床心理學家可以解決。「政治問題仍須政治解決,」阿悅認同這個在反送中運動中常被提到的口號。她認為這句話,同樣也適用在解決香港社會心理健康的問題。
現在仍是每天有警察過度執法不用負責,特區政府官員開記者會說謊話不用下台等狀況出現。「人們的憤怒來源是因為社會上出現了不公義,」阿悅指出,原本長久以來被人們視為圭臬的價值都在一夕之間被推翻了,而人們的焦慮以及不安隨之而來。
因為這些不確定的因素,久而久之,人民就對香港政治上的問責制度失去信心。倘若政府一直對這頭房間內的大象視若無睹,那麼就算是全香港人都接受心理諮商,香港的問題也不會解決。阿悅認為,政府必須讓步、必須滿足示威者提出的訴求,問題才有可能解決。
朱凱迪則認為現在政府部分人士也開始意識到,將反對者丟進大牢裡不會讓社會變得平靜。2016年旺角魚蛋革命時,判了梁天琦等人6年不等的暴動罪刑期,換來的只是更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朱凱迪跟葉劍青都認同,要消除這個沈積了的怨恨,必須要釋放反送中運動裡全部的政治犯。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關了幾年出來之後,不公義並沒有被平反,憤怒並不會消逝。
我們在與麥克的訪談結束之前問了他對香港的未來的看法,問他抗爭有可能結束嗎?
「死掉的人、被捕的人怎麼辦?我們要對得起他們,抗爭還不能結束,」麥可的回答回應了朱凱迪、葉劍青還有阿悅的看法,這一代年輕人堅持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