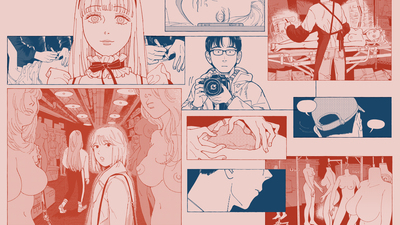專欄【性別有事】

例如在日前,社群媒體Threads上有對其中一部作品的批評討論,認為作品處理「戀足」的方式讓人感到「噁心」,也有「慾望」被消費與商品化引起批評者的反感。社群討論呈現一種明確的態度是,大家並不反對「戀足」,而是不同意藝術家的做法,同時引起大眾對於「藝術」的逾越與界線抱持的遲疑。
「戀足」或多樣的「戀物慾望」這類「非常規」的性,在此之前,似乎同時透過既有的常規被視為「不正常」,亦被性解放論述視為是「激進的」實踐。這兩個力道的匯流,正是出現在北美1960年代末期以降的解放運動中,並且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後,體現在酷兒女性主義學者魯賓(Gayle Rubin)於1984年出版〈性的思考:性慾政治與激進理論的筆記〉(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一文,提出的「性階層」(sex hierarchy)框架。
魯賓認為,現代西方社會根據一套性價值的道德觀,將各種不同的性活動評價為不同的等級:位於金字塔頂端的是「婚內的」、「生殖目的的」、「單偶的」、「異性戀的」性行為,其餘的性行為則依據其偏離標準的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汙名與歧視。
也就是說,在這個社會框架裡,「性」有好有壞,而好壞的標準就是性是否為「再生產」的社會需求服務;再白話點說,就是「一夫一妻、以生小孩為目標的性」就是好的性,其餘歡娛的、非夫妻的、同性的性,都是次等的性。
但魯賓提醒的,並非異性戀再生產機制的問題而已,更需要關注的是「性」如何與「性別」或「階級」一樣,是一種權力關係;而「性階層」揭示的即是以「性」行使的壓迫關係。
如美國文化評論家奈兒(Yasmin Nair)10年前曾提醒:非常規(non-normative)性行為本身與激進的(radical)政治變革毫無關聯。奈兒在彼時回應的是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全國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一事,而他對話的對象不是立法者或一般大眾,正是他自己所屬的酷兒激進與左翼陣營。將「同性婚姻合法化」視為激進的運動,結果可能讓一切能進入婚姻的性都變成「好的性」,與既有的常規體制並不衝突。而在此複雜光譜下,奈兒的提醒並非指向反對同性婚姻,而是要再次聚焦「性的權力與壓迫」,這似乎是我們面對激進的作品與思考所期待的事。
雖然「當代藝術」場域向來被認為是激進與實驗的良田沃土,但也會隨著時代改變其種子與養分,我想試著從台灣每兩年一次的重要當代藝術展覽中,觀察性別相關作品的時代特性,以及前述的爭議作品的時代意義。
自1990年代以來,酷兒運動為了修正過去20年在北美男女同性戀研究中過於「白人、中產階級、順性別」的傾向,激進酷兒們普遍認為,性與個人政治息息相關,也因此那些身為性少數,或實踐性虐戀(BDSM)、多元性伴侶、甚至是持有同性結婚這樣「性正向」觀點的人,經常被認為是「進步的」、「激進的」。
彼時我是一位台灣性別研究生,在許多學術與社運的場合裡,聽到同儕侃侃而談自己的性實踐(其實也就是約炮、性虐、多P)時,也會感覺到自己興/性不在此,似乎就不夠進步與激進。
但如同我初次讀到奈兒的文章時感到被理解的部分:「我們許多人在多年(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上的)性經歷後,才明白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你和多少人發生性關係,與你對資本主義的破壞程度毫無關係。」這裡的「資本主義」與「異性戀常規性」密切協作,(再)生產關係與家庭私有制的維護,也是資本主義運作的重要社會基礎。
簡要來說,「性」本身在長久的歷史裡,一直是貼合著社會發展被納入與排除,但我們期待這個機制以外的社會想像。例如同性婚姻雖然帶來法律上的保護、公民權的實踐,同時那些無法進入婚姻的「性」依舊被排除在認可與保護之外,持續經受原本對於性少數的社會排除。一個微妙的狀態即是,魯賓在1980年代的「性階層」中除了分析出好的性與壞的性,同時也在這中間放了一個「爭議區」,裡頭有著「未婚異性戀伴侶」與「穩定交往的同性伴侶」,還有從20世紀初即被歸納為需矯正的「手淫」。

若由此來解讀前面提及的爭議作品──倪灝(1989-)從社群平台帳號「台灣腳控市集」購入穿過的襪子與穿襪影像所創作的系列裝置作品──「戀足」這一非常規的性,本身只是一種慾望樣態,但在倪灝的作品中,卻與商品化、資本主義密切協作,似乎更加取消其激進性,引發觀者發出「我看不懂他的藝術在哪」的質疑聲音。這樣的批評正反映了性別正常化、主流化後,各種各樣的性本身不「足」為奇,那麼藝術作品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
這部作品其實有著更複雜的樣態:作品陳設的襪子,有來自跨性別女性、懷孕母親、飯店櫃台員工、女性國小老師、年輕父母、男性賣家、同志情侶,系列作品各組裝置標題也對應這些身分(如〈國小老師(下課時間)〉)。另外藝術家也以真實與網路賣家的對話截圖為基礎,製作成動畫影像並展出,有具像的裸足與匿名感,讓整組作品布滿心理學指涉的「詭異而熟悉的感受」(uncanny)。
而將各種各樣的人納入「戀足」這一場域,而非僅呈現「特殊群體」,讓這部作品或許意不在批判也非窺淫,而是揭露一種慾望的「生態系」──慾望如何持續、有機地在網路時代透過資本市場蔓生,有其普世性與時代特性;然而這個生態不一定是朝向永續的未來(環保或再生殖),因此經常被賦予不那麼正面的社會觀感。但當我們認為這個作品奠基於「市場供需交換」、且是「一群成年人共享的喜好」,應該沒有人在此受害的前提下,詭異感就來自於「戀足」的慾望被放進「性的爭議區」裡。但這裡的「性」並非綁定在性行為本身,是一種「性相」(sexuality),比如同性戀、BDSM等樣態。
同時這部作品將「戀足」的隱密與儀式性公開展示,這進一步混淆觀看與被觀看的權力位置。不可諱言,「戀足」與其他的戀物慾望經常置放在被窺視的位子上,在電影中、教育題材裡被劃為「特殊的」存在;但在網路市場與性權論述中,「戀足」具有主動性、甚至處在有力的位置。倪顥的作品似乎正是融合了這兩種位置,呈現性常規與性解放經常指向同一對象,「戀足」在此成為兩造共同成立的辯證主題/體:解放或是保守之間界線模糊,正是在於市場機制、國家法治等「敵人」已不再與「非常規的性」相互牴觸。
那麼,換一個場景來進一步細究「性的激進性」的話,展覽中多部酷兒身體被置放於「教堂」、「青年次文化」、「戒嚴時期」、「奇幻超現實世界」中,又彼此有何扞格之處?我認為這批出生於1980年代的藝術家及其作品,部分反映了策展論述中提出的「思慕」(yearning),將難以明說卻又驅策行動的深層渴望,結合在歷史、家國、性體制上。
如台灣藝術家陳柏豪(1982-)引用白先勇於1983年代出版的《孽子》,以其酷兒性並置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的叔公、及其自身離散北美的經驗,重構一種跨時代的「思慕」經驗中的酷兒史。
近似於德國藝術家托比亞斯.茲耶羅尼(Tobias Zielony, 1973-)的攝影系列《黃金(里加)》、《偽裝(基輔)》回望1991年蘇聯解體後,拉脫維亞與烏克蘭酷兒青年的生活樣貌,將刺青、塗鴉、地下電子音樂等現今已不那麼「激進」的次文化鑲嵌在視覺中。
這兩部作品的創作時間都與「極權」錯身,也不彰顯「受難」史觀,卻在政治上不那麼「激進」的同時,都以不同質地的肖像帶給觀者直視歷史的感受。「時差」在此有如「思慕」的必要距離,就如高田冬彦(1987-)以《公主與魔鳥》這一童話敘事重組「性慾與性別」間的工整性,以鳥語和夢境撐出一個慾望的田園詩歌。或韓國藝術家卓永俊(1989-)在韓國時曾經因基督教傳單中的恐同內容、困惑於信仰的敵意從何而來?而透過混淆「空間與身體」間的對位性,以舞者連結教堂和同志酒吧。
從「耳控」的凝視開始,當《公主與魔鳥》中的兩隻鳥,透過耳語對著睡眠中的少年訴說阿拉伯公主與男兵的性,詳細描述男體毛髮與肛味,少年被撩起的性慾是透過哪一樣素材,而觀者又是如何?卓永俊在《祝你有個美好週日》、《愛你潔淨雙腳的週四》並置教堂和同志酒吧、讓極端性別化的身體穿梭於復活節儀式與禮拜場所、也納入不同族裔膚色與年齡的酷兒身體,亦隱微將宗教儀式與酷兒性愛中的「足控」共存。
這種前衛與古典、異質與正常「共存」的情境,也體現在讓我駐足許久的一對作品。在展場一角,上列藝術家出生前就已離世的畫家席德進(1923-1981)的標誌畫作《長髮藍三角褲青年》與上海藝術家于吉(1985-)的《石肉》雕塑比鄰,幾乎收攏了上述作品中錯置也並置的各種歷史、性、身體的感知。
《長髮藍三角褲青年》的畫中人有著坦然的脆弱,蘊含著時代距離與個人想望;於展場中卻與《石肉─即興的判斷No.1》對望,在鏡頭未及的雕塑後方另有春光。水泥製成的人體部位堅硬厚重、布滿鐵釘,乍看與脆弱憂鬱青年形成對比,但也可以結合成上述所有的非典型慾望、性、身體與身分。
寫到這兒,我也不免自問:上面提到的這些作品中的「性」是否「激進」?或許要放回到「時代特性」來看。因為以激進酷兒的標準,這些作品的內容不僅沒有阻礙資本流通、也未提出政治變革的想像,頂多就是不回應再生殖的要求、或稍微擦邊歷史事件。但這也正正凸顯了我在文章主標的宣稱:性本來就不激進。
如甫獲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的李駿碩自陳,在這個時代拍出《眾生相》細緻重現男同志約炮過程,是「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有一個投資、一個期待,然後有時候當然也會有失望。」男同志「約炮」在上個世紀曾被認為是激進的性實踐,但在當今這個時代裡不再被特殊化,而是回到日常生活的情感、人際中,融入眾生經驗。
以此回到奈兒的提醒,「你的性本身並不激進,但你的政治觀點可以。」當下要討論性的激進性,我認為需要朝向的思考與實踐在於:如何不讓「性」成為受脅迫和貶低的對象,以價值判斷區分性的好壞,忽略「性階層」仍在運作著。若只擁抱特定單一性行為或性/別身分,依舊可能落入將性階層化的思考陷阱,如同「性別主流化」30年來留下的許多未竟之處。
「性別有事」典自著名哲學理論家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經典著作《Gender Trouble》,不僅討論圍繞著「性別」的相關議題和事件,有時也會對「性別」概念與知識找麻煩。
《報導者》性別專欄由台灣女性學學會規劃、撰稿,記錄性別研究大小事,回應國內外在性別議題上出了什麼事,努力每月一更、促進台灣當代社會性別議題新陳代謝。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