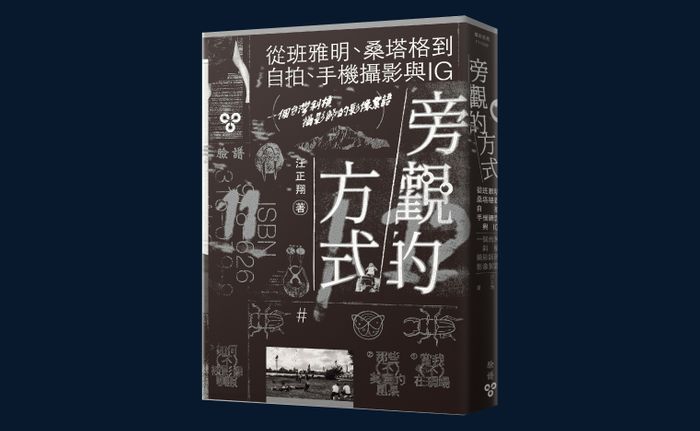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旁觀的方式:從班雅明、桑塔格到自拍、手機攝影與IG,一個台灣斜槓攝影師的影像絮語》書摘,經臉譜授權刊登。本書作者、台灣攝影師汪正翔,在攝影工作中不斷思考影像如何改變現代人的行為與思維。他如何在傳統攝影與數位影像的交界,在社會大眾對「美」的既定印象與創作自主之間,保有思考的可能及感性的靈光,以文字及影像記錄下那些繽紛多元、眾聲喧嘩的台灣風景?
我是一個很愛從工作之中發展創作的人,可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我從來都沒有用人像攝影工作來發展成創作──明明我拍最多的就是人像。可能的原因是人像攝影工作有肖像權的規範,必須取得這些人的授權,才能公開他們的照片,這對我來說太過麻煩了。當然法律不僅僅保障被拍攝者,當別人要使用我所拍攝的肖像,他們一樣要面對我或是發案單位擁有照片使用權這件事。很多時候,我們對於後面這種情況比較寬鬆。譬如我常常看到自己所拍攝的照片,被另一個單位或是被拍攝者本人拿來做為大頭貼、證件照,或是某個活動的宣傳照來使用。有的時候伴隨這些「再使用」的過程,這些照片會經過調色、加亮、裁切或是液化,每次我看到這些修改後的照片,都有一種想要一頭撞死的感覺。並不是說改得一定不好看,而是攝影其實跟許多工作一樣,攝影師所考慮的是一個整體,也像寫文章的、拍電影的,最怕人家沒頭沒腦地引用。這些對照片的再加工,通常沒有考慮到畫面整體的關聯性,一些明明暗色調才能表現的光影變化,一拉亮就全部消失,然後照片就失去了特色。或是有些照片需要帶到一些背景,但是經過裁切之後,整張照片就變得索然無味。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想,這其實反映了一種新時代的現象。在網路時代以前,肖像照片像是一個人的終點。19世紀的攝影師拍攝肖像時,其實是在模仿肖像繪畫,想要將一個人特殊的氣質、美德、身分與階級表現在照片之中,所以這張照片等於這個人的一種註記,甚至於蓋棺論定。但是很快地,攝影師也發現照片總是會展露出意料之外的小小細節,如同細微的火花一樣,在按下快門的當下,於照片之中閃爍。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稱此為「無意識的視像」,它反映了攝影的一種特性,能夠抓住肉眼所看不到的瞬間畫面,而這種畫面不一定跟我們所理解一個人的恆常特質相吻合。
20世紀現代主義盛行之後,攝影師更加擁抱攝影的這種意外,因為現代主義者擁抱媒材的特性,而意外就是他們認定攝影的特性。而到了當代藝術,攝影家更加執迷於攝影的不確定性,他們拍攝人的肖像,可是人物臉上的表情看起來捉摸不定,譬如荷蘭攝影師雷內克.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所拍攝的海邊的青少年。這時候的肖像攝影跟以前那一種句點式肖像攝影完全不一樣了。
可是真正讓肖像攝影改頭換面的是網路時代。過去肖像攝影的特質有一部分跟使用方式聯繫在一起,一張正式的肖像照片,其歸宿通常是擺在大廳或是長廊旁邊的牆壁之上,讓來到這屋子的客人,認識這間房屋的主人或是其成員,理解他們的關係與家族的歷史。可是當照片只存在於網路空間時,照片不再能夠透過實體空間來表現其嚴肅性。這時候出現了一種替代方案,就是大頭貼的欄位。當我們把一張照片上傳到大頭貼的欄位,這張照片就具有某種代表性。但是大頭貼與掛在走廊上的肖像照之間的差別,是大頭貼可以輕易替換,所面向的觀眾更加複雜與多元。所以早期肖像照以家族與社會地位為核心的呈現方式早已不適用,新一代的網路「肖像」常常是卡通、寵物、小時候的照片,乃至於帶有標語的濾鏡,這些圖像並不試圖反映整個「我」,而是某一個我想要對某一族群展露的生活宣言。
名人肖像在這個時代就有點尷尬,因為我們仍然期待名人肖像能夠反映出被攝者整個人的本質,而不是卡通化或是議題化的照片。名人之所以是名人,是因為他們彷彿具有一個比較堅定、恆常的內在質素,而攝影師的任務就是把這個部分給表現出來。有的時候即使我看到了畫面之中出現了某種意外,被攝者對於當下發生的事情有某種反應,或是出現了一個與他形象不相符合但是好看的表情,通常我並不會把這個意外給固定下來,因為這些特質不適合表現一個人的本質。可是當這些照片被拿去做為網路上的大頭貼,你就會發現一切微微變調了。
首先我拍攝這些照片常常需要借助背景來暗示或襯托這個人的某種性情,可是網路大頭貼會把大部分的背景裁切掉,結果不只是背景不見了,人物的個性也因此消失了。第二個奇怪的點是這些照片常常是用高畫質的相機拍攝,可是在網路上卻不如那些卡通照、議題濾鏡與小時候的照片來得吸睛。這有點像是想要拿一張世界名畫當作手機的桌布,但是卻發現效果不如廠商所製作的桌布來得有趣。「廠商」在這裡其實隱喻的是一種文化的體系。當我們使用卡通、哏圖,我們其實是與廣大的觀眾共同身處在一個視覺文化體系當中。然而肖像照所使用的視覺語言卻比較古老,更多時候建立在藝術史或是某種超現實主義的隱喻上。
除了影像的再製,肖像攝影在當代所面臨一個最終極的挑戰就是數位科技,譬如AI。我們都知道AI已經能夠虛擬出看似「真人」的照片。這不由得讓人開始猜想,AI是否也可以模擬出具有「靈光」的肖像照?過去肖像攝影師總是宣稱由於他們跟被攝者之間某種精微的合作,使他們可以拍出一張具有靈魂或是靈光的照片。按理說這是只有人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AI可以模擬出一種充滿靈性的照片,那是不是意味著其中並沒有什麼神祕的元素存在,一切只是一種視覺運算的結果,不過是input 與output,肖像攝影師所宣稱的神奇轉化工夫,在這當中將失去地位。
抱持這個疑問,我進行了一個實驗,把一張打了馬賽克的肖像照,輸入到AI當中,然後觀察AI是否可以將之解碼,重現本人的神韻。我發現結果非常驚人,這些我所拍攝的名人他們經過打碼跟解碼的過程看起來幾乎變成完全不一樣的人,可是我依然可以辨識出他們本人獨特的神韻。甚至可以說,這些照片其實仍然是他們的肖像,只是更加地抽象,就像是諷刺漫畫一樣。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想必會對於這個現象非常有興趣,當他說「擬像」的時候,描述的是一種失去真實源頭的影像。因為在這個時代,大量的圖像經過了複製、修改、二創,到最後已經無法辨識影像究竟是從何而來。可是在我的實驗當中,當名人的肖像照片經過了編碼與解碼的過程,它的神韻卻依然存在。
至此,肖像攝影做為終點的時代過去了,或者至少在網路上是如此。新時代的肖像照片只是一個起點,它將面對無數次的編輯、修改與複製,伴隨這個過程,它的所有權也會逐漸模糊。肖像攝影與攝影師的關係逐步地消解,接著與被攝者的關係也會日趨淡薄。人們可能還是可以辨識出被攝者是誰,但是這張照片並不能代表這個人。就像唐鳳的影像一樣,不斷地被二創,以至於許多照片跟某一個特殊的議題、政策乃至於笑點之間的關係,比起跟唐鳳「本人」更加地緊密。但是說到底,在這個時候「本人」又意味著什麼呢?以拍攝本人為前提的肖像又是什麼?更不用說當Deepfake技術逐漸成熟,本人的影像與本人之間的距離將會史無前例地被放大。肖像照不再透露那個發自人內在的神祕火光,而是觀眾與本人之間一個抽象的符號。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