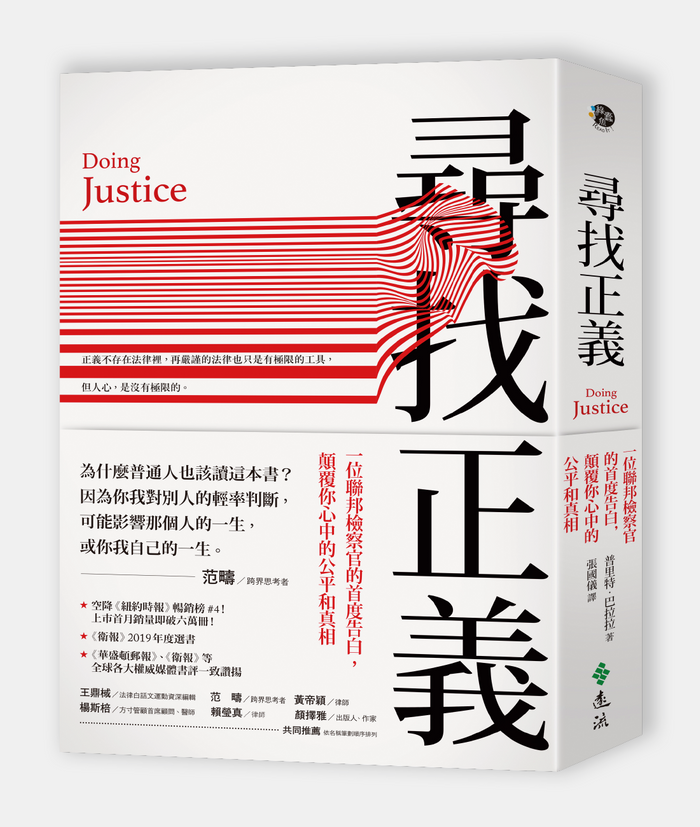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尋找正義:一位聯邦檢察官的首度告白,顛覆你心中的公平和真相》部分章節書摘,經遠流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在司法中最令人迷惑、影響最重大的部分,或許就是與懲罰相關的問題。該如何量刑才能符合一個公平社會所追求的標準,讓懲罰達到必要的程度,卻又不會太超過呢?該如何在懲罰的統一性,以及根據個別案件做出個別判斷這兩者之間達成平衡呢?我們是不是只要專注在罪行本身就好?又或者應該在量刑時,把每一個犯人的狀況都考慮進去,像是家庭狀況、成長背景以及犯罪動機?究竟應該要剝奪犯人人身自由多久,才算是伸張了司法正義呢?沒有人真的知道答案。
所以,司法的最後一個階段「量刑」,具有非常深層的道德、情感,甚至宗教面向。儘管現代的量刑系統嘗試要提供準則,然而法庭上每個活生生的人有各自的故事,不是公式化的計算可以解決的。
本書作者、聯邦檢察官普里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以「卡琳娜嬰兒綁架案」說明「照本宣科」式執法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兩難:被奪走親子時光的父母家人、被綁架但感念養育之恩的當事人、因多次流產犯下自私罪行的竊賊,檢察官為何未採用具有強制最短刑期的法條?法官如何在同理被害者與加害人遭遇後,權衡罪與罰?
該怎麼做才能達到公平與有效懲罰的這個道德困境,並不是只有主審刑事案件的終身職法官才需要面對的狀況。這個為難的處境對許多人來說,都顯得熟悉又苦惱:監管人員必須對違法犯紀的公司做出懲處、上司必須處理行為不當的員工,甚至父母親也必須處罰不聽話的小孩。什麼才叫做符合比例原則?怎樣才叫做有效?該採取什麼樣的懲罰方式才是剛好又不會太超過?
如我所說,這些問題並沒有一個確實或肯定的答案,但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卻時時刻刻都需要有人回答這些問題。而每一天,我們這些平凡的血肉之軀,無不盡了全力希望能夠克服這個難題。
接下來你將會讀到,我們在一件懸宕多年未解、令人悲傷的嬰兒綁架案中就面臨道這個為難的困境。在混亂不安的情緒與悲慘的失去之外,還有我們為了審判所下的賭注,這個賭注可能會讓年輕的被害人再一次落入地獄般的處境之中。究竟什麼才是正確的罰則,這絕不是公式化的計算可以解決的問題。
1987年仲夏,天氣溫和舒適的一天,卡琳娜.蕊芮.懷特(Carlina Renae White)誕生於紐約市哈林醫院。她出生時的體重剛好8英磅,是個健康又漂亮的寶寶,有著淺棕色的皮膚、微捲的頭髮,右手臂上還有個胎記。她的雙親年紀都很輕,兩人尚未結婚,這次的懷孕也並非計畫中之事,但他們非常相愛,並下定決心要一起撫養女兒長大。卡琳娜的母親喬伊.懷特(Joy White)當時才16歲,還在念高中,而父親卡爾.泰森(Carl Tyson)當時22歲,身兼兩份工作,白天開卡車,晚上則是在停車場當收費員。他們並不富裕,但小卡琳娜仍是在雙親與外婆伊莉莎白的期待和歡迎下,來到這個世界,她擁有滿滿的愛與照護,受到家人無盡的寵愛。
卡琳娜出生第19天時生病發燒。她的父母不願冒險,於是在8月4日將她帶回出生的哈林醫院看診,醫生也放心不下,所以將她收治住院一個晚上,並在她的腳上進行靜脈點滴注射。喬伊相信醫院會好好照顧卡琳娜,所以她在凌晨12點半左右匆忙趕回家去,打算收拾一些東西好在醫院過夜。
喬伊一直不知道女兒究竟生了什麼病,因為就在8月5日破曉前,卡琳娜被人從哈林醫院17樓的小兒科病房擄走了。綁架犯把她腳上的靜脈注射拔掉,一把抱起小女嬰,就這樣在完全沒有人發現的狀況下,消失於夜色之中──「就像在酒窖裡摸走一瓶酒那樣簡單」,之後的新聞報導是如此描述。
這件事對卡琳娜的父母造成了難以言喻的沉重打擊。他們一直心懷期待,相信寶寶一定能夠回來。卡爾之後是這麼說的:「我一直覺得我女兒一定會回來。」但是幾天過去了、幾個禮拜過去了,接著是幾個月過去了,警察卻仍是毫無頭緒可言。
而小卡琳娜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那個把她擄走的殘忍小偷到底誰?
這個謎團一直到23年之後才被解開。在卡琳娜失蹤那晚,一個名叫安.派特威(Ann Pettway)、曾因為一些輕罪而遭逮捕的女人,就躲在哈林醫院的走廊上伺機而動。派特威一直很想要有個自己的孩子,歷經幾次流產後的她決定鋌而走險,放手一搏。
喬伊帶著生病的女兒來到小兒科病房時,派特威也在場。她假裝好意關心,甚至假惺惺地出言安慰這位新手媽媽,告訴她寶寶不會有事的。沒多久,派特威發現卡琳娜身邊沒有人在,於是就把寶寶帶走了,沒有人阻止她,也因此後來紐約市立醫院被控告疏失。但儘管警方與相關單位動員傾盡全力尋找卡琳娜和綁架犯,結果卻仍是一無所獲。
派特威將卡琳娜帶離紐約市,來到老家康乃狄克州,並將卡琳娜改名為娜姬亞,對外宣稱這是她剛生下的寶寶。卡琳娜(現在大家都暱稱她為娜迪),一開始是跟著派特威在康乃狄克州生活,後來又被帶到了喬治亞州。
警方對卡琳娜綁架案的調查經過了幾十年,依然一籌莫展。然而,雖然23年前的一場高燒讓卡琳娜落入了安.派特威之手,但最終破解這樁案子的偵探竟然不是別人,而是卡琳娜自己。隨著卡琳娜慢慢長大,很多人都說她跟媽媽長得不像,她們雖然都是非裔,特徵卻完全不同,再加上卡琳娜的膚色較淡,派特威的膚色則很深。卡琳娜並沒有多想,一直到她自己在16歲時懷孕,需要拿出生證明去辦理產前檢查,派特威卻拿不出來,卡琳娜才開始產生懷疑。這個年華已逝的女人終於崩潰大哭,坦白了部分真相:她承認卡琳娜不是親生女兒,儘管說法含糊不清也拿不出可信的證據,但她堅持當年是一名陌生人把還是嬰兒的卡琳娜交給她,接著那人就一去不回了。她只肯說出這些。
接下來幾年,卡琳娜的懷疑日漸高漲,不禁開始想知道自己真實的身分為何。於是她開始搜尋1980年代的失蹤兒童檔案,最後就在2010年接近聖誕節時,她聯絡了美國國家失蹤與受虐兒童援助中心。根據她的年齡、身上的胎記和其他細節特徵,失蹤與受虐兒童援助中心很快就將範圍縮小到兩件綁架案,其中一件就是卡琳娜.懷特綁架案。將剛出生的卡琳娜與幼兒時期「娜迪」的照片兩相對比,就確認了愈來愈明顯的事實:這位一直認為自己叫做娜迪的女孩,其實就是當年被綁架的卡琳娜。
與此同時,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裡,喬伊從來沒有停止思念她失蹤的寶寶。雖然她後來結婚又生了其他小孩,但自己的親生女兒在半夜被陌生人擄走的悲傷,從來不曾稍減。她依然在梳妝台上擺放一張卡琳娜的相片,甚至連電子郵件名稱也是取卡琳娜的名字。她更是從來沒有想過,會接到來自失蹤與受虐兒童援助中心的電話,他們告訴她,她的寶寶還好好地活在人世間。
早在基因檢測的最終結果出爐前,卡琳娜就開始與住在亞特蘭大的喬伊通話了。母女倆沒多久就在紐約重逢,這次重逢感人肺腑且盪氣迴腸。卡琳娜終於見到親生母親、父親、外婆,以及她不知道自己擁有的兄弟姊妹,還有阿姨和表兄弟姊妹。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2011年1月,這個悲傷、曲折,期間長達數十年的嬰兒失蹤案來到了我在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辦公桌上。負責審理這件案子的檢察官是安德莉雅.蘇瑞特(Andrea Surratt),也是辦公室裡一位年輕的明日之星。安德莉雅態度公正、作風嚴厲,除了在法庭上有著優異的律師技巧之外,還是一位領有執照的飛行員和技藝高超的神射手。
現在卡琳娜寶寶綁架案的謎團已經解開,是時候讓安.派特威面對法律的制裁了。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惺惺作態了一陣子表示他們想要這個案子,但根據憲法的規定,這件案子早就已經超過州政府的起訴效期,所以只能夠交給聯邦政府來審理,於是案子就變成我們的了。
在電視上看到自己之後,派特威終於向聯邦調查局的當地辦事處投案。她向該辦事處的特別探員瑪麗亞.強森(Maria Johnson)坦承,自己在1980年代時流產了好幾次,因為太想要小孩,所以就從哈林醫院把卡琳娜抱走了。在一份手寫的自白書中,她說自己「由衷地感到抱歉」。
派特威犯下了刑事罪案,這一點毋庸置疑。就我們來看,她毫無疑問地觸犯了聯邦法律的綁架罪,她的律師羅伯特.包姆(Robert Baum)還想要做些言不由衷的辯護。派特威其實可以修改她的說詞,可以嘗試不讓自己的自白書被呈上法庭,畢竟,當時並沒有可靠的目擊證人看見那天晚上就是派特威抱著卡琳娜離開醫院。不過考量到當時的狀況,我們打輸這場官司的可能性極低,而關於是否被定罪一事,司法判決應該很快就會出來,結果應該也八九不離十。
定罪是這件案子裡簡單的部分。然而,決定要讓派特威為自己惡劣的行為接受什麼樣的公平懲罰,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法律(以及情感)問題,在之後好一段時間裡,這個問題持續佔據了我們的思緒,也進行了非常多的討論。
我所認識的檢察官,絕大多數對於如何讓犯人定罪都相當拿手,卻不是那麼擅長於提供判刑的建議。對檢察官來說,要論證犯人有罪相對容易,一般來說,這其中有著非常清楚明確的道德判斷。每一份起訴書中都呈現了兩種選擇:有罪或是無罪,這裡沒有任何模糊地帶。的確,司法系統也不允許灰色地帶的存在,要讓陪審團定罪,就必須完全肯定此人確實犯下了該罪行,同時要在排除所有合理懷疑的情況之下,才能宣布該嫌犯有罪。這麼一來,我們才有可能在決定嫌犯是否有罪這件事情上,確保司法正義得以伸張。就算是一個看來明顯有罪的人獲判無罪,只要陪審團確實做好了自己的工作、法官沒有在背後操縱結果、律師都遵守憲法的規範,我們就會說,陪審團已經做出了最終決定,司法已然發揮其功能,然後便繼續下一件案子。
但量刑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當問題從「是否有罪」進展到決定刑責為何,事情就開始變得晦暗不清,讓人如墜五里霧中。這時候就不再是二選一,而是有著令人眼花撩亂的不同罰則。如果該項罪行沒有法定強制最短刑期,而且罪行本身也算得上重大,這時罰則的範圍就非常廣泛了,可能是判處幾年的刑期、終身監禁,或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任何刑度。還有賠償、罰款、拘禁,以及判刑確認後的各項限制等等,在在都增加了處罰的選項。
我認為,許多檢察官在主張該對嫌犯處以任何特定刑罰時並不會太認真,也不是很肯定自己的主張是否正確,這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實在太困難了。他們也知道,這份無比艱難的重擔屬於法官。檢察官已經藉由法庭的審判及被告的認罪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很高興能夠把決定剝奪他人多少自由、猶如上帝般的工作交給其他人來處理。這也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法官的原因之一,你要如何才能肯定地知道,究竟要判刑70個月還是80個月才正確呢?又如何知道多增加一天或一個星期的刑期,能為犯人發揮有效的導正作用,還是適得其反呢?
法官沉重的職責就是要在需要進行懲罰的時候,對犯人施以公平的罰則。聯邦法官會根據過去刑案的判例、犯罪性質、從重量刑條件與減刑條件的各項完整數據作為依循,但最終,法律仍是要求必須由法官來決定量刑結果,做出一個「剛好但又不會太超過」的處罰。如果你認為要衡量出這種事情的難度簡直比天還高,你想得一點都沒錯。幾乎所有法官都會坦承不諱地說,穿上法袍最沉重的負擔就是要拿捏出一個「剛好但又不會太超過」的懲罰方式。當他們的選擇受到強制最低刑期的限制時,許多法官自然都會覺得不高興,但是當你擁有可以決定另一個人生命與自由的完全處理權,這也不是什麼輕鬆愉快的事。
公平的罰則可以由人「衡量」出來,這個想法本身其實也是我們長久以來對犯罪與懲罰的迷思。這種數學化的迷思對於要求標準,以及無論種族、地區和其他各種差異都必須一視同仁的司法與公平來說或許很重要,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夠落入這個假象之中,以為充滿缺陷的人類能夠在做出懲罰這件事情上達到完美無缺的公平正義。「剛好但又不會太超過」是神才能做到的標準,也是我們註定無法達到的標準。
所以我們該拿安.派特威怎麼辦才好呢?
由於很早就決定了要起訴,我們也有時間針對派特威接下來的命運進行了許多天的討論和辯論。相關法條裡的一個小節中,有一項法定強制最低刑期:「如果綁架受害人尚未成年,且犯人並非受害人的親戚,那麼最低刑期是20年。」這項法條符合事實狀況,所以我們就按照這個刑度來進行起訴,也就是說如果派特威被定罪,法官判的刑期不能低於20年,她也必須在監獄中服刑滿20年,期間不得假釋。
這無論怎麼看都不會讓人覺得過分、不公平或失望。當時有許多關於公平與強制最低刑期的論戰,但是就這件案子來看,求處這樣的刑期並不會讓人有任何良心不安之處。光是派特威這麼多年來帶給喬伊與卡爾的無比痛苦,還有他們兩人依然持續感受到痛苦和憤怒,就足以讓她在牢裡蹲上20年不為過了。再加上一般傳統會考量的嚇阻作用,這樣的量刑看起來很是公平,所以這就是我們最初採取的做法。
問題是後來才出現的。派特威的律師最後終於說,他的客戶本來已經準備好要認罪了,但是20年的法定強制最低刑期讓她打消了念頭。不過她可能會願意對該法條中的其他部分認罪,再加上任何人都能夠在法官面前進行申辯,最後還是只有法官能夠決定是要判她20年,還是更低或更高的刑期。
這是我記憶中非常難以定奪的一件案子。從一方面來看,生父生母,也就是卡爾和喬伊兩人都承受著極大的痛苦。他們清楚表示希望能夠從重量刑,讓派特威用23年的刑期來補償她將卡琳娜從他們身邊帶走的23年,以眼還眼。但這件案子裡還有另一位受害人,雖然所處的位置不同,可同樣也是一位深受其害的人──卡琳娜本人。不難理解她處於一團混亂之中,而且必須以證人身分出席每一場審判。受害人雖然有豁免權,但他們也可以說是事件中最不客觀也最矛盾的人。角度不同的受害人會想要不同的結果,要在這不同的想望中找到平衡點,其實相當不容易。而卡琳娜想要的,跟她的父母並不一樣。
卡琳娜跟派特威一起生活的日子有好有壞。卡琳娜在學校是個非常受歡迎也很外向的學生,夢想有一天要成為知名的表演藝術家。這段時間的派特威經常吸毒,有時候會表現得像個「怪物」,卡琳娜也看到她持有武器。有時候派特威會打她,但卡琳娜堅持她並沒有受虐:「我不會說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媽媽,但是該做的事她都做了,所以才會有今天的我。」
和派特威一起的日子並不好過,但是即便發現了自己身世的真相之後,卡琳娜還是愛著這個撫養她長大的女人,完全不想跟我們合作將派特威送進監牢裡。此外,派特威還有另一個孩子,對卡琳娜來說也是自己的弟弟,他尚未成年,只有14歲,很有可能會在司法機器的運作之下成為附帶的犧牲品。
2011年春天,在聖安德魯廣場8樓我的辦公室裡,我們開了非常多次的會議進行討論。問題很清楚,但答案可就沒那麼肯定了:我們究竟是要遵循法律條文,照章援引明確且完全適用的強制最低刑期法條,然後在審判時冒著犯人可能不會被定罪的風險,同時加深卡琳娜的痛苦,最後造成危害司法正義的結果?還是我們應該允許被告對同一項法條中的不同小節認罪,然後有可能在審判時讓她被判處過輕的刑期,結果還是危害了司法正義呢?
我們所進行的每一次討論,全然不設限,也歡迎大家提出各種可能的考量。其中有件事直到現在依然深植我心。無論對錯,我不斷地想起兩個年幼的孩子,當時一個8歲,一個6歲,我想起他們在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學中心出生時的情形,毫無疑問,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3天。我想到過去和他們在一起的生活,以及接下來將一同度過的生活,然後我將自己身為一個父親所享有的喜悅,與安.派特威強加在卡琳娜父母身上的空虛和失落相比。只要花5分鐘的時間去想像那樣的狀況,你就會感覺到心中滿是高漲的痛苦和憤怒,只要你是個人,這種感覺就會影響你認為該如何達成正義的看法。
我們可以捫心自問:這是對一位罪案受害人自然而然產生、恰如其分的同情嗎?又或者這正是偏差想法的源頭,更是一種危險的情緒呢?你會希望我們的檢察官有這樣的想法和這樣的情緒嗎?所謂「以滿腔熱血追求司法正義,卻不對任何特定案件懷抱特殊感情,同時始終保持著公正心態」,其真正的意涵是什麼?曾經有一次,我要求在場討論的人投票表決。當時總共約莫有8個人,包含了承辦檢察官、主任檢察官,以及我最優秀的幾位副手。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努力想要理出頭緒,究竟怎麼做才是對的,而這個重擔沉甸甸地壓在我們所有人身上。
我們的這場爭辯中還有另外一個潛藏的重點:派特威養育卡琳娜的方式對於量刑來說是否很重要?她的教養方式與這整件事有關嗎?以綁架犯照顧自己偷來的孩子的好壞程度作為量刑的基準,這是對的嗎?如果今天派特威把卡琳娜養育成一位獲得牛津大學羅德學人獎的傑出女性,一切是否該因此而不同?
表決結果一面倒。多數人贊成求處強制最低刑期20年,少數人則是贊成讓被告對某些罪名認罪,並讓她有機會獲得令人難以接受的輕判。我花了幾分鐘才發現為什麼表決結果會出現這樣的意見分歧。這與資深程度、性別,或個人行事作風是嚴厲還是溫和都沒有關係。我的發現是:每一位贊成判20年的檢察官自己都有孩子,而每一位不贊成的檢察官則剛好相反。所以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只能在那天晚上回家後,比平常再多花幾分鐘抱抱孩子,然後上床睡覺不再多想。
我花了一點時間來思考,最後還是下令選擇走較溫和的路線。到最後,被害人過得好不好,還是戰勝了其他考量,我們不希望因為強迫卡琳娜出席那些她不願意作證的審判,而讓她的心靈再次受創。坦白說,這同時也是種策略性的做法:卡琳娜已經不再是對我們友善的證人了。她中途就停止了與聯邦調查局和我手下的檢察官合作。如果要開庭,她要求必須有傳票她才會出席,而且就算出席了,她的態度也是反覆無常,難以捉摸,而這是你不希望在庭審時出現的情況。這種創傷很有可能會讓她受到二度傷害。
我們保留求處20年刑期的權利,但放棄了求處強制最低刑期的認罪要求,現在一切就看法官要怎麼決定了。有些人可能會說,本來就該如此才對。所以,我們下了決定,也做了了結,同時也放了卡琳娜一馬。
派特威認罪了,而喬伊和卡爾對我們的決定非常不滿。在宣讀判決時,他們以尊嚴的態度,用溫和的口氣說出了他們的心聲,字字句句都是心酸痛楚。卡爾率先發言:「我必須說,23年,安,妳讓我痛苦了23年。妳在我的心頭劃下了一道傷痕,奪走了對我來說非常珍貴的東西。我再也沒有機會為我的女兒慶祝週歲生日、看著我的女兒去上學、送她去搭校車。妳帶給我的傷害實在太深了⋯⋯妳破壞了我的人生⋯⋯他們應該要判妳23年的刑期才對,因為這就是妳從我的人生中剝奪的歲月。」這番話中的邏輯令人難以反駁。
這類的嬰兒綁架案並不多見,但確實會發生。就在我寫作這本書的同時就有一則新聞報導,有個小女嬰在1998年時被人從傑克森維爾的一間醫院擄走,相隔18年之後,她才與親生父母再次團聚。而這件案子裡的父母則是要求對被告處以死刑。
這樣的失去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卡琳娜的雙親並不是唯一受到傷害的人。如同喬伊所說:「這件悲劇深深影響了我的人生、我女兒的人生、我的家庭、她的外婆、她的阿姨,還有她所有的兄弟姊妹。我們的人生從卡琳娜失蹤的那一天開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的女兒找到了我,我卻始終沒有找回我的女兒。」失去的已經永遠失去了,那樣的空洞是永遠填不滿的。
法官卡斯特(Kevin Castel)在宣判時,特別提到他對這件案子有極大的裁量權,這件案子的刑度範圍也非常寬:「基本上,法院有權力決定被告入監服刑的時間長度,我可以判她只要坐牢一天,也可以判她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或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任何刑度。」
所以,他的決定究竟是什麼呢?他判派特威入監服刑12年,對此喬伊和卡爾震驚不已,我手下的檢察官也非常失望,卡琳娜則是沒有出席。法官再次強調這起綁架案中各種令人為難的細節,同時也再次提起派特威不幸的童年生活,其中包括了性虐待、藥物成癮、精神疾病,以及連續幾次的流產。他也提到卡琳娜的親生父母因為這件綁架案所承受的刻骨銘心悲痛,這是一件偷走了23年親子關係、家庭關係和卡琳娜身分的「無終止罪案」(continuing crime)。
但是,或許最能展現事情全貌的是這幾句話:「我考慮了何謂公平的懲罰。這並不是貪婪的犯罪,也不是復仇的犯罪,而是自私的行為。這是一件因為自私而犯下的罪案。」而關於我們的司法體制,在這裡也有幾句該說的話,那就是,司法體制刻意避免發生聖經中那種早已過時的「以眼還眼」式正義。
無論法官在這件案子裡的衡量是否完美,公平的懲罰需要的不只是對被害人的同理心,也需要有對加害人的同理心,去考量犯罪的原因──無論是據此減輕或加重判刑──我們必須將加害人的所有狀況納入考量,仔細思考、權衡兩邊的輕重。這是個不可能達成的任務,我是這麼想的,但法官的工作就是要試著去達成。
這個判決結果是對的嗎?正義獲得伸張了嗎?當時的我不確定,以後的我也永遠無法確定,儘管直到今日,我還是會想起這個令人心痛如絞的竊嬰案。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