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7日,國民法官法庭迎來首件精障者殺人案件,41歲鍾姓男子持啞鈴殺害78歲父親,兩人皆為思覺失調症病人;母親獨自扛起家計,父子在家彼此照顧長達10年,累積的相處不睦加上被告精神病急性發作,釀成悲劇。審理過程罕見傳喚3位精神科醫師作證,試圖釐清被告病史和精神狀態,但一連4天的密集攻防,關於社區精神資源的討論卻付之闕如:除了醫療,這個家庭究竟有什麼社區資源和支持系統可以承接?
啞鈴殺父案照見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的典型困境──孤立。為強化社會安全網,《精神衛生法》在2022年修法,改革重點之一便是增加社區精神資源。目前社區服務的不足是什麼,還可以怎麼做?《報導者》專訪伊甸基金會在2016年成立的「敲敲話行動入家團隊」,他們希望以解決需求為導向的會談長期陪伴,為處在精神危機的家庭創造連結。
「我們做的一切目的都是為了防止孤立發生。」 ──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創始人亞科.賽科羅(Jaakko Seikk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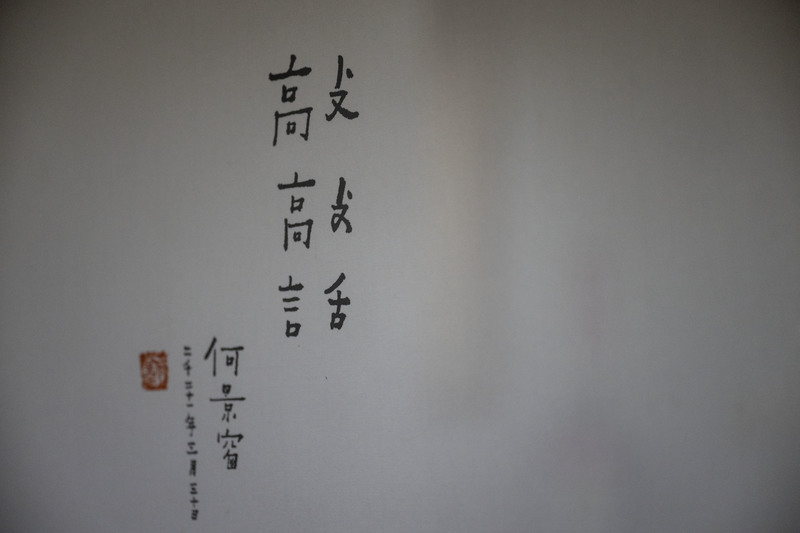
談到啞鈴殺父案,郭可盼認為危機在更早之前就出現了。她說,這個家庭除了就醫服藥,還有使用哪些資源是個問號,另一方面,被告母親承擔照顧和經濟重任,即便有其他資源選項,也根本騰不出時間和機會;而有思覺失調症的父子長期困在家中互相照顧,反倒造成更大壓力,致使病情惡化。
(延伸閱讀:〈國民法官首件精神疾病患者殺人案──法庭之外,未解的旋轉門效應與真空的社區支持系統〉)
目前體制對危機的認定是有「自傷傷人之虞」,但敲敲話重新思索精神危機的定義,認為相關資源應該更早介入案家,只要當事人和照顧者的互動緊張或衝突,就是一種「關係的危機」。郭可盼說,「照顧者負荷過大,有些家屬會用『共病』來形容,當事人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可能家屬也會有身心症狀或是精神官能症。」
對於此案交由國民法官審理,敲敲話個案管理員葉雅欣感到擔憂。她認為,大眾對於精神疾病仍抱持相當的恐懼,且這個家庭與親戚關係淡漠,幾乎完全孤立,把事件搬上公共檯面恐造成二度傷害,加上大眾媒體的高度關注,被告得面對輿論反覆指責他是殺父凶手。葉雅欣說:
「被告可能只能不斷認罪跟痛苦,沒辦法應對法律上講求的證據和時序。對他們(鍾男和鍾母)來說太遠了,都還在那個傷痛跟感受裡,或是孩子的精神混亂裡。有人會說這是個社會教育的機會,但也不應該踩在這些人的傷痛上。」
顧慮其來有自。思覺失調症不只是一般大眾心目中最害怕、未除魅的精神疾病,也是醫療或助人工作者普遍認為最困難的類型之一,無論是治療或理解都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其棘手的症狀包括因幻覺產生的現實認知扭曲,敲敲話也與不少有幻聽的個案接觸過──有人聽到父親要自己「上天堂」,於是嘗試自殺;有人則稱被女鬼追殺,耳邊經常傳來「去死」的聲音。但葉雅欣表示,如果不先入為主,幻聽可以是打開心底深處房間的鑰匙。
原來,上述自殘的個案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沒得到父親的肯定和關愛;聽見「去死」的命令就想執行的個案,真的認同自己不值得活,因為從求學到就業,總是學得比別人慢,深層的自卑讓他的幻聽變得格外沉重。
「你可以把幻聽視為一個症狀,壓制它、不理它,靠藥物讓它減少,也有些人找到方法跟它共存。不過如果可以一開始就面對這個幻聽,可能會發現是來自於真實生活經驗的受傷,或是壓力的對待。」
葉雅欣也提到,不去理會反而讓幻覺建構的故事發展下去,一旦它變得更完整,就更難打破。但陪伴個案一起經歷,不去否認那些恐懼,才有機會建立連結。

敲敲話是從伊甸基金會的「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發展而來,在8年來的接聽經驗裡,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求助家庭,患者都有穩定服藥。葉雅欣直言,藥物當然是治療中重要的一塊,但顯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可惜社會目前談到精神疾病,都還是非常單一的想像,除了醫療,缺乏回到社區的支持系統,第一線的社區關懷訪視員(簡稱社關員)、心衛社工、公衛護理師都被不合理的工作量和績效指標所擠壓。
在社區的精神衛生體系裡有明確的個案分級,人力不足、案量又高的情況下,工作者在系統中評估勾選後,往往只提供「符合法規要求」的服務,難以再給予更多。
以啞鈴案來看,個案有多次的就醫紀錄,葉雅欣推測,「可能大家會覺得有穩定就醫,就沒有那麼follow up他們家其他的需求,或者被排在比較後面的順序。如果這個案家是在比較後面的等級,可能一個月只電訪一次,媽媽又忙著工作,就說沒問題,就沒了。」
但社工如此處理也是身不由己。社區入家工作者專業促進聯盟曾舉辦工作坊,從第一線蒐集而來的問卷顯示,社關員還要做核銷、回公文、打會議紀錄,甚至在疫情期間也得支援防疫業務、回答居家隔離問題、送關懷包等,原本已經多到難以負荷的案量、少得可憐的時間,又再次被外務擠壓。
困境已久,政府也看見沉痾,2022年《精神衛生法》終於修法,預計在2024年正式上路實施,其中一個改革重點就是強化社區精神支持資源,例如連接患者出院後的各項服務(如全日型、日間型、居家型等機構或據點)、開辦照顧者專線、提供喘息服務、建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等。敲敲話肯定增加投入的方向,但也觀察到另一問題:量化績效指標(KPI)太過離地、流於形式。
2021年,敲敲話與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合作創新計畫,表定一年服務27個案家。相較於其他政府標案,創新計畫的KPI已經寬鬆許多,並可共同協商討論,但第一線的執行經驗和官方的想像仍有落差。
對社工們來說,KPI是壓力也是緊箍咒,葉雅欣舉例,政府現在推動各地的心衛中心或協作據點,也都會有服務人數的要求,認為既然投資就要有績效出來。但精障者要出門本就困難,社工得耗費很大的心力,假如據點只是被動地要大家來近用,恐怕不符合現實,但社工出勤的時數能否被算進KPI,又是另一個問題。
為了達成許許多多不同的KPI,社工被要求「短開結」,郭可盼解釋,所謂「短開結」意思是短期開案、短期做完、短期結案,在這種情況下,工作者只能處理最表層的問題,或是想著要把個案轉介到哪個地方接手。個案看似在每個階段都有可以使用的資源,但問題在於:
「每個階段worker可能都不一樣,關係是比較斷裂的。比如說有危機或多重議題的時候,可能是心衛社工,穩定後可能是社關員,但是很多社關員跟我們說,他們因為案量的關係,6到9個月就被要求要結案,然後個案又被轉到公衛護理師。」
郭可盼說,這代表個案常在衛政和社政系統間流轉,關係高度被切割,得要反覆重述困境、重新建立關係,不利心理延續性。
對此,她認為需要一個「家庭個案管理員」的角色,讓社工成為輔具,固定陪著案家去使用資源,有點類似歐美國家中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 GP)的角色,醫師提供的是醫療的諮詢,社工則可以陪伴障礙者家庭面對各種生活困難,媒合適合的服務。
更重要的是,社工可以扮演橋梁的角色,銜接服務之間的缺口,「盡量是把資源做納入,而不是轉介。因為你請他去找別的資源的時候,那個窗口可能聽到他們的自述,會覺得好像不需要服務,或是說還有別的服務,又再一次轉走,常常可以看見家庭在轉介中間有各種原因的掉落,」葉雅欣解釋。

這些年,精神疾病的討論增加,文學和戲劇創作也帶給大眾另一種視野。但接觸過許多案家的郭可盼發現,精神疾病的汙名並未消失,可能只是變得隱晦了──在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後,很多家屬都擔心自己的孩子會不會變成第二個鄭捷,這是他們心底最深層的恐懼。
於是他們加強對患者的控制,例如服藥上有爭執就會演變成更大的衝突;又或者患者其實可以嘗試就業或建立親密關係,「但家人太害怕了,會退回來,以最穩定的方式安排,我寧可讓你退出本來能力可以嘗試的事情,安全優先。」
當這樣的恐懼或汙名持續加劇,家屬甚至很怕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這件事被鄰居知道,即使還沒有任何攻擊行為出現,大家都先嚇壞了,反而讓個案陷入更孤立的狀態。
敲敲話所參照的開放式對話,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重新創造連結,防止孤立。郭可盼說:
「如果一個人的世界沒辦法被理解的時候,那是一個非常孤單的經驗,很愛的人在你沒辦法靠近的地方,對家屬來說也是很孤單的。不理解的時候,就會試圖去控制或改變他,對當事人會創造更多的撕裂和絕望。不一定每件事情理解為什麼之後,問題就迎刃而解,沒有這麼美好,可是至少不那麼被孤立的感覺,人與人的生命是有連結的。」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