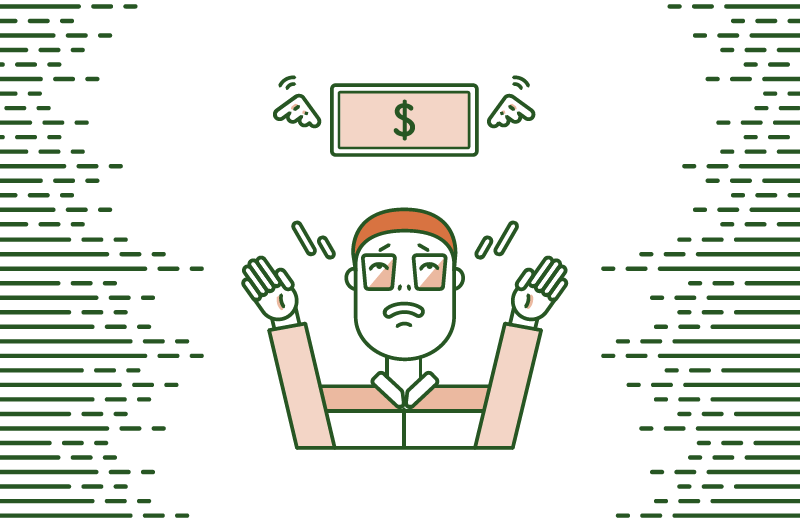社會工作者犧牲陪伴家庭、子女的時間,協助另一個墜落中的家庭或身處脆弱時刻的人們。這份燃燒自己照亮他人的工作,卻存在四高一低的困境:「高工時、高壓力、高危機、高負荷、低薪」。當燃盡熱忱與體力的社工選擇轉身,跟著下墜的,是整個國家的社會安全網絡。
「我雖然才做快2年,但已經是10年來最資深的社工了。」 「3個月來,辦公室5個社工離職了4個。」 「在一年半內,我已經是這個案子的第4個社工了。」 「每個月會收到人資寄信說哪些同事離職,差不多每個月至少有2個社工會離職,多的時候就會一次看到有4、5個社工都離職了。」
訪談各機構和社工,幾乎都有共同的現象,就是社工員都呈現「高離職」狀態。作為維護社會安全網的核心力量,社會工作者的高流動率,動搖的是台灣社會福利的未來。
「怎麼又換社工了?我已經換過3、4個社工了。」服務於身心障礙領域的社工佩佩(化名),接下新個案時,總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
「你現在接下我,真的會繼續嗎?你會不會很快又走了⋯⋯」頻繁換社工的經驗,讓個案不確定社工陪伴的持續性,不敢再輕易相信她。然而,佩佩服務的是因事故致傷的身心障礙者,除了肢體上的復健,中後期需要克服許多情緒上的困境,才能邁向生活的重建。一旦案主不願打開心房,復原之路就會走得更加艱辛。
社工琪琪(化名)曾從事早期療育相關的社會工作,在職的不到1年內就經歷過6、7個同事的離開。機構的高流動率,讓民眾失去對社工的好感,「最後變成民眾只要聽到是某某單位來的人,就不信任,因為單位的人就是一直換。」琪琪語重心長地說,個案對社工的需要是有持續性的,不像是去郵局,一次就可以把事情辦好。
建立關係、累積信任都需要時間。個案要對社工有足夠的認識、了解,才能逐漸產生信賴感,願意將心中最難以開口的問題說出來。每一次重述往事,都要耗費極大的心力、還可能是二次傷害;好不容易敞開心胸接納社工,將社工視為「重要他人」,這時候社工再離開,對個案來說又會是一大打擊。
社工高流動的反覆循環,消磨的是個案對「社工」角色的信賴感。婷婷(化名)投入身心障礙領域社會工作,曾在小型機構任職1年8個月,卻已經是該協會10年來待最久的社工。回顧與個案相處的經驗,婷婷表示,當社工無法和個案建立信任關係時,個案遇到狀況不會說出來,社工輾轉才知道情況,很可能在第一時間錯失協助個案的最好機會。
除此之外,有些機構面對社工流失後的職缺,會進行內部調動,也造成傷害的連鎖反應。在兒少領域工作10年的社工君君(化名),就因爲同事的離職,被迫中斷自己原本陪伴邊緣青少年的方案:「我就會覺得很可惜,或許只是再一年、再半個學期,我們就可以改變孩子的狀態。」對君君來說,這樣的轉調讓他擔心的是,原先他所陪伴的青少年們,很可能就掉出網子外了。
高流動率的背後,反映的是基層社工的勞動困境、過勞與低薪。抱著理想的社工新鮮人投入社工界,面對的是高工時、高壓力、高風險及高負荷的勞動環境,只得靠著燃燒滿腔熱情與體力來支撐工作。
記者採訪了30名不同領域、年齡、機構、經驗的社會工作者,試圖從真實的社工勞動現場,找到那些壓垮社工的的沉重巨石。
30名社工凝聚心酸血淚的職業生涯分享,呈現了社會工作遠遠超出想像的辛勞程度。高工作量帶來的身心壓力、與負荷完全不對等的薪資,種種困境讓社工很難不被壓垮。社工本應是提供幫助的人,卻發現幫不了自己。
細雨濕冷的凌晨4點半,剛安置完個案的社工阿傑(化名),從安置機構外的山坡走下來,進到便利商店買杯熱飲,想坐下來喘口氣。「我剛坐在那邊開始喝,又接到警察局的電話,說有另一個家暴受害人需要安置。」
阿傑再度回到警察局,一樣要全心全意與個案談話、疏導,帶他去醫院驗傷。他一邊抓緊空檔到處打電話,努力找到可以安置個案的機構。無數通電話來回後,終於找到床位,陪同個案去機構安頓下來。這是阿傑出門工作的隔天中午,他已經連續工作超過24小時了。
這樣疲憊的日程不是個例,而是保護性社工輪班執勤(on call)的真實寫照。保護性社會工作的業務常常要接觸、並緊急安置傷痕累累的受害人。
安置個案的工作非常複雜,安撫完個案的情緒、驗傷、體檢之後,找床位是最大的困難。
阿傑無奈地說,「有時候可能把整個縣市相關機構聯繫過一遍都找不到,還要跨縣市才找得到能安置的機構。」他曾在下午4點接到個案,晚上9點才終於找到跨了兩個縣市的床位。有時一邊找床位,一邊還要面對家屬時不時的威脅、嗆聲。如果是法定緊急安置,時間就更緊急,向法院提交安置聲請狀的期限只有72小時,安置完要馬不停蹄地趕辦文書工作。
阿傑從事保護性業務3年多,隨著資歷上升,工作壓力只增不減,身上背負的案量如滾雪球般成長。「我身上背負著100多件個案,幾乎每2天就有新案件要進來,」阿傑說,所有上班時間都拿來訪視也不能消化,每天加班到8、9點是常態,如果有突發狀況要安置處理時,就算過午夜才回到辦公室都不意外。
超出負荷的龐大工作量,如重重的大石壓在阿傑身上。作為保護性社工的工作壓力,讓他連自己的身心狀態都快自身難保,最終不堪負荷,只好帶著滿身看不出的傷,離開這份工作。
不堪工作負荷而轉職的阿傑,是廣大出走社工的縮影。
社工秀秀(化名)過去也從事保護性業務,由於同組的人力不足,秀秀在懷孕時仍然要跑外勤安置個案。有次為了一個個案,從早上8點出勤到晚上8點,因為兒少保護的處理在時間上更緊迫,她還是惦記著要送給法院的緊急安置聲請狀,隔天不能請假,趕在24小時內把申請狀送出。一天下來的勞累與高壓,導致秀秀嚴重宮縮掛急診。
由於懷孕時印象深刻的過勞經驗,加上輪班執勤制度的時間與情緒壓力,秀秀決定離開社工界,轉任一般的行政工作。「我也想繼續做社工,但不可能為了去照顧別人的家庭,沒辦法照顧自己的家庭,」秀秀說。

曾是台南市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以及社工督導的胡勝傑,現在是台南孔廟附近「吉來小早餐」的老闆。從事兒保工作10年後,毅然決定離職的關鍵,不是對工作失去熱情,而是每天忙著協助別人的小孩,卻沒時間陪伴自己的家人與5歲兒子。
「整個體制還是看報表,卻沒考量到我們面對活生生的人,每個個案的複雜程度都不同。」胡勝傑舉例,以台南來說,家防中心社工手上的案件每月大約為20案,還有開新案的壓力。但除得兼顧舊案的家訪,若有新的安置個案,從找床位、寫報告、發公文,流程跑完恐耗費3天。
胡勝傑的太太小壹表示,每次看電影,只要先生的手機一震動,他就得外出接電話,「直到我先生離職前,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看完一場電影。」出國玩接上wifi,LINE立刻湧入海量工作訊息,先生總忙著回訊。「每通電話或訊息的另一端,都是一條人命啊!」胡勝傑感慨地說。
雖是「退除役」的社工,現在,胡勝傑早餐店的小攤車,貼著「我支持社工」貼紙,還為買早餐的社工免費加蛋,是他為在崗位上打拼的夥伴們加油打氣的方式。
「很常有人離職的原因就是burn out(專業枯竭),這是最能描述我們狀態的詞,」醫務社工小萍(化名)這樣說。
作為醫院社工,小萍除了一般的福利諮詢外,也常常需要協助很多沒有身分的人,「很多人就是被丟在醫院,全世界都丟下他 ,那就是我一個人要處理,但醫院立場就是這個人要出院。」小萍舉案例說明,一個倒在路上的街友進院後,醫院要求社工在一週內讓他出院。短短7天內,小萍必須確認他的身分、建立檔案,還要確認他出院後的去向。
「如果不從第一天就啟動,根本來不及。」小萍必須像偵探一樣抓住各種蛛絲馬跡,找警察壓指紋、核對長相、辦身分證、健保卡,找到他的家人,向社會局通報,還要照著名單一一聯繫可能安置的相關養護機構。
工作節奏快又高壓,小萍被醫院、被機構罵都是家常便飯。「醫院逼醫生,醫生逼社工,社工只能逼社會局、安置機構,逼久了都累了,」小萍說。
普遍過勞的社工,薪水卻常常和工作量不對等,而且很難隨著年資成長,缺乏職涯發展的期待與可能性。我們訪談30名受訪者中,有20名社工年資在5年以下,薪資從24K~38K不等;但10名投入社工界6~13年的資深社工,平均薪資竟也不到4萬元。
快30歲的社工阿寬(化名)坦言,「開始有點懷疑這份工作的未來,」5年來薪資只從35K漲了1,000元。「作為男生,想要成家時就會發現,當社工的這個薪水只能養自己,」阿寬說。
「雖然這份工作內容貼近我的理想,但它的薪資條件,不足以支持我後續的人生規劃需要。」投入社會工作3年半的琪琪(化名),被問到5年後會不會留在社工界,掙扎後還是搖了搖頭。不合理的薪資結構,導致了社工的出走與高流動率。
根據2012年衛福部委託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進行的《台灣社會工作人員勞動權益研究》指出,社工的每月薪資水準主要落在25K~35K,約佔了7成5,即使加上超過35K的另外2成5,整體平均薪資仍只有32,072元。
統計上呈現的平均低薪,或許與流動率高的情況下,有很高比例年資較淺的社工有關。然而,除了資淺社工的低薪,每個社工深刻感受到的,還有整體薪資結構的僵化。
調查中發現,有近半數的受訪者表示,任職單位對於同職位薪資幾乎不曾調整;即便曾調整,有3成每年調幅只有0.5%以下,反映出整體薪資調幅微乎其微。琪琪表示,她的督導從社工做起已有10年資歷,月薪才35K,「每年才加500、600元,還不一定每年加⋯⋯假設你(考核)順利,也是2年加1,000元而已。」
不勝負荷的工作量與壓力、不成比例的薪資水準本來就容易動搖留任的決心,再加上看不到未來職涯發展中明顯的加薪升遷前景,灰心受挫之餘,都是社工高流動率主要的因素。
社會工作勞動力市場中的一個特殊性在於,薪資來源大多是由政府經費或者是社會大眾捐款。社工從業人員中,約65%是受民營非營利組織聘雇,據受訪者表示,政府經費可能佔許多非營利社福機構整體財源的一半以上,甚至在許多中小型機構會超過7成、8成。整體而言,政府正是非營利組織的大金主。
政府相關單位常常會將法定的社會福利業務,以「方案委託」的方式公開招標,向民營機構購買服務,俗稱委託案。另外也有由政府劃定部分社福預算,作為各特定項目的「補助經費」,讓民營機構寫服務計畫申請,則稱為補助案。
這些政府方案計畫的經費支付標準中,通常會有一個「專業服務費」項目,說明計畫中所需聘用社工員、督導、中心主任的基本人數,以及政府會支付每個人多少費用。在許多的委託案中,無論是做1年的新手或是從事10年的資深社工,一個社工員的「行情價」,都統一以每個月33,000元計算。
然而,第一線社工實際領到的薪水,卻常常低於政府的標準。
首先,將方案委託外包的政府單位,包含了中央衛福部和地方政府的各局處,不過不同單位、不同方案之間,並沒有統一的基本規範。例如,作為社工人事費用的「專業服務費」到底包含哪些項目?是否包含雇主應支付勞健保金額、6%退休提撥金等?有些契約會從33,000元再外加計算,有些契約則包含在其中,甚至有些契約完全沒有說明。
當契約中出現這些模糊地帶,可能造成政府與機構有調整空間,從表訂的33,000元中扣除部分雇主應負金額後,才是給付給社工的薪資。所以即使有33,000元這樣的「公定價格」,社工員領到的薪資,很有可能都比契約中給付標準來得低。
「當然啊,因為它就是會含(資方支付的)勞健保啊!資方就會覺得說,我又沒有這筆錢!」曾在3個不同地區、不同機構工作過的琪琪指出,機構多仰賴以政府經費支付資方應付金額,因此這樣的現象並不罕見。
婷婷回憶過去在中部小型協會工作的經驗,向政府核銷的薪資帳目數字和社工實際領到的金額,也往往有所差距。
對於許多中小型機構、特別是社團法人形式的各種協會來說,財務來源很大部分仰賴申請政府的補助案。補助案比起委託案,較常要求機構在專業服務費上應有一定的自籌比例,但是小機構可能財務狀況相對不穩,加上募款能力較低,讓自籌經費成為重擔。
「如果是比較有名望型的機構,他們募款會很容易,一次可能募都是10幾、20萬。那小機構,可能名不見經傳,募款都是200塊、500塊。」「景氣不好的時候,連大機構都收不到募款,小機構募款就更困難。」同時,如果機構在評鑑中沒有辦法得到最高優等,政府也會將補助款項打折。
部分機構為了解決無法負擔的薪資缺口,選擇用「報高給低」的不足額給付來應對。假設有一個案子的專業服務費,在契約中已經表定33,000元,但政府只願意支付8成,要求2成由機構自籌。這時機構就會在核銷時,向政府核銷33,000元的薪資給付,但只給社工領到政府補助的8成款項。
除此之外,由於聘用一個人力除了薪資還有勞健保費用,對組織來說也是一筆負擔,同樣有可能被轉嫁到社工員身上。婷婷說明,如果一個人的薪資32,000元 ,勞健保是用薪資33,000元級距,資方支付的勞健保大概要6,000、7,000多元。「如果協會付不出這筆,可能又會從中扣,」婷婷說。
中小型機構是社福生態系中讓服務類型多元化的重要角色,但先天體質和後天限制下,足額給付薪水都是一大難題,更遑論有制度加薪、留任社工。
事實上,不管是規模是大是小,社福機構已數次被點名長久以來有「回捐」的陋習。機構為了方案中拿到更多的經費,瞞著社工,或是以補貼機構訓練費、行政費等各種名目,扣留社工部分的薪水或津貼,然後操作成是社工捐給機構的款項。這些,都讓社工低薪困境雪上加霜。
根據衛福部委託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進行的「2015年社會工作者勞動薪資調查研究」, 21.2%的社工人員實領薪資低於應領薪資,其中有46.7%差額在1,000元到3,000元,原因除了機構將雇主應負擔的勞健保費用預先從薪資中扣除,還有社工界惡名昭彰的「回捐」。
此外,政府給機構的補助款未必編列「加班費」項目,衍生出「加班換補休」勞務型回捐。在「2015年社會工作者勞動薪資調查研究」中,有40.4%的社工任職組織,未依法定計算方式給付加班費,其中54.3%只給予補休,有4成若半年內休不完就歸零。甚至有4.4%的受調查者「功德式加班」,補休、加班費都沒有。
如果說,社團法人、中小型機構有先天上體質的限制,影響所能提供的勞動條件,那麽規模相對較大、財務與營運相對穩定的基金會等大型機構,是否能提供較好的待遇?
以勵馨基金會為例,薪資水準是依據一套機構內部的敘薪機制,學士級的員工起薪去年還是從28K開始,如通過考核、職等升等,薪資會往上調升;而這個起薪標準還是約4年前微幅加薪才達到的水平,在此之前近10年沒有變動,雖然今年調整到30,600元,但仍未達到政府補助的基準。
勵馨基金會研發處處長王淑芬表示,如果一個負責政府委託業務的員工,勵馨按照內部敘薪標準,雇用他的薪資低於政府給付標準,會依法將差額退回給政府,沒有溢領的疑慮,也不會要求員工回捐。
不過,退回經費的作法仍可能引發疑問:既然政府對於社工提供的服務已經明定出薪資價值,為什麼機構不願意讓社工領足政府補助的全額?
王淑芬指出,內部敘薪制度是基於機構內部管理所需設計出的標準。機構的考量包括內部需要一個明確的加薪制度、升遷結構來鼓勵員工,而不是政府制定的不合理齊一標準,而且也需調和補助來源的各政府單位間,對給付規範的差異。再加上機構希望無論是執行政府委託補助案、或由機構自籌款支應的員工,都有同樣的薪資水準,讓內部更一致,考量整體財務營運能力後,選擇採用這樣的機制。
面對政府目前的不合理制度,即使有些機構用自籌經費補貼部分資深社工薪資,建立機構內部的升遷加薪制度與獎金福利來鼓勵留任,但多數仍然需將制度建立在讓資淺社工起薪低於政府標準的情況。

在社福業務大量外包的今日,政府委外契約是整個市場的重要遊戲規則,但當統一定價作為補助上限,就影響了整體薪資結構的僵化、停滯。這背後反映的是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低估,以及因此過低的社福預算。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劉淑瓊指出,社福業務委外的本質,是政府在購買服務,但是在台灣看到的情況是,買賣過程雙方沒有成本的概念。劉淑瓊說,早期的托兒所在地方政府是公辦公營,因為政府曾自己經營、辦理,所以改由委外時,所需成本能抓得很好。但除了托兒所,政府還有很多的服務,根本自己都沒做過就委出去了,所以know-how也不懂,成本也沒概念。當政府沒有負起精算成本與服務品質的責任,導致在編預算時就破壞社工薪資行情,制度也無法鼓勵留任資深專業的社工。
劉淑瓊表示,政府委外的態度就是想省錢,用六分錢做到十分的事情,剩下四分就讓民間團體自行籌措資源。可是政府從中得到好處後,很多問題卻都坐視不管。當政府預算不合理,機構反過頭犧牲社工的勞動條件,看似省下的政府人事費用,其實是重重壓在基層社工人員肩上的成本。社工高流動率的惡果,是由社工和這些需要社會福利的個案來承受,更可能經常出現「永遠用最嫩的社工在應付最複雜的社會問題」的現象。
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沈曜逸認為,要解決社工低薪的困境,可以用國家制度來制定、規範改善社工薪資結構,達到具有合理的加薪與升遷制度。政府可以制定社工基本工資的標準,機構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競爭力、聘雇更優秀的人才,就要高於這個制度。他也舉例,目前非營利幼兒園就是由政府依照工作人員的年資,去劃分薪資級距。反觀社工目前的薪資給付標準中,卻沒有將社工年資納入劃分考量,等於未承認社工工作的專業性。只有天花板沒有地板的規範,更是無法保障社工權益。
衛福部喊出「社會安全網未來3年增加3,000名社工」口號,表面上解決社工人力不足造成的過勞。但台北市社工師公會理事長李宏文憂心,一來若社區精神醫療等資源未到位,不可能單靠增加社工就解決所有問題,二來萬一3年後計畫中止,這個形同中央等級的計畫型人力方案,恐導致社工失業潮。
「政府委外法定業務,是否更該補足合理的人事成本?社福機構與NGO,也都不應閃躲雇主的責任。」長期關注社工勞權的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黃盈豪指出,個案需求不會隨方案終止就消失,社工服務是長遠的,有心長久運作的社福機構與NGO,應將社工當成自己的資產,募得款項不只做服務,還須提撥一部分支持人事與人力訓練,不能接了政府方案,就靠政府補足所有資源,也非今年沒申請到方案,就中斷與社工的勞雇關係。
劉淑瓊也認為,機構的經營理念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應該要認知到社工專業人員是機構最重要的資產,並學習確實精算社會服務成本,在提供服務規模和社工勞動條件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秘書長郭志南指出,即使機構付給社工的財源來自政府,但社工的勞動仍然是為機構帶來效益的,機構不應該迴避自己也該負起的雇主責任,完全推卸給政府。而政府本來就有責任積極確保社工勞動權益不受損害,對於機構的違法情事應確實稽查。
「政府要做好社會安全網,社工人員是一股重要力量,因此政府一定會努力改善社工人力配置與勞動條件,讓社工沒有後顧之憂,全力去幫助他人。」這是蔡英文總統在2017年3月出席社工表揚大會的發言。
長時間以來,台灣的社會安全福利網,都是靠第一線社工以不合理的勞動量、在極不對等的薪資環境苦撐。社工高流動率再持續下去,終究會有潰堤的一天。而社福崩解的成本,還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