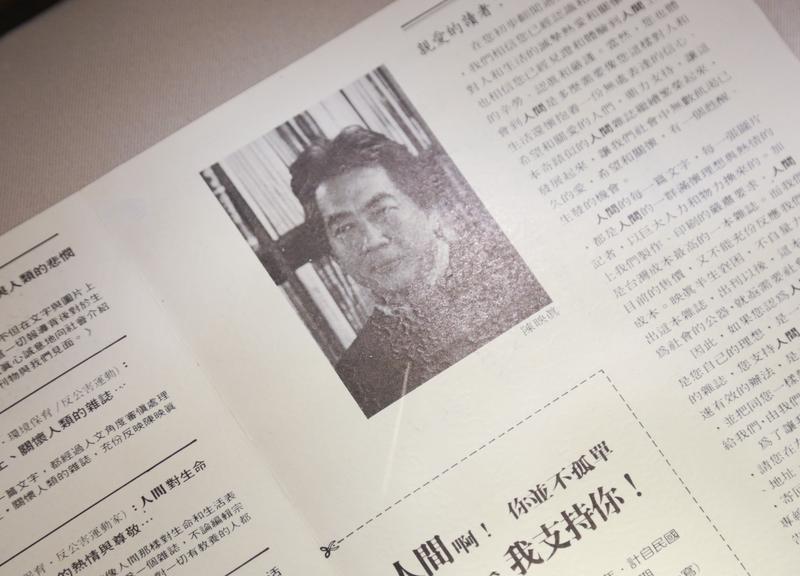「全部拍完之後,我有一次去拜訪七等生,他那天可能難得心情不錯,拉著我去散步。他要我去找其他受訪者誠實講,罵他也沒關係,就是要誠實。⋯⋯但當你真實面對一個人的人生,不管他是不是大師,都顯得有一點殘酷。」
紀錄片《削瘦的靈魂》,片名改自作家七等生作品〈削廋的靈魂〉。削瘦與削廋,一字之差。導演朱賢哲說,電影片名的改寫,來自他對七等生的第一印象──在2018年進行第一次正式拜訪時,七等生剛剛結束大腸癌開刀手術,身體虛弱,身形削瘦。
「這是七等生給我的image,是一個形象,」朱賢哲回憶,初見七等生,他的狀況並不太好,在加護病房受到身心束縛,對他影響甚大,「七等生是一個享受自由的人。」從身體的自由,到精神的自由,靈魂削「瘦」,看似只是對生難字詞常見的誤讀,反倒成為朱賢哲刻劃七等生形象的明確註解:一個身形嶙峋,縛於軀體中,受自由牽引的孤獨身影。
台灣現代主義作家作家七等生於2020年10月24日,因癌症逝世,享壽81歲。七等生的文學創作不受縛於傳統倫常,在世時鮮少接受採訪、公開談話,素來直以作品面對世界。在其過世前的最後兩年半,紀錄片導演朱賢哲帶著攝影器材,近身採訪七等生與其親友,從生平、從創作、從交友往來到家庭生活,完成紀錄片《削瘦的靈魂》,以七等生在人世間的最後身影,為其耽於沉思的靈魂做傳。
朱賢哲首部劇情長片《白蟻─慾望謎網》曾獲釜山影展影評人費比西獎肯定,也曾拍攝記錄SARS的《穿越和平》、關注流浪狗的《養生主》等紀錄片,影像風格凌厲生猛,聚焦社會邊緣的暗影。這次,他不受限於紀錄者的客觀視角,以黑白攝影、口白敘述,重新詮釋七等生作品,用影像回應文字、以作品理解作品,《削瘦的靈魂》如同一場兩位創作者跨越媒介的遙相對話。
「李龍第看見此時的人們爭先恐後地攀上架設的梯子爬到屋頂上,以無比自私和粗野的動作排擠和踐踏著別人。他依附在一根巨大的石柱喘息和流淚,他心裡感慨地想著:如此模樣求生的世人多麼可恥啊,我寧願站在這裡牢抱著這根巨柱與巨柱同亡。」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
《削瘦的靈魂》是「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作品。該系列以文學作家為題,陸續拍攝香港、台灣之作家故事,第一、第二系列共有合計13部長片問世。2016年,「他們在島嶼寫作」籌備第三系列,傳主包括台灣鄉土詩人吳晟、抒情詩人楊澤、文學作家朱西甯、劉慕沙、朱天文、朱天心等人。在七等生長子劉懷拙大力促成下,小說家七等生的紀錄片拍攝案也於此發生。
文化評論人詹偉雄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文學作家本身便是創作者,對於自己的社會形象,如何再現於觀眾面前,較一般人而言會有更多顧慮,這是紀錄片拍攝之難處。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中,又尤以七等生的處境最為複雜,「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氛圍,有很強的集體性。七等生的小說呈現出荒謬的處境、異樣的主張,存在一種對於集體性的反抗。」
七等生於1970年代震撼文壇,小說獨樹一格,彷若對社會做出哲學式詰問,「對於習慣在小說裡找到道德啟示的讀者來說,七等生的文字是讓人很震驚的,」在詹偉雄看來,《削瘦的靈魂》不只是單純重述七等生的文字,更巧妙的是找到1970年代的視覺印象,以近似張照堂風格的黑白攝影,加上舞台劇的表演與調度方式,去除雜質,找到影像的力量。
電影於2018年初開拍,2020年中旬完成後製、混音,製作歷時兩年半。導演朱賢哲加入此案之機緣,來自「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監製楊順清的邀請。從《白蟻─慾望謎網》的創作風格當中,楊順清看到兩位作者遙相呼應的可能性,便找上朱賢哲投入拍攝工作。
「為了要拍攝七等生、要能回應他說的話,我每天看他的小說,」朱賢哲回憶,在《削瘦的靈魂》之前,改編七等生文學的重要電影作品,已有「台灣新電影」導演陳坤厚執導、入圍第22屆金馬獎七項大獎的《結婚》(1985),與獲得第37屆金馬獎評審團特別獎的《沙河悲歌》(2000)等片。前人珠玉在前,卻多是寫實格局,閱讀七等生文學的過程中,朱賢哲則看見了實驗電影般的結構與影像的不同可能性。
在美國雪城大學攻讀電影製作碩士,朱賢哲對電影的理解,從實驗電影的嘗試開始。學成歸國後,他曾以風格前衛的《藝術家的電影》(1994)、《美國大廟》(1995)等短片叩關金穗獎,也與公視「紀錄觀點」合作《影像詩》(2003、2007)系列作品。對於現代詩別具偏好的他,細數鍾愛詩人如零雨、夏宇,或年輕一輩詩人陳繁齊等等,朱賢哲熱愛讀詩,不但在影像中嘗試詩化語法,回頭思考自身創作,也每每有不同啟發。「電影中的畫面,都是我根據七等生文學去做再詮釋,但我沒有包袱,這是我電影裡的創意,就像請一個新的指揮家來詮釋莫札特。我要在電影中重建七等生的文本。」

思考紀錄片拍攝,朱賢哲不滿足於採訪、生活片段跟拍,更另外以實拍片段結合電腦特效,將文學作品影像化。「七等生小說本身就有實驗性質,有電影結構的概念,內涵也兇猛,」要找到表現七等生文學的不同角度,從〈我愛黑眼珠〉、〈灰色鳥〉、〈精神病患〉等名作一一耙梳,朱賢哲說,七等生的小說在細節描寫上鉅細靡遺,對於主流敘事會聚焦的情節,卻常省略不談,敘事的順序與章法不照傳統進行,讓他看見實驗性的趣味。
用灘上沙堡反射內心黑暗、以蟻獸交疊表現集體雜交;在影像呈現上,朱賢哲力求讓觀眾感受七等生文學的魅力,並透過重現片段的編排來回應七等生作品。
電影尾段,朱賢哲重現七等生名作〈我愛黑眼珠〉場景,末日般的洪水來臨,男子李龍第在暴雨中面臨抉擇,捨棄了他的妻子,轉而去安慰一位偶見的妓女。朱賢哲表示,這是台灣文學史上極具爭議的重要一筆,有呈現的必要,但拍攝〈我愛黑眼珠〉仍是很大的考驗,純粹以動畫方式呈現,可能相較是安全做法,最後他選擇用實景拍攝,再結合電腦合成動畫(CGI)完成。「定剪交出去之後,我們又再額外請特效團隊來幫我們修補海浪。當然,原著的描寫,是比我們拍出來的更細膩百倍。他文字裡的驚滔駭浪,以我們拍紀錄片的規格,要來呈現是很難的。」

重現之外,紀錄片拍攝的另一個難題,是如何找到切入角度,展現出敘事者眼見、揭露的真實。
詹偉雄表示,「真實的概念需要釐清,“fact”是事實,真正發生過的事情;“reality”是對事實的理解;“truth”則是根基在前兩者的基礎,詮釋者建構出的生命經驗。紀錄片導演能夠提出“narrative truth”(敘述事實),不是說他能窮盡真理,而是他能做出對人性的揭露。」紀錄片要探究真實,需要完成自己的詮釋。
除了表演實拍、編排文本,《削瘦的靈魂》亦對七等生進行實際的貼身紀錄。在拍攝初期的前2、3個月,七等生不太願意受訪,不只對外人拍攝感到不自在,就算是日常家人相伴,也不總是愉快。「他不喜歡被干擾,」朱賢哲回憶起七等生的性格,並表示,七等生更喜歡與自己獨處,每天都用心在自己的世界,一點一點地探索內心的變化。「他不想受訪。他說,他想講的都在書裡說完了,」朱賢哲說。
要親近被攝者,朱賢哲變換策略,捨棄體積龐大的攝影機,改以單眼相機,甚至是更為輕便的手機進行拍攝。「像這台手機,平常不會買這麼好,為了拍攝,特別選了攝影功能較好的,」隨手舉起手機,朱賢哲笑說,器材轉換之後,與七等生談話的過程,較可以感受到對方自在,慢慢卸下心防,「用大台的攝影機,他就不太自在,會比較像是在講課,他會緊張。」
「剛開始拍攝的時候,我偶爾會打電話給他,有一次剛好被他女兒接到,一聊起來,才發現她是我20年前認識的一位朋友。」紀錄片拍攝能順利完成,朱賢哲也要感謝七等生的女兒劉小書支持。1996年,從美國學成返台第二年,朱賢哲手邊沒有人脈,沒有拍商業案件的機會,更遑論拍電影。一個機緣與關懷生命協會接觸,以數年時間跟拍流浪狗議題,最後彙整成作品《養生主》(2001),並獲得第3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當年,小書有一個網站,她請我把整個《養生主》拍攝的始末寫出來,刊載在網站上,成文一篇約兩萬字的〈流浪狗紀錄片日記〉。迴響滿大的,也是我拍攝紀錄片以來最完整的拍攝日記。」在過往合作機緣下,主要照顧七等生生活起居的劉小書,傾力支持朱賢哲拍攝七等生紀錄片。電影中,七等生與好友簡滄榕相聚的重要片段,朱賢哲不在現場,便由劉小書協助掌鏡,手機與錄音設備也都置放一份在她身邊。
劉小書的參與,也讓朱賢哲能夠切入、挖掘到七等生人生的不同面向。《削瘦的靈魂》少見地描寫傳主私人生活的陰暗面,透過家人在鏡頭前的自白,朱賢哲記錄下七等生在致力寫作時對妻子的有愧,還有感情生活的不忠。
「誠實說,有點忐忑不安,當你真實面對一個人的人生,不管他是不是大師,都顯得有一點殘酷,」對於是否該將七等生私密一面公諸於世、會有甚麼影響,朱賢哲一度沒有把握,尤其擔心七等生會在意外界對他的評價,「然而,他從開始時就表明,這部電影怎麼拍都好,與他沒有關係,這完全是屬於我的創作。」這樣的直率,讓朱賢哲有誠實回應七等生的動力。
「全部拍完之後,我有一次去拜訪七等生,他那天可能難得心情不錯,拉著我去散步。他要我去找其他受訪者誠實講,罵他也沒關係,就是要誠實。你知道嗎?我覺得這是七等生一生信奉的東西,這是他的信念。他很敢批評別人,也不覺得別人需要幫他掩飾什麼。」朱賢哲尋覓作家的靈魂,見到的是不願隱蔽的坦率。

七等生其人其行,圍繞對死亡與情慾的思考。
朱賢哲說,死亡與情慾,剛好是他自己最感興趣的東西,在七等生面前,他更不能逃避去表現這兩個主題。「我跟他相處的時候,很自然把重點放在這上面,這對我來說是再當然不過,你怎麼面對死亡?你怎麼面對情慾?是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如果不拍這個、不寫這個,才更奇怪吧。放著不去談,會錯失理解一個人思維的重要機會,」談到與七等生的對話與應對,朱賢哲也再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
在《養生主》,朱賢哲拍流浪狗問題,看到的不只是社會問題,也是生命面對死亡,更大的苦難與悲劇性。朱賢哲提老莊思想,提存在主義,「我在做這些問題的時候就在思考,說拍流浪狗的《養生主》也好,甚至SARS紀錄片《穿越和平》也好,我想超越人類的情感包袱,不管是存在主義哲學,或是從莊子的角度去看生死。其實都是關於我們要怎麼放下包袱,去用不同的思維看事情。」
在《削瘦的靈魂》中,七等生曾說,「我寫的是宇宙、寫的是地球、寫的是人類,而不是寫你們要的東西。」對應朱賢哲的創作期許,或許可以呼應。
「七等生是一個非常、非常純粹的創作者,這次拍攝的經驗也影響我很大,」朱賢哲說,《削瘦的靈魂》完成之後,他下定決心,往後生命要全心全意投入創作,拍攝也好、寫作也好,他要將生活中的外務卸下,驅動自己回到單純的生活中。
2020年6月,電影完成之後,朱賢哲最後一次拜訪七等生。彼時,七等生的身體狀況已經衰弱,但還是拉著他聊天,甚至喝酒。「就算到晚年,七等生的思維還是很清晰。紀錄片裡面,你們看到他的自信,那不是他一時興起的狂妄,而是他已經把這種自信,內化在性格裡面。」
受到七等生的純粹所打動,朱賢哲有感,在資訊氾濫的時代,或許我們更需要精工冶煉的思想,而七等生的小說正是如此,「這部紀錄片可能是我跟七等生的對話,也是我透過他的話,來跟世界對話。」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