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錄

當代,創傷已經成為一種人們不陌生、也不避諱談論心理狀態;PTSD彷彿成了創傷的代名詞。可是我們是如何使用這個詞?它是否能用來指涉所有的創傷主體?
傅柯說,臨床工作者將「過度老練的眼睛」投射在受苦主體之上,以致在未曾與主體遭逢以前,便決定了自己能夠看見之物。醫療病理的知識框架的確是觀看與理解創傷,進而接近受創者真實經驗的一種方式,但並非唯一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每一次面對受創者、面對受苦的時候,怎樣的「看」與「說」,最可能提供適切的理解途徑,並創造「療癒/遇」的條件?
受創者的傷如何可能被「看見」?我們如何得知她/他究竟如何感知、詮釋這些經驗?一般人對於「變好」的想像為何會致使受創者遭到更多傷害?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長期研究家內性侵、政治暴力創傷,她從她的臨床田野出發,一方面討論當代創傷臨床的病理化,另方面則以她與創傷主體長期工作經驗,討論創傷的被看、被說,以及另一種療癒的可能。
「Boom.磅」為春山、左岸、八旗、衛城與臉譜五家出版社共同成立的知識平台,這裡不會只談一本書,而是當代的重要問題與現象。第二季第五場講座主題為「PTSD之外,心理創傷如何(被)看見、(被)敘說?」,本篇為該場講座側記。
「他的內在還在戰場上。」
講座中,彭仁郁說了關於非洲童兵的故事。她在台灣念的是心理系,到法國做精神分析取向的創傷研究。她的法國督導研究的是非洲童兵創傷,「你可以想像非洲童兵進到精神分析室、躺在沙發上跟你做分析嗎?」
一個從3歲半就被教導怎樣拿著機關槍去射殺另外一個種族的孩子,從3歲半開始練習殺人。7歲上戰場,軍隊用毒品控制他們。12歲,他受傷少了一條腿,沒辦法打仗就被軍隊丟掉。「像這樣的一個孩子,你要怎麼跟他談話?怎麼跟他建立關係?你可能要開大半天的車才能找到他,你要把他拖回你的分析室嗎?但他如果不願意跟你走呢?你可以在現場跟他談話嗎?你有本事讓他覺得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可以開口對你說,他到底經歷了什麼嗎?」那才是真正專業的挑戰。
「Boom.磅!講座」第二季最後一場,講者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主題是她最熟悉的創傷,但是我們為她定了一個看似有點挑釁的講題:PTSD之外,心理創傷如何(被)看見、(被)敘說?在當代,「PTSD」彷彿成了創傷的代名詞,可是我們是如何使用「PTSD」這個詞?它是否能用來指涉所有的創傷主體?而我們更想談的其實是下一句,「心理創傷如何(被)看見、(被)敘說?」
回到法國和非洲。彭仁郁的督導告訴她,他和當地心理師一再開著吉普車回去找那些被遺棄的孩子,一直到不知道多少次之後,原本無動於衷的孩子突然哭了,「孩子突然叫出來,說,『我好痛。』」這些孩子不知道自己原來被當成殺人機器,到現在都不知道人存在是為了什麼。他們不會喊痛,因為他們喊痛從沒有人回應過,所以他喊不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痛。「基本上,如果你沒有辦法進到信任關係,你就沒有辦法讓這個人把他從裡面抽出來的東西,變成一個他自己可以聽得懂的語言說出來。」沒有進入關係,我們就不會看到受創者內在的狀況,就不會知道非洲童兵的內在其實還在戰場上。
「臨床田野就是在做這個。臨床田野用一切辦法進入受創者的生命,讓他知道你在。你不是他的爸爸、媽媽,不是他的誰,但你在。你會一直在。」
回應講題,彭仁郁一開場就點出,當我們用「PTSD」討論創傷時的兩個矛盾。第一個矛盾是,她的臨床田野遇過經歷不同創傷事件的人,如果他們去看身心科或精神科,大概99%都不會得到PTSD的診斷。第二個矛盾是,現在用這個詞,多半是人們日常在告訴身邊的人,自己經歷了一個很可怕的、衝擊性很大的事件。有嚴重症狀的創傷主體如果用這個詞指稱自己,反而是在問:「我是不是有病?」
於是,彭仁郁帶我們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 V)的診斷標準,一條一條解釋,為什麼她會說「99%的創傷主體得不到PTSD的診斷」。PTSD是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縮寫,「光是這個名稱『Post-traumatic』,創傷後,所以首先,你要讓醫生知道你『親身經歷危及生命、對身體完整性造成重大損害的創傷事件(6歲以下孩童目睹重要他人經歷重大創傷事件)』。」現場有第一線的臨床工作者、有曾經看過精神科或身心科的聽眾。進入診間,你有多少時間講自己發生過什麼事?「大部分的醫生不太有時間進入你的生命經驗,去知道你到底經歷過什麼。所以如果你沒有很主動說出,我是921震災的受災戶、我是太魯閣號列車出軌事故的受害者。如果你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在那10、15分鐘裡,說出你經歷了哪些能夠說服這個醫生,自己的生命曾經遭到威脅,你很難獲得PTSD的診斷。」
至於彭仁郁自己臨床田野遇到的個案就更難。「因為他們說不出來,就這麼簡單。他們沒有辦法說,我被我爸爸性侵10年、我是白恐二代。在那10分鐘、在完全不認識那個醫生的狀態下,他說不出這件事情。」第一個診斷標準就如此困難。接下來的幾個呢?重新經驗(re-experience,或是我們常講的記憶入侵[flashback])、迴避創傷關連人事地物、認知情緒(人格)負向改變、過度警覺。這些網路上都查得到解釋,但彭仁郁提醒,一開始的PTSD主要是著重一次性的重大創傷事件所造成的人格影響,但是像童年長時期家暴、性侵的受害者,不一定會出現這些症狀。
「比如說『重新經驗』,他沒有重新,他每天都還在暴力裡。他也不是『創傷後』,創傷對他來說仍是進行式。再來就是他不見得會有明顯的、外顯的情緒跟認知的改變,因為他可能一直以來都是那樣──看起來很冷靜、跟人有距離,甚至很獨立或是很樂觀向上。這是他在長期暴力下發展出的倖存策略,而每個人的倖存策略可能很不一樣。所以我們不會發現這個人有認知或情緒的改變。我們看不出他有創傷。」
這裡她提到了茱蒂斯・赫曼(Judith Herman)1992年出版的《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長期與性創傷倖存者工作的赫曼在這本書提出CPTSD(complex-PTSD)的概念,她想突破PTSD只著重在一次性重大創傷事件的診斷標準,「國際疾病分類(ICD)現在已經加進CPTSD,但是DSM V還沒有。CPTSD其實就是提醒我們,很多創傷對人格造成的影響你看不出來,因為你會以為他的人格特質就是這樣。」
彭仁郁強調,她並不是說PTSD的診斷描述無效,而是你要在某些條件下,才能看到這些描述,「才能看到原來這個人的內在是這樣的情景。而你要怎麼樣讓他把他的那個狀態讓我們看見,就是創傷療癒要做的。」
第二個要處理的矛盾是「病」。傅柯在《臨床的誕生》回顧我們到底是從什麼時間點,開始把人用解剖學的概念區分為不同的區塊。「我抓到書裡一個讓我在看待創傷的時候非常有幫助的區辨,就是當代的臨床論述開始出現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徹底改變——把病人的身體跟『病體』分開了。以前醫生看的是整個人,現在醫生看的是『病體』,生病的部位、致病的原因,或者是病的發展、病的症狀。我本來一直不理解,為什麼DSM的症狀描述幾乎像是一種症狀的分類系譜,讀了《臨床的誕生》之後我才理解,原來我們其實是用一個非常類似疾病存在實體的方式去看待精神疾病。」
回到創傷。創傷是精神疾病嗎?創傷主體「有病嗎」?這當然還包含制度和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如果創傷不是病,為什麼可以去看精神科跟身心科?為什麼可以拿到健保的藥?進一步延伸的問題是,「創傷可以被量化嗎?」主流的創傷研究全部是量化研究,「這又是資源分配的問題,它不得不被量化,我們才能說服政策的規畫者把一定的公共資源分配到這裡。所以我不能說它不是病。因為你一旦說創傷不是病,我們現在的精神醫療體系就沒有辦法介入,那創傷主體要去哪裡?哪裡可以承接、理解他的受苦?」
另一方面,如果創傷的被疾病化、被量化是基於公共資源介入的需求,那麼受創者的主體經驗在醫療框架中被放在什麼位置?「其實我問的是一個傅柯的問題,就是我們人類集體,到底對於人、對於受創經驗的想像是什麼?如果我們把所有的受創經驗都用大腦神經去理解,受創者最後還是只能吃藥解決,那他的關係呢?他因為創傷而破碎的關係、融不進這個社會,他怎麼辦?」彭仁郁再次強調,這並不是說當代臨床醫學無效,她只是想問,有這麼多選擇,為什麼我們選擇的是這一個?為什麼它會變成主流,甚至變成一個論述上的霸權,取消了其他可能的論說路徑的正當性?
「這就不是一個知識可以解決的問題。人際暴力受創,不管是性侵、慰安婦、白恐或二二八受難者的後代,他們面對的問題都是,我怎麼在另一個人的面前還能覺得自己是個人,有資格在這個世界上活下來。當我們用像是4個F(Freeze[僵]、Fight[戰]、Flee[逃]、Fawn[諂媚、討好])這種簡單的原理讓創傷很快地被講完,你會跟人的複雜經驗錯過。但是恰好,這就是創傷主體要測試你的東西。」

跳脫(挑戰?)主流創傷論述,我們逼近每一個創傷主體的異質性,進一步,我們要如何讓創傷主體發話?彭仁郁說,很難。
「你怎麼看我?」、「你是什麼顏色?」、「到底有什麼好過不去的?!」、「是不是我不夠努力?」、「我什麼時候會好起來?」、「我是不是很難搞?」彭仁郁摘錄了幾句不同個案在第一次見到她時、或是會談初期會對她說的話。「心理師會一直很想要聽到『那件事』,但通常我們這麼想的時候,你就什麼都聽不見。這是需要訓練的,我覺得個案願意跟我講這些話都表示有進展,這些話才說得出來。我常說,跟創傷主體工作要做好一個準備:你要知道你看不到他,你看不到他看到的『他』。」
簡報上第一句是「你怎麼看我?」彭仁郁說,他這麼問的時候,表示他沒有辦法好好看待他自己:
「他看待他自己的方式是扭曲的、是負向的、是破破爛爛的,是⋯⋯可能開腸剖肚的。但是他不知道你會不會看到那個他,他擔心他如果開口講『那件事』,你就會看到『那個他』。他不要你看到『那個他』、但他又要你看到『那個他』,不然你不知道他經歷了什麼。這就是困難的地方。我又要你看見、我又要你不要看見,因為你看見,他好像就會像一個標本,被釘在你的標本台上,然後他永生永世就只有那個樣子了。他不要。但是他的內在卻永生永世就是那個樣子。」
這就是受創者很難進入關係的原因,你感受得到他的拉扯。
「你是什麼顏色?」是一位白恐二代前輩問的。
「到底有什麼好過不去的?!」是個案在對自己無法靠意志力超克困局而生氣。
有的個案會問「是不是我不夠努力?」他想知道,努力是不是就會好起來。「我什麼時候會好起來?」意思是什麼時候才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我是不是很難搞?」因為他害怕自己不值得接受幫助。
助人工作困難的地方就在於它沒有標準答案。同一句話、在同一個人身上,不是所有時刻都會發揮相同的功效。同一句話,不一定在同一種類型的個案身上都有用。彭仁郁說她常常被問的問題都是,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做,才可以幫助受創的人?但助人不是一套可以被標準化的專業技術。「你不可能在關係之外知道要怎麼做。首先要進入關係。為什麼?因為不在關係裡面,受創者無法說話。」
但,進入關係,創傷經驗就能被「說」了嗎?「你既然經歷過那件事情,你怎麼會不知道你經歷過什麼,你就說出來嘛。」一般人常會誤以為,說出來很容易。只要有一個對的人、對的時刻,然後就可以說出來了。我們的概念是「提取」,但其實不是。
「創傷敘事需要一個助產士。創傷敘事從來不預先存在,是在關係裡面才能生成。」
「關係」是這場講座不停出現的關鍵字,也是彭仁郁一直提醒,敘說和聆聽的重點。受精神分析訓練的她在講座中談到,精神分析談建立關係,會做兩件事:護持(holding)跟涵容(containing)。
溫尼考特(D. W. Winnicott)說精神分析很愛用隱喻說話,這裡的護持是心理上的護持,是創造一種條件,讓受創者覺得自己在裡面可以像孩子一樣,在地上滾來滾去,可以在裡面哭嚎,但也可以把自己重組起來。當他有這樣的信心的時候,就表示你有做到護持了。「所以護持並不是說我主動、我會,不是你決定你可不可以護持他,是你們一起決定那個護持有沒有辦法發生。涵容也是如此。」同樣也是用隱喻的形容,「創傷無法言說的、感官經驗的碎片,就像水潑出去卻沒有地方可以裝,而比昂(W. R. Bion)所說的涵容,就是心理師的存在可以是一個承裝的容器,讓它逐漸成形。」只是這個形狀也不是心理師決定的,而是和受創者一起,是一個在互動過程中出現的形狀。
接下來兩張簡報的標題分別是「創傷主體經驗現象學」和「創傷心靈地景考古學」,彭仁郁同樣用隱喻說話,借用現象學和考古學的概念,描述她的臨床田野,以及她如何和個案一起工作、個案在她面前的樣貌,還有創傷敘事如何在關係中被敘說、被聆聽。
「臨床田野用一切辦法進入受創者的生命,讓他知道你在,你不是他的爸爸、媽媽,不是他的誰,但你在。你會一直在。你要怎樣讓你的『在』對受創者來說是一件可以被感知的事情?很困難,所以會有一大堆的測試,一大堆看起來很欠扁的測試方法,比如說他會一直來挑戰你、對你說謊,甚至會感覺像是在操弄你,然後我們就會說,『啊,他就是邊緣性人格啦。』」
她也談臨床工作者的挫折。「當臨床工作者不覺得個案有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他不覺得個案願意跟著他一起走,他會很挫折。他可能會用病理化的方法、用臨床的知識『框住』個案,這是讓他覺得自己還有價值的方法。」所以她不會非常責怪病理化個案的臨床工作者,但是她提醒這要小心,工作者要知道自己是怎麼用它。
彭仁郁也提到發洩,她並不覺得臨床工作者不可以罵個案,只是發洩完情緒要想,到底他哪邊戳到我,為什麼我會無法擺放自己?「精神分析的訓練就是,我不是只是在理解『個案』怎麼了,我也要回過來知道『我』怎麼了,為什麼我本來這麼討厭用病理化的字,現在卻會用一些詞彙要把個案『定』住,讓我自己安心。這是精神分析訓練裡面很重要的部分。」
「投射」,受害者會把臨床工作者放在加害者的位置;「傳移(移情)」,個案也可能會把工作者當成自己的父母、戀人。彭仁郁同時也談到與創傷關係緊密的「解離」。包括她自己,很多心理師都會在跟個案工作的過程中遇到個案解離的現象,很多人不知道怎麼處理,甚至會緊張或懷疑是不是自己沒有做好,讓個案變嚴重了。「其實以我自己的觀察和經驗,我發現解離本來就存在,只是因為彼此的信任關係推進到一個地步,它才出現。他覺得夠安全的時候,解離狀態才會現身。而這是我自己覺得滿重要的事情。」
另一個重點是知識的主體位置的翻轉。
「以前我們會認為我們才是專業,DSM、精神病理學,好像知識在我們這裡,所以是我們告訴你,你是DID,你是PTSD,你是這個或那個。可是現在知識翻轉過來了,因為這座龐貝城不是你的龐貝城、是他的龐貝城,你怎麼會知道他的龐貝城是什麼樣子?所以你要跟著他一起回去。」創傷主體不知道他知道,或是他不可以知道他知道。而我們知道怎樣進到另一個人的龐貝城,陪著他安全進去又出來的方式。所以,要怎樣陪著他回去?怎樣去經歷那個很細微地看見他自己一生都在避開的景象,然後安全地回到現在。過去過不去,所以它才會一直在現在影響你。回來的意思也是,「怎麼樣把此時此刻的這個時空,跟那個解離的、但對他來講卻是此時此刻的時空拉開,把他的時間性拉開,這個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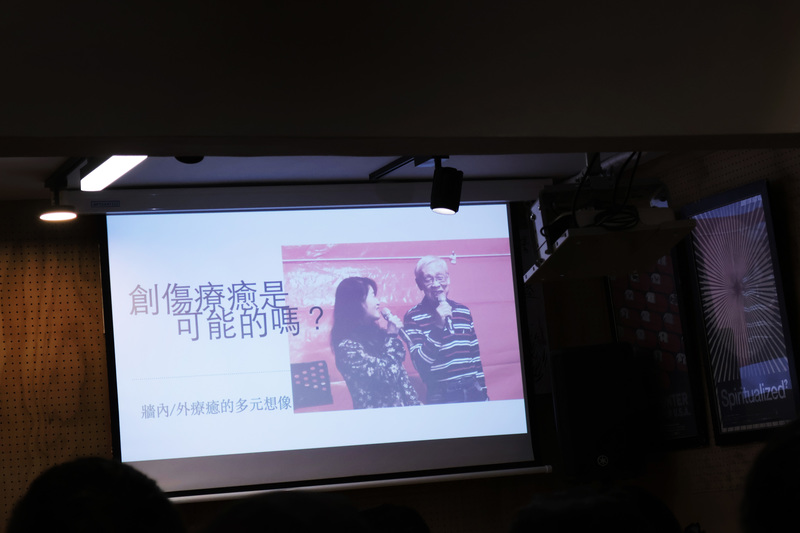
最後談療癒,彭仁郁最後一張簡報放了她和陳欽生(生哥)在人權辦桌唱歌的合照;這一張的小標是:創傷療癒是可能的嗎?
不一定要做精神分析,甚至不一定要做心理治療。彭仁郁想說的是,如果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時空,讓受創的人在那個時空裡可以長成他想要長成的樣子,療癒就會發生了。他會有另外的方法,重新認識他的經歷,重新認識他自己。
陳欽生的經歷,或許很多人都聽過,他是197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警備總部說他是馬共,關了12年,本來判了死刑,在國際人權組織救援下才活了下來。「他那時覺得最丟臉的就是,他回到台灣之後3年沒有身分證,他很長一段時間是街友,去餐廳後面的餿水桶找東西吃。那是他覺得最丟臉,甚至比他被關押、被酷刑吐出血塊又被逼著吞回去,都還要更丟臉的事。所以他一直都不願意講。」直到有一天,彭仁郁跟他還有年輕志工們在一起聊天,他說出了這件事。
「他說出來又要馬上把它關回去,創傷打開之後又要趕快關回去。他說沒事沒事,我不應該講這個。我當時在現場,我說,什麼,你不是說要謝謝那個每天幫你準備兩個便當的自助餐老闆嗎?」雖說不想講,生哥後面還是忍不住吹噓,說他在綠島學會做2、300個人的飯,「他說他煮2、300人的飯不會燒焦唷,就把自己講的很厲害。我們就問他,你要不要來做辦桌?」
所以,生哥一開始不敢說出來的、他覺得最羞愧的事情,陳文成基金會的志工們把它翻轉成一個公共事件。現在,每一年的年底,他們都會在立法院旁邊,青島東路跟鎮江街,他們會在那邊辦桌,「那是他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時空,我們會跟無家者、白恐受難者的後代,我們會一起在青島東路、以前軍法處的旁邊,在那裡一起吃飯。我覺得對生哥來講這是最重要的療癒。這比你把他抓去做心理治療更好,因為對他來說,他需要行動。怎麼樣讓療癒的想法變得更多元,這個是我們正在努力的事情。」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