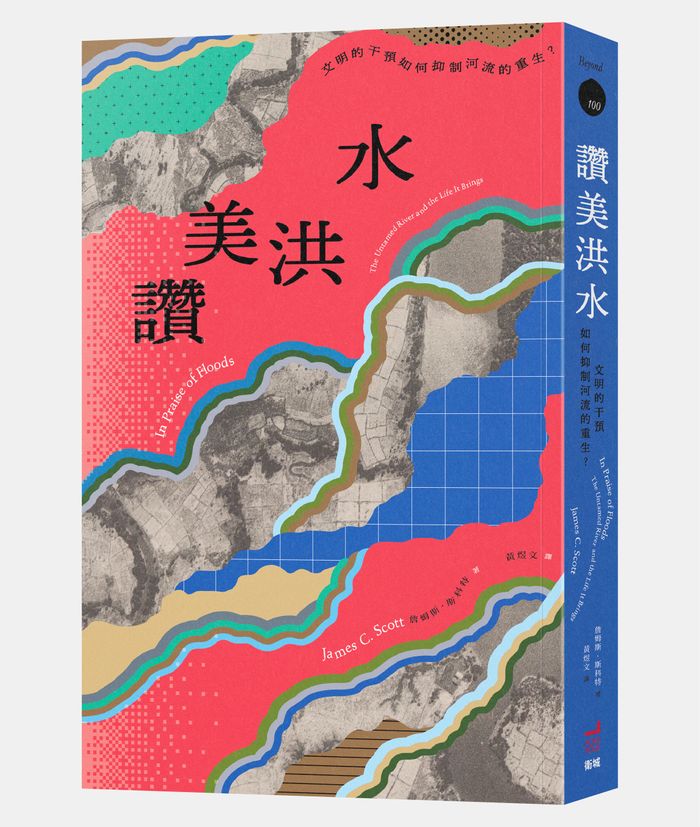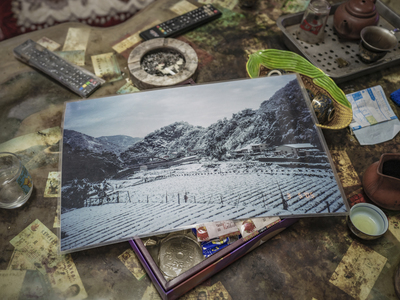書籍導讀

對關心人文社會科學的讀者來說,斯科特(James Scott, 1936-2024)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這位政治學者於耶魯大學任教45年,著作等身。他的重要作品,如《支配與抵抗的藝術》、《國家的視角》、《不受統治的藝術》、《反穀》均有台灣版本。《讚美洪水:文明的干預如何抑制河流的重生?》是他的最後一本書,也是他的遺作,英文版於2025年2月出版。
為何讚美洪水?在一篇發表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書評中,尼克爾.薩瓦爾(Nikil Saval)寫道,《讚美洪水》一書出版的2025年前後,正是洪水於世界各地肆虐的一年。確實,參考非政府組織「全球洪水監控」(Global Water Monitor)於2025年出版的報告,2024年一整年,洪災至少造成8,700人死亡,4,000萬人流離失所,以及超過5,5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就薩瓦爾而言,斯科特選在此刻「讚美洪水」,就像是告訴家園付之一炬的加州人「野火沒那麼糟」,有種「站著講話不腰疼」的意味。
薩瓦爾的用意不在於批評斯科特。他想要表達的是,這位活了將近90歲的政治學者,終其一生,都在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且試著讓那些受壓迫者發聲。《讚美洪水》延續了如此的學術關懷。文明人看待洪水,就像看待所謂「農民暴動」一樣,彷彿就是不受教也不想受教的東西在破壞秩序。在花費大半輩子為「暴動」的農民與逃避國家統治的「蠻族」發聲後,這回斯科特想攬在身上的任務是,讓河流、江豚,河魚、鳥類、哺乳類、軟體動物的聲音可以被聽見。這些生靈(對斯科特而言,河流本身就是活的,以「生靈」稱之,至為恰當)被規劃、被治理、被限制、被囚禁、被教化以及被馴化,他們掙扎求生,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澎湃洶湧的洪水,就如豎旗造反的農民,呈現一種國家、企業、主流科學身為「文明人」的你我難以理解的道德經濟。
薩瓦爾的見解多少有些後見之明。就斯科特而言,他為何要寫一本關於洪水的書?時間回到2021年。當學生與同事慶賀年過八旬的斯科特終於想要退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時,這位政治學者還不打算就此停筆。他有個年少時的夢要達成:為緬甸寫一本書。
1960年代,當斯科特還是個大學生時,他夢想的田野是緬甸。在扶輪社的支持下,他就讀緬甸的仰光大學與曼德勒大學,以緬甸的政治經濟為題,撰寫學士論文。在課餘時候,他騎著一台老機車,與友人四處遊蕩。然而,1962年緬甸政變後,斯科特再也無法長留。他最終去了馬來西亞,以稻作的農村為研究對象。
但斯科特仍未忘情緬甸。2010年至2020年,翁山蘇姬上台,緬甸相對開放,斯科特於是重訪緬甸。這回他乘船遊歷伊洛瓦底江流域。他不時被跟蹤與盤問,當有警察詢問他到緬甸做什麼,他順口回答他在研究伊洛瓦底江。久而久之,斯科特也就「假戲真做」,心想「為何不就為伊洛瓦底江寫本書?」
於美東德拉瓦河河畔成長的斯科特,對於河流並不陌生。然而,伊洛瓦底江打開了他的視野,特別是以整體的視角關照「依」與「因」洪水而生的眾多生靈。在《讚美洪水》中,他詩意地寫道,這些包括在人類之內的生靈,竟然是跟著河流擺動的節拍,形成一個高度協調也能自我協調的整體。斯科特不認為這是什麼至高無上的造物者所設計,若你會為此整體的精巧感到驚嘆,你該好好認識與讚美的,不是什麼造物者,更不是自以為能夠馴化河流的技術官僚或工程師,你應該要讚美河水,特別是那些被人們叫做「洪水」的部分。就斯科特看來,河流是活的,而洪水就是它的脈搏。文明人憎恨洪水,就是因為文明人不認為一條河有資格活著,所以當河流呈現某種生機勃勃的樣態,文明人就急著要把他弄死,封存在鋼筋水泥中,然後稱這是在「治水」。
《讚美洪水》呈現了斯科特一貫的博學風格。結合了生態學、水文學、人類學、政治學、民間傳說、神話等不同的領域,斯科特「以河為度」,丈量地球與智人的地理與歷史。他告訴我們,「在地球長達4、50億年的地質時間裡,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只是個嬰兒」;他也說,與個別人類的生命相比,河流幾乎是「長生不老」,然而「與人類作為物種的歷史相比,河流卻遠比我們年輕許多」。一旦我們學著「以河為度」,斯科特表示:「河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很多事:對人類中心論與人類文明感興趣的人,河流是醒目的例證,顯示人類試圖控制與馴化自然過程將造成什麼結果。」

翻開《讚美洪水》,讀者除了可以欣賞斯科特筆下的大江大河,同時也可跟著這位耶魯政治學者,重訪他半世紀以來的學術軌跡。人的生涯如同一條河,從一段涓涓細流開始,人生之河匯聚無數條支流,往海洋奔流而去,有時有著奇妙的拐彎,有時潛入地下,有時溢出河道,沖刷出一面出人意表的風景。在這過程中,人的思想宛如河流沿線帶走的砂石,愈往下游,就一步步沉積──以小說家吳明益的術語,人有時活成了「沖積扇」,久而久之就成了「沉積層」。
《讚美洪水》宛如斯科特生涯的「沉積層」。不論你熟不熟悉斯科特先前的著作,這本長度只有300餘頁的小書,包含了這位政治學者半世紀以來的思想結晶。斯科特告訴我們,在智人演化的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是以採集與狩獵為生,而智人與其他的生物相同,也會跟著「洪水脈動」,調整生活與生命的頻率。然而,當國家開始在河流的沖積平原上出現後,智人與河流的關係有了變化。斯科特寫道:「早期國家必須有集中的定居農業人口與栽種已經馴化的穀物作物才能維持」、「早期國家是一種侵入性的人為秩序。定耕農業、灌溉水田以及讓地面上的穀物同時成熟,這一切全需要將地貌簡化」。在國家的統治下,人們開始栽植愈來愈多的穀物,因為得繳稅,也因此得砍伐愈來愈多的森林。森林的消失影響了河流,生活在沖積平原的人們,開始受到「洪水」之苦。為了能從人民身上榨出更多的稅收,還有避免愈來愈多的人逃入山中,化身「蠻族」,國家開始規劃設計大規模的水利措施,以堤防、水壩試著馴化河流。但卻適得其反:河流從上游攜帶著沙土,逐步堆積在河底,無法溢出,讓河床愈來愈高。以為因應,國家興建愈來愈高的堤防,結果讓河床甚至比堤外的沖積平原還要高。這就難怪,當極端降雨一來,瞬間暴漲的河水無處可去,便會沖垮堤防,造成龐大的人命與財產損失。
斯科特引用醫學上的「醫源效應」來描述此現象。「醫源效應」指涉人們有時在就醫時感染具有高度抗藥性的病菌。斯科特認為,「我們今日面對的河流災難,絕大多數都是過去為了謀求智人與民族國家的利益,試圖規訓與馴化河流的結果。我們基於自身目的努力改造河流,特別是簡化河流與整個流域,這正是今日河流的主要病因。」
除了前述主流外,《讚美洪水》還有兩道支流:斯科特的緬甸合作者茂茂烏(Maung Maung Oo)與奈因頓林(Naing Tun Lin)對伊洛瓦底河流域的田野調查。如前所述,2020年後,因為緬甸政局的動盪,斯科特再也無法前往緬甸做田野。所幸,他有茂茂烏與奈因頓兩位在地夥伴,為斯科特提供不可或缺的在地視野。
如此跨國合作的成果便是關於伊洛瓦底江之河靈(river spirits,nats〔納〕)的田野調查。斯科特寫道:「對絕大多數生活在伊洛瓦底江的人類公民來說,這條河流的地貌,無論水域還是陸地,也『居住著』各式各樣的神靈。這些神靈在當地歷史中非常重要,祂們力量超凡,既和善也懷有惡意。這些神靈有時被崇拜,有時被安撫,有時被迴避,有時被召喚。」斯科特也說:「納原本是凡人,但祂們在世時的遭遇與曾經生活過的地點,使祂們成為備受尊崇的神靈」;誠然,緬甸主要的信仰為佛教;「發生自然與人為災害時,上座部佛教雖然能提供心靈的慰藉,但無法解決眼前的危機。在這個時候,地方社群就會乞靈『納』,向祂們尋求幫助。」
另一關鍵成果是,不同於先前斯科特的著作,在《讚美洪水》中,斯科特構思了一個「萬物議會」的場景,由伊洛瓦底江的生靈組成,表達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憂心。這場議會的「主席」是伊洛瓦底江的江豚(Orcaella brevirostris),屬於瀕危物種;其他與會者還包括雪鯉、雲鰣、白薑黃、黑腹蛇鵜等物種。會議結論之一是:「我們要從殖民者手中奪回河流!我們想要洪水、淤泥,濕地、樹沼、紅樹林──我們要建立一個由所有物種組成的河流民主制度,這是我們生存的核心條件。」
不管在歐美還是在台灣,河流書寫已成為環境人文一個重要的領域。《讚美洪水》是在這些基礎上的最新成果。這些河流書寫都有個基本立場:河流應被視為一個整體,不是地圖上的一條線,也不是在河道中奔騰的水,更不是國家或技術官僚所規劃打造的水利設施。河流史就是以河流為主體的歷史,且應包含所有依河與因河而生的生命與無生命。此立場也與「河流是活著的,具有某種人格權」的見解息息相關。
以「地景與人心」三部曲聞名於世的環境人文學者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於2025年出版一本新書,書名就是《河流是活著的嗎》(Is a River Alive?,暫譯)。麥克法倫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走訪厄瓜多爾、印度與加拿大的3條河川,與當地的生態學者、原住民族、環境運動者密切互動,探究「自然權利」運動的起源與擴散。「自然權利」為一種嶄新的法律思潮,認為河流有其權利,是一種法人般的存在。麥克法倫告訴讀者,此見解聽來驚世駭俗,但一點都不難理解。有一次,他的孩子問他:「爸,你的新書的主題是什麼?」麥可法倫回道:「爸爸想要探討河流是不是活著的?」小孩則說:「喔,顯然這不會是本太大本的書。」小孩雙手一攤,一副「啊不然呢」的意味。
台灣的河流書寫也正在蓬勃發展。在我書寫這篇導讀的當下,至少就有3本熱騰騰的新書:顧雅文、李宗信與簡佑丞的《島都之河》、蔡嘉陽的《流淌臺灣之心:濁水溪空拍誌》,以及許震唐的《追一條溪:濁水溪河畔記事》;先前則有叫好又叫座的《沒口之河》,作者是黃瀚嶢,闡述了知本溪與知本濕地的環境史,以及卡大地布卑南族人的環境抗爭。
對照斯科特筆下的河川,特別是緬甸的伊洛瓦底江,讀者應會感受到,台灣的河川是如此有特色,但又與世界其他河川一般,捲入某種「現代性」的枷鎖中。與台灣河流相同,伊洛瓦底江為熱帶的河川,有機質豐富,可支撐起多樣多元的生命;伊洛瓦底江也深受季風影響,雨季時不時氾濫,且會不時改道,創造出大面積的沖積平原。不過,依據斯科特,伊洛瓦底江的坡度非常平緩,「在前往大海的路上,平均每公里才下降8公分」,這當然與台灣河川動輒下降上千公尺的情況相當不同。按照斯科特的說法,如果說每條河流都有其「性格」,台灣的河川可說相當「奔放」,且執拗地拒絕國家或技術官僚的「管訓」。究竟這樣的河流可以度量出什麼樣的台灣史?我們還在學習。我們不見得要「讚美洪水」,但我們總是可以如年邁的斯科特一樣,在生命逐漸奔向某個時點時,想起年輕時曾經行過的一條河,接著起心動念,想要為這條河,還有與這條河共存的眾多生靈,做些什麼。
以麥克法倫與吳明益的語言:人畢竟也是個「水體」,行走時就成了河,坐下來就成了湖;活著如同沖積扇,活著活著成了沉積層。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