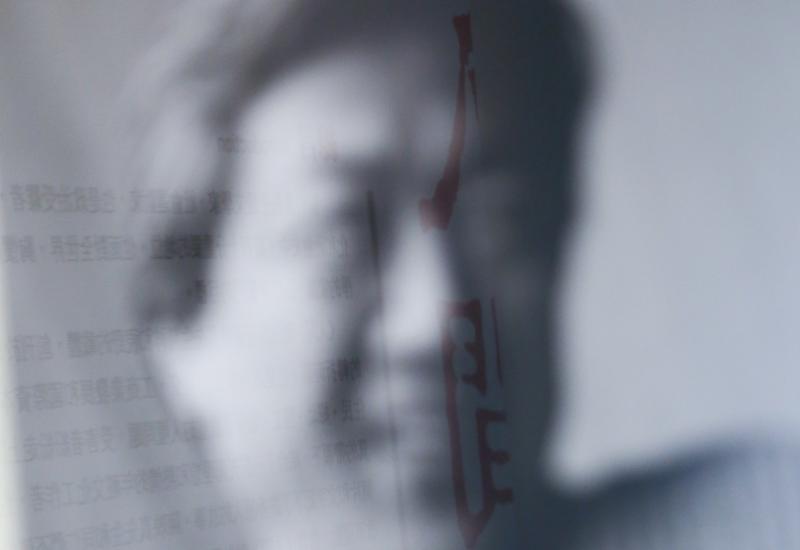評論

2019年初,當我陪著一位外籍記者C君到新莊採訪歐里桑時,我突然發現:我居然快要聽不懂歐里桑說的話了!不過,其實我也知道,這幾年重聽趨於嚴重的歐里桑,可能也早就聽不清楚我們的聲音,我們之間的溝通,可能早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就開始以一種「默契」的方式來進行。
只是我不願意承認而已。
過去幾年有幾次我都在歐里桑演講時扮演即時字幕員的角色,這當然與我們2009年開始的訪談有關。在重複聽他説過一次又一次,那些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第三國際、馬克思、商品、本地人、唐山人、理念、立場、戰略、戰術、紀律、從現實出發、看全面、看發展的概念與思想以後,有時候我幾乎可以在歐里桑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以前,就猜得到他下一句的內容。
並且在猜對以後,一邊敲著鍵盤、一邊暗自竊喜(只是台下的你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當我發現我似乎不再聽得「懂」歐里桑的聲音,除了震驚,更與第一次來拜訪的C君一樣迷惘。然後,則是感覺到有一點擔心,擔心歐里桑是不是就這麼逐漸失去溝通能力,逐漸從聆聽到言說都無能為力、成為自己被圍困在自己世界中的:
孤孤獨獨的一個人。
103歲的史明歐里桑,早已沒有親人的他,故舊也多半早先一步過世,這些年來陪在他身邊的就是敏紅姊(註:史明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黃敏紅)、忠哥(註:陪伴史明長達20多年的李政忠)與後來不得不雇用的兩位外籍看護。事實上,你也往往得真的去一趟新莊,才有機會在沙發、在餐桌、在床榻旁邊,看見史明歐里桑比較少在外面展現出來的那一面,那些不管閒散、坦率、任性或者發脾氣的那一面。
從頭說來的話,我們確實是幸運的一群人。2006年我們在台大門口認識歐里桑,就因為他這一句「台灣人講話siūnn濟,做siūnn少lah,尤其是知識分子,干焦講話無法度改變現實, 著行動 lah,著毋著!」(北京話翻譯:台灣人話說太多,做太少,尤其是知識分子,只有說話沒辦法改變現實,要行動,對不對!)讓當時在台大讀書的我們,決定讓台大濁水溪社重新開始運作。
然後,又在2009年,歐里桑91歲時,因為到日本處理新珍味裝修的關係,積勞成疾、腎功能惡化,在日本昏迷不醒5天,我們因為一種好奇與莫名的責任感,決定趁他終於能夠返台治療的時候,決心挑起了「口述」、「紀錄」的重擔,終至完成了《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史明口述史》、《左翼民族》等書,再與我們協助完成校對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起組構成為我們口中的、非正式的「史明經典重建計畫」。
我們和他的口述總共記錄了120小時,打了近60萬字的逐字稿,後來則整理成15萬字左右的《史明口述史》,成為歐里桑留給我們最珍貴的一份禮物。這份紀錄從他的望族背景、童年與家庭、留學早稻田大學時的左翼萌芽、曾擔任中共地下情報員/赴中抗日、戰後潛回台灣、見國民黨腐敗而預謀行刺蔣介石失敗後赴日,再到後來他創辦獨立台灣會,長期於日本東京經營傳奇的「新珍味」餐廳,作為其籌措運動經費與進行組織教育的基地的過程。而1993年歐里桑返回台灣,在解除政治犯的身份後,持續從事台獨理念的宣傳運動迄今。
相較常人慣稱的「史明」,我們更喜歡用「歐里桑」這個親暱的稱呼,因為我們的年紀與他相差遙遠,中間的輩分難以計算。我們在訪問的時候,感覺歐里桑已不像別人描述的那樣:個性很硬、很難配合。我猜可能是因為他大病初癒的關係,所以對自己的生命紀錄也開始有一定的焦慮感。不管怎麼說,90多歲的他除了有些怕冷以外,每次訪問都是4個小時以上訪好訪滿,結束以後還一定會留我們下來吃飯,不管豐盛如涮羊肉,還是簡單如便當、肉圓。
歐里桑不只說他的生命,更直直接接地讓我們進入他的生活。我們事實上也是在一邊訪問的過程中,一邊開始學習,也才更加地相信他一生的努力必須被看見。歐里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卻也可能是真正信仰自由的人。他從未放棄思考,也未曾停止行動的足跡,這樣的進步思維,不是教條主義所能夠予以簡化詮釋。歐里桑一生奮鬥的不外是希望讓台灣人可以明瞭自己的身世,為了讓我們知道:即使作為弱小民族的我們,還是能夠有順服以外的選擇。
於是,當我們後來出版了那本薄薄的、只有100出頭頁的《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時,歐里桑也用他的信念與意志,告訴我們什麼是一位革命者應該要有的態度與容顏。
我們一開始在台北辦了4場座談,後來還去了石牌的陽明大學、新竹的清華大學、台中的中國醫藥大學、台南的Masa咖啡與台南神學院、花蓮的東華大學等,歐里桑他從不嫌遠,也從來不問現場會有幾個人出席。他永遠都用盡全力,讓台下的年輕朋友們可以知道:
原來我們也可以為了自己作為一位台灣人而驕傲,而光榮。
有時候我是這麼想的:那幾次校園巡迴與後來的新書座談,會不會讓歐里桑想起自己,想起他1980年代就是這樣穿梭在美利堅的各所大學當中,對著台下那些飄零海外的蕃薯子們,說著他們不知道的、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身世呢?
這幾年,可能會有人誤會,以為史明歐里桑從1993年回到台灣以後,就一直是廣為人知的革命者,台灣獨立運動的「教父」。然而我們不會忘記,2005年3月,當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決心到台大門口靜坐12天的歐里桑,其實是相當寂寞的,因為那時候根本還沒有什麼年輕人記得他、關注他。然而也正因歐里桑有那樣的意志,才讓我們有機會與他連結,開啟後來這一切更多基於偶然的可能。
事實上,這幾年我們可以看見,歐里桑是一位不抱守傳統價值與生活方式、真正與時俱進的進步主義者。他一直以來力挺同婚,對於各族群、國家也一視同仁。那麼多年過去,歐里桑就是用一次又一次的講演,一趟又一趟的戰車繞行,證明意識民族存在的先知,總有一天可以喚醒沈睡的人民,台灣人也一定可以和世界平坐站(peN che-khia)。
於是,即使後來獲頒總統府資政,或者是重新被新世代的台灣青年認識與接受,對我來說,我所見證的歐里桑:其實就是一個朝下緩緩挫敗殞落的過程,不管是身體,或者是經濟方面。
有點像忠哥在《革命進行式》中接受訪問時說的一樣:
「其實他(史明)做很多事情都失敗。」
我們開始訪問的那一年,其實就是歐里桑開始正式對外募款的時候。日本新珍味近20年來的收益有限,2009年重新整修又所費不貲。我想1993年回到台灣時都已經75歲的史明歐里桑,可能也沒料到自己居然還能夠耗盡帶回台灣的數千萬資產,口袋空空、孓然一身,還仍然得為了獨立建國的理想而奮鬥吧!
同樣的,我也是就這麼看著歐里桑從還能在戰車上擊鼓、喊話、發旗子文宣,到這次住院時還硬撐著在病床邊寫稿;從可以高速公路追逐阻擋赴北京和中國共產黨積極談判和簽定共識的國民黨高層,到後來必須將麥克風掛在胸前,終至口齒含糊。
(最後才與C君一起發現:其實我快要聽不懂他說的話了。)
身體的退化,時間的殘忍,歐里桑最後會用一個什麼樣的面貌存在?其實是我們從最一開始、2009年訪問以前就經常質問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的不是一座銅像,更不是一座神主牌。然而近半年來當我有一次麻煩歐里桑簽書時,看著持續發顫著的筆尖。耳邊傳來敏紅姊的聲音。
「伊現在只能簽史明,簽不出施朝暉了。」
就像吳叡人(註:中研院台灣史副研究員)曾經說過:「運動需要英雄,但不需要英雄主義。」然而英雄總是得由人來扮演,而人會老會累,即使他堅持超過一個世紀了,終至有口難言,終究壯志未酬。
這就是這位奮鬥百年,未曾放棄與懈怠的勇者,生命最後階段的一些片段。
我們抵擋不住的,終究還是時間。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