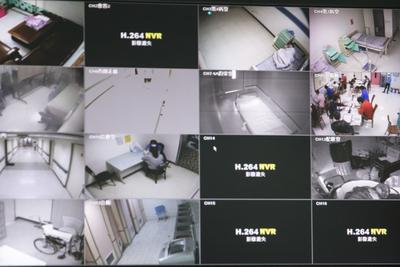評論

那年9歲的黎光(化名),在河灘邊失去了童年。20多年後,《報導者》的追蹤報導重新喚醒了那場被遺忘的悲劇,不只是因為被害者的名字,更因為加害者林國政,成為台灣性侵害刑事司法體系的鏡像。
(※關於林國政案:〈【獨家追蹤】回到9歲那年的河灘── 一位童年性侵倖存者,29年後獨立蒐證追尋真相〉)
林國政涉有多項前科,從妨害自由、竊盜,到多起性侵案。2002年第二次因性侵案入監後,曾接受心理輔導與行為治療;2011年出獄僅40天,再度犯下震驚社會的「葉小妹姦殺案」。監察院在2011年的調查中嚴正指出:矯正系統評估失靈、資料轉銜斷裂、社區追蹤不即時,讓一名高風險加害者重返社會而無防護。
然而,更值得追問的是:假若這一切程序都「完整執行」,結果會不同嗎?或許,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對某些性侵犯罪者而言,治療並非萬靈丹,「教化可能不可得」。
大眾常將性侵害理解為「性慾失控」,但臨床與司法精神醫學研究早已指出,性侵犯並非單一族群,而是多樣化的病理譜系。
一般,我們可以從動機與樣態簡單區分為3類:
- 機會型(opportunistic):受情境刺激或酒精影響,一時衝動犯案,常缺乏計畫性
- 憤怒報復型(anger–retaliatory):以性為手段,宣洩挫折或憎恨,暴力程度高
- 性偏好或施虐型(paraphilic/sadistic):例如從他人痛苦、昏厥或死亡過程中獲得性興奮,具有高度固定性與再犯風險
從林國政的犯罪軌跡,鎖定低齡兒童、先行勒昏、再行侵犯、最後滅口。若其並非受情境刺激,而是以「支配與毀滅」為慾望核心,而非「性」,那麼,對犯罪者而言,受害者的恐懼與失控才是刺激來源,見到受害者痛苦、掙扎反而不能同理、停手。
以台灣目前性侵害防治制度預測再犯機率的「靜態風險量表(Static-99)」為例,若以林國政的「客觀紀錄」:犯罪年齡、前科數、被害者性別、是否陌生人、是否同時有暴力行為而言,已多次被治療者認為具有「再犯高風險」。
「靜態風險量表(Static-99)」是1999年由加拿大學者R. Karl Hanson及David Thornton發展出的性侵害再犯評估量表,主要依據加拿大及英國監獄之性侵犯樣本1,086人,分別追蹤5 年、10年及15年再被起訴之再犯率,結果分別為18%、22%、26%,並以之為該量表之再犯率基線。
發表以來,受歐美各國犯罪矯正部門廣為運用,台灣也在同年由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將其引介,在此影響之下,從2003年2月開始編製本土「性罪犯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TSOSRAS)」,至2005年定版,迄今廣受國內矯正、社政、衛政及警政運用。
Static-99共有10項「危險成分」,依據各項評分標準加總,得分愈高再犯風險愈高。
- 以前的性侵害紀錄
- 之前任何判決確定的犯罪次數
- 曾犯「非身體接觸」之性侵害而定罪
- 本次性犯罪中是否有「非性之暴力行為」
- 之前是否有任何非性的暴力行為
- 是否曾侵犯「非近親」受害者
- 曾侵害「陌生」受害者
- 曾侵害男生受害者
- 年輕
- 單身
該量表問世以來已歷經數次翻修,台灣仍繼續使用最早期版本,造成與實務現況有可能脫鉤的問題。現任基隆地檢署主任觀護人林順昌曾於2021年撰文〈性罪犯再犯危險評估與Static-99之本土化轉置〉指出:
「茲有疑義者,乃Static-99問世20年,期間歷經數次翻修,國內各領域的使用者並未跟進調整,有關量表的使用及後續監督密度形成脫鉤現象。事實上,Hanson及Thornton在2002年就另提Static-2002版,後來發展2002R《編碼手冊》。2009年再針對Static-99提出修正,並使用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及德克薩斯州對於『性暴力掠奪者』(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SVP)的檢定,進而為『民事監禁』(Civil Commitment)提供依據。2012年又提出Static-99R《編碼手冊》,此時已建議不再使用2003年《編碼手冊》(編按:應指2002R《編碼手冊》)中的累犯準則,同時因為發現過度高估再犯風險的情形,提示2009年版的Static-99不適合評估60歲以上的犯罪者。嗣於2013年,針對Static-99R提出修正;2016年又針對Static-99提出修正。此外,研究團隊也在2012、2015、2016及2017年陸續針對Static-99R與Static-2002R提出比較研究。至於最新版本,在最近一次的修正是2019年2月版。質言之,Static-99雖然一直在各界廣為運用,惟就國內使用該量表之情況觀察,迄今猶以1999的版本為依據,而且漠視台灣與英美國家法制差異而未加調整,此在與時俱進之立場,洵非妥當。」
另一方面,許多研究指出,施虐型加害者的「性喚起模式」在腦部掃描中,與一般的性行為迴路顯著不同,常呈現杏仁核過度反應與前額葉抑制功能不足的現象。這樣的神經機制異常,反映出其深層情緒調節與衝動控制的失衡,也暗示人格結構的根本偏差。當性慾、攻擊與支配衝動交纏時,理性教化往往無法觸及這些原始的神經與心理根源。
因此,面對此類加害者,若深層神經迴路與人格結構的偏差難以改變,則「治療」的可能性也就受限,社會必須承認其復元與再犯風險的結構性困難。這也是英國在2017年針對監獄版性犯罪治療計畫(prison-based Core Sex Offender Treatment Programme, SOTP)在長期追蹤中發現並未降低再犯率,反而使高風險者的性犯罪再犯率由8%上升至約10%,隨即中止SOTP計畫,對於性侵害的高風險犯罪者治療日趨保留的原因。
在台灣司法體系裡,「治療」常被賦予一種近乎宗教的信仰。
英國、加拿大及澳洲的長期實證都顯示,治療的效果高度依賴個案動機與自我反省能力;而對「無動機、高操弄性、具暴力傾向」的個案,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反向。
治療若被誤解為「確保安全」的保證與「代替監控」的手段,就等同把社會安全寄託於理想化的人性。當制度把悔意當成風險評估,把心理治療當成免責依據,無異於將公眾放在處刑台上。
真正有效的社會防治,必須建立在4個層次:治療、監控、更生與法律責任上。當這4層網絡能協同運作,治療才有其意義;否則,強制治療只會淪為制度的幻術,在紙上延長「安全的假象」。應承認有一部分人,受限於人格結構、神經迴路與早期創傷,無法透過現行治療達到安全標準,這類人需要的不是更多輔導,而是更穩固的刑事司法制度,才是務實、負責任的做法。
在10月初的苗栗男子隨機傷人案,嫌犯即是剛出獄半年多。一名基層警察無奈地說「矯正無效」,這句話聽來殘酷,但卻是長期在第一線面對「制度漏網者」的工作者真實心聲。因此,我們必須勇於面對「治療也可能無效」的現實,重新設計風險治理架構,為了讓每一個黎光、每一個葉小妹,都不再成為制度缺口的代價。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