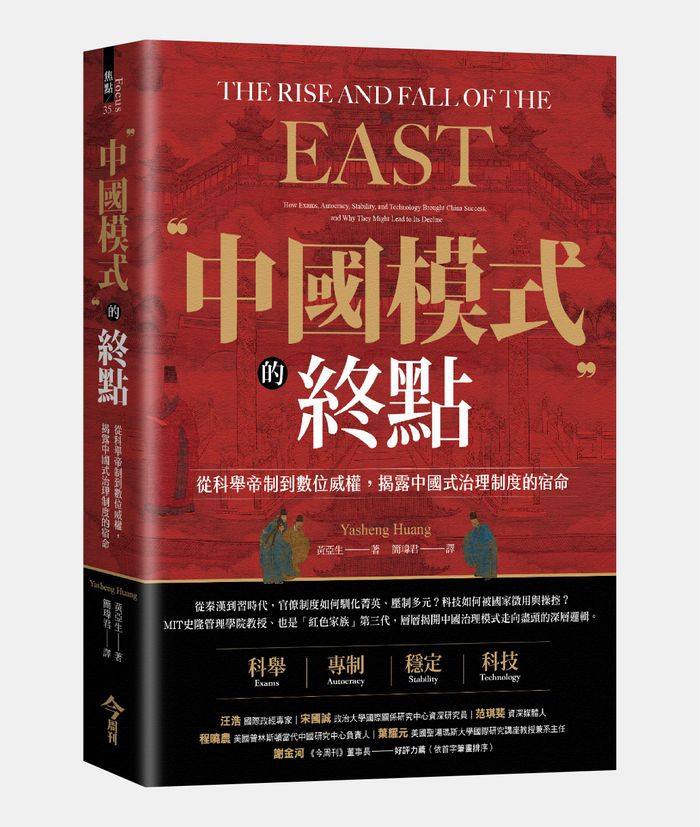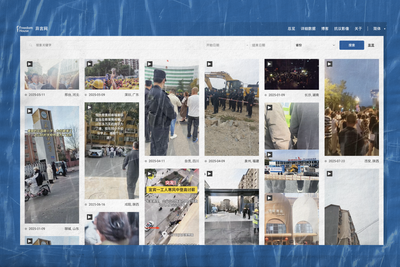精選書摘

過去40年,世界驚嘆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這是一種結合了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獨特「中國模式」。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放緩、社會監控緊縮,不少觀察家預測這個超級強權正步入寒冬。不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著作《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中提出一個觀點:要理解今天的習近平,必須先看懂沿襲1,300年的「科舉」制度。
黃亞生不僅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出生於中國、受教於哈佛、祖父黃負生是中共建黨57位元老之一、父親黃鋼是文宣體系高幹卻被捲入文革的獨特視角。這種身分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能力。
也因此,黃亞生以他橫跨歷史、經濟、政治與制度分析的視野,提出一個大膽且具啟發性的模型:「EAST」。這4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Exams(科舉)、Autocracy(專制)、Stability(穩定)與Technology(科技),他認為這正是中國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的4根支柱。這樣的模式下,衰落的可能在哪?
本文為《中國模式的終點》第10章〈突破「中國模式」?〉部分書摘,經今周刊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1990年代興起了一種被稱為「亞洲價值觀」的論述。它常被用來反對西方價值觀。其核心主張是:西方制度──包括法治、民主與言論自由──與植根於儒家思想的國家格格不入,也不適用於這些國家。
這個論點有問題。西方價值觀並不是西方人與生俱來的「基因」。言論自由與個人權利確實最早出現在西方,但其起源與演變,始終充滿爭論。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與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認為,一些經典的「西方」思想,其實源自與原住民的交流。據說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回答「個人自由概念何時出現在西方」這個問題時,曾表示:「我沒有發現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古代世界有任何關於個人自由的明確論述。」
我們經常借用和引入其他文明創造的思想。部分原因是:我們自己祖先創造的一些價值觀,用今天的標準看,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人會為纏足和車裂辯護。思想屬於哪個文明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的還是假的、是有用的還是沒有用的。我們應該討論的是思想的效用:哪些有效,哪些無效。這場辯論的結果,很可能會讓我們拒絕某些西方價值觀和做法。但這裡有個弔詭。要達到這個結論,我們需要一些自由。特別是表達意見的自由、批評與被批評的自由,以及辯論的自由。這也就是所謂的「討論民主」。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先肯定某些西方價值觀,包括言論和辯論自由,才能評估亞洲價值觀,並拒絕那些我們認為效用不高的西方價值觀。
中國人是否應以「民主與儒家不相容」為由拒絕民主?支持這種說法的人,似乎把日本、韓國和台灣排除在亞洲之外。他們也混淆了兩個不同概念:創造新事物,以及使用既有發明。科舉制度確實遏制了市場經濟與民主概念,但今天的日本、韓國和台灣,卻清楚證明:儒家思想與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完全相容。
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確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我也沒有發明電腦,我卻每天在用它。我們使用的東西絕大多數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相較於發明,使用往往更有優勢。正如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言,後進者擁有「落後優勢」。作為採用者而非發明者,我們可以從先行者的錯誤中學習,避免初期高昂成本。當然,選擇必須謹慎且深思熟慮,但「非我族類」從來不是判斷對錯的正確標準。
反對西方價值觀的另一種說法,是西方歷史汙點斑斑。我們怎能接受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國家的價值觀?例如美國和澳洲對原住民的大規模屠殺、奴隸制、種族主義,以及普選遲遲才到來。這種批評完全公正,也完全正確。但問題在於:這項批評究竟是為了從歷史吸取教訓,還是為了替今日獨裁政權的類似行為辯護?兩者差別極大。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曾任薄熙來的政策顧問。他把天安門事件與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在1932年鎮壓抗議退伍軍人的事件相提並論。先不談兩者在實質上的巨大差異,這是一個試圖為天安門鎮壓的荒謬辯護。崔的邏輯就是因為美國犯了錯誤──鎮壓抗議者,所以中國也可以犯同樣的錯誤。試想,如果有人告你,今天每位天文學學生都必須重蹈托勒密地心說的錯誤,你會認為這種說法值得認真對待嗎?恰恰相反,我們應從西方那些可怕錯誤中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順便說一句,當西方國家犯下這些錯誤的時候,它們較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否更接近今日中國的專制政體?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西方過去曾汙染環境、侵犯智慧財產權,所以我們也應該這麼做」這類論點。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今天的國家可以學習過去,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而不去重複過去的錯誤。這也是「後發者」的一個優勢。

專制政體賦予菁英特權與權力。最終決定國家未來走向的,也正是這些菁英。那麼,有沒有一種能吸引中國菁英、出於利己考量的論點,用來支持民主制度?為了說明這點,我們可以借用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這是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在這個思想實驗中,一個個體被假定為理性、自私,而且漠視他人福祉。羅爾斯問:在什麼情況下,這個人會選擇一套原則,來組織一個可被視為「正義」的社會?答案是:當這個人被剝奪了對自身具體條件的認知時。比如性別、種族、天賦、社會地位。也就是說,他被置於「無知之幕」之下。在這種狀態中,對他而言,選擇建立一個沒有偏見、歧視與壓迫的社會,反而最符合自身利益。這樣的社會願景能造福所有人,而非特定個人,由此所產生的社會就被認定是「正義」的,也具備公理上的合理性。
羅爾斯的原則,提供了一種能打動中國菁英自身利益的思路。有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的體制經常對自己的菁英成員極為殘酷。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便是例子。自1989年以來,在經歷短暫的政治寬鬆後,中國政治環境又變得尖銳了。權力與特權或許唾手可得,但轉眼間也可能灰飛煙滅。
劉少奇沒能繼承毛澤東。他最終孤獨病逝,還以化名掩埋,裹屍草席草草下葬。1959年廬山會議上,與毛澤東衝突的2位軍事巨頭──林彪與彭德懷元帥──都死於非命。林彪死於飛機失事;彭德懷死於獄中,癌症也未獲治療。今天的中國政壇雖不像過去那樣血腥,但仍可能攸關生死。2007年,一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與一名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被處決。2010年,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亦遭處決。2021年,財務高階主管賴小民亦被處決。更常見的,則是酷刑逼供。《紐約時報》報導過福建省落馬官員王廣龍的遭遇:他「挨餓受凍,飽受毆打,在冰冷的房間裡被連續審問多日,不准躺下睡覺,甚至連坐下或倚靠牆壁都不被允許」。薄熙來也暗示,他的招供是在「巨大心理壓力」下做出的。
中國政治菁英落馬的情況層出不窮。過去20年,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4大直轄市中,有3個城市的黨委書記都是從最高職位直接被送進監獄裡去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加劇了中國官員的心理壓力。2012年至2016年間,約有120名官員自殺。這遠高於2003年至2012年間的68人。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其文章〈中國菁英為何步履維艱〉(Why China's Elite Tread a Perilous Path)中,以中國電視名人芮成鋼為例,描寫一位自信滿滿的人,似乎「看似無緣無故地」不見了。前一年還在達沃斯(Davos)與富豪名流觥籌交錯,第二年卻身陷囹圄。拉赫曼援引中國媒體報導指出,截至2011年,中國共有72位億萬富豪,其中14人被處決,15人被謀殺,17人自殺,7人死於意外,19人死於疾病。
一夜之間,施暴者可能就變成受暴者。這點在一個著名的中國傳說中說得很清楚。傳說裡,武則天派官員來俊臣去查另一位官員周興。來俊臣向周興請教,如何逼供犯人招供。周興說:「方法很簡單。準備一個大甕。在甕的四周燃起炭火。然後讓犯人進去。」於是,來俊臣照做:準備大甕,點燃炭火,並請周興入甕。從此,「請君入甕」成了中國司法中「迴旋鏢效應」(自食惡果)的絕佳寫照。來俊臣也沒能逃過自己創造的宿命,後來被武則天處決。
2016年,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任命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為主席,引發普遍擔憂。外界擔心中國會利用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政治異議人士。2018年,孟宏偉在中國出差期間,給妻子發了兩封簡訊。第一封是「等我電話」,第二封則是一個刀子的表情符號。孟妻把這解讀為危險訊號,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孟宏偉隨後被逮捕。那個表情符號的意義,在這裡非常恰當。在中文裡,「刀把子」指的是執法機構。孟宏偉傳達的意思是:他已落入他曾給別人設下的「大甕」。2018年以來,9名公安部副部長中,已有3人入獄:2018年孟宏偉、2020年孫力軍、2021年傅政華。另有一位副部長李東生在2013年被捕。
持刀者經常發現自己處於刀刃邊緣。史達林手下的警察局長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 Beria)曾經說過:「給我一個人,我就能找到他的罪行。」這句話的諷刺意味可以由他自己來演示:他被史達林的繼任者處決,與其前任部長結局相同。曾掌控中國整個安全系統的周永康,如今身陷囹圄;曾執行多次死刑的重慶市公安局長文強,其死刑的執行者王立軍,最終也被逮捕入獄。許多掌握國家暴力壟斷權力的官員,最後也難逃暴力的制裁。中國有句諺語:「伴君如伴虎。」正是如此。
當你聽到中國官員批評西方的個人權利時,你大可放心:他們在發表這些話的同時,往往正享用著豐沛的個人權利。中國的戰狼外交官常在推特(現為X)上譴責西方的虛偽。但他們的同胞卻無法使用推特溝通。這種虛偽的意味,除了戰狼自己,人人皆知。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曾嘲諷美國司法系統執迷於個人權利,並讚揚中國司法迅速而公正。然而,2012年,她丈夫失勢後,谷開來在一場為期一天的公開審判中,因謀殺英國商人被判死刑緩期執行。我們可以肯定,她如今對司法效率的看法已完全不同,因為她自己也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
中國制度有不少賦予的權利,但前提是:你得有權力才能獲得這些權利。改革制度的動機,正是因為人們意識到這種制度安排並不穩定。假設你不知道自己進入政治局或入獄的機率是多少,你會選擇什麼制度?一個理性且利己的人,會選擇一套保障普世權利的制度。這種權利適用於所有人,包括現任與前任政治局委員。民主制度就像保險。當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會遭遇意外時,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投保。
中國體制的陷阱在於:人們往往在意識到羅爾斯正義論是有道理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紅衛兵把劉少奇拖出來批鬥時,劉少奇手裡揮舞著憲法,徒勞地抗議自己是有權利的。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皈依民主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國家的囚徒」。2021年,曾在2003年至2013年間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在一份澳門不知名的報紙上發表悼念母親的文章。文章裡,他表達了對自由與民主制度的一點嚮往。但文章遭到審查,並從中國網路被刪除。身為總理的他,是否預見到會有這一天?他當總理的時候本可以在新聞自由方面有所作為。2002年至2012年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位的時候堅決拒絕改革政治體制和加強法治。是他這個選擇,讓他的繼任者在幾年後,可以把他從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逐出。
羅爾斯的推理能否在中國引起共鳴?這取決於中國政治變幻莫測到什麼程度。善於察言觀色的林彪,敏銳意識到這點。爭奪國家主席失敗後,他感到處境危險。於是他起草致毛澤東的信,提出「四不」政策:不逮捕、不拘留、不處決、不解雇現任和候選政治局委員及地方高級軍事指揮官。林彪本人就符合其中一項或多項條件,他確實說出了當時許多中國政治菁英共同的焦慮。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錯失了永遠擺脫制度殘酷性的良機。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菁英階層,摧毀了許多人的生活與生計。當時,從高位權傾一落千丈,轉變是即時的,快到無法把權力和失去權力畫出明晰的界限。這是能夠體會「無知之幕」最好的時機,也是為什麼1980年代,中共推動了真正的政治改革,目的在於防止內鬥重演。文化大革命也讓這些領導人學會同理心,也就是能從勝利者與失敗者互換的角度去看待政治。1980年代的政治寬鬆,確保了政治家之間──比如鄧小平和陳雲之間──一定程度的「相互容忍」。
但是這些改革沒能繼續,中國的政治精英又一次面臨體制的殘暴。人們或許可以預期,習近平對中國菁英的全面打擊,會不會在將來引發類似文化大革命後的那種反思?如果發生的話,包括目前掌握權力的官員在內,可能會有更多人意識到:限制權力本身,是一種自我保護。把所有權力集中在單一領導人或單一國家機構,對自己,對國家,本質上極其危險。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