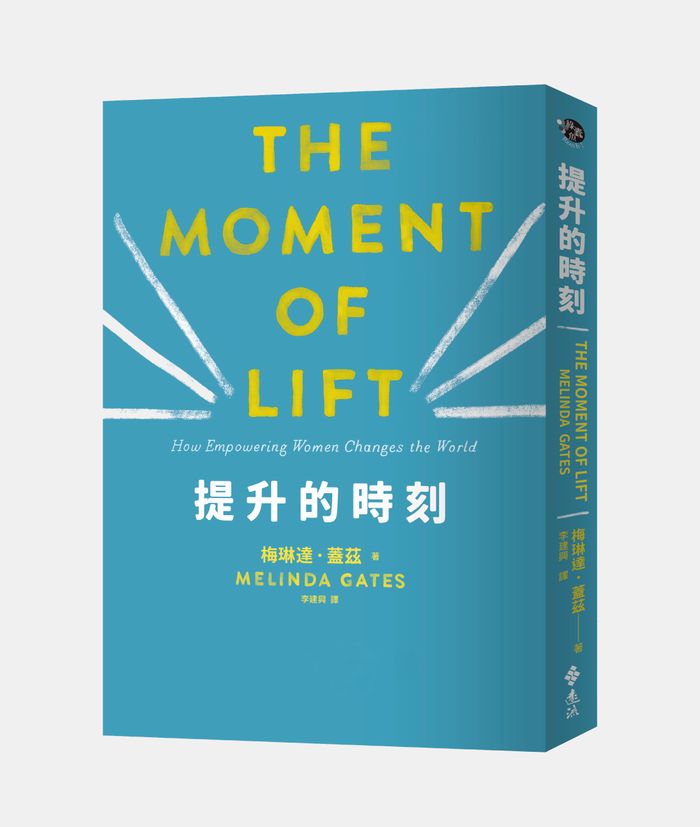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提升的時刻》部分書摘,經遠流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作者梅琳達.法蘭琪.蓋茲(Melinda French Gates),是「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共同主席,負責設定這個世界最大慈善機構的方向與優先事項。她也創立了樞紐創投公司(Pivotal Ventures),致力於從美國的婦女與家庭帶動整體社會進步。
梅琳達在德州達拉斯長大,具有杜克大學電腦科學學士與福夸商學院的MBA學位,職涯前10年在微軟開發多媒體產品,與比爾.蓋茲(Bill Gates)結婚生女後離開微軟,專注在家庭與慈善工作。
在本書中,梅琳達分享她從工作與旅行中認識的人身上所學到的啟發與教訓。在這段旅程中,有件事讓她愈來愈清楚:如果想要提升一個社會的進步及繁榮,就必須停止壓抑女性。她介紹許多平凡但傑出的女性,並且證明了人際連結的力量。當我們提升別人的勇氣,他們也會提升我們的勇氣。近年來,她毅然從幕後走到台前,為自己也為沒有聲音的婦女發聲。
「我的目標不是讓女性崛起、男性跌落。而是希望男女都從爭奪宰制的地位變成夥伴的狀態。」除了到世界角落關懷家庭計畫、童婚等問題,從#MeToo運動開始後,梅琳達更觀察到,你我都可以做的,是從改善自身職場性別不平等開始。
#MeToo運動和每個對它有貢獻或因此崛起的女性與組織,都在為兩性贏得共同重要的勝利,但這只是開始。如果我們想推廣和延續這些進步,必須了解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怎麼回事?改變為何要花這麼久的時間,卻又來得這麼突然?當女性在其他女性的經歷中聽到我們自己的聲音,我們增強勇氣,單一聲音可能變成合唱。只有男女各說各話的時候,女性贏不了。但若是「他說/她說/她說/她說/她說/她說」,就有機會公開透明,陽光可能照進侵害氾濫的地方。
2017年,侵犯者一直說謊,但維護他們的人放棄了,他們無法繼續掩蓋真相,水壩崩潰。當女性發現比較多人站在指控者這邊而非侵犯者那邊,許多一直憋在心裡的經歷全倒出來了,侵犯者非滾不可。
當遲來的改變終於發生,會來得很快。但侵犯者為何能掌控這麼久?部分答案在於當女性判斷我們是否該出面,我們不曉得別人會不會站在我們這邊。這經常讓許多女性必須聯手啟發其他女性站出來。
我認識比爾之前,有過一段不健康的交往。男方在某些方面鼓勵我,但在其他方面壓抑我──他絕不想要我超越他,他不把我當成有自己夢想、希望和才能的女人,他把我當成能在他生命中扮演有用角色的人,所以他希望我成為某些樣子,如果我不是,他可能變得很虐人。我確信那是我現在看到女性被壓抑或維持在特定角色會這麼生氣的理由之一。我在她們身上看到了自己。
我剛開始跟他交往時還很年輕,在那個人生階段不可能做我自己或找到我的聲音。我很困惑,我感覺很糟,但不懂為什麼。雖然也有足夠的支持時刻讓我想要忽視虐待及必須逃脫的感覺,但回想起來,顯然我失去了很多聲音和自信,我花了很多年才了解我的損失並且找回來。
即使事過境遷,我還是不太懂發生了什麼事,直到我逐漸有了幾次健康的戀情。但其實我結束那段感情多年後仍未完全理解那段虐待式關係的病態威力,有次我去一場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尋求女性與家庭庇護的募款活動,有個穿藍色俐落套裝的女士站在講台上述說她的經歷,那是我第一次大澈大悟告訴自己:「天啊,那就是我的遭遇。」
我相信那位受虐女士可能曾經沉默,但我們從未停止尋找我們的話語可以造成影響的時刻。2017年,我們找到了我們的時刻,但除了指認侵犯者,我們必須做更多的事:我們必須治療支持侵犯者的不健康文化。
對我而言,虐待式文化就是想要區分與排擠某個群體的任何文化,這種文化總是缺乏建設性,因為組織的能量從提升眾人被轉移到壓抑眾人。它就像自體免疫系統疾病,身體把自己的器官視為威脅開始攻擊它們。虐待式文化最常見跡象之一,就是把女人置於男人之下的錯誤階級,其實有時候更糟糕──女人不只階級低於男人,還被物化。
在全世界的職場中,女人被迫感覺我們不夠好或不夠聰明。女人的薪酬比男人少,有色人種的女性更少,我們加薪與升遷比男人慢,我們缺乏男人爭取職位的訓練、指導和贊助。我們也比男人更常被互相孤立──所以女人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發現我們感覺無法融入不是我們的錯,而是文化現實。
虐待式文化的另一個跡象就是認為被排擠群體的成員「不夠資格」。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沒有太多女工程師,那是因為女人不適合當工程師。」我難以想像這句話邏輯有多麼脆弱,而且竟然很多人相信。機會要平等,你才能知道能力是否平等,而給女人的機會從來不曾平等。
當人們看到培養不良的影響還稱之為天性,就不會鼓勵訓練女性從事關鍵職位,強化了不均衡是因為生物性差異的看法。這種生物學主張的陰險在於,它會破壞女性的發展,讓男性擺脫自我檢視動機和行為的責任。性別偏見就是這樣「植入證據」導致某些人看到他們自身偏見的影響,卻稱之為生物學,因而延續女性不想加入的文化。

讓我很洩氣的是,現代女性在許多領域仍面對敵意的文化,我尤其不滿這些問題讓女性難以進入科技業。這些都是很刺激的工作啊!很有趣,能創新,薪水又高。它們對未來的影響愈來愈大,每年還有更多職缺出現,但是不僅如此,科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產業,正在創造我們往後生活的方式。如果女性不參與科技業,就不會有權力。
電腦科系畢業的女生比例從我大學時代以來遽降。1987年,我從杜克大學畢業時,全美國35%電腦畢業生是女性,現在是19%。減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一是個人電腦進入美國家庭的時候,經常被行銷為男性的遊戲裝置,所以男性比較常使用,讓男性比女性多接觸電腦。電腦遊戲產業興起時,許多開發人員開始創作有自動槍械和炸藥的暴力戰爭遊戲,讓許多女性不想玩,製造出男性為男性創作遊戲的封閉圈子。
另一個可能原因是,早年觀點認為理想的電腦程式員最好沒有社交技能或外界興趣。這個觀點普遍到有些雇主甚至在聘雇過程中找出顯現「對旁人沒興趣」又不喜歡「涉及親密人際互動之活動」的人選。這就刷掉了很多女性。
最後──這顯示出在我們文化中考慮誰適合某項任務時的性別偏見──當軟體工程被視為比較事務性質又比硬體方面容易得多,主管階級會雇用與訓練女性來做。但是當程式設計逐漸被理解為非事務性又比較複雜時,主管們開始找男性訓練成程式工程師,不再繼續雇用與訓練女性。
隨著這個部門的男性數量增加,愈來愈少女性進入科技業,又讓科技業中的女性處境更艱難,於是更少女性進入科技業,男性開始宰制這個領域。幸好,也有些鼓舞人心的轉變。讓電腦科學成為男性俱樂部的力量在軟化,產業裡的人也在努力扭轉性別偏見。這些改變可能已開始往正確方向改變趨勢。
另一個挑戰是創投業的女性比例太低,甚至低過電腦產業的女性。創投業是剛創業無法申請銀行貸款的企業家的重要資金來源,投資人給這些企業成長所需的資本以交換部分股權。這可能就是成功與失敗的差別。
創投業合夥人僅2%是女性,僅2%的創投資金會投入女性創立的企業(創投資本投入黑人女性創立之公司的比例更僅有0.2%)。沒有人會認為這在經濟上是合理的。女人會想出一堆男人絕對想不到的好生意點子,但很不幸,「誰會有最令人興奮的商業點子?」不是影響決策的問題。
當你資助新創公司,因為初階段投資中什麼才有用的資料極少,金主會把錢給他們認識的人──上過同一間學校、參加過同一場會議的人,那是包含年輕人的老人俱樂部。2018年,美國黑人創投家理查.柯比(Richard Kerby)普查了1,500個創投業者,發現40%上過史丹福或哈佛大學。如果有這麼密集來自同一群體、同一部門、幾間學校的人,資助自己同儕網絡的衝動會驅使你投向一批同質性的公司。當你想要資助網絡外面的人,公司和金主可能都覺得不太「適合」。
所以我才會投資創投基金,包括資助女性領導的公司和有色人種創立公司的Aspect Ventures。在這方面我不是要做慈善,我期待良好報酬,也有信心得到,因為女人會看見男人看不到的市場,黑人、拉丁裔和亞裔女性會看見白人企業家看不到的市場。我想我們10年後回顧起來,會發現沒有更多投資流向女性和有色人種了解的市場真是太可惜了。
性別和種族多元性對於健康的社會很重要。當一個群體把其他群體邊緣化,並且擅自決定要優先追求什麼事情,決策會反映出它的價值觀、心態和盲點。
這是老問題了。幾年前我讀過尤瓦.諾亞.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大歷史》(Sapiens),這本書涵蓋人類的歷史,包括認知、農業和科學上的革命。我特別記得哈拉瑞對漢摩拉比法典的描述,大約西元前1776年這套法律被刻在黏土板上,影響了後世成千上百年的法律思維。
哈拉瑞寫道,「根據法典,人類分成2個性別和3個階級:上等人、平民和奴隸。每個性別和階級成員有不同的價值。女性平民的性命值30個銀幣,女性奴隸則是20個銀幣,不過男性平民的一隻眼睛就值60個銀幣。」
男性平民的一隻眼睛價值是女性平民生命的兩倍。法典針對上等人對奴隸犯罪只略施薄懲,奴隸對上等人犯罪則是重罰。已婚男性可以有婚外性行為,但已婚女性不可以。
有沒有人懷疑法典是誰寫的?就是「上等人」。法典推廣他們的觀點,反映他們的利益,犧牲掉他們認為低下者的福祉。如果各國社會要提升女性跟男性平等,宣稱任何種族、宗教的人都和別人有相同權利,那我們就必須讓男人、女人和每個種族與宗教團體一起來寫法典。
這是我對於多元性的終極主張:多元性是捍衛平等的最佳方法,如果來自多元群體的人沒有參與決定,社會的負擔與利益就不會公正平等的分配──任何社會撰寫規則的人都確保他們自己享有較多利益,分攤較少負擔。如果你沒被拉進去,就會被出賣,你的命就只值20個銀幣。沒有任何群體能委託別人保護他們的利益,所有人都應該為自己發聲。
因此我們做出形塑文化的決定必須納入每個人,因為即使最優秀的人也會被自己的利益蒙蔽。如果你在乎平等,就必須擁抱多元性──尤其現在,因為科技業的人正在寫我們的電腦程式,設計人工智慧,我們正在AI的嬰兒階段,我們不知道它會被使用在哪些用途──健康用途、戰場用途、執法用途、企業用途──但影響會很深遠,我們必須確保它公平。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反映出同理心、團結與多樣性的價值觀,誰來寫法典就很重要。
喬伊.珀薇妮(Joy Buolamwini)是個自稱「程式詩人」的黑人電腦科學家。喬伊的研究揭露科技中的種族與性別偏見,受到媒體報導之後,我才聽說她的故事。幾年前她大學時期在喬治亞理工學院製作社交機器人,在玩躲貓貓遊戲過程中,她發現機器人在特定光線中無法辨認她的臉。她借用室友的臉完成那個計畫之後就忘了這回事,直到她去香港拜訪一家製作社交機器人的新創公司,那裡的機器人除了她以外認得每個人的臉,而她是唯一的黑人──她想通了,機器人使用的是跟她在喬治亞理工學院時一樣的臉部辨識軟體。
「運算法偏見,」喬伊說:「可能以很大的規模在散播偏見。」
喬伊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研究員之後,她測試了IBM、微軟和中國公司曠視(Megvii)的臉部辨識軟體,發現辨識淡膚色男性的錯誤率不到1%,而辨識深膚色女性的錯誤率高達35%。喬伊跟各企業分享她的結果。微軟和IBM說他們已經在設法改良他們的臉部分析軟體,曠視則沒有回應。
你只要停下來反省「辨識」一字的各種意義,就會對軟體辨識不像程式工程師的面孔這麼緩慢感到心驚。軟體會不會有一天告訴政府人員「我們不認得這個人,她不能登機、刷信用卡、銀行提款或入境美國」?其他程式會不會複製工程師的偏見,否決人們取得貸款或買房子的機會?白人設計的軟體會不會不合比例的叫警察逮捕黑人?這種偏見的可能性很嚇人,但這只是我們能預料的偏見。我們無法預料的程式偏見呢?
喬伊說:「合乎倫理的人工智慧不能有排斥性。」
美國黑人婦女只占科技業勞動力的3%,西班牙裔女性僅1%。女性構成大約科技業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只占有15%的技術性職位──這些數字低得危險又可恥,所以我才對科技業的女性和有色人種這麼熱心,不只因為那是全世界最大的產業,或未來10年內經濟體系會增加50萬個電腦相關職位,或科技業的多樣化團隊會帶來更多創意和生產力,而是因為這些職務的人會塑造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一起決定。
我的意思不是女性應該被放到她們沒有努力就爭取到的科技業職位。我的意思是女性已經爭取到也應該被雇用去做。
我對科技業女性的價值所知,幾乎都是向一位科技業男士身上學的:我爸爸。家父是女性參與數學和科學的強力鼓吹者──不只為了自己女兒,也為了他從事的職業。我說過跟他和家人觀看太空船發射的興奮感,但我小時候同樣難忘的是見到我父親團隊中的某些女性。阿波羅計畫的工作結束後,他參與過太空實驗室、阿波羅-聯盟號測試、太空梭和國際號太空站,而且在每項計畫中都刻意招募女性。每當他能夠雇用女性數學家或工程師,他會在家跟我們分享他的興奮。他說,能雇用的女性不太多,但如果有女性加入,他的團隊表現總是會比較好。
家父在1960~1970年代開始發現女性的額外價值。當時沒什麼資料支持他的看法,但現在有了──而且很多,令人印象深刻。試舉一例:2010年有項對於團體智慧的學術研究發現,工作團體的集體智慧跟三個因素有關:團體成員的社交敏感度、團體輪流貢獻的能力,以及團體中的女性比例。至少包括一名女性的團體在集體智慧測試中表現超過純男性團體,團體智慧也跟性別多樣性而非個別成員的智商有更多關聯。
性別多樣性不只對女人好,對每個想要成果的人都好。

那麼我們如何打造為女性拓展機會、促進多樣性、不容忍性騷擾的職場文化呢?雖然沒有標準答案,但我相信聚集朋友和同事創造一個有新文化的社群很重要──尊重現有文化的宏觀目標,但強調實踐的不同方式。
很不幸,創造推進女權的文化面臨一個障礙挑戰:研究顯示,女性的自我懷疑程度可能超過男性,女性經常低估自己的能力,而許多男性高估自己。記者凱蒂.凱(Katty Kay)和克莉兒.席普曼(Claire Shipman)對此寫了本書叫做《信心密碼》(The Confidence Code)。凱在一段訪談中解釋:「女性經常比男性難以採取行動,因為我們比較趨避風險,我們恐懼失敗的毛病很嚴重,似乎比男性的情況更嚴重。」他們舉個例子:在惠普公司的一份個人紀錄評估顯示,女性只會在自認百分之百符合職位要求才申請升遷,而男性自認符合60%就會申請。
低估自己能力的傾向,對可能有此毛病的人而言,在壓抑女性時扮演了一個角色,很難不去想像那又是想要排擠女性的男性宰制文化的結果。這些力道經常是間接的,可能柔和又隱匿——不直接攻擊女性,而是攻擊最可能挑戰男性的女性的特質與個性。
這個角度似乎受到另一份研究的支持,研究暗示女性的沉默不是因為缺乏自信,而是出於算計。2018年《大西洋》期刊有篇文章引述的研究說,有自信的女性「只在她們也表現出⋯⋯造福他人的動機時」獲得影響力。如果女性表現出缺乏同理心或利他主義的自信,會面臨「『反挫效應』──因為不遵守性別規範受到社會與職業制裁」。根據另一項研究,因為畏懼這種反挫才讓女性不敢自我主張。
女性可能因為缺乏自信或出於算計比較不敢堅持,但男性宰制文化仍是這兩者的關鍵潛在原因。不要求太多,顯露自我懷疑,不尋求權力,不大聲主張。想要討好人的女性就會受到社會認同。
這些性別期待對我和我認識的許多女性意義重大,因為她們具備的特質導致完美主義──只能努力做到完美以補償低劣感。我很清楚,完美主義向來是我的缺點。簡短表達重大真理的天才作家布瑞妮.布朗(Brené Brown)在她的書《脆弱的力量》(Daring Greatly)中掌握完美主義者的動機與心態:「如果我外表完美,做什麼事都完美,就可以避免或極小化令人痛苦的恥辱、批判與責備感。」
就是這麼回事,我也身在其中。
對我來說,完美主義源自我懂得不夠多、不夠聰明、工作不夠努力的感覺。如果我要參加大家不贊同我的會議,或要向懂得比我多的專家演講,完美主義會刺激我──最近這種事經常發生。當我開始感覺不夠格,完美主義發作,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瘋狂收集資料。我說的不是基本準備,是不該有我不知道的事情的願望驅使下偏執的收集資料。如果我告訴自己不該過度準備,另一個聲音就會說我太懶惰了。爆炸。
到頭來,完美主義對我的意義是隱藏自我,是盛裝打扮讓我想要討好的人離開時不會覺得我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聰明或有趣,源自不讓他人失望的迫切慾望,所以我過度準備。我發現奇怪的是,過度準備之後我反而沒那麼仔細傾聽,我會搶先說出我準備的任何東西,無論適不適合當下的問題。我錯失臨機應變或妥善回應造成驚喜的機會。我心不在焉,不是真正的自己。
我記得幾年前基金會有個活動,讓我的完美主義大發作。
我們超有創意的基金會執行長蘇.戴斯蒙赫爾曼(Sue Desmond-Hellmann)是科學家、醫師和喜歡逼迫比爾跟我(和她自己)的創意領袖,為基金會領袖們安排了一場不太自在的演練,以培養主管與員工的感情,讓我們很難堪。我答應了第一個上場。
正如那天晚餐時孩子們在餐桌上跟我說的,「好痛啊!」
當下因為意識到鏡頭在拍,我爆笑起來── 一部分可能因為緊張,一部分因為寫得太直白了,一部分因為我很高興有人認為我做到了。我邊笑邊說:「希望你知道我有多麼不完美。我在人生中許多時候很混亂又懶散,但我努力收拾爛攤子,發揮自己最好的一面,以便幫助其他人發揮他們最好的一面。我猜我必須多扮演的模範角色是坦然接受混亂的能力。或許我該拿出來給人看看。」
當時我是這麼說的。事後回想,我發現或許最好的自我不是修飾過的自我,或許最好的自我是我夠坦白勇敢說出自己的懷疑或焦慮,承認我的錯誤,心情低落就說實話,然後大家對自己的混亂就可以感覺比較自在,那樣的文化比較好生活。那肯定是員工的觀點。我必須繼續跟蘇以及其他人合作,在基金會創造我們能做自己、找到自己聲音的文化。
當我說「我們」,這可不是修辭,我自己也包括在內。如果我沒幫忙在自己的組織裡創造所有男女都能找到他們聲音的文化,那我就還沒找到自己的聲音。我必須做更多才能成為別人的模範角色,就像派蒂對我,還有現在的蘇那樣。我想要創造一個人人可以展現他們最人性、最真實自我的職場──我們都預料與尊重彼此的怪癖與缺點,省下所有浪費在追求「完美」的精力,把它用在我們工作所需的創意上。我們才能放下不可能的負擔,提升每個人的文化。
適合女性的職場不只會原諒我們的不完美,還會適應我們的需求──尤其最深層的人性需求,就是想要互相照顧的慾望。
我們必須創造一個跟家庭生活相容的職場。這需要最高層的支持,或許還要從基層力推。在現代職場形塑員工的生活規則,經常不重視員工在職場外的生活,這可能讓職場成為敵意的地方──因為它讓你的工作和家庭互相競爭,其中一邊非輸不可。
在現代美國,我們把女兒送進為我們的父輩設計的職場──基於員工有個伴侶會留在家裡做家事和照顧家人等無薪工作的假設而設立。即使當年也並非人人如此,現在則幾乎沒人那樣了──除了一個重要群體。社會上最有權力的位子通常被妻子不必出外工作的男人占據,那些男人可能不太了解他們底下員工的生活。
2017年,美國勞動力的將近半數員工是女性,家有未成年子女的美國女性7成在勞動力之中。這些家有小孩的女性大約三分之一是單親媽媽。
家裡有專職主婦打理的老式假設對單親爸媽尤其嚴苛。這不只是個人問題,也是全美與全球的問題。人口在老化,美國與全世界皆然,而照顧衰老父母的任務不成比例的落在女人身上,更加重已經存在於無薪工作的性別不平衡。
當人們被工作與家庭的需求拉扯,可能減損家庭生活的樂趣。我們需要雇主了解我們對家庭的責任,家裡發生危機時我們希望職場能有同情心。
我回想在微軟當主管的時期,有好多時候我原本可以更努力讓公司文化對員工家庭更寬厚一些,但我在這方面的領導力不太強,所以我希望讀者原諒我在此說個我做對的故事。
將近30年前的某一天,有個在我團隊裡工作了一兩年、很有才能的人往我的辦公室探頭:「妳有空嗎?」
「當然,」我問:「有什麼事?」
「我想告訴妳我弟弟生了重病。」
「真遺憾。我可以問什麼病嗎?」
「他得了愛滋病。」
他要有多大膽量才敢開口。在1990年代初期,當時對於愛滋病還有很多無知與汙名,我盡力表示同情,無法多幫忙也感覺不太舒服。他告訴我一些他弟弟的事,講完他想說的話之後,他站起來說:「謝謝妳聽我講。」然後走出我的辦公室。
我推敲了我們的對話好幾天,逐漸領悟他為什麼要告訴我。我說過,當年微軟是個特別操勞的文化,非常緊繃又競爭,很多人不度假,我們大多數未婚,也幾乎沒人生小孩。我們都在短暫的剛成年階段,幾乎沒人需要我們,所以沒有什麼私人事情耽擱工作。那位年輕人的表現特別傑出,所以我想他心裡其實很擔心,他被困在家庭和工作之間,但他兩者都喜歡。我想他認為如果告訴我實情,萬一危機來襲讓他績效下滑時我不會對他不利,因為他對兄弟忠誠,希望花時間多陪他。
大約一週後,我在走廊上看到他,把他叫進我辦公室。他問:「怎麼了?我做錯什麼事嗎?」
「我一直在想──專注在我們今年前十名的經銷商對你會很重要。」當年軟體還是透過零售店販賣的。
「喔,沒錯,我正在做。我拿名單給妳看。」他讓我看名單,他已經把經銷商都排好名次。
「具體上,我想你最好專注在Fry's Electronics公司。」
「喔,是啊,他們在前十名內。我已經在做了。」
他沒聽懂我的意思,所以我又說了一次:「不,我認為Fry's很重要。我們必須培養跟他們的關係,你隨時有需要過去就去。我不需要知道細節,放手去做。」
Fry's或許在他名單的中段,沒有上升或下降,所以我猜他沒聽懂我想強調的。但他突然頓悟,眼中泛淚,點頭說:「我會的。謝謝。」然後走出我的辦公室。
我們再也沒提起這件事。不需要。我們都知道怎麼回事,我們在創造自己的小文化。Fry's Electronics 就在他弟弟住的灣區,我希望他知道公司默許他隨時可以去探望。早在有那個名稱之前,他和我就隨機應變創造出有薪家庭照顧假和病假了。
有薪家庭照顧假與病假讓大家在必要時能夠照顧家人與自己。我們當時得隨機應變是因為公司還沒有相關政策,國家也沒有。現在公司有了,但美國政府還是沒有。美國是全世界僅剩7個不提供有薪產假的國家之一──其餘是巴布亞紐幾內亞、蘇利南和一些島國。這是美國在滿足家庭需求方面遠遠落後其他各國的驚人證據。
我是有薪家庭照顧假與病假的鼓吹者,因為效益巨大又長遠。很不幸的,我們手邊沒有有薪假帶給家庭各種好處的資料,但我們可以量化某些效益。有薪育嬰假跟降低新生兒與嬰孩死亡率、提高哺乳率、減少產後憂鬱症、新手爸爸扮演更積極的實務角色都有關。如果生小孩能請有薪假,母親們比較可以留在勞動力之中贏得更高薪資;如果男性能請假,家事勞動與照顧重分配可以持續到他們回來上班以後。
美國缺少有薪假,是仍然苦於性騷擾、性別偏見和普遍漠視家庭生活的職場文化症狀。這些問題被一個現實惡化──具有權力職位的女性不足。男性宰制的文化比較可能強調有薪假的短期成本,並把長期效益極小化。重視家庭生活責任的職場有巨大的個人效益,那些個人效益也會轉變為社會與經濟效益。不幸的是,具有權力職位的女性不足,讓文化塑造的工作落入比女性不懂也感覺不到家庭需求的男性手中,那些效益變得不算數。
這對我們是個巨大挑戰。女人尤其難以要求金錢、權力、升遷或更多時間陪伴家人,甚至假裝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比較輕鬆。但如果我們因為自己的需求而尷尬,不符合我們需求的職場文化就會持續。這現象必須改變,如果我們要做自己,必須集體反抗,在不希望我們擁有的文化中要求我們需要的東西。這才是創造符合每個勞工需求的文化的唯一辦法。
我們在全世界目睹性別不正義時,要批評很容易,但我們也必須在大多數人感受得到又能夠處理的地方發現問題──那就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