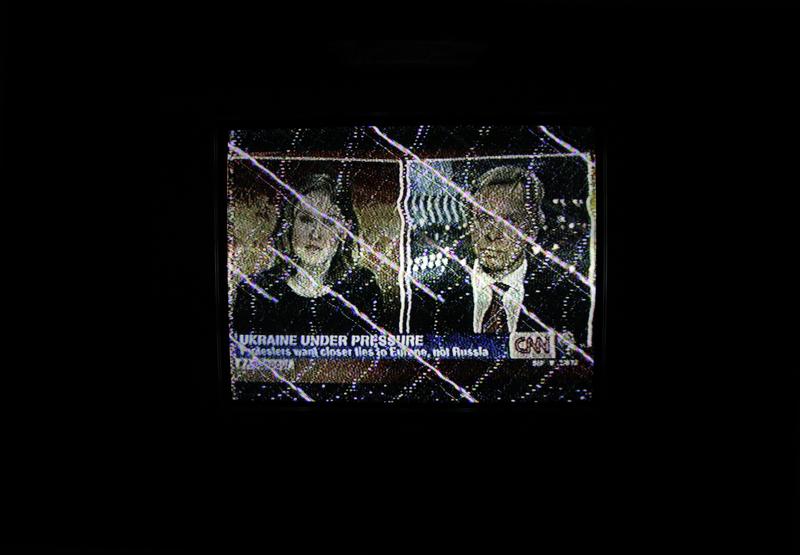評論

細觀石黑一雄作品當中的職業描寫,管家之外,還有畫家(《浮世畫家》)、音樂家(《無法慰藉》、《夜曲》)、看護(《別讓我走》,雖然是比較特殊的設定)、偵探(《我輩孤雛》),似乎不單是為了讓角色能夠有血有肉。他未必每次都花大量的篇幅去描寫職業景象(如同他說過,強調每個寫實的細節不是必須,而是要把關鍵的東西精準地拿出來)。透過這些職業者,石黑一雄專注的,是得以在他們所屬的世界中,在那個獨特的位置上(像《別讓我走》的主角,就座落在那整個未來的世界中最好的說話位置),讓他們一一述說。如我們所見,石黑經常展現出的,是由角色的話語逐步引入內心回憶探索,並依此來展開故事的敘事能力。那麼,職業則像是命盤一樣,它冥冥決定你踏上某條路,又隱隱指引你的思緒與活動,所謂命運。在那位置發出的聲音、所見與所想,關乎個人最裡的,也關乎世界:時代、國族,甚至人類全體。
石黑一雄是可以不只值得讀一本書的作家,且因為他謹慎出手且品質穩定(當然客觀來說,並未每部都是完美),稍有餘裕得以全部讀完。每位讀者難免會有私心偏好的作品。於我而言,最喜愛的是《我輩孤雛》。至少,初讀與重讀中,這部作品仍舊給了理解石黑一雄的重要的向度。
尤其,那位自述者,克里斯多夫.班克,是位偵探這件事。
平心而論,小說裡關於偵探這一行對描述,在石黑的作品當中是相對匱乏的。我們可能看到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名偵探的社交生活,而非辦案解謎的過程。只是細節的缺席偏偏讓讀者意識到一件事:作為記憶迷宮的探究者,偵探確實是不能再好的隱喻。偵探總是在事件(而且多半有所缺憾)發生之後現身,靠著線索、痕跡,去重構整個現場,與揪出那最終的謎底。而記憶呢,至少在石黑的小說中,往往是事過境遷後不可靠的導引。回憶之人牢牢地被細節所絆住,也許連過不去的事情都難以碰觸,遑論真相。回憶者像是總是被自己誤導的偵探,懵懵懂懂間才撞見了真相,然後才知道一直以來信仰與活著的那個「記憶的以為」,是虛構出來的。
虛構的故事,要以故事的虛構消解,所以石黑一直說著故事。
石黑一雄寫起偵探,不像愛倫坡專注迷戀在各個能指間的快速跳接串連而快速擊中核心(《莫格爾街兇殺案》、《金甲蟲》),巧妙漏掉了內容(《失竊的信》),探偵者總輕鬆在案件結束後離開。若愛倫坡偵探裡的極高度的邏輯理性,近乎於瘋狂,那麼,石黑一雄在《我輩孤雛》當中所有的追尋,似乎只是為了迷路,且充滿了情感。在謎中迷路,像是德國哲學家班雅明練習習得的,在現代的都市裡刻意迷途。
必須迷路,必須迷惘。直到最新的作品仍像是石黑的記憶探尋準則。
譬如《我輩孤雛》中偵探說到關於線索的段落:
「其實,有時候等案子發生一陣子再來調查也有好處。」 「真的嗎?好高深呦。我總以為最好儘早趕到現場,好找些蛛絲馬跡,您懂我意思吧。」 「正好相反,要找您所謂的蛛絲馬跡,永遠不嫌晚。」
要明白,石黑要的真相,並不是真的以為能留在過往時空那個點上,尚待發掘的不變事實。若沒有時移事往,也無法前進到那個足以回望的關鍵點上。石黑的小說裡,回憶的關鍵時刻,或多或少都在某種主體當機的狀態。像《長日將盡》放長假的老管家,或是《別讓我走》撐得過久即將身退的看護,《無法慰藉》到達奇特小城旅店的音樂家。種種,度過人生泰半的日常,在某個懸置的時間狀態裡,回憶的缺口打開(伯格森?)。然後進入迷宮。重點可能在於,迷宮,不在於使人脫逃或困住某物事,而是試圖迷途到最深最深處,尋找那個米諾陶。若石黑的米諾陶有個名字,與其叫作記憶,毋寧說是遺忘。遺忘並非空缺而是同等的實體,與記憶一樣需要淘洗,翻轉重構:
老實說,在過去這一年裡,我愈來愈專注地回想往事;這樣的專注背後有個動力,那就是我發現我的記憶—兒時的、父母的—近來開始變得模糊。最近有好幾次,我現現兩、三年前我相信會永銘心頭的事情,現在卻要想半天。
追尋的動力不在於逐漸清晰的時光,在於逐漸地模糊關鍵時刻,在記得與遺忘的邊緣,即是石黑的迷宮道路。《我輩孤雛》裡偵探的職業選擇不是偶然,是在於童年上海租界時,與日本朋友秋良的約定遊戲:一起尋找失蹤的父親。
也許只是一個意志使然,對於過往時光,不是普魯斯特式的「失而復得」。因為與其認為失去,石黑那則是失蹤。跟著線索(能指)所做的,石黑當然不會是愛倫坡的杜邦,在線索間從容穿梭,對「內容」毫不在意(見《失竊的信》)。不問過程、手法、解決方式(例如真的如他一開始以為的父母仍被囚禁。如何可能帶他們脫困?何況如此多年,以常理推斷也不可能一直在那被囚禁?),只是執迷於某種情感,石黑筆下的偵探最終失格。只是想要找到,於是過度深入,自己走向失蹤。然而醒悟,要贖回,正是要以許多年後的「我」去填補失蹤本身(偵探變成瀕臨失蹤者)。換言之,這是不可能的說話位置,因為終極的失蹤,是話語的失蹤,一切能指如煙消散。然後醒悟,「我」回家了,儘管「(童年之)我」與「家」,皆已物是人非:
「我跟你說件奇怪的事情,秋良。這個只有你會懂。我著英國的這些年來,從來沒有家的感覺。而公共租界,那裡永遠是我的家。」 「不過公共租界⋯⋯」秋良搖搖頭。「非常脆弱。明天,後天⋯⋯」他舉手一揮。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說:「我們小的時候,感覺上好堅固。不過就像你說的?那是我們的家鄉村子。絕無僅有的一個。」
又:
「我們一旦長大成人,兒時就變得像另一個國度。」 「對我來說,那可一點都不是另一個國度。從許多方面來看,我的一生都是在那裡度過的。直到現在,我才開始踏出那裡,展開我的旅程。」
一切的旅程,偵探以自身的失格,完成自己的失蹤/歸鄉。石黑之探,不是要解救過去,而是自過去解救。迷霧散去,真正地踏出步伐。
「她對我的感情,永遠存在,不需仰賴任何事物。」
那便是偵探最後安然擁有的遺忘或記憶,或兩者都是。在謎面與謎底之外,在線索與真相之外,真正重要的是探索的勇氣與讓你願意傷痕累累且徒勞前行換取的,不需仰賴任何事物之愛。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