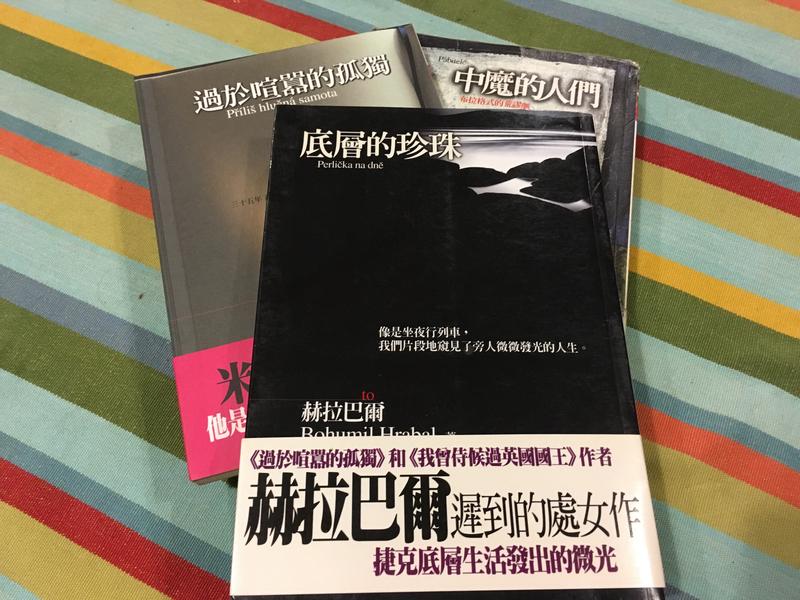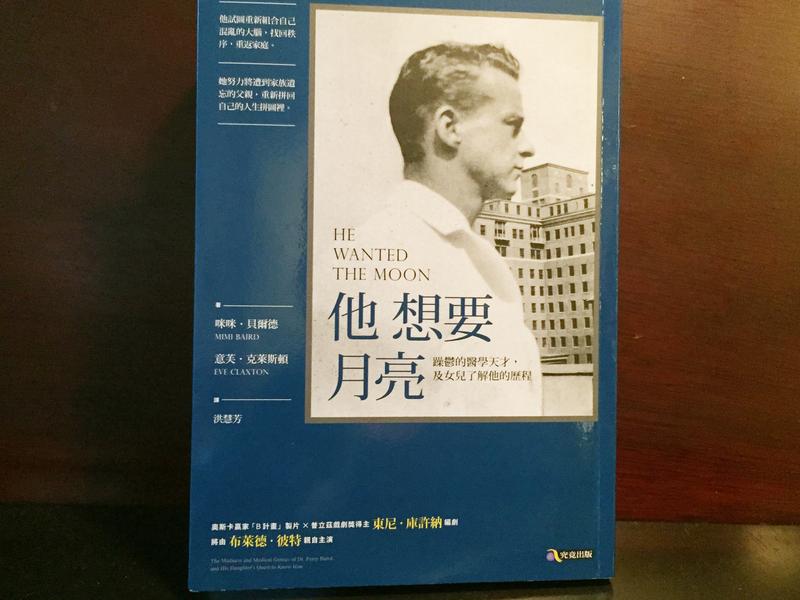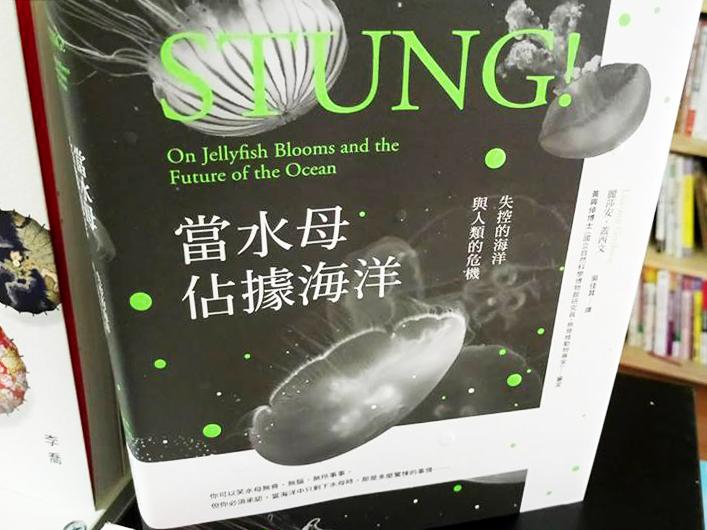【閱讀現場 X 小小書房】

會開始看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小說,是因為我從小是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的粉絲。他扮演電影《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裡的管家,簡直像是小說裡走出來的人物般:英式特有的迷人矯飾禮儀、文謅謅地節制腔調,戒慎謹守自己設下的每一條界線,小說裡的管家史帝文與安東尼.霍普金斯的形象不時重影交疊,讓我在閱讀這本書時愉快無比。
我手上的皇冠版,封面是電影海報中,安東尼.霍普金斯與艾瑪.湯普遜(Emma Thompson)站在窗前的那一景。電影已遠,也許,新世代的讀者需要重新進入這本小說。《長日將盡》新版重譯本(2015,新雨)換上白底,掩去書封上一位男人的一半面容,迷霧般的白色書衣,讓人無法一眼看清。
《長日將盡》並非石黑一雄的作品裡我最喜歡的。時常會浮現在我的腦海裡的,是故事情節並不完整的《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1982)、被遺忘的毒霧籠罩的《被埋葬的記憶》(The Buried Giant,2015),以及唯一一本沒有譯出的超厚大作The Unconsoled(暫譯為《無可慰藉》,1995)。
他的處女作《群山淡景》裡便揭露這個日裔英籍作家特有的興趣:探查記憶斷裂、掩藏與虛構之處──個人的、集體的,以及國族的。
《群山淡景》故事一開始,是透過敘事者亦是主角悅子(Etsuko)的回憶展開。這一天,悅子住在倫敦的女兒霓紀(Niki)回到鄉間來看她,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知道,悅子還有一個女兒慶子(Keiko),與霓紀是同母異父的姐妹,乃是悅子在日本所生。慶子跟著母親遷居英國,成年以後,某日在租屋處上吊自殺身亡。
也是在霓紀回來的這一天,悅子不知道為何想起在長崎時認識的一個女子:幸子(Sachiko)。當時,美軍正在打韓戰,而長崎依舊滿目瘡痍,悅子與丈夫次郎住在公司所配購的公寓裡,公寓臨河不遠,中間有一大片廢地,在廢地盡頭有一間幾乎就在河邊的小木屋,幸子與她10歲左右的女兒真理子,就住在那裡。
幸子與悅子很明顯會成為對照組:悅子,懷孕三、四個月,傳統婚姻的家庭女性,恭順、壓抑;幸子,寡婦,帶著年幼的女兒,一心所想的是:她的美國情人將會帶她和女兒一起到美國生活。小說情節進行得非常平淡,悅子的這一段回憶,環繞在幸子與她的幼女真理子的「衝突」上。但是,一般小說裡的「衝突」或者說事件,往往意味著揭露與解決,石黑一雄卻反其道而行,他總是截斷它,讓它成為一個謎、或坑洞、懸念,就讓它留在那裡。
譬如有一景:有一天真理子不見了,幸子跟悅子去找,她們到河對岸,那是幸子平常不讓真理子去的地方,在接近樹林的草地邊,她們發現真理子倒在泥坑裡,身上與大腿內側有血:
「我的記憶可能隨時間而模糊了,也許事實並非完全如我現在記得的樣子。可是我非常清楚的記得我們站在漸深的黑暗中,望著河邊那一團東西時,那種像被奇異的魔咒鎮住的感覺。」(《群山淡景》,頁43)
這個魔咒的、黑暗的場景沒有延續,也沒有被釐清,它立刻返回日常,被消解了。幸子說,真理子說她爬樹掉下來,傷口是摔傷的。悅子質問,真理子常說,河對岸有一個女人會來找真理子,說要帶真理子回家,跟那女人沒有關係嗎?
幸子笑了。「悅子,不可能的。那女人已經不在了。聽我說,悅子,這個女人的這些事,只是真理子故意搗蛋時編造出來的。我早就習慣她這一套了。」 「可是她為什麼好好的要編出這些事來?」 「為什麼?」幸子聳聳肩。「小孩子喜歡編這些事情。等你自己當了母親,悅子,你也得習慣這些事的。」(《群山淡景》,頁45-46)
之後,悅子又回憶幾件類似的事件,但都如前面的橋段一樣。在這本小說裡,表層高潮起伏的衝突是沒有的,石黑一雄透過角色對話所呈現的,都像是記憶裡被打撈出來的浮渣;真正的洪水,隱藏在這些平淡的、日常的對話深處。悅子為何離婚、離開日本,她如何到英國、再婚,慶子為何自殺,這些種種傳統小說裡會處理的情節,石黑一雄都讓它們隱隱浮現在記憶的斷裂與虛構之處,不講白,也沒有不講。
「記憶往往是不甚可靠的。回想往往把過去染上不同的色彩。我現在敘述的事自然也不例外。」(《群山淡景》,頁170)
瞭望記憶之處,就像你從遠處看著群山一樣,深深淺淺的,但你看不清全貌,也無法接近那所謂的真實之地。
像《群山淡景》這樣,閱讀的時候你會感到滿足,闔上最末頁會感到飢渴的小說,石黑一雄顯然不太願意立刻再嘗試一次。它可以被視為結構上的瑕疵:長崎與英國的悅子,在整本書裡,有非常多有趣的、值得探究心理變化,閱讀的愉悅來自於此;然而,長崎回憶的占比雖然非常重,但它卻是一個不清晰的、有頭無尾的故事──這個「洞」,成為故事的回聲之處,無法被固定,也無法被填補。
雖然石黑一雄的小說,每本談的主題都不同,然而,記憶之扭曲、錯置、喪失,或者不可靠,在他的長篇作品裡,每本都會出現。只是,大部分的作品,諸如像《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1986)、《長日將盡》、《我輩孤雛》(When We Were Orphans,2000)《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2005)都情節完整,謎題也多半會被解答,獲得閱讀上的撫慰,敘事結構也沒有像《群山淡景》這般,有著強烈的缺陷與不平衡感。
那麼,最後我們要來談談,那本唯一沒有被譯成繁中版的The Unconsoled。這本書,沒有被翻譯的原因,除了厚以外(原書有五百多頁),評價完全兩極──要不就是上乘的藝術之作,要不就是石黑一雄的大敗筆。
我是很愛,非常愛。除了我熱愛那種形式怪異的作品以外,The Unconsoled 可以說是石黑一雄對於「記憶」這個主題最為強烈、迷戀之作。主角Charles Ryder,同樣也是一個「不可靠的敘事者」,這是石黑一雄最擅長運用的敘述手法。
什麼叫做不可靠的敘事者?意思就是說,因為讀者往往只能透過小說裡說故事的這個人,來理解所有發生的事情,可是,石黑一雄的主角(他的主角通常就是敘事者)要不是記憶經常出錯、遺忘、記錯事情、不確定,或者言行前後、裡外不一⋯⋯等等,讀者向來慣性倚賴敘事者,很少懷疑說故事的人自我欺騙,甚至騙你。但是,一旦你發現,你被迫倚賴的是一個「不可靠的敘事者」時,事情就會變得很有趣,你會拉長一個距離來觀察他、尾隨他,不再時不時被他拖著到處走。
這就像是,你要前往的目的地,雖然只有這個領路人才能帶領你,但等到你發現,他自己都會迷路時,你就會開始半信半疑地跟著他,看著他點點滴滴修正、彌補,或者無法修正、無法彌補自己的記憶,慢慢的跟著他前進。
這種懸念、擔憂,會讓你一邊為這個主角搖頭嘆氣,卻又忍不住一直讀下去。
The Unconsoled,是這種敘事方法的極致,這是一個像夢一樣的、奇怪又荒謬的故事:一個舉世聞名的鋼琴家Charles Ryder,在漫長的飛行旅程中,終於來到一個小鎮(應該在歐洲,確切地點不明),來到一間旅館,他顯然比原訂時程延宕了一些,然後,就開始他一連串奇異的遭遇。
首先,是他遇到的每個人,都會興奮地提醒他,邀請他來到這個小鎮,是為了「星期四之夜」,顯然是一個音樂演奏會,大家都熱烈期待著他的到來。接著,他遇到的每一個人,諸如旅館的行李挑夫、旅館主人、旅館主人的兒子、議會長⋯⋯等等,每個人都對他有「小小的請求」,請他幫「小小的忙」。鎮上的每個人,似乎都被自己的某些過去所綑綁,他們請求Ryder先生幫的「小小的忙」,某個層面上,都是要請他協助他們一起去面對那個「過去」。於是,他不停地被拉入、捲入各式各樣非常非常小的事務漩渦裡。
而最奇怪的是,讀者原先會以為,這個小鎮他明明是第一次來,不久之後卻訝異地發現,他似乎曾經在這個小鎮居住過,他跟行李挑夫的女兒Sophi有過一段情,跟她,還有她的小兒子Boris住在一起過,而他在小鎮迷宮般的巷弄行走時,也會遇到他青年時期的友人、大學時的朋友⋯⋯這些人們不停地提起對他的期望、期待,喚醒他模糊又不確定的記憶,但是,某些被召喚而出的場景或景象,又清晰無比⋯⋯這太奇怪了,Ryder先生,你難道患了失憶症嗎?
他總是都睡不飽,總是躺下沒多久,就被電話聲吵醒。為了履行日前的某個承諾出門、在路上又遇到對他有所求的人,他只好答應,但是,他所有的承諾都還沒有完成,就又被捲入下一個場景與事件中。
Ryder先生不停地被拖著往前走,而讀者我們,也只能踉蹌地尾隨他,他的無可奈何、疲憊、他未能履行承諾的、失憶的悔恨、對於各種越形逼近他的日常,他的恐慌與不得喘息⋯⋯都讓這本小說從內部膨脹起來──無法紓解、無法獲得解答的各種謎題,像理不清的毛線般,纏繞在Ryder先生身上。
在這些糾葛的線團之中,閃現的記憶斷裂與虛構之處,是人與人之間不停堆疊的誤解與疏離,讀者會強烈地感受到,這個古老的城鎮因為這些誤解與疏離,逐漸崩解中。Ryder先生疲憊地奔走、試圖串起這些斷裂記憶之時,你不禁會開始思考:Ryder先生,看起來像是一個將過去全然拋棄的新世紀的人,那他現在又為何如此拼命地想要憶起、彌補過去種種呢?記憶既然如此狼狽,那麼,就把過去全都遺忘與拋下,又會如何呢?
《被埋葬的記憶》裡,被毒龍迷霧籠罩的村莊、逐漸遺忘了所有過往的村民,像是The Unconsoled 裡的小鎮與鎮民的另一個顯影。他們遺忘了歷史、遺忘了戰爭、遺忘了過去的一切,遺忘了那些不願意也陷入遺忘而離開此地的人們。為了將村莊從迷霧中解放出來,一對老夫妻,艾索夫婦,決定離開村莊去殺了那條龍,當他們千辛萬苦與同樣也想要解決掉毒龍的戰士,一起來到垂垂老矣的毒龍洞穴時,保護著這條龍的爵士說:
「昔日埋葬傷亡的地方已經長成茂密的草地,年輕人對此一無所知。我求你離開這個地方,讓魁里格再效命一段時間。牠頂多只能再活幾季,然而即使只有一兩季,就足以讓陳年的傷口復原,讓我們永享和平。看牠對生命多麼眷戀啊,戰士!你就發發慈悲,離開這裡,讓這個國家沉醉在遺忘中。」(頁322)
戰士拒絕了他,他說:
「蛆蟲四處流竄,舊傷如何復原?還是你認為靠屠殺和幻術建立起來的和平,可以永遠維繫下去?我看得出來你多麼盼望昔日的夢魘化成灰燼。然而這些夢魘和白骨一樣,埋在土裡等著被人發現。」
倘若,殺了毒龍,迷霧散去,屆時回來的,將不只是美好的記憶,過往的一切暴烈、殺戮、不堪、謊言,也會一起回來;而人們,準備好要面對了嗎?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