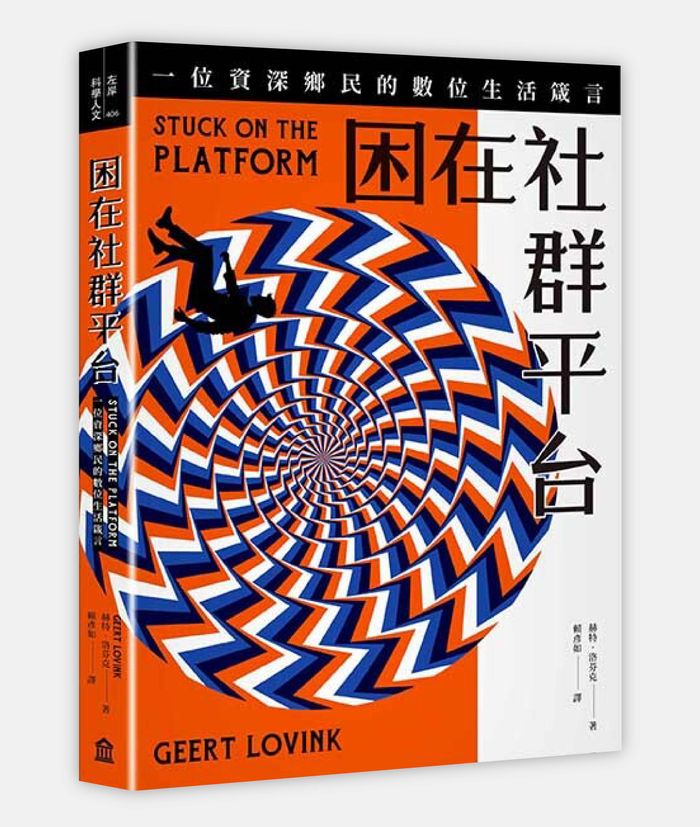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困在社群平台:一位資深鄉民的數位生活箴言》第5章部分書摘,經左岸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社群平台衍生各式難解的困境,大至結構制度失衡的雲端封建主義,小至個人層次的doomscrolling(像殭屍一樣,盲目地滑動捲動,不再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在資訊超載的失序狀態下,我們愈來愈自戀,愈來愈習慣公開談論自我的內心,也愈來愈憂鬱。不僅如此,我們還愈來愈容易受到陰謀論和假新聞的影響,也容易被引戰。我們都意識到這個現象,卻奮不顧身、持續被社群平台綁架,不論是心甘情願或放棄抵抗。這一切不是我們自恃不足,更多是平台本身Sad by Design (你的悲傷是被設計出來的)。
網際網路曾經許諾了一個光明未來,是人類追求平等解放的道路;結果卻在歷史洪流的發展中,轉變成問題的一部分,無法扭轉從自身蘊生的破壞力。在當今生態、經濟、金融危機相互交織、彼此影響的「危機的堆疊」裡,網際網路的失敗更加深了危機的不可解。
《困在社群平台》作者赫特.洛芬克(Geert Lovink)是歐陸知名媒體理論家,也是網絡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的創始人。他從哲學和媒體理論的觀察出發,綜論各種變革的可能間隙,實驗各種可能的替代平台,他認為我們得放棄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轉而尋求一系列多樣化、因地制宜的網路工具,來協助完成特定的工作。任何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都是起點。
在這個故事裡,終極解決之道並不是替代平台的崛起,而是群眾奪回鄉民的能動性與對網際網路的想像力。集體退散卡住眾生的平台,轉而建立自主協作,創造連結動能的網絡。行動的第一步,始自對於數位衰退的深刻理解。
我們要如何組織一場社群媒體的大出走?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說過:「全人類分成三群:不可移動的、可移動的,以及真的有在移動的。」可悲的是,我們這些使用者屬於不可移動的那一群。數十年來,矽谷壟斷且扼殺了通訊和商業的創新。使用者被困在「虛擬牢籠」(virtual cages)中,毫無頭緒該如何逃脫和繼續前進。幾乎所有行動主義者、藝術家和技客都再也無法想像出走的可能,更別談學術界、非政府組織和文化領域了,他們儘管「心知肚明」,卻仍然冷眼放任現狀繼續。
為了把我們的思維從令人窒息的壓抑感和有條不紊的樂觀中解放出來,讓我們開始勾勒一下如何可以擺脫主流平台的束縛。首先,有一些文化技術(cultural techniques)可以讓我們忘記社群媒體:一旦關閉了通知,應用程式就很容易消失,不再吸引我們的注意。這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網友們實在是太忙了,根本沒時間按照複雜的指示來刪除帳戶。不,我們更可能會看到的情況,是應用程式被廢棄不用、密碼被遺忘、手機搞丟。斷絕打擾是一種下意識的行為,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安東尼.奈恩(Anthony Nine)表示:
將所有讓你頭痛的家人、討厭的同事、一起上學的同學、你在某個場合遇到的陌生人都加入,製造一種你們是「朋友」的假象,然後登出,再也不看它。
眾人淹沒在噪音中,漸漸感到無聊,就紛紛登出了。
徹底刪除你的個人檔案,不要只是刪除某些「好友」。是的,這也意味著我們要取消跟奪回主流平台的演算法、通訊錄和資料庫,因為最初提供這些資料的正是我們每一個人。將世界從新興創業投資模式、超高速成長驅動力和其相關的「免費」服務解放出來,可能引領社交網絡工具的復興,這些工具不以個人檔案為中心,而是著重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係。比起評論和點讚,對話和討論更要緊。誰在害怕異議設計(adversarial design)?去中心化的應用程式可能一開始用起來會很混亂,但它將促使先前的「使用者」重新成為行動者,而不是悲慘猶如喪屍的消費者。
多年來,有關平台危害的證據持續增加,但已多到令人無感。我們需要一份完整的藍圖。有沒有可能像中國的比特幣礦商在結束營運時那樣,一個機櫃接一個機櫃拆除資料中心?在全球通訊協議下,我們將如何實現科技多樣性呢?我顧慮「大出走潮」(exodus)這個詞語的聖經意涵甚至救世主色彩,但很欣賞其中的行動感。我們到處奔波,把帝國式的設計拋諸腦後。光就「可能有另一種網際網路」的急迫性達成共識,已經不再足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如果我們能夠成功突圍,痛苦終將結束。
大出走潮不再帶著尋找烏托邦的動機。數百萬使用者已經體驗過大規模遷移,留下了LiveJournal、Tumblr、GeoCities、Hives和Blogger等網絡鬼城,但後來發生些事情,遷徙這項實用技能就被丟失遺忘了,如今的網友似乎沒什麼活力,因為線上群體實在太大了。我們需要記得如何一起拋棄某個平台,重新獲得數位自主權。讓我們建立起未知的#WeToo集體形式,而不是另一種「只關心我、我、我」的版本。有什麼運動能夠打破無聊,讓我們瞬間忘卻痛苦呢?你希望有點事情發生,但要發生在哪裡呢?我們只是在尋找著什麼,什麼都好,焦慮著迎接永遠不會到來的下一件事。所以請小心腳下,想辦法簡化個人檔案,加入迷失靈魂的關鍵多數當中。
環境倡議者喬治.蒙貝特(George Monbiot)在《走出廢墟》(Out of the Wreckage)一書中強調:「唯一能取代故事的,就是故事。」平台也是一樣。蒙貝特認為:「喋喋不休的群眾形成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喧囂。如果沒有一個連貫穩定的敘事,運動就依然處在被動、分散又危險的狀態,始終面臨著倦怠和幻滅的風險。」這裡的問題是,如何將其他平台工具轉化為「有說服力的敘事」。平台替代選項的發展,遠不止於策略性的社群媒體領域。我們不需要依賴Airbnb或Uber來找出租房間或叫車。新服務的用意可能是要做數據防範,而不是保護。給點對點(peer-to-peer)網絡一個機會,讓我們想想其他辦法來搜尋資訊跟找到彼此。
事態緊急。在COVID-19危機中,許多追蹤程式幾乎都是一夕之間冒出來的。既然做得到這一點,那麼歐洲完全有可能在主流社群媒體以外,建立不依靠廣告、不會提取隱藏數據的替代方案,而且在幾個月內就可以創建出來。從變革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關閉很多機構,因為它們已經無力回天。矽谷尤甚,目前亟需新的商業模式。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保持禮貌,不質疑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那什麼都不會發生。
過多的擔憂和理論分析,可能會阻礙必要的行動。流言蜚語太多,關於替代平台及其進展的故事卻不夠多。我們需要反思,究竟是哪些盲點和惡性循環,才導致技術方面停滯不前?過去十年裡,是什麼阻礙我們打造下一代的網際網路、平台或替代程式?發現資料會帶來更多資料是一回事,進一步掩蓋其意識形態基礎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能說治療會帶來更多治療嗎?我們很容易在情感的鏡像世界中迷失方向。
目前有幾種可能方案,但還需要更多。在任何情況下,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都是起點,其次才是開始實驗的意願,無論規模多小、概念多簡略。第一種是網路藝術家本.格羅瑟(Ben Grosser)所稱的平台現實主義(platform realism),也就是在平台本身進行鬥爭。這或多或少就是現狀。第二種是對大出走進行宣傳,遷移到Fairphone、DuckDuckGo、Jitsi 和Etherpad等現有的替代方案上。第三種方案則是完全不處理平台問題,全力投入發展替代平台,使之成為主流。藝術家組織「瓦里亞」(Varia)就是採取這種策略,他們專注於Mastodon社群的「聯邦宇宙」(fediverse)生態,並結合Discord、Signal、Telegram以及自主自生的後部落格社群網站。第四種是「離線萬歲」(offline matters)策略,強調(自我)組織的詩意和美學。這些激烈的改造行動,超越了黨派、地方倡議、合作社和傳統工會模式。
小型網絡不可能在平台耀眼的聚光燈下形成。應用性自主(applied autonomy)既是一種技能,也是一種基本權利。沒有這項特質,自我組織行為就只能隨機、短暫地出現,而且最重要的是,會變得很被動。離開平台是一種選擇,希望我們能夠遷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對大多數人來說,替代的可能性存在於分散的狀態中,得放棄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轉而尋求一系列多樣化、因地制宜的工具,來協助完成特定的工作。格羅瑟補充:
去中心化肯定為人們逃離大型科技平台的夢想,帶來了一線希望,但去中心化這種作法本身並不是萬靈丹。我們只需要看看投資性融資和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的加密夢想,就可以略知一二:誰對去中心化最興奮,理由又為何。
過去幾年裡,我一直無法將網路上的悲傷狀態跟什麼政治色彩連結。從以前到現在,很多人的確從我的文章和演出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了解權力如何運作確實很重要,這樣我們就不會自願或下意識依循原本的模式。但經過了3年的(虛擬)巡迴演出之後,我不得不體驗一下我一直以來都知道的東西。助長沮喪或憤怒,會是一場危險的遊戲。這種相互認同很短暫,而且不會導向集體行動。對社群媒體的批評也是如此。光是了解「推特機器」本身,也還是缺乏一個政治綱領和變革的藍圖。激進的媒體創造了其他開端:不是問題,而是渴望。這裡有不可思議的邂逅、隨機的連結、不相關的上下文,往往還搭配過時的技術。奇異混搭之下,迸發出新事物的火花。平台也是如此嗎?最快、最昂貴和最複雜的技術,往往對我們沒有什麼益處:虛擬實境、量子運算或人工智慧都是例子。
我們在大型科技公司的平台上遇到的負面問題,根源在於它們服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全球平台反映了利潤導向的商業價值觀:追求成長、規模,不惜代價。科技龍頭當初就是受到這樣的價值觀驅策,才建構出那些平台,難免就把使用者視為資源,隨時可以挖掘、操縱、轉化為利潤。這些基礎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格羅瑟認為:「如果沒有私人獲利動機,大型科技平台的許多問題就會消失。」
如果一個平台能夠讓過度沉迷使用的情況和緩一點,而不是繼續引發這種狀態,這個平台會是什麼樣子呢?或者,它會希望使用者少付費,而不是支付更多錢嗎?或者,它所鼓勵的時間觀,是否偏向緩慢而非快速呢?
我跟格羅瑟一樣,看到各方努力要瓦解科技巨頭的控制時,共享著同一套價值觀:
- 緩慢: 我們需要媒體積極、有意識地對抗平台資本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一向認為提升速度和效率既可取又有生產力。
- 減量: 我們需要新的替代方案,這些替代方案反對追求規模和數量。Facebook對於2016年之後平台規模帶來的負面影響,給出的回應是要將「群體」(Groups)放在首位,「賦予人們建立社群的力量。」4年後,平台產生的權力將種族主和威權主義推向了新的高度。
- 公共: 擁有30億使用者的社群媒體設施不應該受利潤的驅使,也不該由單個個人所控制。商品流通(Amazon)和資訊存取(Google)也應該適用同樣道理。
- 誘餌: 為了培養一種拒絕平台的文化,我們需要新的計畫滲透到平台中,幫助使用者擺脫對它們的依賴。
我們還能如何對抗平台邏輯?為了探索替代方案,我跟藝術家兼研究者喬安娜.莫爾(Joana Moll)進行了對話,她的回應是:「主要問題在於,我們試圖配置平台或整個網際網路,但所玩弄的,還是使權力核心存在的同樣變數。」
我們正試圖撼動這些變數,希望將它們顛倒過來,以扭轉既有的權力結構。我們試圖獲得有形基礎設施的主權,阻擋追蹤技術,期望替代科技(alternative technologies)能讓我們做到在主流平台上做得到的事。為了翻轉或動搖權力,我們需要增加權力核心中不存在的新變數,如限制他們使用能源和剝削自然資源,這些限制變項可能迫使公司改變其營運模式,還得放棄部分權力。到最後,科技公司極度依賴使用電力,這一切的發展會變得很有趣。
我們需要多樣化的平台,各自帶有不同的價值觀。埃馬努埃萊.布拉加(Emanuele Braga)希望我們能夠發明新的數位平台,以取代大型資本平台的壟斷地位。
在疫後的未來,數位平台將更加決定我們的社會行為。這種權力集中的唯一替代辦法,就是增加對社交平台的民主控制,通過多種可能的方式,將其置於民主國家的掌握之中。同時,我們需要發展數位平台的合作模式。從知識歸檔(knowledge archiving),到物流、分配、福利服務、食品和能源鏈,我們必須發展自我組織的合作平台,實現分散治理,組成再生和生產聯盟。
他看到了一個雙重的運動:
加強民主國家在發展和控制數位基礎設施方面的角色,將其定位為福利和非商業導向的服務,同時發展由下而上的平台,既能合作,又能保持各自的獨立性。這兩個方向只採一個的話,可能會表現出軟弱或專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促進兩者共存發展,相輔相成。
舉個簡單的例子,讓我們來看看一個新的貨幣協議的發展,貨幣協議是一種方法,來幫助結束自由制度、為藝術家的作品支付報酬以及重新分配財富。我們該如何恢復貨幣真正的社會資訊功能?魯本.布拉夫(Ruben Brave)建議回歸「貨幣網路協定技術」(Money over Internet Protocol),這建議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擁護者簡潔地概括了其理念:「雖然穩定幣(stablecoins)可能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成功的區塊鏈架構必須透過消費者直接使用的應用程式,與傳統的法定技術之間形成一座無縫接軌的橋梁,來實現將貨幣作為協議的作法。」這個想法很簡單:不要再把加密資產集中在可以輕易被壟斷的應用程式和區塊鏈中。壟斷進一步將網路平台化推向少數人手中,例如創投業者、大宗交易者和加密貨幣創始人。當然,認定「比特幣是右翼自由主義的產物,持續不了多久」是很常見的說法,要確切指明一個基於共有的制度會是什麼樣子,更是難得多。從身分自主權到量子加密和時間戳協定,還有許多相關的技術問題待解決。然而,儘管面臨這些挑戰,鲁本.布拉夫還是讓一個曾經爆紅的概念重新流行了起來,此計畫開始指明如何開發一個安全、公有且無涉費用的網路貨幣(money-over-IP),每個人都可以使用,但又不屬於任何人。
一個可行的方法,是讓網際網路再次充滿魅力。阿姆斯特丹的科技、媒體與藝術中心De Waag提出了「公共堆疊」(Public Stack)概念,匯集了一系列開放、公平和安全的選擇方案。他們點出的問題不是以立法術語表達,而是簡單的修復用語:「我們如何修復破碎的網路?」這裡的重點是技術如何成為集體設計行為:失敗之後,就會產生解構和重塑。此處的「堆疊」是指:
網際網路的不同層面,相互之間缺一不可。用這種方式來觀察網際網路很有幫助,我們能夠對各種層次進行解析,研究哪些地方出了問題、哪些層次可以用其他選擇取而代之。
De Waag對「堆疊」的觀念跟布拉頓(Bratton)的現代主義觀念不同,前者認為堆疊狀態不像一個分層蛋糕,而是一座冰山,只有尖端為人所見,那就是公民所使用的應用程式。大部分底層的技術堆疊仍然隱而不顯,也不在公眾辯論之列。
雖然這麼一個建設性的提議包含多種價值和權利,但如何讓那些大客戶接受參與式的包容性堆疊設計,仍然是未知數,畢竟他們對改變毫無興趣。如何把玩具從孩子們手中拿走?這將是下一輪「公共堆疊」的戰術挑戰。泛荷學社也像布拉頓一樣,所提出的「數位未來藍圖」(Digital Future Roadmap)勾勒出電腦韌體和驅動程式、數據和協議、應用程式和操作系統等不同層次之間的區別。下一階段需要納入對立政治的辯證法,光有誘人的替代選項是不夠的。我們如何一併考慮地緣政治的權力博弈、政治遊說以及疲憊不堪、對什麼幾乎都漠不關心的公眾?換句話說,在一個充滿幻滅的時代,我們該如何進行對立性設計?
對社群媒體平台的不滿,需要被珍視和培養。在這一點上,花力氣拒絕和花力氣尋找替代方案得同步進行,互為補充,當然最終目標應該是集體出逃。但同時我們也需要其他選擇,讓一般人能夠有條出路。拒絕總是需要一個催化劑,一個起點。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走下公車,許多人也跟隨她的腳步。所謂的從眾行為,在漫長的出逃旅程中非常重要,這就是網絡動力的關鍵。社交網絡MySpace發生的事情,有朝一日也可能發生在Facebook和Google身上。矽谷擔心,網絡效應的這種潛在記憶有一天會被重新喚起,再次恢復活動,因此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從人群中抹除那種集體記憶。我們被困住了,堅信沒有出路,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十年來,小型藝術和科技先鋒派有意識地到處遷移,卻還是一直停滯不前。雖說現在有很多其他選項,但我們仍無法解決雞生蛋、蛋生雞的難題。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