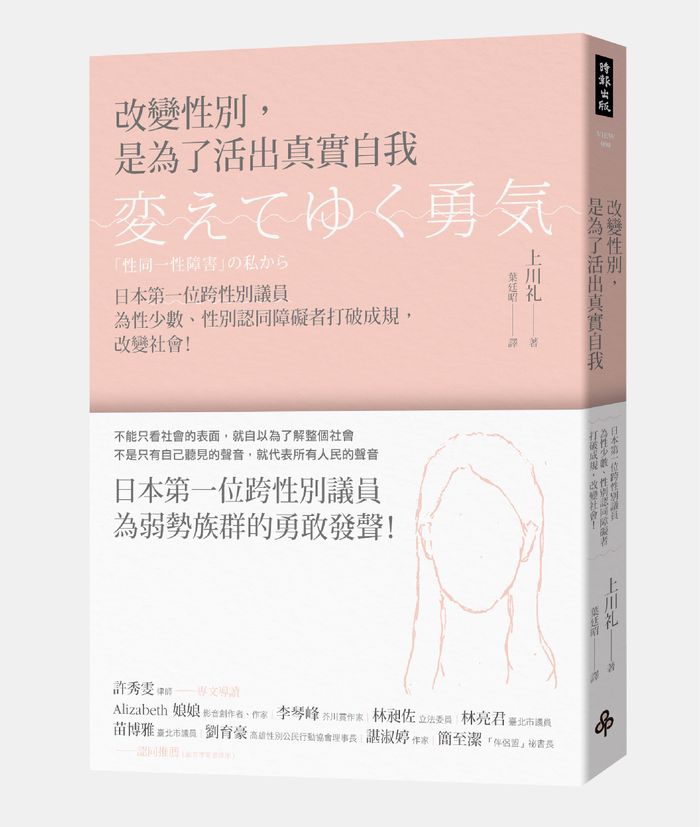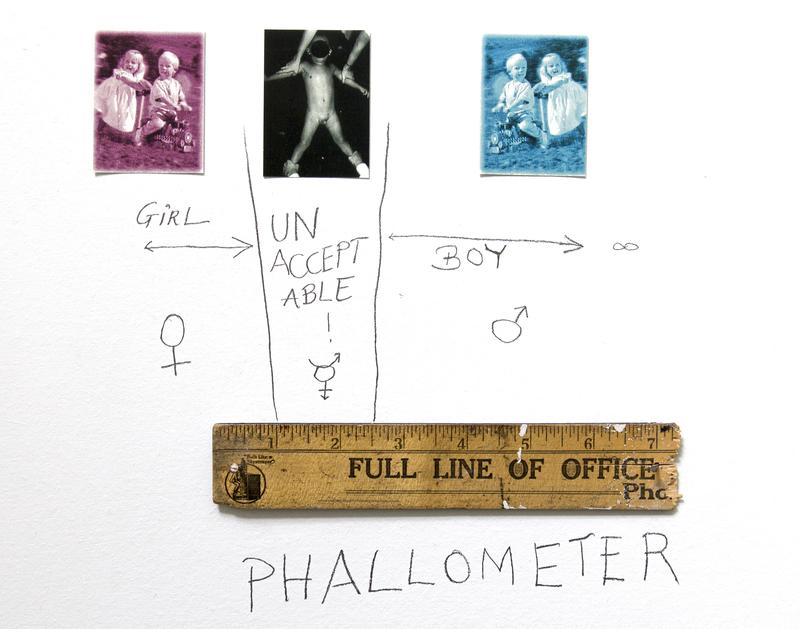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改變性別,是為了活出真實自我:日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為性少數、性別認同障礙者打破成規,改變社會!》部分章節書摘,經時報文化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本書作者上川礼,為日本第一位跨性別議員。出生時為生理男性、三兄弟家庭的次子,上川礼從小對自己的身體和性別感到困惑,30歲後,開始以女性的身分過活。然而在體制下難以變動的戶籍性別,和社會對跨性別的不理解,仍舊阻擾著跨性別者正常的工作、求職、與人交流、享有合理的保障。
2003年,上川礼公開身分,成為日本第一個競選議員的跨性別者,並於同年當選東京世田谷區議員,此後創下5屆連任紀錄至今。她和一群倡議者共同促成日本於2003年7月通過《性別認同障礙者特別法》──這項專法為跨性別者申請性別變更開了先例,但也立下了幾項的前提:辦理性別更變必須拿到性別認同障礙診斷、摘除生殖器官、且不得已婚和擁有未成年兒女(無子條款),幾項嚴苛的條件至今仍備受爭論。
上川礼在書中自述作為跨性別者的成長經驗;也回顧當年在特別法立法路線上,「先確保專法通過」和「堅持更好的法律規範」間的兩難和抉擇。本篇書摘節錄自第三章,描述上川礼在改以女性身分生活前,嘗試以醫療手段改變自己的身體──並非所有的跨性別者都會選擇接受手術,她的經歷,也提供我們照見跨性別者在面對手術時的風險與艱難。
我認識的夥伴當中,有人採取具體行動來消除生理上的不適應感。其中一種方式就是賀爾蒙療法,看到那些夥伴的外貌大幅改變,我也開始好奇女性賀爾蒙會給我帶來什麼變化。
我在17歲那一年向母親坦承自己的性別認同。事隔10年,我再次對母親訴說我的想法。我百般猶豫,只敢用不確定的語氣告訴母親,我的性別認同很可能是女性。
母親也記得我以前的自白,盡可能冷靜聆聽我的苦惱。母親依舊寬容的態度,讓我忍不住流下淚水。從那一天起,母親成了我最親密的商量對象。害母親操煩我也過意不去,無奈當時我沒有心力顧慮那麼多,一股腦將所有的辛酸苦惱都跟母親說。
那時的我不是渴望當一個女人,而是渴望活出自己。我很清楚自己的現狀有問題,因此試著做出改變,只是這樣而已。
我聽從朋友的建議,去新大久保地區的婦產科接受賀爾蒙療法。一個男人獨自進入婦產科需要莫大的勇氣,我在醫院前走來走去,始終不敢跨進醫院大門。最後我用附近的公共電話,打去詢問男性可否接受賀爾蒙療法。院方倒也乾脆,直接跟我說沒問題。我前往醫院接受醫生的診療,醫生向我說明賀爾蒙療法對肝臟的副作用,在我的臀部打了第一劑女性賀爾蒙。打完後我鬆了一口氣,這下我的身體終於能「恢復原狀」了。就這樣,我每週都會去醫院接受一次治療。
第二次注射後,我的身體開始產生了變化。首先是乳頭有疼痛感,乳腺還有一點似有若無的發脹感,當我發現這是青春期體驗過的感覺,真的非常開心。每次洗澡我都會確認自己的生理變化。我的胸部如同少女般逐漸膨脹,下盤也多了些脂肪,雙腿的曲線更加柔和。腰部一帶的觸感也比以前柔嫩豐潤,皮膚也變得敏感又細緻。
我心想,這才是我該有的身體。
不過,我的理性很清醒。這些生理變化對我來說很正常,在別人眼中卻很詭異。我必須好好隱藏,為了避免胸部被看出來,我連在家中都得駝背生活。外出上班時就穿胸前有口袋的襯衫,順便在口袋裡放點東西,有人靠近我就趕快雙手環胸護住自己。問題是,生理變化不可能永遠瞞下去。公司通知我去健康檢查的隔天,我就下定決心準備辭職了,辭職原因我只寫了「個人因素」四個字。真正原因我只告訴過兩個人,一個是我年資尚淺時,調侃我是處男的那位前輩,另一個是比我晚一年進公司的後輩。
在歡送會上,那個後輩毫不在意眾人目光,哭著替我送別。前輩也替我加油打氣,他說我不管到哪裡一定都能過得很好。我這次離職其實沒有什麼未來展望,前輩的鼓勵帶給我很大的勇氣。
接受賀爾蒙療法後,我的外貌變得愈來愈中性。要持續改變自己的生理性別,就不能跟家人一起生活,於是我前往新加坡。新加坡有一種對性少數族群較為寬容的印象,但現實不斷讓我失望,我才住8個月就回國了。
1996年7月,我回國沒多久,埼玉醫科大學倫理委員會宣布,同意有條件承認「變性手術」(詳情容後表述)。媒體大幅報導這則消息,我也是在那時頭一次知道「性別認同障礙」這個字眼。性別認同障礙被當成正式的議題探討,媒體的報導論調也十分嚴肅,我心中產生了一絲希望。

互助團體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安身之處,去那裡我可以說出真心話,交到更多好朋友。只是,他們多半知道自己要什麼,參加活動純粹是要收集必要的資訊,我卻不曉得自己的方向,因此多少有些焦躁。幸好我在那裡學到了很多知識,例如法律和制度的問題,還有心理諮詢、賀爾蒙療法、變性手術等醫療資訊,甚至學了處理家庭關係的方法,以及化妝的技巧,那些知識帶給我很大的幫助。
1995年5月,埼玉醫科大學綜合醫療中心整形外科教授原科孝雄先生向該校的倫理委員會申請「變性治療臨床研究」。隔年7月,該大學的倫理委員會經過12次審議後,給出以下列答覆:
一、性別認同障礙確實存在,只要有人對自己的性別感到不適應,使用醫學手段減輕其煩惱是正當手段。
二、外科的變性手術是性別認同障礙的治療手段之一,但日本還沒有進行外科變性治療的環境,得先經過下列程序做好準備。
- 請相關學會和專家團體,制定明確的診斷基準和治療規範。
- 召集各領域專家,例如整形外科、精神科、婦產科、泌尿科、小兒科、內分泌專家,成立性別認同障礙的治療團隊,選擇合適的治療對象,擬定恰當的治療方法,做好術前和術後的照護體制。
- 加深對性別認同障礙的理解,設法解決變性手術可能造成的各項問題。例如,尋求法律專家的協助,共同解決現實層面的問題,或是讓性別認同障礙者一起參與活動,努力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
上述答覆公布後,日本精神神經學會在厚生省的指示下,於1997年5月,終於制定出《性別認同障礙的診斷與治療規範》。
「治療」主要分為3個階段,分別是精神療法、賀爾蒙療法、手術療法,需要的治療程度也因人而異。若當事人接受精神療法即可獲得心靈上的平穩,就不需要接受其他療法。若否,則可以在專家謹慎的判斷下,接受賀爾蒙療法。賀爾蒙療法也不管用的話,同樣在專家的謹慎判斷下,可以接受最後的手術治療階段。
這一套規範成立後,性別重置手術在日本總算成為公認的醫療行為。
過去性別重置手術在國內並非正當醫療。曾有婦產科醫師未經充分診療就替當事人進行「變性手術」,違反了舊《優生保護法》,在1969年被東京地院判決有罪(史稱藍男孩事件,1970年最高法院也判決有罪),長久以來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實際上,這個判決有提到「性別重置手術的正當條件」,在那個年代是很劃時代的判決,但大多數的人只注意到「動手術被判有罪」的部分。
總而言之,醫療規範制定後,「性別認同障礙的治療」被視為正當醫療行為,當事人得以在國內接受治療。從這個角度來看,制定醫療規範有其重大意義,現在日本國內有5家醫院提供手術治療。
醫療規範剛成立的初期階段,在運用上比較沒那麼靈活,因此不按照醫療階段自行接受治療的人,會被視為「特例」,沒辦法接受性別重置手術。這種長期以來不受體制保護的案例也層出不窮。
2002年7月推出了修訂版本,初版醫療規範不適用的案例,也可以重新安排治療措施了。賀爾蒙療法的法定年齡也從20歲降到18歲;乳房切除從第三階段改到了第二階段,甚至在接受賀爾蒙療法前就能切除,變化不可謂不大。
2006年1月修訂的第三版,在下一章提到的《性別認同障礙者特別法》實施後,應用上更添了幾分靈活性。本來接受性別重置手術要經過倫理委員會的個別審查,現在這一條規定也廢除了。當事人有權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療法,所以目前採用「自助式醫療」,當事人在獲得充分資訊的前提下,能自由決定治療的方式或順序。
這段期間,醫療人員在第一線聆聽當事人需求,不遺餘力地改善醫療措施,這份功勞值得我們銘記在心。不過,從當事人角度來看,相關醫療還是有許多問題待改善。首先,「沒有他人認可,就不能進一步治療」的基本方針並沒有改變,而且缺乏專業醫師,尤其在東京近郊的初診當事人,幾乎掛不到專業醫師的精神療法。
再來,跨性別診所是由精神科、內科、整形外科、婦產科、泌尿科等科部組成,但各科間的協調機能稱不上完善。由於各部會缺乏合作,當事人很難在一天之內安排有效率的診療行程,有的人連要掛哪一科都不清楚,院方也沒有提供完善的診斷和治療說明。當事人必須自行安排一連串的看診計畫。

新加坡沒有我的容身之處,我決定去舊金山碰碰運氣。舊金山的互助團體在短短10天內就召開好幾次集會,這點令我嘆為觀止。可是,其中一個成員對我說了一段很具衝擊性的話,讓我放棄了去美國生活的念頭。
「這個城市不是我們的天堂,除非你變得很漂亮。在你變性成功前非常危險,你要做好被殺害的心理準備。」
我這才明白,原來那裡的跨性別者如此團結,就是要對抗強烈的偏見和迫害。在東京生活頂多被嘲笑而已,至少沒有性命之虞。於是,我決定回到日本生活。
從舊金山回國後,我在家中繭居將近2年。雖然日本國內已經有正式的醫療措施,我也參加了互助團體,但我一直沒有想清楚自己未來該怎麼做,也沒有一個明確的願景。半男不女的外貌連我自己都不適應了,我很在意旁人的眼光,完全不曉得該如何自處才好。人一缺乏自信,也就不敢外出找工作或租房子了。
看著積蓄一天比一天少,我也一天比一天焦躁。以前念書時打過工的一家二手錄影帶店店長邀我回去工作,大半夜一個人守著空曠的店鋪,旁邊只有大量的成人錄影帶相伴,真的會覺得自己很落魄潦倒。
我每天晝伏夜出,整天待在房裡,只有打工和參加互助團體的活動才會外出。家人也不曉得我白天到底在睡覺還是醒著,他們開始注意我的舉動,我連離開房間都要小心翼翼。
我很討厭這樣的自己。再這麼耗下去不是辦法,該如何活出自我呢?當我思考這個問題,發現自己討厭跟別人碰面的主因,在於我臉上有鬍子。我得把剩下的錢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不然我擔心自己會繼續沉淪,因此我決定嘗試永久除毛。
我首先嘗試的是電針除毛,這是把細微的電針插入毛囊中,用電力分解毛囊的作法。施術前得先用鑷子夾住鬍鬚,所以要先讓鬍鬚長出一定的長度。整個施術過程更是痛到眼淚直流,施術完皮膚還會紅腫發炎。考量到體毛的生長週期,要去掉所有鬍鬚少說得花上好幾年。我花了10萬元除毛,卻感受不到效果。為了消除一個煩惱,得耗費這麼大的心力,光想就快受不了了。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拿了雷射除毛的報導給我看。我前往報導上介紹的診所,施打一次要價1萬元,鬍鬚全部除毛要價50萬。我實在不想花這筆冤枉錢,於是打給醫療器材代理商,不斷尋找有同樣器材的醫療機構,最後找到一家施打一次100元。
我一進診療室就說自己想除去鬍子,醫生聽了頗為訝異。以施打一次100元計算,第一次除毛療程費用是1萬2,000元,第二次是8,000元,之後再花個幾百元補足療程,整個除毛療程就算結束了。沒有了鬍子,我跟別人面對面談話不再感到痛苦,對自己的臉也沒有不適應的感覺了。除毛確實讓我減輕了煩惱,我連腿毛也除掉了。
我思索其他可以改變的部位,尋找具體的改變方法,用實際行動來獲得成果,結果也令我滿意。這樣的嘗試也幫助我擺脫了繭居的生活。
我的外貌愈接近女性,走在街上也愈多人發給我女性才會拿到的廣告面紙。從男性轉變成女性的跨性別者,會計算自己拿到多少電話交友俱樂部的面紙,這是客觀了解自己外貌的方法之一。
我們也會利用電話交友俱樂部做發聲練習。利用電話交友俱樂部閒聊,彼此不用揭露自己的隱私,從頭到尾都沒被對方發現自己是男性的話,就代表自己的「女性嗓音」合格了。跟第三性閒聊的電話俱樂部也很受歡迎,我們可以說出自己真正的心聲,就好像其他圈子替我們開了另外一扇窗。反正遇到討厭的人直接掛斷電話就好,我抱著這種輕鬆的心情嘗試了幾次,遇到一個很有好感的對象。那個人認真聆聽我的煩惱,也給我很大的鼓勵。我們的年齡相近,也很有話聊。有一次,我們說好隔天要出來約會,電話一掛斷我就驚覺自己說錯話了。
那個人知道我的問題,但他喜歡的還是我「女性化」的部分吧。然而,我沒有適合穿去約會的洋裝,也沒替自己化過妝。萬一他對我失望,受傷的會是我自己。
我打電話給其中一位女性朋友商量,她二話不說就答應要幫我。我去她家裡學習實際的化妝技巧,還借了一套洋裝。隔天我到相約碰面的地點,那人驚訝地望著我,他以為自己被騙了,因為我看起來跟一般女性沒兩樣。
有了美妝和女性的服飾,我在別人眼中就是一個女性,而我自己也不覺得奇怪,這讓我意外「發現」了不一樣的自己。
那天過後,我去參加互助團體活動時也會打扮成女性的外貌。話雖如此,我在鄰居眼中是「上川家的次子」,所以出門時都穿T恤和牛仔褲,行為舉止也像個「頭髮比較長的男性」。我會跑到鄰鎮的車站女廁換裝,先用手撥開頭髮,畫一下口紅,看起來就像個化淡妝的女性了。到女廁換好女裝後,再對著鏡子仔細梳妝打扮,充滿女人味的女性便大功告成。回家時就把同樣的步驟反過來做一遍,先到廁所換回T恤、牛仔褲,再去無人的巷弄擦掉臉上的妝,變回「頭髮比較長的男性」後才敢回家。
在一人分飾兩角的生活中,我深刻體認到「女性」那一面,才是我的重心。
打扮成女性的時間愈長,我對自己的女性身分就愈有認同感。不過,我不認為自己應該要裝得很有「女人味」。
我重視的是「活出自我」,而不是符合社會「觀感」。我嚮往的外在條件:包括體型、聲音、服飾、言行舉止、談話內容⋯⋯只是剛好符合社會上的「女性」範疇罷了。旁人把我當成一個女性,我發現自己也能坦然接受這件事。那種契合的感覺,讓我「女性」的那一面更加安定。

然而,我很不習慣自己有喉結。過去我還把自己當成男性時,也不能忍受喉結的存在。這跟理性無關,純粹是情感上無法接受。萬一喉結害我的生理性別曝光,那我以往的努力就付諸東流了。
隨著「女性」的自我逐漸安定,我仔細思考手術能改變的程度以及相關的風險。我到東京、橫濱、京都、大阪會見了4名整形外科醫師,請教他們的意見。我問他們喉結最多能削掉多少?削掉又有什麼風險?每個醫師的答覆都不一樣。我認識的朋友也沒人削過喉結,煩惱了半年後,決定找京都的醫師動手術。
我希望節省手術費用,醫師同意減少2萬塊,手術只用局部麻醉進行。可是,手術一開始我就後悔了。雖然切開的創口才8毫米,但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被切開喉嚨非常恐怖。我盡量不讓自己發抖,以免醫師動刀出什麼差錯。護理師也看出我很害怕,在40分鐘的手術過程中一直握著我的手,這算是唯一的救贖。
那天,手術推遲了一段時間才進行。醫師動刀時有些急躁,據說之後還有幾臺手術要開。喉結削太多聲音會變低,手術時患者要一邊發出聲音,測試聲音的變化。護理師提醒醫師不能再削下去,醫師卻說再削一點點就好。結果醫師加重削骨的力道,手上的鑿子瞬間打滑。
當下我真的嚇到面無血色。醫師叫我試著發出聲音,我的聲音變得詭異又低沉,或許已經無法挽回了吧⋯⋯我難過得想哭,手術也到此結束了。
等我搭乘新幹線回到東京時,喉嚨完全發不出聲音了。
過了兩週,我的聲音並沒有恢復,講話聲音跟蚊子一樣小。我悵然若失⋯⋯失去聲音後該怎麼活下去?幸好某個擔任音樂教師的朋友替我做發聲練習,我花了快半年,總算恢復到長時間說話也不會沙啞的程度。不過我再也沒辦法像以前那樣,輕鬆唱出女性歌手的音域了。
手術無絕對,有得必有失。這點我非常清楚,但實際失去寶貴的聲音還是帶給我莫大的打擊。當然,我的際遇算得上不幸中的大幸吧,好歹我恢復了很接近「女性」的聲音。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思考,究竟該不該動性別重置手術。從個人感官上來看,我對自己的性器官很不適應,真的要我選擇其中一方,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女性的性器官。畢竟在日常生活中如廁盥洗,我們一定會注意到自己的性器形狀。有了女性的性器官,我一定可以表現得更加自然,夜晚入睡時也能跟自己心愛的人坦誠相見。
可是,精神科醫師問我要不要動手術時,我沒法給出十分篤定的答覆。
我告訴醫師,我確實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自在,擁有女性性器官對我來說才叫正常。但手術有多大的風險?成效又有多大?在訊息不明確的情況下,我不想動刀。
精神科醫師斷定我適合動手術,醫院的治療團隊經過討論後,也同意我動手術。然而,我還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思考。
性別重置手術沒辦法形塑出完美的女性性器官,只是外觀和機能相近罷了,不見得會有滿意的結果。而且可能影響排泄功能,造成性方面的知覺受損。我動過喉結的手術,心知不能光靠期望做決定,要詳加分析風險和手術極限才行。
另一個原因是,變性在社會制度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當時我以OL的身分從事非正職工作,沒辦法跟公司請長假。除此之外,萬一日後法律允許我們改變性別,進行非正式的手術或去海外動刀,可能會影響個人權益,我不希望留下這樣的麻煩。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