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攝影工作坊──在地影像紮根計畫

班雅明認為,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突破爭議,讓攝影術更有進展。他認為其中有個深具意義的現象是,一般辯論總是侷限在和「攝影作為藝術」相關的美學上,但是相反的,像「藝術作為攝影(或藝術以攝影形式呈現)這個更確切具有社會意涵的問題卻甚少受到注目。」換言之班雅明認為,攝影術不需要再去爭論自己是不是藝術,而是要改變策略、面對社會,使自己具備社會意義,才能更上層樓。班雅明以廣告攝影為例,他認為廣告這種攝影無法掌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攝影的目的是為了把拍攝的題材商品化,而其對立面則是面具的摘除或建構(construction)。因此班雅明指出,照片必須要能進行某種建構,而超現實主義的成就即是為這種攝影開路。班雅明舉的例子就是阿特傑(Eugène Atget)。
攝影是不是藝術這個問題在台灣總是鄉愿地被討論與歸結,很少人會說攝影不是藝術,說了彷彿是一種政治不正確。攝影在台灣藝術界眼中究竟是不是藝術,答案看起來很明顯,而攝影者如何看待攝影與藝術才是問題。
若將紀實攝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的形式,在當代似乎沒有什麼不能,也早已有很多人這麼做。只是,紀實攝影所拍攝的題材有時會涉及某些弱勢族群,這就會產生一些疑慮。
創作者想要以弱勢為題材並以紀實的形式進行「藝術創作」,只要被攝者願意被拍、兩情相悅之下,自由社會裡好像找不出什麼可以說嘴之處。創作者藉此以藝術創作之名避開了對題材進行批判反思的大傘。
此時我不禁想問,這種所謂的藝術創作又是什麼意涵?若藝術是作為人類心靈活動的具體呈現,那麼這樣的藝術作品又想呈現什麼心靈活動?
此外,也有許多攝影者在以弱勢(或相對弱勢)為題材時,抱著某種人道關懷或社會正義之名進入田野,但最後呈現作品時卻又說不上什麼人道、什麼正義,而是以藝術做結。似乎是想要以紀實為形式,就非得以弱勢為對象;或者,既要擁抱人道主義,又要擁抱某種古典的藝術意涵,但又不能同時承認二者。
直白地說就是,若要找個弱勢對象來進行藝術創作,為何不能大方承認?承認了,就去面對可能帶來的質問,這是藝術創作者在呈現作品時難以逃避的事。
舉一個極端一點的例子。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攝影展座談會,那是幾位攝影記者以社會新聞現場所拍攝的照片為作品,將照片集結、整理,並加上一些簡單的裝置與音效(例如無線電、消防隊與救護車的通話聲),嘗試以某種「藝術」的形式來呈現。與談中我透露了我的疑慮,這些照片在拍攝時是因為攝影者具備了記者的身分(與權力),所以能拍攝到事件的現場、傷患甚至屍體。但是攝影者最後卻把這些照片放大、直矗矗地展現出來,成為一種攝影「作品」。
儘管他可以找尋某些藝術理論來包裝,但是那些被拍的傷者、死者怎會知道這個記者在幾年後把照片公開展示在非新聞用途的攝影展上?這樣的藝術又是什麼心靈活動?當攝影者不斷的挪用看似前衛的藝術表現形式作為證明自身是藝術的方法時,與畫意攝影的企圖並無二致,這也僅是古典的方法,並無前衛之處。
從《攝影小史》來看,班雅明認為藝術以攝影的形式呈現才是這項技術的重要特質。如此一來,不僅不用再去爭議攝影是不是藝術,同時也能展現出攝影所具備的社會功能。這也是展開紀實攝影更多可能性的路徑。正因為藝術表現作為紀實攝影的形式,所以紀實攝影既可以維持其紀實精神以及在不同時代社會所產生的可能形式,同時也維持了紀實攝影的社會意義與功能。
何經泰在拍攝都市底層、白色檔案等議題之前,並不是先拍了一堆照片才開始了解這些故事的脈絡以及未來該如何包裝呈現,而是對這些議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謹慎地思考拍攝手法與表現形式。沈昭良的《Stage》並不是先拍再說,而是長時間地進行田野調查,才能醞釀出獨特的表現手法。他們的作品既是紀實,也是一種藝術表現。
攝影家何經泰4月前來《報導者》分享他創作生涯的經驗與作品。何經泰雖然年屆60,但是思想絲毫不落後於年輕人。他採取了非常開放的態度與觀念看待攝影藝術。在分享過後的Q&A時間,《報導者》攝影主任余志偉與何經泰的互動中,提到了時下青年在挑選專題時,經常還是挑選老掉牙的社會弱勢議題,諸如街友、移民移工、身心障礙者、迫遷⋯⋯等議題,而這些議題正也是早期報導攝影經常關注的老現象。
然而,難道這個時代沒有這個時代特有的壓迫與困境嗎?這樣的現象確實也從工作坊學員所提案的題材中,以及我在教學現場所遇到的狀況獲得相同的觀察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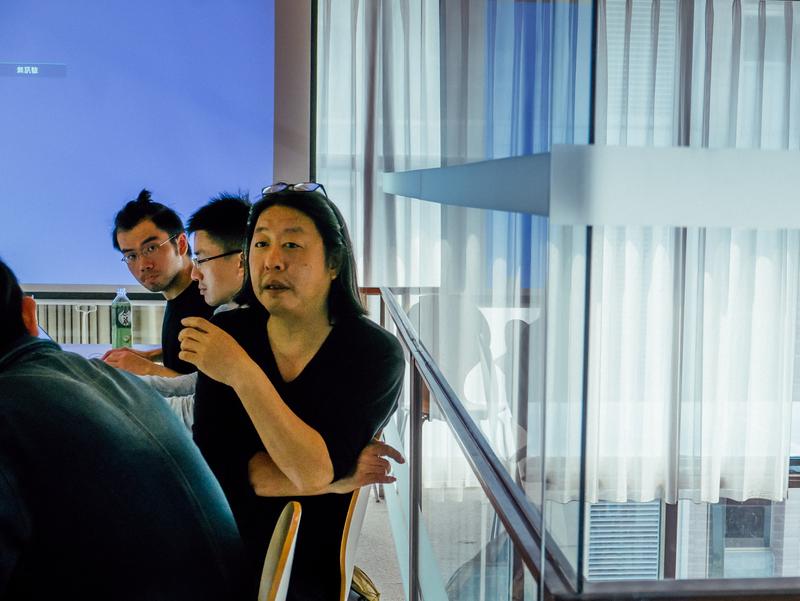
我經常看到學生的提案不外乎是訴諸溫情的傳統/現代文化衝突、街友、移工、迫遷⋯⋯等議題,而且同學總是難以搔到癢處地看待這些問題,而不去探究、觸碰結構性的問題。
舉例而言,我不只一次看到學生想以街友為題,而且企劃書總是寫著,「希望透過拍攝來了解街友,讓大眾知道街友與我們沒什麼不同,不應該對他們有所歧視」。
我對這段文字非常有意見。
首先,同學希望透過拍攝來了解街友,而不是先了解街友再進行拍攝;其次,同學在還不了解街友的情況下就預設了街友與我們沒什麼不同,如此便迴避了探究結構性的問題這項功課;第三,他們直接了當給的結論就是不應該有歧視,而不是去探究歧視如何產生。如此一來,他們便可以放心地去找街友、找NGO組織,把自己良善的立意告知對方,認為這樣的題目執行起來既有意義又有賣點。
這種現象,我認為符合郭力昕所指的濫情文化、溫情主義。而且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台灣的報導攝影文化,也普遍存在於紀錄片文化。創作者經常只談溫情、人情,而不探究結構,他們時常認為,溫情是台灣社會的特徵,感性是藝術表現的一種方式,藝術表現沒有一定要去思考硬梆梆的結構性問題。
對我而言,這種看待紀實的態度某程度是用藝術用來推辭紀實的社會功能(說硬一點就是責任),並且難逃消費弱勢的嫌疑。再以學生的作業企劃書為例,他們總是寫著「街友與我們沒甚麼不同」,但我總會反問同學,「你會去台北車站地下停車場、艋舺公園睡覺嗎?你會把所有的家當隨身帶著嗎?如果不會,那又怎麼會相同?街友明明就與大多數的人不同」。再者,要呼籲大眾不應歧視街友,卻不問街友如何產生、歧視如何發生,這就是忽略結構問題(無論是刻意還是非刻意)、去脈絡化。
若要說這是一種藝術表現,那絕對不是紀實攝影的精神,紀實在這裡,充其量是形式而已。這樣,與將新聞照片放大沖洗,外加一些裝置擺設而宣稱這是一種攝影展又有何異?
這並非說當代攝影師不應該拍這些題材,而是說,有更多貼近當代青年攝影現實感的社會問題沒有被注意到,青年人更應該注意到這些議題。
這麼一來,就可以回應一名學員所說的,好的題材都被拍光了,他不知道該如何找題材。我也曾經回應過學生,世代正義在2、30年前很少被提到,但是在當代卻是個大問題。安樂死、尊嚴死這件事在過去很少被正視,但是在當代卻經常在媒體上討論,怎麼很少人做這些攝影議題?此外,在學習與訓練的過程中,這是自我要求絕佳的機會,退休於政大新聞系的攝影老師林少岩過去常要求學生作業不准以老人、小孩、狗、廟會、荷花⋯⋯洋洋灑灑七、八項為題。這種方式的目的是強迫學生去觀察多數人沒察覺到的問題,但我還要再加上一項,不止是察覺問題,還要探究問題的成因,而這正是作為一個報導者應有的本領。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