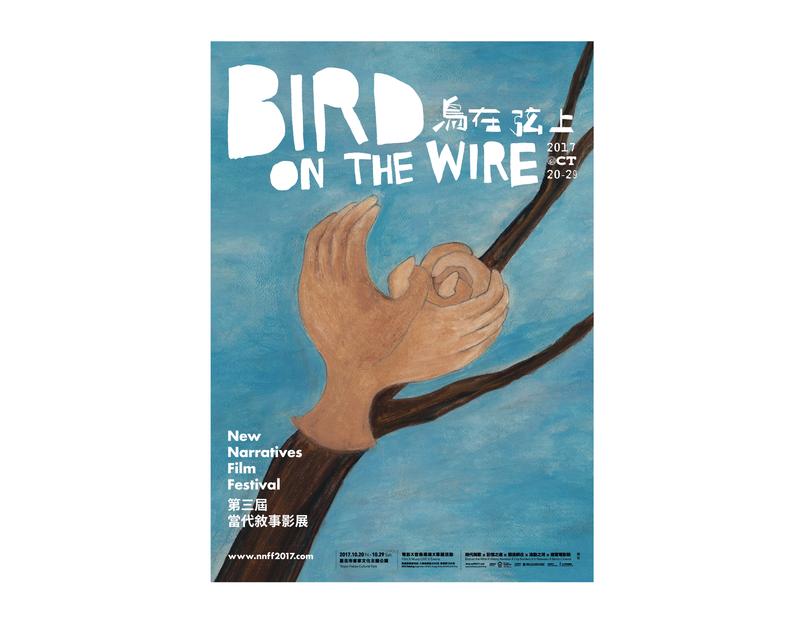1953年柬埔寨脫離法國獨立時,舉國歡騰,當時的 Sokha 穿著高中制服,在課堂與同學打鬧,在校園裡與朋友追跑玩耍,青春熱血,沈浸在重獲自由的氛圍。
然而緊接著越戰開打,美軍戰機在柬埔寨、寮國、越南邊境展開秘密戰爭,光在柬埔寨即投下約 270 萬頓的武器,是美軍二戰期間在日本投下的兩倍以上,戰火波及無辜柬埔寨百姓,無情炸毀柬埔寨多處村莊,死傷無數,使柬埔寨再次陷入黑暗恐懼。
1975 年赤柬軍隊攻入金邊,人民以為越戰帶來的黑暗可以就此結束,卻不知是下一段恐怖的開始──柬埔寨進入赤柬時期(Khmer Rouge,亦稱紅色高棉)。赤柬軍隊將人民下放至農村集體勞動,並展開大舉屠殺,兩百萬人口在三年內被殺害,恐怖政權籠罩全國。 Sokha 當時被帶著惡魔面具的赤柬軍官包圍,她被迫與家人拆散,身旁朋友則在哭喊中被活活虐待致死。
赤柬過後,國內仍內戰不止, Sokha雖幸運地倖存,但絕望恐懼還在,創傷還留在Sokha心裡,她在希望與夢魘間無止盡的糾纏拉扯。最後 Sokha 被家人帶往泰柬邊境的難民營,她在難民營裡遇上了一位藝術老師,才因此改變了她的命運。她選擇戰勝恐懼,並回到柬埔寨,以藝術治癒更多的孩子,領他們走出傷痛與貧窮的輪迴。
這是柬埔寨暹粒馬戲團「Phare, The Cambodia Circus」 最經典的戲碼《Sokha》,劇本描述著一位女孩Sokha在經歷赤柬之後,從復原自己到決心回鄉治癒更多孩童的創傷。
《Sokha》整場的音樂、燈光、營造的氛圍都隨著劇情高潮迭起,並融入許多暗喻與意象,加上以「現場作畫」當作轉場,更將整齣戲的張力拉至最高點。畫家在令人戰慄的節奏下,將祥和的村莊魯莽地刷黑,蓋上象徵美軍投下的多枚飛彈;畫家也將一尊畫得精緻的佛像放肆摧毀,畫上死亡的骷顱頭,代表著赤柬屠殺下的慘絕人寰,更暗示宗教信仰、文化也被一夜掃盡。表演者不只融入精準高難度的特技、雜耍、疊羅漢、空中翻滾,在劇情主軸下,更同時以生動的表情肢體詮釋每一分情緒,表達當時人民在獨立後的喜悅、在內戰期間的恐懼、焦慮與不安,以及統治者的張狂、詭譎、噁心與壓迫,都在他們五官的細微抽動、肌肉的瞬間使力、額頭的滿佈汗珠,呈現地淋漓盡致。
Phare馬戲團的行銷總監Craig Dodge在受訪時表示:「 Phare不是隨意展現雜技的傳統馬戲團,最獨特的是主軸皆以柬埔寨文化和歷史作為故事線,例如戰爭、創傷、歧視、貧窮、文化等,故事靈感也皆來自表演者及老師們的真實經歷,他們都屬於這個故事的一部分。」
自2013年以來,來到柬埔寨暹粒市的觀光客,除了必訪的世界遺產吳哥窟,多了一樣不能錯過的選擇,便是在旅遊資訊Tripadvisor上表演類排名第一的Phare馬戲團。每晚8點準時開場,帳篷內幾乎場場爆滿,旺季甚至一票難求,他們在柬埔寨成功打造了全新的表演體驗──「沒有馴獸、小丑的馬戲團」。
他們糅合劇場、音樂、特技、雜耍、舞蹈、現場作畫等元素,生動地呈現關於柬埔寨自己人的故事,劇本像是《Khmer Metal》,談柬埔寨的酒吧文化,糅合搖滾樂、流行元素甚至是同性戀題材;《Influence》則傳達受法國殖民統治所受的文化衝擊和影響。Phare馬戲團所有的表演者皆畢業於馬德望(Battambang)的非營利藝術學院Phare Ponleu Selpak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PPSA),是在赤柬後,由9位生活在泰柬邊境難民營的柬埔寨青年所創立。

1975到1979年赤柬時期,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殺害,赤柬軍隊進入金邊,趕盡殺絕,幾乎所有人被下放至農村集體勞作,90%的知識份子皆被殺害。即使赤柬結束,內戰仍未止歇,數萬名孤兒在街上乞討,許多柬埔寨人因此逃到泰柬邊境的難民營。
「我不清楚確切發生什麼事,只知道赤柬結束後,我爺爺帶著我逃往難民營,一開始被送到軍營裡的兒童中心,但爺爺被派往前線支援後就再也沒回來了,後來被送到其中的孤兒院,自此後,那裡就是我的童年。所以自我有意識以來,我是在孤兒院獨自長大到22歲,儘管我不是孤兒。 」(他一直知道家人還四散各地,1993年從泰柬邊境回國後,與家人團聚。)
「我當時真的好孤單。」
除此之外,起初難民營裡沒有學校,僅有短期的軍隊訓練課程,他因此從小學習的是武術與體操,長大後就是當軍人。提起在孤兒院的生活條件,他不斷地搖頭:「情況真的很糟。」他形容著孤兒院潮濕悶熱的氣味,封閉且令人窒息的空間,約 50位孤兒住在一間教室裡。加上難民營管制森嚴,儘管有20萬人居住在同個難民營,仍像個無牆的監獄,哪都不能去,當時柬埔寨仍處在內戰期間,赤柬政權在邊境的叢林裡組織游擊軍隊,出去隨時都有生命危險。「那裡是牢籠,但外圍更隨時有衝突和戰火。當牢籠比外頭安全的時候,我感謝至少我是被困在裡面。」
直到1986年,聯合國相關單位開始進駐後,情況才稍有好轉。當時一位法國的社會工作者Veronique Decrop,到Det所待的孤兒中心帶藝術工作坊,著重於「藝術治療」。她透過繪畫和水彩,讓孩童練習表達內在情緒,緩緩治癒他們的創傷。
當時Det不到20歲,已無法回想哪幅畫是被啟發的關鍵。但他回憶道:「Ms. Veronique付出非常多心力帶領我們,漸進地把我們心中最底層的創傷拉到畫裡。最重要的是,老師讓我們相信有一天我們會回到柬埔寨。」講完這段話後他特別激動,停頓幾秒後才又接著說:「我們9個夥伴和老師一起約定好,回去(柬埔寨)後要成立藝術專案計畫。當時我們甚至在泰柬邊境舉辦一場大型展覽,並拍攝一部微電影,募得第一筆款項建立藝術教室。」
1992 年,在聯合國的協助下,近20萬大批難民被分配回柬埔寨各個省份,Det和家人總算也再次回到故鄉──馬德望。難民剛從泰柬邊境回歸後,迎面而來的是沒有家可回或是父母早已不在。滿街的孤兒和受暴力虐待的兒童,這些孩子都被迫在街上賣蔬菜水果,幫路人擦鞋,或是僅能乞討或搶劫。除此之外,仍有三分之一到 二分之一的居民都還活在赤柬留下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裡。因此他們9位在難民營一起長大的孩子,決心在自己的家鄉,以藝術重建孩子們的未來。
1994年9位在難民營長大的孩子回到馬德望後,決定一起創立藝術學校PPSA,在柬語裡是「藝術光輝」之意,他們讓馬德望的孩子們可以免費學習藝術,致力以藝術治癒心靈。
一開始,僅有一間簡陋的木屋作為教室,提供基礎繪畫課程,然而孩子長期受暴或迫害,又缺乏基礎教育,上課期間時常爆發衝突,因此雖是繪畫課,老師們著墨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當時不是什麼創辦人,僅是一位社會工作者,花最多的時間是去了解每個孩子,讓他們理解暴力無法解決問題。一方面也同時了解孩子的家庭狀況,及和父母溝通,說服他們讓孩子來這裡學習。」他解釋最一開始,自己比較像是協助心理輔導的社工。
1994到1998年是他們最辛苦的一段時間,這份理想還無法支付每位創辦人的薪水,僅能補貼伙食費,所以有4位隨家庭離開到金邊或泰國工作,法國老師Veronique Decrop也在兩年後回到她的國家。Det說:「我當時也很想要離開,但這些孩子總讓我想到我在孤兒院的日子,我知道孤單是什麼滋味,這過程同時也在治癒我的傷,是他們讓我堅持到現在。 」
之後開始有政府教育局(Ministry of Education Cambodia )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加入協助計畫,學校發展終於漸趨穩定。他們首先提供的是馬德望貧困孩童「完全免費」的基礎教育,並提供保險、膳食、教材甚至是住宿。此外,他們更設立獎學金制度,若學生參與長期課程,每年就學可獲850美元,高年級可獲1,200美元。
這筆「獎學金」對許多偏鄉家庭每年賺幾百美金而言,是相當可觀的收入,也因此比起輟學幫忙家務,到PPSA藝術學校上課反而可以補貼更多家用。是這個原因讓家人開始願意讓孩子來這「免費學」。而原先家人認為「藝術不能當飯吃」,但在Phare成功讓學生們透過藝術生活,還能照顧家人後,這「可預見的未來」讓Phare在社區裡慢慢累積起聲望。Det說:「讓父母願意送孩子來,再讓孩子願意把這當作家,並找到一生志業。」
2013年PPSA成立了Phare馬戲團,2016成立Phare Creative Studio(創意工作室),讓學生畢業後能直接將所學轉成職業。自2013至今,每年參加PPSA藝術課程的學生超過1,200位,約70位學生成為職業藝術家,有的在街頭彈吉他演唱、有的開自己的藝廊,在金邊、馬德望、暹粒觀光區都有他們的影子。
這23年以來,孩童來自赤貧家庭的比例,已從90%降至30% ,PPSA現在並不強調收孤兒或弱勢學生,而是廣開大門讓馬德望的適齡者接觸藝術管道。PPSA在馬德望,已成為孩子重要的藝術天堂,僧侶們也都搶著來上課。他們現在做的,比止傷更積極,他們透過藝術、繪畫、插圖、設計、動畫等連結世代間的記憶,讓下一代正視柬埔寨過去的歷史,並能延續脈絡,去拆解現今仍存在的社會問題。
例如Phare的視覺與應用藝術學院 (Visual & Applied Arts School )帶領學生製作動畫,講述非法移工到泰國漁船上工作的經歷,例如設計倡議海報,揭露柬埔寨嚴重的男性酗酒和家庭暴力問題,以及女性受暴後能採取的法律途徑。例如透過影像,討論緊鄰洞里薩湖的水上村莊,面臨的湖水污染問題。又採訪當日,設計學院三年級的學生,19歲的Hai Sopheak,興奮地解釋著他的畢業作品,他以嘲諷的手法談論關於「柬埔寨的交通失序」。
歷經過內戰與逃亡的Det,在校園裡受訪時不斷有學生上前來與他擁抱Det告訴我:「所有在PPSA的表演者和藝術家,都是我最想溝通的對象。」
《Sokha》就是他最經典的案例。Det 自2001年到法國修讀馬戲團教育學(Circus Pedagogy),並接觸劇本寫作,回國後將其自身經歷改編後親自編導,並由柬埔寨90後演出他們版本的赤柬世代。「我先和他們一次次分享我的親身經歷,並找來許多位經歷赤柬的倖存者和學生們分享,我們佐引考證資料、紀錄片、照片等等。赤柬時我僅是3歲嬰兒,但我希望《Sokha》不只是我個人的故事,而是能記錄這代人共同的記憶,讓生還者們能好好地說。」

這些表演者,皆約20歲出頭,沒有經歷過那段黑暗歲月,卻要背起演好這段歷史的責任。Det花了6個月完成劇本,近一年時間排演練習,為了讓劇裡的每個細節活出來,好幾次排演氣氛相當沈重,學生幾度情緒崩潰。但最後完成時,學生和他說:「能作為這齣戲的演員,是我們一輩子的驕傲榮幸。」
而他最希望透過這齣戲傳達給下一代的訊息是:「即使離赤柬已40年,但人民最深沈的一塊,仍然沒有和平。」
柬埔寨30多年來,始終披著表面的和平,卻無法真正走出貧窮與創傷,約半數倖存者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後群,極端的家庭和性別暴力仍每日上演;而政府貪污腐敗,忽視人權問題:砍伐林木、土地掠奪、饑餓貧窮、人口販運、毒品走私等依然未有大幅改善,政府只顧自身利益,延伸至官員收賄和知識份子的低薪生態,使得「無罪(impunity)文化」在社會深耕,老師收學生「補習費」,醫生拿病人「禮金」,警察向受暴婦女索「遮口費」等仍是常態,只要與當權者有關係,這些惡行都不會被處罰,惡行者也不必付出代價。災難後的重建未竟,惡性循環至今,正義難伸。
1993年聯合國耗資30億美元,天真地在柬埔寨買了一場「民主夢」。柬埔寨裹著民主的外衣,2013年全國大選,金邊街上仍有槍戰,人權鬥士與社會運動者仍難逃政府羅網;2018年7月的大選前夕,已有8間獨立電台被迫關閉,柬埔寨唯二英文報紙中的一間被強制停業,反對黨直接被最高法院解散,人權中心也即將宣告關門大吉。
威權統治之下,人民心中仍普遍存在著深沉的恐懼,赤柬的遺毒,流在百姓血液裡,「害怕改變、害怕變動」成了當權者的把柄,他們擒著人民的傷口,以「穩定」為口號暗示著人民「想改變」的下場,各個為求一己生存,放任政府的暴行40年之久。
政府的失能,人民啞忍,並將球丟給國內至少3,000個以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也因此「長期仰賴國際援助,不覺自己能夠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成了柬埔寨自赤柬以來的致命傷。
然而這些時代記憶,包括赤柬時期兩百萬人口如何被自己領導人殺害,以及現任政府多年以來踐踏的人權,赤柬後代幾乎被蒙在歷史的空白裡。回顧赤柬30年後,直至2009 年正規教育的歷史課本裡, 才開始解釋「赤柬」和「波布(Pol Pot)政權」等歷史紀錄,這段歷史也僅於 9 到 12 年級的課程中提及,柬埔寨至今仍有高達70%學生無法完成9年級 ,意指到今日,這群人可能都沒有機會透過學校教育碰觸赤柬的歷史脈絡。諷刺地是,每年上百萬來柬的觀光客可能都比他們自己人還要清楚。
「這是我想持續和下一代用藝術溝通的原因,是他們能決定柬埔寨將往哪裡去。」Det 語重心長地重複這段話。
「我還是相信會改變,只是要等,不是現在。」一位畢業於暹粒建明大學(Build Bright University,BBU)的大學生告訴我。在暹粒戰爭博物館(War museum)的當地導覽員則說:「我們真的經不起再一次的戰爭,但我們沒有放棄改變,我們還有選舉。」
他們自1993年開始懂何謂選舉,當年90%的人民上街投票,結果是被政府背叛;他們仍有民主該有的框架,有三權分立有國民議會,只是已被執政黨扭曲,獨掌權力。在這裡政治冷漠不是選擇,是一種必須,即使生活不斷受政治的擺盪影響,仍被逼著繼續過「正常」生活。
然而他們並沒有真的放棄。在意公民參與的年輕族群漸漸自城市裡抬頭,枝椏在緩緩延伸,午餐時間他們聽廣播報新聞;在角落裡談論政治;在市區舉辦工作坊、展覽和講座;在金邊仍有小規模的抗爭示威活動。他們爭取工廠勞工權益、反抗土地掠奪等,甚至在2013年大選過後,50萬人在反對黨的帶領下,抗議選舉不公,要求再次選舉。相較國家權力下,這些或許仍舊動搖不了上位者,但他們還是要關心,仍然得把「改變」放在心中。
柬埔寨黑暗時期還沒有真的走過,年輕世代要改變,沒經歷過那段歲月,也不能直接跳過。Det口中的「仍沒有和平」,是即使他栽下自己的半輩子也還未能看見。當今的馬德望藝術學校PPSA,帶著年輕人去觸碰柬埔寨的歷史傷口,以繪畫、設計、戲劇、音樂、舞蹈與馬戲等更多元的軟性媒介,讓赤柬後世代能在和平真正來臨前,「先記得自己的歷史,關心自己的問題」。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