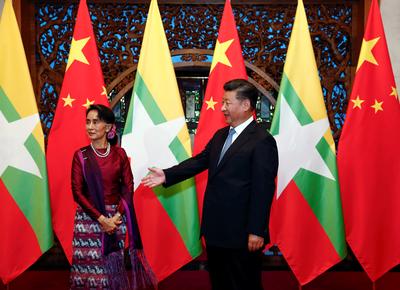「我們的工作並不是幫緬甸宣傳,而是報導真相」

在夜晚遭到便衣情治人員跟蹤,並且在網路上不斷收到陌生人的死亡威脅訊息之後,普立茲新聞獎得主艾斯特.圖珊(Esther Htusan)離開了出生長大的緬甸。但是面對緬甸政府與翁山蘇姬支持者的撻伐與抹黑,不得不離開緬甸的圖珊仍沒有放下自己選擇記者一職的初衷:「身為一位記者,我們的工作並不是幫緬甸宣傳,而是報導真相。」
I will not be silenced(我不會被噤聲)。
2015年,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以壓倒性勝利擊敗軍政府,2016年政黨輪替後,緬甸正式進入民選政府時代,也積極向世界開放。但讓緬甸人和他國都感意外的是,緬甸的民主與自由不進反退。甚至在2017年,緬甸軍隊大規模迫害羅興亞人,並造成70萬羅興亞人逃亡,淪為難民。
原本對緬甸民主化抱著希望的圖珊發現,這個政府跟以往軍政府的行為,其實很像。
圖珊來自緬甸克欽邦,在近7成人口都是緬族的國家裡,克欽族與羅興亞人一樣,都是人口佔不到2%的少數族裔。圖珊從小就知道身為少數者在緬甸不公平待遇的命運,於是在26歲進入《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後,她關注的議題都與人權有關,她說:「身為被歧視的一員,我深知人權的重要。」
像是在2015年,圖珊與《美聯社》同事一起調查東南亞漁工遭到奴隸般的對待。此報導獲得了2016年普立茲公共服務獎的殊榮,也讓她成為緬甸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記者。
圖珊也將調查報導的精神用在揭開緬甸軍對於羅興亞人的迫害上。從2016年開始,她頻繁前往羅興亞人居住的若開邦進行調查、探訪,將羅興亞人被集中在物資匱乏的難民營內的狀況報導出來。並且在2017年羅興亞人遭迫害加劇引起國際關注時,她的報導進一步揭露了政府與極端分子合作,聯手掩蓋迫害羅興亞人的事實。這些報導也讓她成為政府的眼中釘。政府除了長時間派遣情治人員跟監,也將她抹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讓她必須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最後在2017年12月,她不得不離開了故鄉。
在她離開緬甸的這段時間裡,她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尼曼獎學金的支持下學習,也多次前往泰國、中國等緬甸周邊國家,採訪克欽族婦女被販賣至中國的相關報導。
《報導者》特別專訪了圖珊,以她的親身經歷來讓讀者了解,緬甸正在經歷惡化的種族衝突,而新聞工作者在其中揭露真相所要遭遇的危險與黑暗。以下專訪以問答形式呈現。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2016年妳跟《美聯社》團隊製作的「血汗海鮮」(Seafood from Slaves)議題,以及最近年做的羅興亞人議題都是跟人權有關,為什麼會選這些議題報導?
圖珊(以下簡稱圖):選擇人權這個議題的原因,跟我從小長大的家鄉克欽邦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克欽邦長期處於內戰狀態,緬甸政府軍與當地克欽族的軍隊持續對抗。我的父母在1960年代因戰爭必須逃難,甚至在今天,那裡仍有零星戰火。其實緬甸的法律與政策長期對少數民族不公平,甚至侵害我們的人權。身為一位被「合法歧視」的少數族裔,在人權遭到合法迫害的環境中長大,我自然會想要為這個議題發聲。
我年輕的時候雖然有這樣的想法,但一直不知道該怎麼做,尤其是在軍政府時期,這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在2010年離開克欽邦來到仰光,那段時間我也曾在國內一家現在已沒有營運、名叫《政治》(Politic)的週刊工作。2012年的時候,軍政府開始開放、轉型,言論自由相關法規開始鬆綁。雖然政治上開始不再像以往這麼受到政府嚴格控管,但是緬甸的記者仍然相當謹慎,不會寫太多有關於政治的內容,不批評政府、不批評軍隊等等。在地方媒體工作的時候,我一直感覺被限制。
2013年加入《美聯社》之後,我去了羅興亞人居住的若開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親眼目睹集中營。就算我是一個在戰火中出生的克欽族人,但是看到緬甸政府把數十萬羅興亞人丟到集中營裡,那種慘不忍睹的畫面讓我感到非常驚訝,我完全沒有想像過這樣的事情居然是發生在我所生活的國家裡。
克欽族或是羅興亞人等少數民族所受到的待遇,讓我報導的方向都是落在緬甸的人權這個範圍裡。
報:在緬甸從事記者這個工作並不容易,尤其是專注採訪人權議題更是困難重重。這樣高度敏感的工作是否對妳的家人有產生影響?
圖:小時候,母親曾經要我不要在家裡以外的地方討論政治,因為怕被抓。當他們知道我要當記者時,他們跟我說這麼做等於是選擇去坐牢,希望我去做別的工作。但我只是想要把緬甸發生的事情說出來,把故事講好,所以我堅持了自己的選擇。
在2016年《血汗海鮮》的調查報導得獎後,有上百位緬甸漁工因為報導得以離開受迫害的地方,回到緬甸跟家人團聚。從那時候開始,我的家人才知道新聞與記者所捍衛的價值,他們變得非常支持我。
雖然如此,為了家人的安全,住在仰光的我一直刻意跟仍住在克欽邦的家人保持距離。在克欽邦的家中,你看不到一張有我在裡面的照片,所有跟我有關的東西也都被他們藏起來。為了把我跟他們的關聯降到最低,他們只好假裝沒有我這個女兒一樣,這樣軍方的人也比較不會每天去問他們一大堆問題。這是好的,因為我也不希望家人受到牽連。
報:在緬甸採訪人權相關的敏感議題時,政府是怎麼樣讓妳感受到壓力?
圖:得獎之後有愈來愈多人開始認識我,政府給我的壓力也漸漸明顯。當然這不只是只有我,其他記者都也有遇過這樣的事情。通常就是軍方的情治人員會穿便衣跟著,記錄記者做了些什麼、去哪裡、跟誰說話等等,這對很多記者來說是相當恐怖的疲勞轟炸,讓人無時無刻都感覺被監視,感到相當不安全。有一天晚上,有人在我家附近的暗巷裡突然大喊我的名字,大喊之後就一直跟著我,他們就是想讓我感到害怕。
2017年初的時候,政府在機場殺了一位呼籲國家進行憲政改革的律師吳可尼(U Ko Ni),他是我的朋友。當有這樣的例子出現,而我在晚上又被軍方的人跟蹤,我的朋友們也一直勸我趕快離開等等因素,我覺得這些加起來狀況真的太嚴重,所以決定離開緬甸。
我很慶幸我及時離開,因為在我離開幾週之後,我朋友跟我說,政府的人來到我住的地方找我,要逮捕我,但還好那時候我已經離開了。
通常他們想抓一個人卻抓不到,這個人的名字就會被放上黑名單。所以我不能確定我是不是在黑名單上,回國會不會被抓。
報:緬甸政府抓妳最大的原因是指控妳寫假新聞,指控妳錯誤解讀翁山蘇姬的言論。妳對他們這些指控有什麼看法呢?
圖:這就是我們緬甸記者每天正在面對的另一種壓力。因為政府擁有自己的媒體,像是一些國營媒體電視、電台、報紙或是緬甸政府官方網站等等,多數政府釋出的聲明都是扭曲事實或是掩蓋特定訊息的新聞。但若我們不跟著政府的腳步報導,我們報導的真相就會被他們說是假新聞。
報:可以給我們一些案例嗎?
圖:在羅興亞迫害發生後,事發地點都被封鎖,沒有許可不能進入。但有時候政府會組織媒體團去若開邦看羅興亞人居住過且被焚燒過的村子,並且宣稱那些房屋是羅興亞人自己燒的。但有一次我們進去之前,軍方給了我們幾張照片,跟我們說那是一位羅興亞婦女在離開前放火燒自己房屋的照片。
然後我們被帶到一個政府搭蓋的避難所,軍方安排了幾位當地民眾(軍方宣稱他們被羅興亞人迫害)給我們採訪。結果我們發現裡面受訪的婦女中,其中一位就是照片中軍方宣稱的羅興亞婦女,甚至她受訪時穿的服裝還跟照片一模一樣。這也就是說,照片中正在焚燒房屋的人根本不是羅興亞人,全部都是軍方自導自演。
還有一次我們抵達另一個正在被熊熊烈火燃燒的村子,但裡面一位羅興亞人都沒有,很明顯就是軍方放火燒的。但當我把這些事實都寫出來,不跟著政府的腳步做事,就會被指控為假新聞製造者。
報:因為翁山蘇姬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緬甸多數人民都非常支持她跟政府。而這個政府指控妳是假新聞製造者,那翁山蘇姬的支持者會怎麼對妳呢?
圖:威脅都是來自社群網路,尤其是2016年跟2017年那段時間。在Twitter、Messenger、Facebook這些地方都會有人貼文指責我是叛國賊,或寫訊息給我、威脅我不要再報導羅興亞事件等等。我不曉得網路上的那些人是誰,當我走到街上,根本不曉得誰會突然攻擊你。而相反地,他們卻都知道我,讓我感到出門都很危險。那時的壓力真的非常非常大,甚至有時在做報導的時候,壓力會大到讓我喘不過氣來。
報:那段時間都是怎麼排解這些壓力呢?有尋求幫助或是報警嗎?
圖:警察跟他們是一夥的,打電話報警沒用。剛開始我在社交網路上收到死亡威脅的時候,我去報警。但是他們說因為是在網路上,所以沒辦法幫我。
我在接到威脅之後,會緊張個2、3天,然後久而久之就淡忘了。因為我還是要繼續寫作,繼續報導,所以必須習慣這些壓力。但新的威脅出現後,又會開始緊張一陣子,然後又必須去習慣它,就這樣一直這樣輪迴下去。
在2017年8月,羅興亞人受到大規模迫害的事情爆發後,緬甸內部仇恨言論的狀況變得更激烈。在那時候,我連在要刊出報導之前,也會開始擔心會有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那些政府的支持者都會指控我在詆毀緬甸的國家形象,而不是在幫助國家形象成長。但身為一位記者,我們的工作並不是幫緬甸宣傳,而是報導真相。
報:在妳離開緬甸不到一個月,兩位《路透社》記者瓦隆( Wa Lone)和覺梭(Kyaw Soe Oo)因揭發了緬甸軍方在若開邦殺害羅興亞村民的事實,而遭到逮捕。他們被指控觸犯了英國殖民留下來的《政府保密法》,各被判了7年徒刑。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政府在今年(2019)5月釋放了他們,你覺得這是緬甸政府對人們的讓步嗎?
圖:我不覺得。有多少世界上的現任跟前任總統呼籲緬甸政府釋放他們,政府受到如此大的國際壓力後,才釋放這兩個人。這兩位記者有500多天在監獄裡,就只因為他們報導了事實。就算他們釋放了兩位《路透社》記者,但是他們停止迫害其他記者、停止壓迫言論自由了嗎?沒有!他們仍在這樣做,他們還在逮捕記者、紀錄片導演或是各種異議份子。我不覺得釋放兩位記者就可以代表緬甸政府開始尊重言論自由。
報:在一些妳曾受訪的文章裡,妳說到現在這個政府跟前軍政府愈來愈像,為什麼這麼說?
圖:2016年我們有了新的政府,直到現在,有100多位的異議分子因為批判政府被抓。這樣的狀況顯示了什麼現實?民選政府若開始轉型,他們應該這樣抓人嗎?看到這樣這麼多人遭到逮捕,其實就是代表了這個政府並沒有真正想要讓國家民主轉型。
報:因為堅持不懈報導事實付出代價、被迫離開緬甸,如果一切重來,妳會仍然選擇做一位記者嗎?
圖:當然會。我覺得記者的工作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這種高壓的政府之下,我看到緬甸從軍政府轉變到民選政府的這段時間,記者扮演相當重要推動改革的角色。新聞報導可以改變社會,可以對國家做出影響。所以只要我仍可以報導,我想我會一直報導下去。
當被噤聲這麼久,終於可以發聲之後,要我再回到無法發聲的年代,是不可能的。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