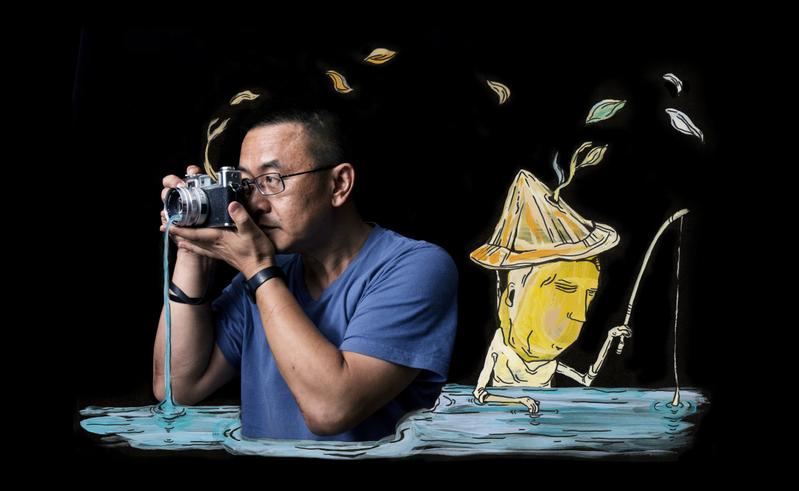閱讀現場

本文為《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部分章節書摘,經台大出版中心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編。
作者吳介民多年深入廣東出口加工區進行田野研究,從農民工、台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多層次互動的角度,研究廣東世界工廠崛起與陷入當下危機的底蘊。《尋租中國》針對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連結的模式,提出完整的解釋。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台商作為「中間人」,在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搭橋,協助中國與世界接軌 ;中國政府牢牢掌握這個機運,藉著全球價值鏈的移入,順勢將中國打造為世界工廠,汲取豐厚的經濟剩餘,從廣東賺取第一桶金。這桶美金作為「原始積累」,迂迴造成「中國崛起」。
最近10年,中國政府利用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誘餌,嘗試打造自己主控的價值鏈體系,卻遭遇美國的強力挑戰。以美國為首,對中國圍堵的地緣政治態勢也在形成之中。處於這雙重風暴,在習近平口中「功勞簿上要記上一筆」的台商,是否還有可供北京操作的價值?吳介民認為,在中國追求世界霸業的想望上,台商仍有利用價值。第一個是政治身分上的價值,第二個是產業升級上的價值。
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 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必須付出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而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在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
中國民工工資與社會福利待遇遠低於一般具有城鎮身分的「職工」,因此企業可以用「最低工資」聘雇低廉民工勞動力,並繳納較少的社會保險費用。最低工資本來是保障民工的薪資地板,但在實務上卻變成時薪的「天花板」。政府利用此二元勞動力市場來維持低廉勞動力供給的穩定性,並從中獲取尋租的機會。
在此勞動體制下,(中國的)工資占GDP比例長期偏低。觀察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1994~2003年平均為51.8%。2005~2007年遽降為40.6%,2009~2012年回升為45.5%,但仍偏低。反映在最低工資方面,中國實質最低工資(調校過物價指數)長期接近停滯(1990年代)或低成長狀態(2000年代),跟不上GDP成長率。2000年代開始,中國沿海地區出現勞力短缺現象,面臨工資上漲壓力,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工資才較快提升。長期的工資壓抑使得中國的大眾階級購買力不足,也造成消費性內需產業發展的限制。
中國對民工的制度化剝削,凸顯與台韓等發展型國家的差異。此身分差序勞動體制具有「制度黏性」,雖然中國政府頒布新政策試圖改善民工待遇(如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2011年的「社會保險法」),但勞動體制對民工及其家庭的剝削與歧視仍然持續。而且,大型城市基於本位利益,強勢執行對外來人口(民工為主體)的歧視,北京政府在2017年的寒冬大規模地驅趕「低端人口」,足證公民身分差序體制持續在發生作用,並在國家機器專制權力支撐下,獲得進一步的鞏固⋯⋯過度讚譽中國發展模式,將無法看到高剝削與高積累造成的經濟結構失調,以及不斷堆疊、深化的社會矛盾。
- 地方政府被國家許可或默許創造租金與尋租的空間;
- 尋租不僅發生在ISI部門,地方政府也對EOI部門尋租;
- 地方官員通過在地鑲嵌治理場域,而積極介入價值鏈中汲取經濟剩餘。
一般而言,在EOI發展過程中,經濟剩餘主要是通過勞力密集產業而創造,因此充裕的低廉勞動力便是必要條件。當勞動力要素價格相對提高、勞力密集產業趨於衰落、產業升級效果逐漸出現後,假設其他條件維持不變,從勞動力擠壓出經濟剩餘的比例就會降低。因此,對出口部門進行機構化尋租的空間就會縮小。在中國,這是2000年代末期開始浮現的狀況。因此在目前階段,中國的尋租發展模式可否持續,便是很大的難題。一方面,產業結構在快速調整中,國家賦予地方政府的「合法尋租空間」正在縮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機構化尋租具有依賴性,因此改採其他變形的尋租手段,惡化為財政掠奪行為。目前這兩股力量仍在拔河、拮抗之中。
從黨國體制的轉型角度來比較台灣與中國,饒富意味。在台灣研究中廣泛使用的「黨國資本主義」概念,和本書所描述的中國的「列寧主義式國家資本主義」有所區別。主要差異包括:
- 政權性質的起點不同:台灣的國民黨威權主義政權結合了準列寧主義政治控制與傳統王朝統治;而中國則是個典型的列寧主義式極權政權。
- 國民黨以執政黨的位置,透過「國庫通黨庫」而獲得龐大「黨產」;然而在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共產黨本身並沒有類似國民黨黨產的元素,而是通過「太子黨」掌握了龐大的國家經濟資源。
- 中國經濟歷經40年「開放改革」,依然具有高度「集權式管理」的性質(Lin 2011),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甚為鞏固;而台灣的黨國資本主義在1980 年代已歷經「經濟自由化」與「私有化」的過程。
經過40年發展,中國在世界體系中已經鞏固半邊陲地位,在一些製造業項目快速爬升全球價值鏈階梯;並且通過國家強力介入,試圖繞過核心國家主導之價值鏈霸權,創建自主掌控的價值鏈體系。全球價值鏈霸權背後是由美國主導的全球新自由主義支配結構。雖然中國在全球層次仍然無法和美國全面抗衡(Hung 2016),但中國在地緣政治與總體經濟力量上已是區域強權。中國增強自身的協商籌碼,試圖修改遊戲規則:制定技術規範、培育本土型供應鏈、創建亞投行、執行「一帶一路」戰略以輸出過剩資本。
在廣東發展經驗中,我們觀察到中國的國家(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通過在地鑲嵌治理,介入全球價值鏈的治理,以稅收和尋租手段汲取經濟剩餘,並通過產業政策強勢主導產業升級,強力整治汙染產業等等,進一步回饋到國家權力的增長。而具有能動性的在地體制,則挾其國家資本與茁壯中的製造能力,與全球資本(核心國家)展開競爭關係。就此點而言,中國試圖從半邊陲向核心挺進,採取類似加強版的韓國路數,即所謂「大推進」(big push)策略,但中國政府扮演比韓國政府更積極、強勢的指令角色。
回到本書對中國發展的歷史性考察,在中國高速成長過程中,廣東模式是中國發展模式的原型,也是核心組成部分;台資則是廣東外資中的關鍵構成元素。我們不妨做一個反歷史事實假設的思考實驗:若無台資,則難以想像廣東模式;沒有廣東模式,則沒有後續的中國崛起。因此可以推論台資與廣東模式在中國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地位。
根據本書「全球資本─產業群聚─在地體制」三邊互動的分析架構,在全球資本與在地體制的互動場域中,台資具有雙重角色:一方面,台資作為全球資本代理人(所謂「半邊陲手肘」,大部分為中小型跨國台企)執行在中國製造現場之價值鏈治理,這是支配角色;另一方面,則作為技術與管理知識的擴散者,培育了在地陸資廠的人才,促進產業升級與本土供應鏈系統,這是協同角色。此雙重角色從傳統產業到ICT產業都可觀察到。就後者而言,以台灣起家的IC設計廠商聯發科為例,對中國最初山寨手機製造生態的促進作用即相當顯著(參見第六章)。
中國近年來大力推動半導體工業,新建多座晶圓廠,引進不少台灣高階管理人員與工程師。由於台灣人才的協力,中國半導體工業產生與台灣(以及核心國家)的複雜競合關係,例如之前台積電與中芯的法律訴訟,目前尚在興訟中的美光科技控告晉華集成電路與聯電偷竊其知識產權。在這裡,我們看到台灣資本與中國資本的互動與整合、競爭與合作。
※引用文獻: Cheng, Tun-jen. 1990. “Political Regim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p.139-78 i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edited by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yo, Frederic C.,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eyo, Frederic C. 1990.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Popular Sector.” Pp.179-204 i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edited by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ng, Ho-fung. 2016.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oo, Hagen. 200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in, Nan. 2011. “Capitalism in China A Centrally Managed Capitalism (CMC) and Its Futur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7(1): 63-96.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