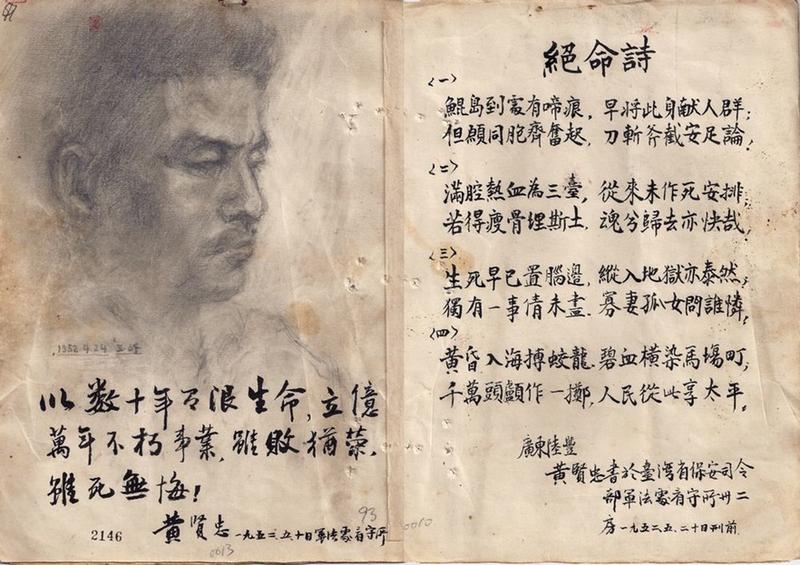評論

(編按: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後3天,基隆火車站前矗立近70年蔣介石銅像被市府拆除,依舊引起不同意見的民間團體矛盾與衝突。再多的疾呼、研究或紀念,似乎無法改變台灣社會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各種轉型正義分歧的記憶。而創傷的歷史記憶與其產生的強烈負面情感,如果沒有好好正視處理,便會傳承下去,造成一代代分裂的記憶⋯⋯。)
美國雖然是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可是內部種族不平等的問題仍然嚴重,成因很複雜,跟地方政府的隔離、差別待遇政策,還有長期經濟分配不均有關。但是民主政府畢竟還是人民選出的,長期分裂的歷史記憶,是許多政策改變的阻力。
台灣也有也有偉人銅像的問題。二二八事件和平紀念日後3天,矗立基隆70年的蔣介石銅像被市府拆除,引起不同意見民間團體的強烈抗議。即使近年紀念的主軸為「和解共生」,諸如此類的矛盾與衝突,每一年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上演,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不只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也是「記憶與記憶的戰爭」。
事件已過去了74年,台灣民主也走過了風風雨雨的30多載,當時間已邁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上世紀初誕生的耆老多半凋零,在民主化之後才出生的年輕世代,對黨國威權體制下的生活,沒有真實的經歷,更遑論二二八事件本身。甚至他們的父母長輩,很多也是在相對開放的1960、70或是80年代成長。對於政治肅殺的1940與50年代,記憶晦澀模糊。我們必須認知到,對於二二八的歷史記憶,台灣已漸漸進入「後記憶」(postmemory)的世代。
「後記憶」這個詞和後現代或後殖民理論,其實沒多大關係。這個概念在1992年由比較文學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剛開始用於了解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兒女們跟他們父母輩創傷記憶之間的關係;後來被廣泛運用、擴大解釋,泛指年輕世代對發生在遙遠年代的不幸事件,所產生的體驗、共鳴、想像與情感等等。因為沒有實際的經驗與感受,身邊也沒有親人或朋友直接受害,或是受害的長輩們早已離世,「後記憶」世代多半透過第二手的歷史故事、影像、詩集、藝術作品、紀念活動與社交媒體等,來了解與體會如同二二八這樣的集體創傷事件,以及其背後所彰顯的歷史教訓、國族認同與道德價值。
但是,再多的疾呼、研究或紀念,似乎無法改變目前台灣社會對二二八分歧的歷史記憶。圍繞著分歧記憶而形成的「記憶群體」(mnemonic communities),彼此之間有著許多矛盾與負面情感。這些矛盾與負面情感對「後記憶」世代造成不良的影響,延續甚至加劇上一代的對立,或是產生事不關己的冷漠感,而這些情形則會進一步影響未來的歷史研究,阻礙轉型正義的推行,而且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或老一輩的逝去而削減。衝突的觀點代代傳承下去,之後融入不同世代的環境與政經情勢發展,再加上揮之不去的中國滲透與統戰因素,成為社會對立衝突的潛在因子。

二二八的歷史研究,經過台灣文史工作者幾十年來的辛勤耕耘,基本的輪廓已大致清晰。白色恐怖研究,雖然有很多地方仍需努力,但是我們現在所掌握的史料與歷史知識,也比30幾年前還要多得多了。然而,歷史研究不僅是驗證基本事實,更重要的還是對這些已知事實的詮釋。
一場暴亂、屠殺與逮捕為什麼會發生?什麼樣的人、團體或是政黨要為這件事情負責?這場悲劇對於現在活著的人,意義何在?對彼此共同的未來,有什麼樣的一個啟示?我們為什麼需要記住這段令人心痛的過往?
當我們開始認真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認識到,歷史詮釋與歷史記憶本身是相關聯的。不同的詮釋產生不同的記憶;不同記憶的人組成不同的記憶群體。
政治學者吳乃德,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精闢地分析二二八的歷史記憶,指出3項圍繞在二二八事件歷史詮釋上的爭論,而這些爭論在13年後的今天,仍然持續存在。
第一個爭論是:二二八是「反抗外來政權」的民族鬥爭,還是「官逼民反」? 綠色陣營或本土意識較強的人,會是前者的觀點;藍營群眾,中華民國意識、或是只是大中華意識較強的人,還有為數不多的大中國紅統派等等,則會比較同意後者的觀點。
第二項爭論是:二二八是否為「族群衝突」? 綠色陣營或傾向本土的人(這其中也可能包括一些國民黨的本土派),會覺得答案是肯定的;傾向中華民國歷史記憶或是紅統的人,則持相對保留的態度。他們大都認為,族群的概念,是民主化後政治操作的產物。
第三個爭論是:要不要將二二八放在更大的歷史脈絡(國共內戰與冷戰)中加以理解? 在這點上,可能各方都能同意這樣子的說法。但是,從綠營/本土的角度來看,大歷史不能用來掩飾蔣介石、陳儀或是國民黨官員歧視本省人、經濟剝削、貪汙腐敗、任人為親、治理失能和鎮壓屠殺的責任;傾向中華民國歷史記憶的人,則用國共內戰大歷史來解釋統治失當和鎮壓的原因,軟性地幫蔣介石還有國民黨做開脫。紅統的左派,則站在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美帝國主義還有台獨的立場。
從歷史事實上來看,二二八比較接近官逼民反。但是這樣子的詮釋,有些本土派的人完全無法接受。對於吳乃德而言,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要的是歷史真實還是歷史啟示?我們的工作是分析過去,還是指引未來?至於二二八是否為「族群衝突」,對這個概念持反意見的記憶群體(傾向中華民國歷史記憶、大中華主義或是紅統的人),通常都假裝看不到,早期在台灣的國民黨是一個完全由外省人主導的政權。在二二八發生之時,雖然有少數的外省人在暴亂初期,被憤怒的本省民眾打死,但是這個政權歧視、壓迫和屠殺的大多都是本省居民與原住民。雖然當時沒有「族群衝突」的詞彙來形容這個情況,但這並不代表,不同群體間權力關係的不平等與壓迫不存在。
3月8日是蔣介石派21師登陸基隆,開始進行大規模清鄉鎮壓的日子。如果我們把整個事件,放在大歷史中看,是否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幫蔣介石開脫,或者是減輕腐敗國民黨官員與後來執行清鄉的軍警情治人員的責任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如同吳所說,我們必須認真看待人在歷史結構中的責任。掌握歷史事件的大結構,當然是必要的。可是,這些知識不能夠用來為掌權者與執行者辯護。
人不全然是他生長家庭與時代背景的奴隸,而是活著會思考的生物。就算在諸多條件的限制下,也還是可以做出許多自由意志的選擇,掌握權力愈大的人,能夠做的選擇也就愈多。面對台灣人民對他統治的反抗,蔣介石選擇的不是公平調查,了解事情的原委,懲罰應負責的官員,改善政府的施政,而是下令清鄉屠殺。不能因為戰爭戎馬倥傯,或是當時在中國大陸上都是用這類非常手法對付共產黨,諸如此類的理由,合理化蔣介石的行為。國民黨就是因為這些嚴苛與不公的處置,搞得民心盡失,才把整個中國大陸丟掉了。而在台灣的鎮壓,造成了無數家庭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痛與我們今天所有的爭議。歷史人物要為他自己的選擇負責,不論是生前還是死後。
相信有部分的讀者,對於加諸蔣介石或是國民黨的責難,一定很不以為然,這想法背後強烈的負面情感,反映出圍繞在二二八事件上的爭論,至今未能平息,也許永遠也不會平息。歷史研究可以讓我們趨近過去的事實。然而,因為史料遺失、人為故意銷毀、還有文獻資料或口述歷史本身的一些局限,歷史學者通常沒有辦法完整的還原事件的每一個面向。就連最基本、最重要的,到底有多少人死亡,到目前為止也只能推估,而無法得到一個確切的數字。
這樣子的不確定性,在某些程度上,助長了分歧的記憶群體。即使在台灣意識因領先全球的防疫與經濟表現而強烈凝聚的當下,分歧仍然深植於一般民眾的心中。人們或許可以認同蔡英文總統「中華民國台灣」的最大公約數。他們可以出席同一場紀念儀式;聆聽同樣一場音樂會;相約去看同一個展覽,但他們心中對這個事件的詮釋與想像,卻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吳乃德在他2008年的文章中認為,在一個民主社會中,這一些不同,甚至是對立的看法,完全是健康的。此一看法並沒有錯,嚴謹的歷史考證,本當建立在不斷的發掘、質疑與辯證之上。民主社會理應兼容並蓄,提倡多元觀點。但與此同時,他恐怕也低估了,不同記憶群體進入「後記憶」世代之後的發展與長遠影響。
在吳文發表後的13年,我們看到的是持續分裂的記憶群體,還有因為不同創傷歷史記憶所產生的強烈不滿情緒,包括受辱感和受迫害感。分歧的記憶群體,不會輕易放棄他們自己的看法,也多半無法認同其他群體的看法。因為這一些群體的形成,與每個人的出身背景、政黨支持、文化認同、國族認同等等,息息相關。
該如何緩解記憶分歧所帶來的問題?首先就是要正視這個問題,不要把這些紀念活動的爭議與陳抗,看成簡單的情緒宣洩或拙劣的政治表演(鬧一鬧就沒事了。這就是民主嘛!大家也就是吵吵鬧鬧)。民主社會理應鼓勵多元觀點,但是我們對於分歧的創傷歷史記憶,要花一些心思去共同討論與處理,這其中當然包括了歷史教育與政府推行的轉型正義。創傷的歷史記憶與其產生的強烈負面情感,如果沒有好好地正視處理,會傳承下去,造成一代代分裂的記憶,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文章剛開始提及的美國,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緩解記憶分歧,具體上要怎麼做?這是整個台灣社會與學界,需要共同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我在這裡提出一個與「後記憶」同音異義的概念叫「厚記憶」(thick memory)。這個概念的靈感來自於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理論。格爾茨的民族誌強調,要精準地解讀他者的文化現象和其背後所代表的真正意義,必須從深度理解這個文化族群的歷史背景、風俗、宗教信仰、語境象徵等角度出發。
「厚記憶」,簡單來說,是將歷史記憶視為一種文化現象,探討與其相對應社會記憶群體之間的關係。嘗試理解某種歷史記憶如何被一個群體所接受,如何產生強烈認同感以及情感,然後不斷地在志同道合的社群裡面發送、在親屬關係中傳承。更重要的是,這個歷史記憶對「後記憶」世代群體裡面的個人,它所代表的真正的意義為何?
答案可能很複雜。例如每年去參加公民團體舉辦的二二八紀念遊行的人,很多都並不是受難者家屬,他們為何要參加這個活動?二二八的歷史記憶,對他們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跑去損毀蔣介石銅像的學生,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是如何看待的?對中華民國藍或是紅統派的年輕人而言,二二八代表了什麼呢?「厚記憶」研究能夠幫我們深入了解「後記憶」世代。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才能夠進一步討論該怎麼辦。
真正的和解共生,並非遙不可及,我們也應該繼續保持樂觀進取的態度,只是它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困難,需要做的工作,遠比我們預想的還要多,不是每年放個假,花錢舉辦一些紀念活動,就可以達成。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