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廠煙下
中油工人的
最後一天

2015年10月底,《報導者》採訪團隊在高雄煉油廠停工前夕深入廠區,藉由現場目擊與拍攝、訪談多位中油不同世代員工,綜合寫成一名工人阿昌的故事。阿昌並非真實人物,但從真實素材而來。此數位專題將以他的遭遇、回憶及情感,在灰濛的廠煙下,描繪一整代高廠工人的輪廓。

阿昌和往常一樣,早上五點半起來,燒好一壺熱水,泡好麥片,他下意識地瞄了瞄日曆上的日期,10月30號,在半年以前,他已經做了記號。
今天他工作的硫磺工場是最後一天運作,他已在高雄煉油廠工作35年,以為將在這裡退休、老死,沒想到會因為關廠提前離開,出門前,他的腳步顯得徬徨,踏出去之後會走向何方,他不知道。
他所在的第七硫磺工場是高雄煉油廠最後熄燈的工場,工作採輪班制,24小時都須有工人輪守。硫磺工場長年發出惡臭,讓後勁居民抗議,阿昌待在有冷氣的控制室裡,渾然不覺。阿昌去福利社買早餐時,遇到他的建教班老同學阿明,阿明所在的五輕工場,去年四月已停工,大部份人轉去大林廠,只剩下他一人留守,空空蕩蕩。
阿昌以前不能體會阿明的感覺,現在他回到硫磺工場,倒數計時關場前,大家工作起來沒什麼勁,他終於能理解阿明的失落感。
最後一天特別焦躁,阿昌整個上午盯著觸控螢幕,忙著用無線電確認最後關閉管線的流程。在場裡工作不能抽煙,犯癮的時候他總是走到樓梯間看管線發呆,各種不同顏色的管線像纏繞的蟒蛇,他可以明確指出每條管線的作用,但他知道總有他看不到的東西。
去年初夏,氫氣外洩造成爆炸意外那天,他也是這樣站著。
突來的一陣晃動後,他聽到一聲巨響,無線電傳來嘈雜的對話,夾雜著消防隊由遠而近的鳴笛聲。
阿昌急忙跑進控制室時,來不及換成防塵的室內拖鞋,一雙泥鞋踩進去,直到重油脫硫工場的火勢在一個半小時後受到控制,他才發現地上都是自己凌亂的腳印。那天除了中油專屬的消防隊外,外面的消防車跟救護車都進來了。
這些年他很少想起這個故事,以前有一個老工人,某天巡視時,突然無預警地全身燃燒起來,因為氫氣是隱形的惡魔,無色無味,看不到,聞不到,無法預防。氫氣外洩只有晚上看得到,像一蓬一蓬淡藍色的鬼火,阿昌想起那個畫面時還會不寒而慄,他感覺,那好像是殉職同事的魂魄。

作家楊青矗的父親曾經是高廠消防隊員,這裡雖然不是父親隸屬的小隊,但仍然讓楊青矗勾起許多對父親的記憶。(攝影/林聰勝)
阿昌16、7歲讀建教班時在公用水處理廠工作、跟著輪班。雖然調了單位,但他還是習慣騎著腳踏車繞去看看,找老同學敘舊。以前公用水處理工場有個比游泳池還大的水池,同學們都會在這裡游泳。
民國60年代,他雲林鄉下的家還在燒柴,廠裡就有動力工廠,有巨大的鍋爐,將水暖化成蒸餾水,再提煉成實驗室所用的純水,以供煉油廠裡的精密機械使用。
那幾乎是最好的青春年代,高廠裡的一切都讓阿昌大開眼界。
廠裡還有自己的水廠,不需要經過自來水公司提供,廠裡的水經過石灰沉澱,硬度比外面的水低,水質良好,用來做中油冰棒,吃起來就是和外面的不一樣。
阿昌回憶起從前的歲月,有苦也有甜,小時候家裡窮,以前在家能燒柴來洗澡,是非常奢侈的事。在這裡因為將動力工場鍋爐的蒸汽回收,工人們有源源不絕的熱水可以每天洗澡。用蒸氣來煮飯,不到十分鐘米就熟了,好像變魔術一樣,阿昌放假回雲林跟弟妹講,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像天堂一樣。

高廠西門內矗立的蔣介石銅像是目前少數還留存的銅像之一,如今成為威權時代的象徵。(攝影/林聰勝)
往宏南社區得經過西門,阿昌想起25年前,由於後勁居民在西門圍廠抗議,阿昌上班時都要繞一大段路,從北門還有新北門進來,當時他覺得好麻煩。出廠他特意回頭看了一下大門,不知道那些剽悍的抗爭者後來怎麼了。廠內還有一座蔣介石銅像,看起來比平常還高大,關廠後,這座威權時代的遺留,大概也要被拉倒了。
午餐時,阿昌不想去員工餐廳,想去宏南社區走走,也想帶一些高廠的麵包回去。
女兒愛吃,最後一天了,以後不知道要去哪裡買。
住在宏南社區的都是中油高級主管,網球場、高爾夫球場,應有盡有,綠樹成蔭。
阿昌17歲念建教班的時候,追求年輕女工娟娟,那時參加高廠的籃球隊,娟娟常來場邊幫他加油。在運動場上沒有身分貴賤,阿昌的球技硬是比那些科長、經理好,常常一個漂亮的過人上籃,就可以抵得過他在工廠被使喚的委屈。
40年前,在貧瘠的高雄,有籃球場、保齡球場、溫水游泳池是很稀奇的事,外面的人連聽都沒聽過。阿昌在那幾年學會游泳,他還記得過年回家說給弟妹聽時,他們吃驚的樣子。
高爾夫球場始終很神秘,阿昌心想,只要能走進去看看也好。
但他知道那都是高官在打,去了難免要鞠躬哈腰,他領的薪水也實在付不起那些昂貴的球具。
那些日子,阿昌往往跟同學借了摩托車,載娟娟到宏南的林蔭大道散步,一間一間房子都像小別墅一樣。
娟娟眼裡發光,但阿昌知道,以他這種基層工人,不可能住在這裡。
以前在路上處處可見戴黃色安全帽的工人。安全帽顏色是區分用的,阿昌多待在辦公室,戴橘色安全帽,另外那些監造工人、維修工人戴黃色安全帽。戴藍色安全帽的廠商在不進原料後幾乎見不到了。倒是要關廠前,戴白色安全帽進來採訪的記者變多了,穿著高跟鞋的女記者穿梭在管線複雜的地區時,阿昌為她捏把冷汗,以前根本不可能讓閒雜人等進來。
回硫磺工場的路上,阿昌幾乎見不到幾個人。
樓起樓塌、灰飛湮滅。
回工場前,阿昌遇見老同學阿勇,他戴黃色安全帽,阿昌建教班畢業後去念技術學校,所以能在控制室工作。阿勇沒繼續升學,始終是第一線的工人。阿勇常跟他講第一線工人的命不值錢,歲末維修時,機具停工維修,讓黃帽工人進去油槽、管線裡清理,不時傳出一氧化碳或沼氣中毒事件,進去了就再也沒出來。



監工葉天德(右)與許進興到高廠服務超過30年,現在高廠即將結束營運,他們感嘆萬千。(攝影/余志偉)
輪完最後一天的班,天微微暗,阿昌決定散步到半屏山的高台。他平常不是那麼容易感傷的人,但今天忽然想起很多老同學跟同事。
爬上高台,氣喘吁吁,阿昌沒有年輕時打籃球的肺活量。還在喘氣的同時,阿昌看到一幅熟悉的風景,像個360度環繞鏡頭,看見全景。這麼大的廠,人在裏頭像小螞蟻一樣,阿昌無法想像說停就停,讓他感到世事無常,沒有不會消失的東西。
高雄捷運開了以後,阿昌搭過幾次捷運來上晚班,從窗戶看出去的高廠,是他最喜歡的景色之一。每當看到熊熊冒火的燃燒塔,阿昌就有回家的熟悉感覺。不過現在大部份工場關閉,半屏山腰的五輕廢氣燃燒塔,去年就沒有運作了,以前他從捷運上望過去,燃燒塔就真的像中油LOGO一樣,黑暗中不滅的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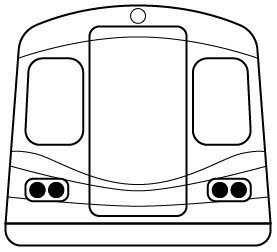
這火光,對阿昌是人生的指引。
但在抗爭的那幾年,阿昌耳聞,燃燒塔對於居民,就像地獄的象徵。
回家前,阿昌打電話給太太,說晚飯可能趕不上了,想去以前住過的單身工人宿舍看一看。民國60幾年,阿昌住進來時還是全新的,但現在牆壁都剝落了,長滿壁癌。宿舍兩人一間,住起來蠻寬敞,高廠為了照顧工人,餐廳常加菜,炒豬肝、熬魚湯。後來什麼大魚大肉沒吃過,但記憶裡,那是阿昌喝過最鮮美的魚湯。
阿昌遇到舍監,居然還記得他,叫得出他年輕時代的小名,40幾年的歲月彷彿就在瞬間停滯,阿昌眼眶濕了。他還想到娟娟,後來嫁給一個男工,就再無聯絡了。娟娟以前常來樓下,叫阿昌的小名,阿昌開窗就能看見她的身影,婷婷玉立,讓阿昌馬上飛奔下去。
阿昌想起附近以前是保警宿舍,煉油廠曾經是國防重工業,有上百個保警駐紮於此,如今早已人去樓空。
高廠全盛時期,從幼稚園到殯儀館一應俱全。多年後,宿舍旁的殯儀館在前幾個月被檢舉而停業。
從幼兒紅撲撲的臉蛋,到停屍間裡冰冷的遺體,路程只有十分鐘,都在高廠裡。
阿昌想起年少住在宿舍時
半夜聽到守靈誦經的聲音,總會覺得特別悲涼,那時他還沒跟娟娟交往,是孤伶伶的一個小工
不知將來該往哪裡去。